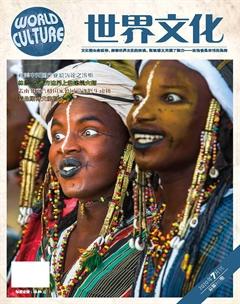林璎:东西方边界上的建筑大师
谢天海
1982年秋,美国财政部会议大厅当中挤满了媒体记者,长枪短炮对准室内的一张长桌。桌子上摆着一个黑色的建筑模型,模型旁边放着很多小国旗和几个迷你士兵雕像。桌子周围坐着一圈衣冠楚楚的美国白人,对着这些东西指指点点。他们轮流走到麦克风前,对着记者发表着言辞激烈的讲话,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争论的关键就是要不要把这些国旗和雕像安放到建筑模型的旁边。众人讲话之后,一个小个子亚洲女孩儿站到了话筒前面。她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穿着一身浅蓝色套装,斜戴着一顶时尚的宽边帽,脸几乎完全被帽子挡住,长长的黑发扎在头后,圆圆的脸上显出几分稚气。她手里拿着一份稿件,说话声音微微颤抖,说出的话语却坚定不可动摇:“这座纪念碑给了每个人以自由的空间去想象那些参加越战的人们做出的牺牲和奉献。它不是献给政治、战争抑或辩论的,而是献给所有曾经为我们的国家服务过的人们。它将人们带入一个静默与沉思的空间,使他们成为纪念碑的一部分,成为美国历史的一部分。那些附加的设计对于原作来说无异于一种造成缺陷的入侵行为,丝毫不顾作品的空间美感。而5英尺高的塑像也已经超过了纪念碑本身的高度。这些塑像凌驾于那些名字之上,已经破坏了原作的涵义。”
这个女孩就是林璎,美国著名华裔建筑师,争论的焦点就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华盛顿越战退伍士兵纪念碑的建造计划,从这一刻起,她开启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华盛顿越战纪念碑:少年天才铸传奇

时间退回到1979年,美国越南战争正式结束四年之后。马里兰州退伍军人简·斯库鲁格斯受到电影《猎鹿人》的启发,觉得美国政府应当为战死在越南的美军士兵建立纪念碑以供士兵家属缅怀逝者,同时也让全国人民永远铭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他发现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方面的意向,于是发起成立了越战纪念碑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募集基金并游说美国政府完成这一计划。在他的努力下,1980年7月1日,卡特总统签署了专项法案,纪念碑项目正式上马。基金会成立了一个由七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共征集到了1441个不同的方案,其中不乏建筑大师和著名设计公司的作品。此时,林璎年仅21岁,是耶鲁大学建筑系大四学生,正在和几个同学一起进行毕业设计。一个朋友看到了方案征集的消息,觉得可以将其作为毕业设计题目。于是几个人来到位于华盛顿的纪念碑选址地实地考察。林瓔在回学校的路上,一个惊人的意象摄住了她:两道黑色的墙壁,像一双黑色的翅膀向两边展开;像两片黑色的刀锋,深深切入大地,与之融为一体;又像一道伤疤,时时提醒着美国人民战争的残酷;墙壁上镌刻着五万七千名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士兵的名字,供每个前来凭吊的人寻找和永远铭记。她后来回忆时说道:“宝贵的生命成为战争的代价, ‘人无疑是第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因此这项设计的主体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当你接受了这种痛苦,接受了这种死亡的现实之后,才可能走出它们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她回到宿舍,迅速将灵感记录了下来,并写下了一篇短文作为设计思路阐述。结稿时间将至,她甚至没来得及将设计稿件打印出来,就匆匆寄了出去。就是这样一份匆匆完成的作品,却受到了七位评委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虽然初看上去平平无奇,但看得越久,越让人为之动容。当他们发现设计图背后的通信地址竟然是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的学生公寓,他们才意识到这件伟大的作品竟然出自一名学生之手。


当林璎接到来自华盛顿的电话,通知自己的设计被采纳时,她感到大喜过望,然而麻烦和压力也接踵而至。一些心存嫉妒的设计师讽刺说:“她真是幸运,只在纸上画一道黑线,就得到冠军。”而一些退伍士兵的家属集会抗议,认为这个设计只不过是一个“令人羞辱的阴沟”“丢脸的破墙”,有一位退伍军人称它为“黑色的伤疤”。抗议声中也不乏种族主义言论,有人指出“我们美国人的纪念碑,绝对不能让一条东方狗来设计”。与此同时,一些身处华盛顿的退伍士兵开始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进行游说,写信给一些政府要员,包括将军、国会议员和内政部长,诬陷评审团成员中存在反战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方面提出了三点修改意见,要求将墙体改为白色,在建筑的高处插上国旗,并在建筑旁边增添三组美军士兵的雕塑。如果这些修改一旦实施,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林璎的设计初衷。评审团不得不邀请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对于林璎的项目进行论证,论证过程向媒体开放,让林璎有机会和民众说明自己的意图,也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戏剧性的一幕。
在林璎的坚持之下,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最终通过了她的设计,纪念碑工程也正式开工。但麻烦并没有完全结束。作为为纪念碑设计的人,德州商人罗斯裴洛对这一设计非常不满,自己出钱请一些退伍士兵来到华盛顿进行抗议,同时还出资邀请雕塑师哈特设计一个美国士兵的雕像,就放置在林璎纪念碑的正前方,对此林璎无可奈何,认为这就像是在自己画的素描上添了两撇胡子一样,不可接受。1982年11月,纪念碑正式揭幕,但宣传册上只有哈特的雕像,而没有林璎设计的围墙。在开幕式讲话时,林璎的名字未被提到。这种社会对于艺术家的歧视受到了有良知的艺术家群体的反对,美国艺术界和建筑学界的人士决定对所有参赛作品进行再次评选,而林璎的设计再次荣获第一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设计的艺术价值也越来越得到人们认可。1987年,当林璎从耶鲁大学博士毕业时,当地的退伍士兵代表罗伯特·史密斯向林璎致辞时说道:“我想感谢你为设计越战纪念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没有任何其他的设计更能安慰我们死去的战友了。数字只能是数字。而那些密布在纪念碑上的名字将不断地提醒我们自由的可贵。我们对亲密战友的记忆将透过你美丽的设计而得以长存。”
民权运动纪念碑:自由泉涌万年流
虽然越战纪念碑令林璎声名鹊起,但在这其中受到的种种歧视和非难,使她感到身心俱疲。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她决定暂时告别美国,在日本和中国进行了一些设计工作。回到美国之后,林璎进入纽约一家建筑公司实习。1988年,她接到了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南部贫困法律中心的埃迪·阿什沃斯打来的电话。他希望林璎能够为民权运动中的牺牲者设计一座纪念碑。最初,林璎对这一邀请心存芥蒂,不想被人认为是一个只会设计纪念碑的建筑师,也不想再次陷入有关种族问题的争议之中。况且她长期生活于美国北方,对于美国南部的文化和种族问题知之甚少。阿什沃斯先生满怀热忱地告诉林璎,在此之前美国还没有任何一座为人权运动设计的纪念碑,并且承诺林璎可以完全不向任何人负责任,独立展现才华。林璎受到了感动,接手了这个项目。在动身去蒙哥马利之前,她用几个月的时间阅读了大量法律中心寄来的材料,并且观看了很多20世纪60年代以来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像资料,渐渐地,这一美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事件在她的脑子里变得越来越具体。在重读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言辞华美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时,有两句话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句是:“只要拥有信念,我们就能从绝望之山上采下希望之石。”另一句则是:“只有当公平与正义如水流般直下时,才能真正使我们感到满足。” 刹那间,一个精彩的创意出现在她脑海里,她决定将流水和岩石作为这个纪念碑的设计核心。

1989年11月5日,在一年建设之后,纪念碑正式竣工。有6000余名當地居民出席了落成典礼,大家惊讶地发现,一座纪念碑将中心的入口分成了上下两个广场。纪念碑选取了奇特的不对称结构,只有一端设置了台阶。这一看似反常的设计表达了林璎在种族问题乃至美国国家起源上的立场:“人们没有必要为了获得平等而强求一致。”上方广场上是一个安静的池塘,一层薄薄的水帘从池塘前端汨汨流出,沿一道9英尺高、40英尺宽的黑色弧形墙体缓缓流下,墙上镌刻着的正是马丁·路德·金的那段名言。广场下部设置了一个黑色的圆形大理石桌。林璎将法律中心提供的53件黑人人权发展史上的53件重大事件和53个重要人物,呈辐射状刻在了石桌面上,从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开始,到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被刺为止。整个石桌看上去像一个日晷,一股清泉从桌子的中心不断涌出,平静地流过石桌的表面,见证着一段段黑人民众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在这6000多名当地居民中,既有亲身参与过这些民主运动的老人,也有为黑人权利献出生命的民权斗士的家属,他们紧紧地围着石桌,眼泪不住地落在石桌之上,场面极为感人,林璎回忆道:“那个时刻,我知道我们都成了美国共同历史中的一部分。”
林璎与东方:为有源头活水来
自此以后,林璎又为美国多地设计了许多独具一格的建筑和艺术雕塑,包括纽约非洲人艺术博物馆、田纳西州休斯图书馆、马萨诸塞州韦伯别墅等等。虽然林璎接受的是西方建筑学的正统教育,但她的设计反映出与西方建筑基本理念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理念。如果说传统的西方建筑属于天空,注重对空间的把控、对结构的具象呈现和对神圣与崇高的追求,林璎的设计则属于大地,强调建筑所产生的心理作用和情感意义,注重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和互动。她曾经解释自己的艺术哲学理念:“我希望能够加入一种安静的秩序,如果人注意观察就会发现,反之就会消失。我希望创作的作品能够安静地融入到背景之中,让观者无法确定这是人造的还是自然存在的物体。”无论是退伍士兵纪念碑与大地融为一体的围墙还是民权纪念碑的水帘,都形成了某种隐喻结构,象征了个人与社会、世界乃至整个宇宙之间存在的各种微妙而生动的联系。这些内涵与东方文化中“天人合一”“ 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可谓不谋而合。在这个意义上,她所受到的家庭影响起到了关键作用。

林璎的父母都是来自中国的移民,父亲来自福建,原来在中国大学做行政工作,来到美国后改学陶艺,后来在俄亥俄大学求得了一份教职,最终成为艺术系的系主任。母亲是上海人,出身于医生世家,后来成为一名大学中文系的教授 。但她父亲骨子里面很有叛逆精神,在国内家教很严,不允许他学习艺术,因此他出国后成为艺术家。林璎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著名建筑学家、文学家林徽因的侄女,但她直到大学毕业,才从父亲那里偶然听说林徽因的故事。林璎小的时候和她的兄弟是所在小镇上仅有的华裔,父亲希望她能够融入美国社会,因此不教她说中文,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之下,林璎对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接受很困难,在耶鲁时她拒绝成为亚洲学生协会的会员,和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在一起让她觉得困惑,她用了将近二十年才逐渐接受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即便如此,东方文化对她仍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家里,心灵手巧的父亲制作各种带有东方风格的陶器,包括吃饭的碗,还有中式家具。那些工艺品简洁的线条和色彩之美,无时无刻地塑造着林璎的艺术审美观念。林璎曾经回到父亲在福建的老家参观,发现那里的家具是一种东方艺术的混合体,既有中国艺术的精巧,更带有简约而朴素的日本艺术气息。林璎承认自己从来没有阅读过禅宗或者道教方面的书籍,但东方艺术对她产生的直觉上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她的艺术设计当中,东方哲学思想也奠定了她设计当中的核心理念。在一次采访中林璎明确地表达道:“我非常反对那种辩证法式的教学方法,也就是说观众进来后我会告诉你从这件作品中能够获得什么,我只负责将作品呈现出来,由你自己得出结论。”
林璎家庭教育当中也体现出独特的传统中国理念。与美国的功利主义教育不同,林璎的父母从来不会强迫林璎和她的兄弟去学习谋生的手段,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商人,在他们看来,这些职业不会被长久的记忆,因为他们过分地贪图物质生活。同样,父母也教导两个孩子不要受到西方对于美籍华人的刻板印象的影响,将自己定义为远离主流文化,只会自我设限的小群体或者练习中国功夫的怪物。这种“君子不器”的人生态度使得林璎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梦想,并且将自己的东方文化观念逐渐带入美国建筑设计之中。在一次采访当中,林璎说道:“我觉得自己永远生活在各种边界之上,在艺术与科学之间,在艺术与建筑之间、在大众与私人空间,东方和西方之间,我一直试图在这些互相对抗的力量之间寻求平衡,发现这些相反的事物交汇的空间,我不会活在任何一边,而是活在这些事物的分界线上。”
2000年,林璎出版了一部名为《边界》的著作,书中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自己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念。书的封面上只印了林璎的一只手,手里握着一块圆润的紫晶原石。当记者要求她解释这个封面的来历时,林璎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喜欢四处收集石头,觉得它们很美。所有人都觉得它们很简单,只是被流水打磨成了现在的样子了,但如果你去分析它的形状,每条曲线都那么复杂……自然就是那么复杂。” 也许就是对这种浑然天成的追求和拒绝被标签化的态度,使林璎获得了横跨东西方的文化视野,成为生存在边界上的建筑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