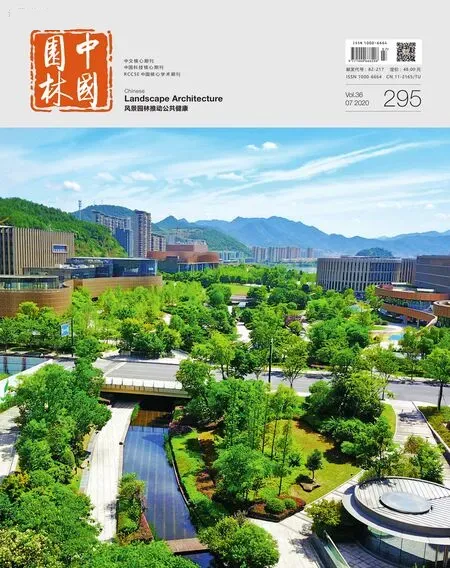畅春园植物考证及植物景观营造
郭灿灿
朱 强
尹 豪*
姜骄桐
唐予晨
“三山五园”是对清代北京西北郊皇家园林集群的总称,反映了清朝皇家园林营造的最高水平,具体所指一般为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近年来,“三山五园”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在植物景观营造层面,相关研究从营造背景、植物选择、营造手法和意境四方面对明清皇家园林植物的造景特点进行了总结[1-2];更为深入的研究是针对“三山五园”的单个园林如圆明园、颐和园等进行的植物景观考证研究[3-5]。可见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保存完好或有遗址的园林,但对于地面上仅存2座山门的畅春园,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史角度,对畅春园的各方面历史风貌加以描述,对于植物景观的专项考证和分析较为不足。因此,本文基于已有的空间复原研究成果[6],在山水及建筑空间的基础上,对畅春园植物进行考证,进一步还原畅春园盛期的植物景观风貌,并分析植物景观营造的特征,这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畅春园和清初皇家园林的植物景观。
1 畅春园植物考证
1.1 研究对象
1.1.1 畅春园建设的历史分期
根据对畅春园历史沿革的相关研究,畅春园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始建,雍正时期闲置,乾隆时期重新启用作为皇太后园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太后去世并进行最后一次改扩建,之后,畅春园长期搁置与荒废[6]。可推断,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四十二年期间,为畅春园景观风貌最完整的时期,也是本文植物考证研究的历史时期。
1.1.2 畅春园植物景观研究范围
目前畅春园平面复原最早为乾隆时期,占地面积约56.64hm2,西边为建造于畅春园之后的附属园林西花园。畅春园内利用前后湖对建筑群落进行了空间分割,有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其分为宫廷区、前湖区、后湖区、北湖区和农耕区[6],可以大略反映乾隆时期的景点布局,为后文植物位置的确定提供了依据。西花园由于史料较为缺乏,故不纳入此次植物考证范围。

图1 《万寿庆典图》与《圆明园四十景图》植物对照(作者绘)
1.2 植物种类考证
1.2.1 主要依据
直接依据主要有高士奇《蓬山密记》、康雍乾三朝御制诗文、畅春园景名及楹联匾额和清代宫廷绘画中描绘畅春园场景的作品,均为一手文献、史料,直接反映了畅春园的植物材料信息,同时,也体现出一些植物营造特色,供后文进行分析。
间接依据为乾隆三十三年(1786年)内务府所颁奏折——“泉宗庙、圣化寺宫殿院内各处栽种各样树株数目,价钱银两事”[7],详细记录了泉宗庙、圣化寺及六郎庄附近新堆土山上种植树种的情况。泉宗庙、圣化寺和六郎庄一带土山,从《畅春园内务府则例》来看,均属畅春园管辖范围,表明其植物配置规格与苑囿无异。此奏折记录树木共35 000余棵,30种,其中数量最多的有山桃、榆、柏等10种,占总数的96.7%,提供了一份京师苑囿有代表性的主要绿化树种清单(表1)。可为畅春园内土山上植物种类考证及乡土植物运用情况分析提供佐证。
1.2.2 考证与梳理
1)《蓬山密记》记述的植物考证。
《蓬山密记》是清初名臣高士奇的笔记,记述了在其告老还乡时受邀游览畅春园全园的体验[8]267。《蓬山密记》里对所见植物提及颇多,且往往直接对应畅春园景点位置。有记载的植物里,大部分古名与今名无异,或极易根据记载和古名查询到今名,如“箓竹”出自《诗经》“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是荩草的别名;个别植物的品种在记载原文中不太明晰,如“少顷,至东岸,上命内侍引臣步入山岭,皆种塞北所移山枫、婆罗树,其中可以引纤,可以布帆,隔岸即万树红霞处”,“婆罗树”又名“娑罗树”,北方“娑罗树”一般指七叶树,这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香山寺的《娑罗树》诗中得到了验证:“香山寺里娑罗树,种自何年不得知。翠色参天叶七出,恰如七佛偈成时。”“山枫”对应枫树,暂无法明确树种。根据《蓬山密记》可以考证出在畅春园应用的植物有12种。
2)清帝御制诗文记述的植物考证。
康熙、雍正和乾隆御制诗文中涉及植物名称的共19篇,提及植物18种,由于是抒情诗,描述不如《蓬山密记》精确。但御制诗文数量多,涉及景点广泛,对畅春园植物材料的考证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从康熙和乾隆在畅春园里作诗内容来看,康熙的诗大多与花有关,如牡丹、玉兰、荷花等,主要是对植物直接吟咏和赞美,植物个体特征较为细致;雍正诗文提及畅春园植物的仅有一篇《畅春园芍药花开作》,描写芍药花开的景象;乾隆诗词多是寓情于景,多与母后请安事宜、家事国事相联系,由植物景观联想到自身处境,其描写的植物群体出现频率高,个体特征不明显,对应片植的景观,如松、柏、柳和杨等。
3)畅春园景名及楹联匾额植物考证。
中国传统绘画、诗词与园林艺术都将意境作为审美的最高追求,园林景观的营造深受诗词绘画的影响,景点取名、楹联和匾额往往与诗画意境相对应,而比德观影响下植物的选择和配置,是构成意境极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整理出楹联匾额中与植物相关的记载有12处,考证出植物共8种,既可作为畅春园植物材料考证的补充,也能为植物景观文化的分析提供依据。这其中,有的景点名称只是为了文化寓意起名,有的的确种植有相应植物应景,都表现出植物文化对皇家园林中景观构建的显著影响。
4)有关畅春园的清代宫廷绘画中的植物考证。
清代宫廷绘画具有较强写实性,且植物的绘制技法大致相同。对畅春园相关清宫绘画——康熙六十大寿时的《万寿庆典图》及民国时期《北京颐和园和八旗兵营图》进行植物辨认,以圆明园四十景图的植物考证为基础[9],以华北气候带的植被特征为参照,考证出国槐、旱柳、绦柳等9种植物(图1)。

表1 主要绿化树种名录

图2 畅春园已知植物位置分布(作者根据参考文献[6]绘制)
1.3 畅春园植物考证汇总及位置分布
通过古籍、诗文和宫廷绘画的研究,考证出共32种植物(表2),其中,推测成分较高的有6种。为了清晰地表达植物在畅春园的分布情况,参照已有研究对乾隆时期畅春园布局景点复原平面图,绘制出植物的分布位置①(图2)。
植物分布图显示,宫廷区园林部分和前湖区主要以3条花堤为特色,绛桃、兰草、白丁香在不同时节绽放;其所包括的建筑群中,瑞景轩临水,有荷花点缀,凝春堂的松柏给人以深沉的色调感,渊鉴斋多开花植物,乔木有玉兰,花灌木有蜡梅,多年生花卉有“开满阑槛间”的牡丹和芍药。后湖区被周围不高的土山环绕,山上种植高大树木,如山枫、婆罗树;水面上有荷花、芦苇等水生植物以供观赏;水中伫立一岛,种植有玉兰、牡丹;西侧集凤轩有大面积葡萄种植,自西域进贡,有10余个品种。北湖区涵盖清溪书屋、西北延楼两大建筑群,种植有竹、樱桃、蜡梅。畅春园西侧还有一定面积的农耕区,种植有小麦、水稻、菖蒲,一派田园景象。考证出的植物中,以前湖区和后湖区种类为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畅春园植物景观的重心。
2 畅春园植物景观特色
2.1 植物材料选择与应用
对考证出的32种植物进行整理得出表3,在树种使用方面,常绿乔木2种,落叶乔木14种,落叶灌木4种,乔木灌木树种比为1:0.25,常绿落叶树种比为1:9,这与北京地带性植被为落叶阔叶林是吻合的。在数量上没有明确统计,但从诗文描述看,可以推测常绿树有大面积的使用。
2.1.1 因地制宜,符合地域特征
从生长习性来看,北京属典型的温带季风性气候,对植物抗旱、抗寒能力有一定要求。考证出的32种植物中,有22种耐寒、18种耐旱,表明大部分植物能够良好适应北京的生境,大面积使用的开花植物如牡丹、丁香、绛桃等,都是自明代起北京常见的花木;而有记载的乔木中,杨、柳、油松、侧柏、枫树和梧桐(青桐)等则是北方有记载的常用树种[10]。
2.1.2 外来植物的引种
考证植物中结合文献能确认的引种植物就有6种,其中既有从南方移植的蜡梅[8]268和梅花[11],也有从西域哈密移栽的葡萄,还有原产塞北的山枫和婆罗树[8]268。另外,高士奇曾记录过一次游园经历,“上指莲花岩小松,云:此尔随朕清凉山时所移者,今已成树尔,可登岸摩挲之”[12],可见,园内还种植有清凉山(今五台山)移植的松树,畅春园俨然一座汇聚了南北方花木的植物园。
2.1.3 观赏与实用并重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皇家园林植物往往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13]。畅春园中的生产景观是一大特色,荷花、小麦、水稻是有明确生产功能的植物,这一部分植物使用范围涵盖了农耕区和水域,形成了作物景观背景。樱桃、葡萄则作为兼具观赏功能的果木,充当点缀性的生产景观。
2.2 植物配置分析
2.2.1 观赏植物与季相
畅春园内的植物根据观赏要素不同大致可分为4类:观花类、观叶类(秋色叶,常年异色叶)、观果类和常绿类,其中,常绿类无季相变化,作为植物景观的背景。畅春园植物观赏性较强的时期集中在2个部分,一是春夏之交的5—7月,二是秋季的10—11月,分别为观花和赏落叶的时节。从整体来看,畅春园即使在冬季也有可观赏的花木,正如康熙《畅春园记》所提“芳萼发于四序”,体现出四季有花、季相分明的特点。
2.2.2 植物与其他要素的配置
1)植物与建筑。
从考证出的植物来看,和建筑相对应的植物描写较为具体,且多和建筑的楹联匾额呼应,体现出植物配置的文化性。
另外,约翰贝尔《旅行记》(1720—1721)里曾提到宫殿区的植物布置:“院内种植几行树木,树直径八时许,估计是菩提树一类”“道路的两侧均有美丽的花坛和水沟”。由此可见,宫殿区可能采用规则式种植,且两侧砌有花台,以体现建筑的等级规格。个别特殊的建筑如澹宁居,王士禛《居易录》中描述为“止三楹,不施丹艧,亦无花卉之观”,甚至没有植物装饰,以突出理政的功能。

表2 畅春园考证植物

续表2 畅春园考证植物

表3 植物种类组成及生长习性
2)植物与山水。
从道光年间地盘图可以看出,地形与水面构成了园林中山环水绕的结构特色。根据畅春园平地造园的性质推测,山体不高,主要起屏障和限定空间的作用[14]。表2明确提到种植在山坡上的植物有松柏、山枫、婆罗树,均为高大乔木,且成片种植,营造出郁郁葱葱的“山林”景观。由此可见,在山体上的植物一方面在竖向上改变了视距,强化了空间感;另一方面大片乔木也充当了其他植物的背景,凸显其他焦点观赏植物的特色。
水岸的植物以成片的白丁香、桃花为特色,如对3条花堤的记载:“缓棹而进,自左岸历绛桃堤、丁香堤。绛桃时已花谢,白丁香初开,琼林瑶蕊,一望参差,[8]267”给人以震撼的视觉效果。除开花树种外,御制诗词“远入烟堤近柳前”也提及柳树在水岸的栽植,这与传统栽种方法是比较符合的,如《长物志》中提及对柳树的种植建议“更需临池种之”。
2.3 畅春园植物文化
2.3.1 植物种类文化寓意
楹联匾额往往反映了园主人的审美偏好及其追求,其文化性和意境营造也体现在植物的选择上。表4整理了楹联匾额中明确出现的植物,而这些植物在全园中往往大量运用。“松、竹、兰、莲”4种植物在文人园林经常出现,其寓意与士大夫精神追求相对应,表达高尚品格和脱俗气节[1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皇家园林受到儒学士大夫思想的影响;“萱草”的使用在这里较为特殊,是否真的运用在庭院中尚未可知,考虑到寿萱春永殿是乾隆母亲的住所,笔者推测这里是借“母亲花”的寓意表达对太后的孝心和爱戴。
2.3.2 整体文化意境
1)江山永固。
明清皇家园林多用油松、侧柏、桧柏为基调树种。松柏老枝苍劲,因四季常青,寿命较长而被赋予了延年益寿的文化寓意,色彩稳重肃穆,能烘托出皇家园林的氛围[1]。畅春园诗词里有对松柏文化的反映,如乾隆十二年(1775年)的《纯约堂》诗“即看阶砌畔,应茁万年枝”,再如乾隆十三年(1776年)所写“畅春松柏茂南山”,都反映出对松柏生命力旺盛、寿命长久的赞扬;寿萱春永的匾额也表达了长寿之意,并种植有松树。畅春园考证出有植物运用的建筑类景点共13处,而运用松柏的建筑类景点至少有5处,可见松柏和建筑的关系密切。这反映出松柏作为文化载体,寄托了帝王江山永固、长寿安康的愿望。
2)君怀天下。
畅春园沿用了清华园时期的稻田景观并将其作为皇家水稻引种的基地,反映了康熙皇帝的重农思想和科学精神,也对后期在其他多座皇家园林中设置农耕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有意引种非乡土的观赏和生产性植物到御园之中,江南、塞北和西域地区距离统治中心有较远的距离,又能反映出盛世初期时帝王对拥有广袤疆土的占有欲和表现欲,这为乾隆时期大量写仿各地名胜甚至是引种外国植物埋下了伏笔。在这一点上,畅春园为清代皇家园林的鼎盛做出了很好的尝试。

表4 楹联匾额涉及植物及其文化寓意
3 结语
通过研究畅春园相关史料考证出32种植物,以此为基础分析畅春园的植物景观特色,在植物种类选择上,既有地域性植物的栽植,也有南北观赏植物的引种,同时注重生产性植物的运用;在植物配置方面,畅春园四季之景各异,植物与建筑和山水结合凸显文化性,强调空间感;在植物文化意境方面,楹联匾额中的植物与士大夫精神追求所用植物相近,但作为皇家园林,畅春园具有独特的植物文化,如松柏体现帝王对江山永固的期望,稻田景观宣扬了皇帝对黎民百姓的体恤之情。
畅春园作为康熙帝创建的首座离宫式皇家园林,是平地造园的典范。作为一座以植物景观为主的御苑,尽管简朴,但畅春园为研究清代皇家园林植物配置模式、植物文化提供了案例。未来对于畅春园植物造景上的挖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注释:
① 考证出的32种植物中,大宫门处植物是由康熙《万寿庆典图》(描绘场景为康熙六十大寿,即1713年3月)得来,在之后(1713年6月后)扩建九经三事殿时改建,植物布置往往随建筑增减而变动,因此,大宫门处植物极可能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扩建后有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