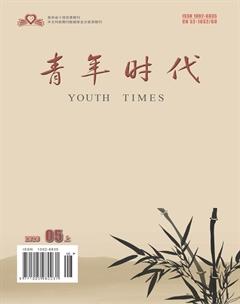月与诗:《心灵史》的审美特点浅析及反思
罗崇蓉
摘 要:本文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代表张承志的代表作《心灵史》入手,分析回族小说中所具有的独特少数民族审美特点,并结合作家其本人的生平经历反思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与审美特征的界限与延伸。
关键词:少数民族;张承志;审美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研究大多数从民族风俗习惯和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鲜少涉及少数民族小说文学形式的审美特色研究。少数民族小说作品集中反映了该民族人民群众最常态、朴实的生活风貌,是少数民族大众审美挖掘的最佳地点之一。笔者认为,研究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审美文化特色,一方面是对少数民族审美文化系统的完善与发展,另外一方面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系统研究的弥补与深入,是少数民族审美实践活动的延伸和提高。文章选取了回族当代文学代表人物张承志和他的回族文学代表作品《心灵史》为研究对象,力图从他身上窥见回族文学生活的面貌。
一、作者其人
张承志,回族,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张承志早年作品以小说创作为主,后期以散文写作为主。作品风格浪漫充满诗意情怀和理想主义气息,其代表作品有《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心灵史》《清洁的精神》等。
作为作者写作题材转折点的代表作品《心灵史》,是作者深入大西北四余年所见、所闻、所感的集结,一发表就经历了不少争议,作者的写作风格也从此转向。《心灵史》内容线索主要由一个个宗教历史人物和事件串联起来的,讲述中国回族教派哲合忍耶历史渊源的小说文学作品。全书共计22万余字,分为七个章节讲述教派导师及其门徒与清朝政府斡旋对抗的叙事作品。《心灵史》中不乏夹杂张承志本人深刻的人生思考,作者在经历大西北过程中,亲历人们所行进过的路程中的感怀与反思为历史事件的再现增添了感性关照。
二、《心灵史》的民族审美意象
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与一般汉族作家作品有着天然的区别,少数民族作家作为审美主体,他们的民族主体意识浓厚,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审美基因和心理活动。他们特殊的思维方式和生活阅历会给小说打上民族的印迹,这些印迹散落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人物的设定、情景、情节之中,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作者小说中经常描写的意象来提炼出这种审美偏好,透过可感可知的“物”把握作者民族身份背后隐匿的特殊情怀。
(一)月亮
《心灵史》中常出现的一个场景就是皓月当空,“月亮”这个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并在事态发展的转折时期起着呼应人物内心的作用。例如:“赞颂你十五的满月,圣光的照耀一切光芒都黯淡了主啊,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脸庞上如此苏莱提的人你是太阳,你是月亮你是光辉,你是灵芝你是心灵的灯光。”作者通过月亮比拟宗教中造物主的恩典,这一段也是在歌颂族人的崇高信仰与坚韧。
《心灵史》中不乏对“月亮”的反复提及与描写,小说中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圆月啊,你照耀吧,唯有着皎洁的本质……今夜,淫雨过后的天空,终于升起了皎洁的圆月,我的心也清纯,它朴素的像沙沟下的荒山,然后,我任心灵轻飘,升上那清风和银辉,追寻着你,依恋着你,祈求着你,怀念着你。”在这样的美学关照之下,月亮不仅饱含了作者深厚的民族情节,“而且展现了作者对肃穆庄严,崇高博大,深沉的美学风格的崇尚,以及对诗性,象征化艺术手法对独特追求”[1]。对月亮的审美是回族人特殊的审美观照体系,因为月亮所具有的高远、圣洁、静谧、谦虚、美好等特点是回族人对自身民族性格写照的反映,月亮暗合了回族人对精神境界的至美追求。
月亮在回族人那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矿石,也不同于汉族人给予相思团圆之意,月亮作为一种更加神圣不可触犯的物像悬挂在那里,夜夜谨醒。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常以月亮作为标示,清真寺建筑顶端也常有月亮的标识,月亮不是唯一神的代替或者化身,更不是崇拜物,在回族和世界穆斯林那里,月亮是一个宗教符号,因为穆斯林的斋月纪历就是从推演月亮的升降时间起算的。“远古,阿拉伯半岛的穆斯林就观察了月亮出没和盈亏圆缺等有规律的变化,并把这个看作全能真主的无数迹象之一,作为宗教的一个象征,从而对月亮产生了一种亲近的感情。”[2]这种感情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月亮反映的回族人的“信仰”在张承志的小说中尤为明显,“一弯新月”是给暗夜中踽踽独行的人们充满希望的指引和慰籍。族人将自己沉静隐忍的品行与月亮的精神暗合在一起,月亮承载了一个坚韧不屈、勇敢前行的民族精髓,是回族独特的审美意味,是张承志《心灵史》的灯塔。
《心灵史》第六门第二章“瞬忽的弦月”中写道:“在一个人声鼎沸的公园里,红男绿女们不会注意一些戴六角白帽的粗鲁农民。他们勉强找到了一个地方,跪下,脱了鞋,深深地致礼,点燃远道带来的安息香。然后,在游艺场的喧闹中,在稠密的人流中,他们开始诵经悼念。有一线不易觉察的弦月,悄然地高悬在晴空之上。事情完了,主观的心情已经熨帖。他们站起身来,摘掉头上的六角白帽走进人群。汴梁城并没有察觉。莽莽尘世中根本没有他们的痕迹。他们体味了进城的苦涩,他们看见了瞬忽的弦月,然后他们就消失了。这就是现代中国都市与哲合忍耶的关系。——还不是写出心灵的体验。只是朦胧的、表现心灵的一种意识。我放浪于他们的风土和故事,也放浪于这种奇异的文学之中。”心灵的“寻道师”哲合忍耶信徒经历百年沧桑浮沉,外面的世界早已姹紫嫣红,而他们固守的最干涸的土地,最荒瘠的田野,身处繁华之中内心却如平原上的一轮新月一样静谧与安详,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洁净的灵魂与信仰,这种不易察觉的、微小的力量,正如傍晚暮色时分悄悄挂上天边的新月一样,虽不绚烂但是亘古不变。“月”是回族人特有的清洁静谧的精神世界,是《心灵史》反复强调的精神追求。
(二)水
除了月亮以外,《心灵史》中另一个明显的意象就是“水”。《心灵史》中描写大西北的回族人在水比金贵的乡村窖雪度夏,正常的生活饮食用水依然非常艰难,而坚持宗教沐浴的回族却家家以浴水的清洁为首要大事。“旁人不能理解,盛着一瓢脏泥水下锅——为什么要留着那么干净的水沐浴。最重要的是劳碌之余,当教外人除了上炕吹灯睡觉之外,再也寻不出一星半点事情时,清真寺里悠扬有秩的念诵在黑夜里传扬。世界不仅于此,做人尚有美好的希望,这种现象就在荒凉的裸露的石脉,千里滚滚无边的一望焦黄之中,不可思议的成了现实,成了主宰。”回族日常的礼拜前需要进行宗教沐浴,称“大小净”,需要水淋浴全身,净化心灵,达到身体精神表里纯净的境界。水自然是宗教人士进入神圣领域的媒介,一捧清洁的水是回族人的精神中介,所以它成了回民族审美意象的又一独特领域。在回族那里達到清洁的一个途径便是通过水。
《心靈史》中描写了一个将作者带进哲合忍耶历史的大西北回族农民马志文,作者邀请他参加作者朋友间的一次小型聚会,在众多大使、作家面前,他满面通红,表情严肃,正襟危坐,始终笔笔直直坐在那里,不喝一口水不吃一口东西,任别人在他面前载歌载舞,他只等着作者。“而马志文头戴白帽,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如一座山。他一个人便平衡了我的世界。”他们只崇尚水的清洁,除了眼见水的来源以外,拒绝喝来历不明的水,远离他乡的信徒行囊里除了果腹的食物以外,剩下的就是清洁的水,喝的和沐浴的水。水的清洁在回教徒那里有着不争的界限,只有干净清洁的水才能洗涤身心,才能使自己心安理得的走向圣殿叩拜。水所意味的清新洁净的审美世界,是《心灵史》中人们追随的境界:“水又是净身时洗在肉体上不可或缺的物质。水代表的“精神洁净”是回族人生的支撑,水也展示了一个民族对生命神圣意义的理解。《心灵史》第六门“叩开现代的大门”中写道:“南京师傅,正用手边捧边饮。他同样坚守清贫,一如他的导师。”南京师傅手捧的正是从洁净故土上带来的清水,带了千里万里路途的清水,“水”除了洁净以外,还有坚守的意味,坚守用清洁的水洗涤身心,“水”的洁净美好意象在《心灵史》中得到全面深刻的展示。
(三)荒原
《心灵史》中除了有美好的审美意象,更有令人绝望和伤感的意象。小说中多次对残酷恶劣的大西北自然条件进行描写,“在西北荒凉的人间,绝望的穷苦农民又有了希望。一个看不见的组织,一座无形的铁打城池,已经出现在他们之中。穷人的心都好像游离出了受苦的肉体,寄放在、被保护在那座铁打的城中。”一方面是描写那个时候人们绝望的生存环境,“在大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人应该习惯一种淡漠。无论是对无休无止的风沙,对传说中歉收和灾害的消息,对家人的衰病丧亡。走上黄土高原的人,心里都有一层细尘般的绝望。但是还要生活,还要送往迎来,因此人又是疲懒的、对什么都不太希望的。”“在这种生存中繁衍,一代代的黄土高原居民便养成了一种朴实、开朗、平和,但是底气很硬的气质。抒情常常只是一瞬间地排排闷气,只是一眼看见平川或突然欲望冲动时,那发泄般的吼叫。”另一方面,侧面烘托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人们内心的起伏,这是一种强抒情的感伤艺术,它是与黄土高原格格不入的,它应该湮没得很快。可是这种抒情的异端偏偏就在这种单调的自然界里流传着。久而久之,它已经变成一种基因潜入了集体血统,成为人们对荒原的别样情感。
荒原意象背后代表了一种格调悲壮的审美叙事风格,张承志在《心灵史》中用荒原烘托悲凉的气氛,让读者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和悲剧壮美的审美趣味,让人感受到少数民族精神世界的强大和坚韧。
三、反思
少数民族作家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时,民族历史、民族心理、民族文化会融于作品之中,使之呈现一种具有特殊审美特点的旨趣,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民族文学中的民族审美特点。在《心灵史》中,“月亮”“水”“荒原”三个审美意象几乎可以涵盖回族人全部精神内核特征——信仰执着,精神圣洁,肃穆不逐世。笔者对张承志《心灵史》这三种审美意象特征的提炼也可以领略回族小说的整体审美风貌和回族人整体的生活风貌。张承志作品众多,早年风格比较统一,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等,善用诗性手法抒情描写,作品充满感性浪漫的味道。但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心灵史》《清洁的精神》等作品明显具有民族时代感。
笔者正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定义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呢?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界定究竟以作家身份为主,还是作品内容为主,这个问题在学界至今莫衷一是,并且在张承志这样的作家身份定位上出现了明显的复杂性和不规则性。李鸿然教授曾经对民族文学作品进行了界定:“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就是看作家的民族成分,以作家的族属确定作品族属,也就是说,只要是少数民族出生的作家创作的所有作品,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3]那么按照此种说法,一个世代从小居住在汉族生活群体之中,很少受到本民族生活方式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品一定要归到民族文学中去吗?在未有民族自觉前写作的文学作品,是否应该划分到非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去,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思考的。
参考文献:
[1]马慧茹.当代回族小说中的审美意象与精神追求[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25-128.
[2]邝琰.霍达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1.
[3]李鸿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12.
——从叙述者“我”的角度解读心灵之作《心灵史》
——从《黑骏马》到《心灵史》看张承志文化身份认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