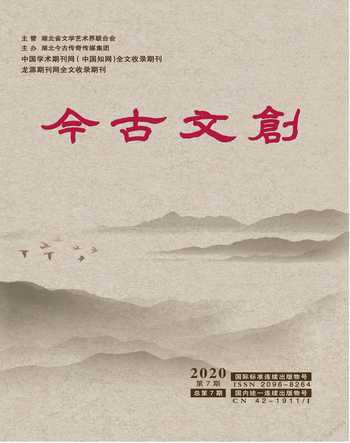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研究
刘畅
【摘要】 萧红,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女作家。她创造了大量的文学形象,她高度关注父权制社会里中国北方农村底层妇女的生存困境,以自己敏锐的女性意识和饱含血泪的笔墨细腻描写了她们的悲惨命运,沉重地叩问了女性的解放之路,揭示了封建传统礼教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人格精神的摧残。本文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之上,着重分析萧红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与女性形象,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萧红及其作品。
【关键词】 萧红;女性意识;女性形象;生命价值;女性解放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7-0015-04
一、萧红的人生经历与女性意识的萌发
(一)萧红生平经历
萧红(1911-1942),中国近现代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1911年(农历五月初五),萧红出生于呼兰县城一个地主家庭。其父亲张廷举,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1926年,受父亲阻挠、逼婚,萧红小学毕业后就没能继续上中学。
1929年祖父去世,在家庭中感受不到爱和温暖的萧红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毅然逃婚到北平,设法进入女师大附中继续读书。后因生活困难,萧红只好无奈离开北平返回呼兰,与未婚夫汪恩甲解除婚约。后来全家到阿城县福昌号屯,在有老封建思想的父亲的严厉管教和监督下,萧红不准与外界来往,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恰是她在福昌号屯生活的这段经历,为萧红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她的一些小说、散文就是以这里为背景写的。
在家“软禁”期间,受同是悲摧命运的两个家庭女人的暗中帮助,萧红成功逃离家庭,与汪恩甲在哈尔滨某旅馆共同生活了半年,在萧红怀孕即将临产之际,汪恩甲却毫无征兆地不辞而别,再无音讯。走投无路时与萧军结识,开始一起生活。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7月,因为与萧军在感情上出现了裂痕,伤心欲绝的萧红只身东渡日本。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两人在武汉结婚。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因肺结核病逝,享年31岁。
(二)萧红生平对女性意识萌发的影响
葛浩文说:“萧红在本质上是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的自传体式作家。”毫无疑问,萧红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不幸的几段婚姻,都对其文学创作的基调和倾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激发和催生了蕭红对女性意识的思考和呐喊。
女性意识,是女性在对自己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我意识,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是女性自我觉醒的产物。萧红自出生后,封建家庭冷漠的氛围、支离破碎的童年、不幸的婚姻生活,因为女性性别遭受家庭的歧视、遭遇人生的不幸,正像萧红自己所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其悲剧的一生,对萧红文学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萧红一生都在漂泊和动荡不安中度过,她缺失母爱、不信任亲情的破碎童年以及感情不顺的坎坷人生经历,成为了萧红深刻的人生印记,这些情感对其之后的写作有极其大的影响。基于自身的人生经历及身为女性的社会体验,萧红的小说创作带有浓郁的悲剧气息,并呈现出浓厚的女性意识,她将自己的亲身经历熔铸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体现了对下层女性悲惨命运的悲悯情怀,通过一个个女性生存困境的描述,无声鞭挞着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充分揭示了男权主义等对女性的摧残和迫害,呈现出显著的批判性。
作为女人的萧红,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两面家庭感情,一面是父亲的冷情冷酷、未婚夫的始乱终弃、丈夫的背信弃义、爱人的临阵逃离、生母的早逝别离、继母的形同陌人,一面是祖父对她的呵护和慈爱。她本人曾说:“从祖父那里,我才知道了人生除掉冰冷和憎恶外,还有温暖和爱。”萧红经历的悲惨人生对她日后的思想影响极大,在其作品中她用真实的人生体验对男权社会和女性地位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弗洛伊德认为:“文艺的功能就是一种补偿作用。”因此,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无法避免地将这种对男权主义的憎恶及对女性的悲悯情感融入她的创作中。
二、萧红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萧红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与不幸,都是因为我是女人。”受封建传统礼教以及男权主义的压迫,女性意识长期缺失,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五四运动等进步思想的传播,女性接受教育、参与社会活动的数量和范围不断增加,整体唤醒了社会上对女性意识的尊重和重视。萧红生活在这个时代,亲身经历和感受着随着时代进步发展女性意识的逐渐苏醒,并成为典型代表之一,其小说创作呈现出显著的女性意识。
(一)对男权主义的批判
萧红深受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的影响,其女性意识充分觉醒,她深切感受到男权主义对女性的摧残压迫。自创作《生死场》起,萧红打破原有的以男性视角居高临下叙事的写作,在对女性悲剧命运进行描绘的同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男权主义。萧红的一生,就是与男权主义进行抗争的一生,萧红的作品,都融入着她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形成了对女性意识的呼唤、对男权主义的深刻批判。
萧红经历了时代进步的思想和文化撞击,创作之初受左翼文学的影响,其作品更多地同情着底层的民众,尤其是被阶级和男性双层压迫的女性,其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多以女性、儿童、老人为主,女性居多,有着较激进和明显的女权主义思想。
“三纲五常”“男尊女卑”这些传统封建礼教以及伦理道德,对女性是无形的枷锁,用社会力量对女性进行禁锢和束缚。萧红的作品就是从揭示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人格的扭曲和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践踏为出发点,对传统封建礼教的糟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例如,她因幼时受的父亲绝情绝义的漠视,在作品里直接塑造了许多丑恶父亲形象(如《商市街》《呼兰河传》),都是她作为生活中直接受害者以亲身感受对男权主义的猛烈抨击与批判。
(二)对女性自身的剖析
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是从其本身的人生经历所散发出来的。她带着自己深痛的生活体验,源于对命运的关注,源于捍卫女性的个性尊严,萧红以其“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栩栩如生地描绘着她笔下的芸芸众生,从而使其女性形象生动真实。
萧红在批判男权主义的同时,也深刻自我反省和剖析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中,长期受到封建礼教及其伦理道德的说教和精神禁锢,导致多数女性无意识在自身潜意识深处恪守封建礼教,造成女性人格的扭曲和践踏。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女性的沉默不反抗无声地支持并维护了男性权威,成为推动女性悲剧命运形成的一环。
《生死场》中的金枝被男性粗暴占有之后,受封建礼教贞操观念的约束,女性的亲人不是感到受到了欺负、受到了伤害,而是感到无地自容,全家人都怕因这个事件而在社会上受到非议,甘愿屈辱地接受木已成舟的事实,任由女儿不自愿、不体面地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日复一日忍受男人的无端打骂和凌辱,还不能有丝毫的反抗和不满。面对懦弱且跛腿的二里半的厉声呵斥,麻面婆没有毫无反驳的意识,更不说敢有什么反抗的举动了,因为“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争斗,她的心像永远贮藏着悲哀似的,她的心永远象一块衰弱的白棉。”这就是当时女性悲惨生活、悲剧命运和悲哀心理的真实写照。
作为一种封建传统的社会现象,女性默默遭受着男权主义的凌辱和压迫,还对同性所遭受的悲惨命运麻木地视之为当然,甚至雪上加霜。比如《呼兰河传》中描写的垂死挣扎的女性群体,一方面忍受着男性冷漠无情地肆意践踏和凌辱,另一方面又做着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愚昧无知地使用惨无人道的暴行迫害着别的女性。更可悲的是,这些女性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去争取、去反抗,在长期封建礼教的禁锢下,灵魂和思想日渐同化、荒芜和麻木,甚至在耳濡目染中默认了男权主义的封建思想,并成为积极的“病态”维护者,非但没能成为奋起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觉醒者,反而沦为封建礼教实施罪恶的得力帮凶,使自己和别人全部沦为封建礼教以及伦理道德的殉葬品。
萧红在其小说中,通过自己的女性意识,向读者展示了作品中女性个体及群体的悲剧命运。她对女性固有的奴性病态和愚昧无知进行了直白的描述和无情鞭挞,深刻批判了封建礼教及其伦理道德,揭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男权文化禁锢了女性的身心,摧毁了女性的生命价值。
(三)对女性解放之路的探索
萧红基于自身的女性意识和敏锐的目光,探询和叩问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从社会角度、文化层面重新审视了女性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呼吁唤醒女性意识,对女性解放之路有著积极推进的意义和作用。
萧红用犀利的文字表达了对女性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被践踏和摧残的愤懑不平,传递了对女性的奴性病态、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和国民劣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观点,期待能够通过自己的发声对当时的女性现状有所改善。她对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从萧红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悲剧结局来看,她虽是当时社会的叛逆者,但却无力改变这黑暗的社会。萧红所期待的女性解放仍需要长路漫漫地追寻,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仍是需要探索的,不过萧红以其创作的女性形象以及文学经典带给后世非常具有价值的参考启示。
三、萧红小说中女性意识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寡妇,无家可归的弃妇,帮人做工的佣妇,以及童养媳,几乎都是北方农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村妇,萧红对这些形象给予了同情与哀愤,她用自己切身生活的感同身受和新文化思想中敏锐的女性意识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均有一些共同特征:
(一)生存的艰难卑微
中国社会历来重男轻女,正如《诗经·小雅·斯干》中描述的,“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女性的悲哀命运从一出生就注定了。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用较多笔墨来描述生活在呼兰河畔的女人们生存的悲哀。老王婆下地干活,把女儿小钟放在草堆上,孩子不小心从草堆上掉下来后被铁犁压死,老王婆面对亲生女儿的生死离别却毫无人性地说:“孩子死,不算一回事,你们以为我会暴跳着哭吧?我会嚎叫吧?起先我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以后麦子收成很好……到了冬天,我和邻人比着麦粒,我的麦粒是那样大呀……”这样无情无义的话听着既伤心,又恐怖可怕,出自一位母亲之口中,简直难以相信。
还有《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只有12岁的女孩子,纯真率性,却因其性格被村民们认为是“不懂规矩”,反遭家人打骂,甚至以迷信思想让庸医“治病”,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残害她的人就是自己的邻里女人,也是常年遭受男性压迫与摧残,经历过无数磨难的可怜之人。她们执着相信并遵循着封建礼教,虽然也这个孩子无冤无仇,但却变态地把自身惨痛磨难扭曲地转化为复仇心理,演化成为了男权社会冷漠无情的帮凶,构成荒唐可悲的扭曲社会。
(二)灵魂的的麻木病态
中国经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男权主义思想潜移默化植入在人们心中,而男权主义对女性的压迫,不仅仅在于身体的伤害,更多的在于对女性思想灵魂的摧残。萧红笔下的女性大多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生活在愚昧偏远的东北农村,她不仅关注受难女性的个体不幸,更注重千百年来劳动妇女的整体悲惨遭遇,从整个社会层面揭示看客、帮凶的病态灵魂。
在男权社会里,耳濡目染的是女性对男人的绝对服从,只要触犯封建礼教,必遭她们的指责管教,即使同为女性,也心理病态麻木,看不惯“出格”的人和事,童养媳小团圆媳妇就遭到邻里女人们的各种非议,在封建礼教的唾沫星中被活活折磨死,婆婆却认为这是为她好,是帮她成为一个符合传统标准媳妇的善意举动,同是女人却因着这愚昧的迷信封建而没有丝毫的愧疚。《呼兰河传》中,胡家大媳妇被丈夫毒打后,她没有丝毫反抗,也没有丝毫抵抗、抗拒的思想意识,甚至认为理所当然,轻描淡写地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封建礼教滋生着女性的奴性心理,女性的默认和顺从,自觉地充当了封建礼教罪恶的帮凶,助长着奴性心理的泛滥和社会认同,就这样,胡家大媳妇心安理得地忍受着丈夫的毒打。
《生死场》中,农家少女金枝在都市中惨遭强暴,周围的女人们虽然也和她有着相同遭遇,却都以麻木和漠然的心理,没有给予她丝毫的怜悯和安慰,就连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没有对女儿进行抚慰与关心,更没勇气站出来为女儿维权伸张正义,反而沉迷与金钱的诱惑,甘心牺牲催逼女儿的尊严,逼迫再度以肉体的被凌辱为代价,去换取极微少的金钱。这就是作品中一个病态麻木的母亲,一个心灵扭曲缺少温暖的女性,一个社会现象的映射和反映,她们不仅沉默忍受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更是在封建礼教的约束下、在女性意识的缺失下,将痛苦施加在其他女人甚至是自己女儿的身上。
(三)生育的苦难刑罚
在医学条件不甚进步的那个年代,生育就是每个女人必经的一件“走鬼门关”的事。而萧红认为,对生育这件事,男人从来不以为然,对于女性的痛苦视而不见。萧红在很多作品中都写到了女人的生育,萧红认为女人的生育就是“刑罚的日子”,在女性意识缺失的社会中,女人在家庭中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生育是她们命定的劫数和苦难之源,却丝毫不会引起男人的同情关爱。
《王阿嫂之死》中的王阿嫂,也是个悲剧人物。丈夫被地主活活烧死,她成了贫困潦倒的农村寡妇,挺着大肚子还得下地给地主干活,休息时被地主看见,竟然惨无人性地踢打她即将临盆的肚子,最终难产而死,两个生命成为封建礼教和女性意识的寻常代价。
对于女人的生育,《生死场》第六章《刑罚的日子》描写得具体生动,大部分都写生育的场景,有动物的繁殖场景,也有妇女临盆生育的场景,两种场景交汇描述,并且互相关联起来对比描写,画面感极强,冲击力极大。比如文中专门描写女人的生育,大着肚子的女人们,还得和往常一样一刻不停地在地里忙碌着,既愚昧又是封建礼教牺牲品的男人们,没有丝毫家人情意,对怀孕在身的妻子没有一点体恤温存,甚至板着面孔满口粗话。即使女人临盆生产,也得不到半点安慰。五姑姑的姐姐被迫在光着的土炕上生产,就是迷信怕犯了忌讳。她疼痛难忍,还不敢发出声响,生怕惹得自己的丈夫不高兴,而粗暴的丈夫还是冷酷无情地泼了她一身的冷水,产妇的脸色由灰白转至青黄,腹中的痛苦更是难以描述。女人除了要忍受生育之痛,还要遭受男人的打骂折磨,在他们眼中,看重的是传宗接代,而妻子承受生育之苦是理所应当,而且,痛苦的生育过程还让他们感到嫌弃厌恶。
(四)封建礼教的束缚禁锢
萧红在《小城三月》中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沉痛地祭奠了被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迫害的广大女性,并更进一步地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表现了萧红的女性意识和反封建精神。
萧红在《小城三月》中对翠姨这一女性,表现了广大女性被封建礼教的束缚抑制,对封建礼教及其秩序的畏惧和恪守。翠姨自小长期接受封建礼教的种种贞洁节烈观念,在耳濡目染下也认同了封建礼教下的包办婚姻制度。然而翠姨对才华横溢的堂兄产生了真挚热烈的爱意,可她矛盾地遵循着封建礼教,压抑着爱情,将对堂兄的真爱深深埋藏在心底。同时,翠姨没有对包办婚姻流露出丝毫不满,听任家庭对她的命运进行安排,顺从地接受订婚,只是顾影自怜地把真正的爱埋藏在心里,将自己的爱情悲剧归结为命运不好,甚至还拼命地糟蹋自己的身体,想死得越快一点儿越好。然而,她的堂兄,直至翠姨死去,也未能明了翠姨对他真挚炽烈的爱情。
四、萧红小说中女性意识的意义与价值
萧红的文学创作深受鲁迅小说的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思想的影响,在其女性意识产生的同时深度思考探索女性问题,萧红小说女性意识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对女性解放的探索、社会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女性生命价值的揭示。
长期的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顽强地禁锢束缚着女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培养了沉默顺从的女性,甚至以贞节、德行等对女性进行思想约束,消除女性逾越、突破封建礼教的意识和勇气,遏杀了女性对新事物的认知和追求,使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沦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沦为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的殉葬品。
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女性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完全丧失,生动揭示了封建礼教以及男权主义的践踏压迫,通过对封建礼教以及男权主义的血泪控诉,勇敢地呼吁女性的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尊重。
虽然萧红对女性解放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从萧红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其难逃厄运的悲剧结局来看,她在当时社会是勇敢者、叛逆者、觉醒者,但却无力改变这黑暗的社会。萧红所期待的女性解放仍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五、結语
萧红以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思想和敏锐的女性意识,以犀利的文字高度关注并描写了男权主义社会里中国北方农村底层妇女的生存困境和悲惨命运,她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礼教以及男权主义,深刻揭示了长期受封建礼教禁锢的女性问题和麻木扭曲的病态社会,呼吁整体社会对女性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的尊重。
萧红的作品以小见大,从女性悲惨的生活状态入手,不仅直接抨击了封建礼教以及男权主义,还立足社会发展,从文化层面和思想层面对封建文化的落后性和劣根性进行了深刻批判,深化了小说作品的思想主题,提升了文学创作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尽管她所期待的女性解放仍需要不断探索,不过,萧红以其创作的女性形象以及文学经典带给后世非常具有价值的参考启示。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小说全集[M].长春:时代出版社,1996.
[2]梁馨予.萧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D].东北师范大学,2018.
[3]霍慧玲.萧红笔下女性的生存困境分析——民国女性悲剧意识研究之一[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