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猫狂欢》:小事件如何通往大历史?
刘 东
一
罗伯特·达恩顿 (Robert Darnton)《屠猫狂欢:法国文化史钩沉》(The Great Cat Massacre-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的英文标题很耐人寻味。中译本直接依照字号大小,将之分成了主、副标题。这种处理看似简明,实则“粗暴”。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标题。用大字号高亮出“屠猫”一词,很明显是为了抓住大众读者眼球。但随后出现的“and”就将“屠猫”暗暗拉回到与其他个案相同的起平线——它们都是漫长法国文化史中的片段(episode)而已。这种处理带来了一种相当暧昧的阅读效果,我们自然可以将之理解为一整个主标题,但也未尝不可看作是主标题 “缺席”状态下的副标题。
这样一来,中文标题里没能出现的“Episodes”(片断)一词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从各章标题中也能看到:
Chapter 1 Peasants tell tales:the meaning of Mother Goose
Chapter 2 Workers revolt: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
Chapter 3 A Bourgeois puts his world in order:The city as a text
Chapter 4 A police inspector sorts his files:the anatomy of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Chapter 5 Philosophers trim the tree of knowledge:the epistemological Strategy of the encyclopedia
Chapter 6 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
每一章的标题都是“主体+动作”组成的。农民、工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分属不同阶层的群体共同在法国18世纪的大舞台上表演,他们的动作仿佛随机地定格在达恩顿的视野中,先被赋予了一个恰切的理解,而后被诠释出或浅或深的意义。这里的“片断”,一方面描述出了达恩顿应用的史料的性质——故事书、印刷工人手记、警探档案、订书单等诸如此类的“边角余料”;另一方面作为整本书的组织结构——法国18世纪的六个分属不同社会阶层的片断的组接;同时也是达恩顿的“方法论”——他完美地从历史中打捞出了几块闪闪发光的鳞片,反复摩挲、把玩,而后把它们镶嵌到更大的社会结构之中。
对非常规史料(文学文本)的使用,对“阐释”的看重,以小见大、四两拨千斤的学术期待,我们也正在这里看到了近年来新文化史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原因。我将在下文中首先强调这种研究方式带来的启发,而后,我将以同样描述相同时段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为参照,指出这种研究思路的局限和可能性。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深入理解《屠猫狂欢》是必要的,《屠猫狂欢》面对正统史学时表现出的那些“灵巧”与“困窘”,正让文学研究者心有戚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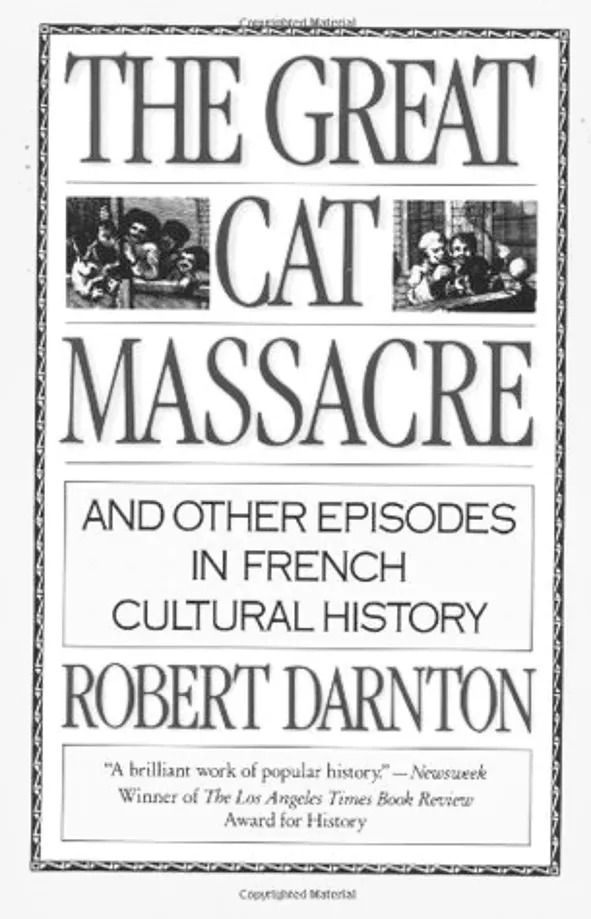
图1 《屠猫狂欢》1984年初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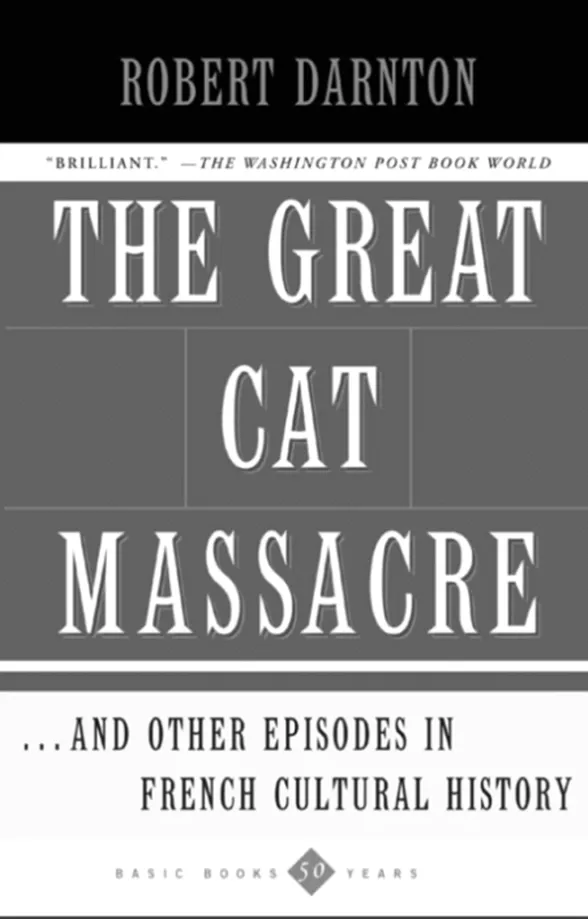
图2 Basic Books版本《屠猫狂欢》封面
二
识者都指出了达恩顿所代表的新文化史研究对人类学的借鉴,克利夫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文化的阐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及“深描”(Thick Description)等概念被深入贯彻到了达恩顿的研究中。这种研究思路首先得益于新历史主义以来的“历史文本化”的趋势。正如达恩顿在书中所言:“诠释与事实纠缠不清,我们永远不可能分得清楚。我们也不可能跳过文本杀出一条生路直达文本所不能及的确实真相。”①[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6页。既然我们始终处在文本的“镜城”之中,那就只有借助对文本的阐释,才能捕捉到真相的踪迹。而能够进行阐释的前提是,我们相信文本同语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拔起萝卜带起泥”,个体的行为准则就是全社会的“语法”。用达恩顿的话来讲,“(不是)文献如何‘反映’其社会环境,因为那些文献全都嵌在既是社会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象征世界中”①[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6-287、287页。。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这种立足于文本解释、以一篇文本带动整体语境的研究方式是再熟悉不过了。以上种种,其实也大都是文学研究者共同分享的前提。
以一则原始材料入手,大量引述民间文学研究、社会史、阅读史、书籍史等相关前研究作为背景,立足于对文本语义、结构、叙事、风格的深入阐释,在文本与文义格局之间来回穿梭,进而导向一个虽然被归于“心态史”、但往往具有某种社会史意味的判断,无怪乎以大量数据和史料为基础的传统史学界会认为这种研究方式过于“轻巧”。但文学研究者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却往往能看到其见解的独到透辟之处。
以本书中相当精彩的第一章为例。达恩顿虽然借鉴了民间文学的研究方式和法国社会史研究,但全章的结论其实正是在细腻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依靠挖掘故事设定上的共性,寻觅法国18世纪的社会背景;同时横向对比,在故事变奏中寻找出近代法国的独特性。这两种思路本不独特,真正的功力在于达恩顿靠着同文本的“贴身肉搏”,一字一句抵达了最后结论。而繁密的故事举例并非多余,正是依赖语言对故事的复现、在复述中强调侧重、突出关节,结论才“水到渠成”地呈现了出来。
这种强大而流畅的叙述能力在其他章节中也能见到。第二章分析了印刷工人孔塔的手记,整个论述成功的关键,其实是将孔塔作为“叙事者”的面向引入到对文本故事的解读中。孔塔手记完全是一个圈内人写给圈内人的叙述,只有把握他的社会身份(印刷行业协会瓦解前夕——师徒关系的变化,青年——狂欢节的主力),我们才能把屠猫的寓意(巫术、性、偷情)予以更为妥帖的安放。第三章的独特性在于结构。达恩顿在三层叙述中细腻地分析出了作者意图与不同“套语”/意义系统之间的错位与契合,我们也得以在这篇通篇歌颂权力、贵族与高雅文化的记述中看到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在第四章里,达恩顿则充分关注到了“沉默”的意义。相比于警探写出的,被隐藏起来的部分才最为真实地呈现了社会尚未将作家看成独立社会身份对待的“潜意识”。至于第五章从序言入手解读百科全书派的作书心曲,第六章从卢梭读者来信入手发现一种“新型”作家—读者关系,这些处理文本的态度和方式,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就更不陌生了。
达恩顿强调自己是撞上了“不可思议”、而后找到了“进入陌生心灵的有效切入点”,这种表述似乎在全力表现写作时的随意与偶然。但其实无须借助达恩顿的自述,我们就能想象到那份警官档案是怎样深埋于浩如烟海的档案堆里,而达恩顿又是怎样“灰头土脸”地在纳沙泰尔公司成千上万份往来书信中翻到了兰森的书单。归结到底,这种研究方式的优长之处还是在于向我们展示了“四两拨千斤”的技法。如何发现并使用一份不常见的材料,并进而借助这则材料撬动整个既有的学术叙述,这是达恩顿工作的精彩之处。他首先发现了这些奇形怪状的小石头,而后见招拆招,在把握文献独特性的基础上,对每则文献都做出了独到的读解。正像他自己在后记中所说:“证据如此模糊,竟至于有人索性放弃这一番志业。但是我认为,和致力于未尽妥善的诠释比起来,排斥民间故事之为用是更大的错。”②[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6-287、287页。这句话对其余各章也同样适用。
让不可说的东西变得可说,达恩顿的研究模式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第一章对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在版本对比中寻找法国精神的思路其实并不罕见,中国研究者早在顾颉刚上世纪20年代的孟姜女故事流变考中就见到了这种思路的有效性。我以为这里更为重要的是达恩顿对民间故事文献性质的基本判断:讲故事既能呈现出人们无意识下的某些习惯,也能反过来呈现出“匮乏”。那些天然拥有的会成为故事的背景设定,而那些无法具有的则往往在故事中获得一场想象性的胜利。而新材料的引入势必要更新我们对总体历史的理解。第二章作为全书中最精彩的一章,确实向我们呈现出了既有研究无法呈现出的新意。借助一本怪异的孔塔手记,达恩顿很有效地向我们勾勒了18世纪法国工人所处的民俗、传统、仪式的氛围。在大工业生产尚未完全铺开的法国,技工文化有着怎样的驳杂和丰富性。第二章的结论强调“风险正是玩笑的一部分”,拉伯雷的笑声既消解大众反抗的动能,又不断在真实情况边缘游走与试探,“杀猫之举有可能变成公开造反”。这一看法显然借鉴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而玩笑/革命的辩证,正以一种高度文学的方式,拿捏好了心态史的分寸。
第六章达恩顿试图借助卢梭的个案重新启发我们对“阅读”行为的理解。他不满足于一条从“精读”到“泛读”的大的历史轨迹,而希望能具体到作家同他的读者之间关系的层面来理解阅读作为行为的意义。这一思路当然高度巧妙。作为一位有着高度“作者意识”的作家,卢梭利用“卑微文体”却成了畅销书作家;他完全不是被文学市场哺育出来的,却无形中反叛了他所处的沙龙—赞助人制度。他的前言设置了召唤理想读者的结构,他的书信集里留存着大量的往来通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恩顿成功勾勒出了一种“新型的作家文化”(a new cult of the writer),并尝试松动我们对文艺及出版现象概念化的理解。
当然,对“小事件”的读解常常是见仁见智,拿捏好分寸的“当止则止”有时也可能是还“隔一层窗户纸”。达恩顿将卢梭所代表的文学视为“反文学的文学”,并试图将之归结为宗教的影响——“为了要跟卢梭写信联络,觉得有必要向他告白(Confess),就像它们认为他是在向他们告白”①[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49页。,中译本在这里显然有缺憾,因为正是这个“Confess”最为明确地向我们提示着:“阅读乃是为了直接吸收‘上帝之道’。”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虽然很难估量宗教对于西方社会的意义,但同样也很难信服地将卢梭抬升为一个转折点,然后用“宗教情绪”轻易地越过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联想到福柯《何谓作者?》(What is an author?)中的教诲,就会无法满足于达恩顿目前对这些有趣问题的解答。
三
达恩顿的《屠猫狂欢》本质上还是一种阅读“小事件”的方法。而小事件如何通往大历史,这是新文化史受争议的地方,也是达恩顿无法完全给出答案的地方。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处理的时段同《屠猫狂欢》高度一致,二者正可相互参照。事实上,《屠猫狂欢》的案例中的很多描述都可以看成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注脚”。我们看到了农民阶级饱受繁重税捐的压抑、同贵族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第一章),我们看到了城镇手工业行会的解体、逐渐变化的师徒关系,世界日益分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群体”(第二章),我们看到了处在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如何去想象一个新秩序并期待着成为自己的主人(第三章),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如何具有政治抱负(第五章)、作家如何脆弱(第四章)但却具有政治家般的吸引力(第六章)。这些都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处理了的问题。所不同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里的这些细节,都紧紧围绕在一个整体论述展开。托克维尔勾勒了法国贵族制逐渐被摧毁、中央集权愈加完善的历史过程。农民、贵族同资产阶级三者之间不断分裂且不可挽回,终于在一次总爆发中走向了瓦解。大革命充满理念性,看似一切都是全新的,但新国家正是在旧制度的瓦砾中重新被搭建了起来。法国知识分子/文人在政治上的独特位置造成了大革命的观念性和理念化。
我们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看到的是一幅更加完整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如《屠猫狂欢》所说,“资产阶级如何想象成为新主人”,但我们也同时需要看到他们是如何因为贵族特权的壁垒而无法成为“主人”。我们确实看到了知识分子们的政治抱负,但百科全书派更新知识系统的诉求是在怎样的社会结构中导向了一种政治行动,在《屠猫狂欢》中又付诸阙如。而卢梭的阅读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一条浪漫情调(Romantic Sensitivity)的“滔滔泪河”而已。
达恩顿在结尾强调自己在证据(Proof)/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两个维度上受人质疑,其实归结起来,达恩顿需要回答的是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对民间故事的阅读诚然能够理解那一时代农民们匮乏、无望、鼓吹机智以求生存的状态和心态,但农民们的处境,只有在资产阶级城乡二元结构确立后乡村被日益抽空,农民们面临着领主放弃对农民的责任、中央集权加强、税负加重而落后的包税制度仍然实行、大量的制度成本被分摊在农民身上等等诸如此类更为具体的现实中才能得以理解。萨特解读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写法时高度赞许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每个事实一旦被确定,就要作为一个整体的部分被观察和解码……在马克思那儿永远找不到实体,它们在研究的范围内通过它们自己来自我确定。”①[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5页。细节只有在总体的图景中才能被镶嵌定位,细节一定存在,解读一定精彩,但达恩顿每一次精彩的“停止”,到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大的视域?
反观达恩顿的几个案例,可能唯一的总体性被归结为“一个同我们今日的情感结构相隔绝的世界”这一点上。这些案例中,作者同我们似乎都隐隐地感觉到了变化。作者在第一章中说“玩笑同革命不啻霄壤”,他认为农民们身上体现的还是保守的、可为体制消化吸收的力量。他在第二章中在巴赫金“狂欢理论”的意义上旌表“拉伯雷的笑声”,认为工人阶级的狂欢相较于革命而言,虽不中,亦不远矣。我们其实还是能感受到作者高度强烈地希望捕捉到更为广阔的现实的诉求。不过如何捕捉,这应该还是达恩顿的困惑,所以他才在第三章中径直认为:“文化上的阶级概念靠拢,此一阶级概念塑造了城市的新主人;就确认城市新主人的身份而论,‘资产阶级烹饪’所发挥的作用超过工厂。”②[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50、33页。尽管小城并没有工业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的主人身份,绝对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烹饪”就能命名的。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告诉我们,主人的命名必然是有旧主人和仆人作为参证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注定是一场与别人共同完成的交响。达恩顿这里的跳跃显然有些轻易。我们不得不承认:达恩顿的研究,其实是拉开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距离。
达恩顿其实无意与托克维尔对话,但托克维尔的幽灵却似乎总是徘徊不去。达恩顿引入人类学视野,一直在强调一种陌生人的阅读方式。达恩顿认为18世纪的法国文化其实早已不是我们今日的逻辑能够完全把握的,“他们人已作古”,我们是在“时过境迁之后”,发现那些“幸存的意义”。这种态度对法国人托克维尔来说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③[美]罗伯特·达恩顿:《屠猫狂欢》,吕健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50、33页。如果说真的存在“文化史”,那文化就应该是一条绵延的河流,18世纪的法国文化必然通于20、21世纪的法国,而前者的意义,也要在以后者为时间轴而非孤立的前提下,才能得以确认。
文化的具体表现在被历史思维科学厘定后成为研究者案头的研究对象,如何利用这些具体表现,在如何在抛弃经济决定论、抛弃文化系统只是社会秩序的“冲击—反应”等机械观点后,仍能走到同样抽象的层面,这显然是达恩顿面临的一个并不容易解决的课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位文化的意义?
达恩顿面临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问题。文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的争议是,如果要达到一个实证性的历史结论,为什么不是数据、不是核心史料,而一定要利用文学文本?而如果是文学内部的问题的话,又如何能够带出更为广阔的意义?文学研究者当然也可以做好自己的独特文本的诠释,得到一个颇为中肯的结论。只不过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找到自己的总体地图?本雅明在选择波德莱尔的时候应该会有人来向他询问:为什么一定是这块“鹅卵石”能反映出19世纪巴黎的文化底层。这反过来都提示着我们不能将文学研究简单处理为文化史。它们诚然精巧,但可能也因此而忽略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结构。它们可能反映部分的现实,但却很难说是有鲜明理念支撑的“真实”。这也正是我在文章的一开头说这本书没有“主标题”的原因。小事件如何通往大历史,《屠猫狂欢》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当然,这也可能是达恩顿故意悬置起来、不想给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