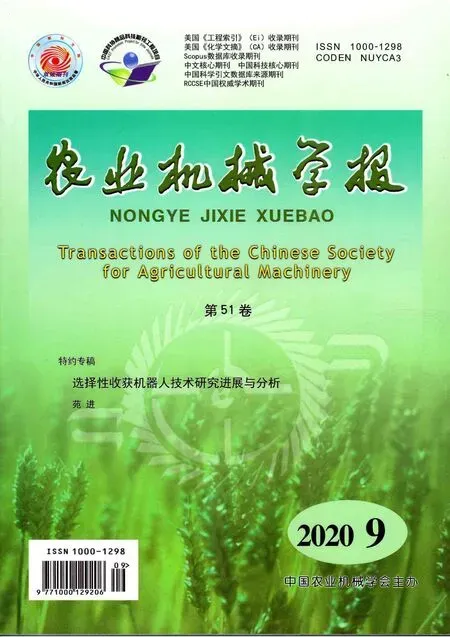基于GIS与RS的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格局演变
苏 凯 孙小婷 王茵然 陈 龙 岳德鹏
(1.北京林业大学精准林业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3; 2.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系, 台北 10617)
0 引言
目前,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环境破坏和退化的威胁,不合理的经济开发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1]。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特别是在干旱地区,随着土地开发规模和强度的急剧增加,土地荒漠化问题日趋严重[2-5]。中国是世界上土地荒漠化严重的国家之一,最新普查和调研结果表明,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1.16万km2,沙化土地172.12万km2,近4亿人口受到土地荒漠化的影响[6]。有研究表明,我国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1 281.41亿元[7]。为保障我国生态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主体功能区划基础上提出了“两屏三带” 国家生态屏障方案[8]。研究者对国家生态屏障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静等[9]通过对南方丘陵山地带NDVI的时空变化研究,认为实施生态工程是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的重要原因;辛良杰等[10]研究指出,在内蒙古防沙屏障带,高程对草地NPP降低的影响力大于降水量与气温;王晓峰等[11]从国家尺度研究了“两屏三区”生态系统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北方防沙屏障带作为“两屏三带” 国家生态屏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北方地区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12]。虽然有关生态系统格局时空变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较多,但针对北方防沙屏障带的生态系统格局演变的研究较少[13]。国家自然资源部(环境保护部)曾开展“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2010年)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14-15],进行“国家生态屏障带生态环境十年评估”,但在近10年中,受全球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屏障带生态已经出现较大变化,已有研究结果不足以为新的决策提供支撑。定量掌握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状况及结构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特别是研究其生态系统正向与逆向转换变化趋势,评估生态保护对其发挥生态保障功能的作用,可为后续北方防沙屏障带监测与评估提供科学基础,对于其管理决策及绩效评估考核具有重要意义[16-19]。
本文以北方防沙屏障带为研究区,利用GIS与RS技术,根据2005、2010、2015年的MODIS遥感影像,提取7类生态系统类型及其空间分布数据,从生态系统结构、生态系统正向与逆向转换、景观指数变化等方面分析北方防沙屏障带2005—2015年生态系统格局及其变化,掌握近10年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环境状况、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以期为北方防沙屏障带的生态保护、生态恢复和生态发展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北方防沙屏障带从西往东由塔里木防沙屏障带、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和内蒙古防沙屏障带构成,呈细长的带状横跨我国北部[20](图1)。其中塔里木防沙屏障带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克拉玛干荒漠北部;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位于甘肃河西走廊地带,包括甘肃省和青海省部分区县;内蒙古防沙屏障带包含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河北省部分区县。共涉及7个省区的102个县市,总面积89.06万km2,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带,年降雨量在30~450 mm,从东到西逐渐减少;年均气温为-1.9~13.5℃;屏障带内土壤粗砂含量高, 土壤有机质较低,以荒漠化土地为主;北方防沙屏障带风速较大,据统计2010年平均扬沙速度(大于5 m/s)在6.5~8 m/s[4]。

图1 研究区位置Fig.1 Location of research area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土地覆盖数据来源于MODIS的土地利用产品,来源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官网(https:∥ladsweb.nascom.nasa.gov/search)[21]。在该土地覆盖数据中基本的土地覆盖分类包含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nternational Geosphere Biosphere Programme,IGBP)定义的17类,其中包括11个自然植被类型、3个土地开发和镶嵌的地类和3个非草木土地类型定义类。通过投影转换、图像镶嵌、裁剪等进行图像的预处理,对IGBP的土地覆盖分类体系进行重分类,提取研究区域内的生态系统类型信息,见表1。
1.3 研究方法
1.3.1生态系统格局转移矩阵
生态系统转移矩阵能直观反映研究初期阶段和末期阶段的生态系统分类结构[21],体现了研究期间内各生态系统类型的转变状况[22]。不同类别的景观面积占比为

表1 北方防沙屏障带一级生态系统分类体系Tab.1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he first-class northern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1)
式中Pij——生态系统分类体系中基于各级分类的第i类生态系统在第j年的面积比例
Sij——生态系统分类体系中基于各级分类的第i类生态系统在第j年的面积
TS——评价区域总面积
n——生态系统的类型数
1.3.2PNTIL模型
正向和逆向转换指数(PNTIL)模型可分析生态系统格局的演变趋势[23]。基于各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将生态系统转换划分为正向变化和逆向变化,建立生态系统正向/逆向转换规则(表2),利用北方防沙屏障带2005—2015年生态系统转移矩阵,对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PNTIL进行定量评价。正向转换率越大表示生态系统越稳定;逆向转换率越高表示生态系统越脆弱。生态系统转换指数计算公式为

LCTRi,k=100(ΔSi,k/Si)/t (2)
式中LCTRi,k——第i个区域内生态系统类型向k个方向的转换率
Si——第i个区域内所有生态系统总面积
t——时间
ΔSi,k——向k类型转换的总面积;k=1表示区域内生态系统正向转换率,k=2表示区域内生态系统逆向转换率
1.3.3景观格局指数
景观格局指数是景观异质性的具体表现,同时又是包括干扰在内的各种生态过程在不同尺度上作用的结果,采用单一研究方法或单一指数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的复杂性,同时不同景观指数之间往往存在相关性[24], 在利用PNTIL模型评估生态系统转换趋势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评估景观格局及其变化可以综合反映生态环境状况。因此本研究通过借鉴学者研究成果并结合研究区实际特点,在类型水平上分别选取斑块个数(NP)、斑块密度(PD)、边缘密度(ED)、平均斑块面积(AREA_MN)、景观形状指数(LSI)、某类斑块所占百分比(PLAND);在景观水平上选取斑块个数(NP)、斑块密度(PD)、边界密度(ED)、平均斑块面积(AREA_MN)、景观形状指数(LSI)、蔓延度(CONTAG)、修正的辛普森均匀度指数(MSIEI)、聚集度(AI)等景观格局指数对北方防沙屏障带景观格局特征变化进行综合分析[25]。
2 结果与分析
2.1 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结构特征
从生态系统类型构成来看(图2),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类型中草地和荒漠分布最广,其面积约为60万km2。草地主要分布在塔里木防沙屏障带的北部、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的中部、内蒙古防沙屏障带的大部分区域。塔里木防沙屏障带内的荒漠几乎分布在其南部的塔克拉玛干荒漠,其他地区荒漠分布较少;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荒漠主要分布在东南角,为甘新库姆塔克荒漠,中部零星分布;内蒙古防沙屏障带荒漠主要分布在西南区域,少量分布在东北地区,自西向东依次为腾格里荒漠、乌兰布和荒漠、巴丹吉林荒漠、库布齐荒漠、毛马索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荒漠边界处也是森林分布的主要区域;农田集中分布在内蒙古;城镇占比在1%~2%,零星分布于地势平坦地区,少有分布于山区与平原交界处;湿地主要分布在德令哈市、刚察县和海晏县,其他地区呈点状离散分布,占0.1%~0.2%,以水系为主;裸地和湿地所占面积较少,在8%~10%之间,分布无明显规律。

图2 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空间分布图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system in study area
图3为北方防沙屏障带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及变化率对比。10年间,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类型构成变化趋势较为明显。森林类型在2010—2015年增幅明显,总计面积扩增了46 221 km2;城镇所占面积比例虽小,但是变化率非常高;草地在2005—2010年、2010—2015年均呈上升趋势,但其在2010—2015年间增幅更为明显;湿地、耕地和裸地总体均呈减少趋势;10年间荒漠面积持续减少,减少32 749 km2,表明治沙效果明显。

图3 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类型变化面积与变化率Fig.3 Change area and rate of landscape types in northern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从分屏障带来看,在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其草地在2010—2015年增幅明显(图4),总计面积扩增了16 049 km2;城镇所占面积比例虽小,但是变化率非常高,达到91.83%;荒漠面积持续减少,10年间减少6 457 km2,治沙效果明显;森林、湿地、农田和裸地总体均呈减少趋势。

图4 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类型变化面积与变化率Fig.4 Change area and rate of landscape types in Hexi Corridor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在内蒙古防沙屏障带(图5),森林类型在2010—2015年增幅明显,总计扩增了25 688 km2;在2005—2010年、2010—2015年草地呈上升趋势,但其在2010—2015年间增幅更为明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面积增长迅速;湿地、农田呈减少趋势,但湿地的变化率较大,达到58.05%;荒漠面积持续减少,10年间减少18 822 km2,治沙效果明显。

图5 内蒙古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类型变化面积与变化率Fig.5 Change area and rate of landscape types in Inner Mongolia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塔里木防沙屏障带(图6),在2010—2015年森林类型增幅明显,总计面积扩增了21 417 km2;在2005—2010年、2010—2015年草地、湿地和裸地呈减少趋势,但其在2010—2015年间减幅更为明显;农田和城镇总体均呈增加趋势;荒漠治理取得一定成效,10年间荒漠面积减少7 057 km2。

图6 塔里木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类型变化面积与变化率Fig.6 Change area and rate of landscape types in Tarim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2.2 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景观格局演变分析
2.2.1生态系统转移类型和转换方向
受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等外界干扰因素作用,生态系统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各类型之间产生了类型转换。2005—2010年间,农田转出约占总面积的4.32%,其中主要流向草地和森林,面积分别为5 385.7、23 857.3 km2,这表明重要生态功能区的退耕还林工程取得显著效果。城镇用地面积逐年稳定增加,且有转换速度呈逐渐加快趋势,增加面积主要来自于农田,约为2 165.8 km2。约有20 864.1 km2的荒漠转换为草地,1 428.6 km2的荒漠转换为森林,治沙效果明显。另一方面,有24 238.1 km2草地、5 546.3 km2森林转为农田。 由此可见,屏障区内在滥砍滥伐、垦荒复耕等行为仍存在,仍有2 518.2 km2农田、20 204.2 km2草地转为荒漠,由此可见,农用地撂荒,草地过度开发等活动仍是造成荒漠化因素。2010—2015年间,草地、农田、荒漠等转换程度较前期剧烈。农田的转出约占总面积的5.83%,其中主要流向草地和森林,面积分别为11 802.7、31 263.8 km2,同时有草地29 048.6 km2、森林6 564.8 km2转换为农田,总体来说退耕还林工程仍取得一定效果。城镇用地面积逐年稳定增加,且有转换速度逐渐加快的趋势,增加面积主要来自于农田,约为5 489.4 km2。约有53 331.4 km2的荒漠转换为草地,12 387.7 km2的荒漠转换为森林。2005—2015年间,森林与草地、草地与农田、城镇与农田、荒漠与草地,这4组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较多。同时可以看出,这10年间各地类之间的转换比例不大但比较明显。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转移矩阵及各子屏障带的转移方向见表3、图7~10。
2.2.2生态系统类型转移趋势
运用生态系统正向和逆向转换指数(PNTIL)模型计算出2005—2010年、2010—2015年各生态系统正向逆向转换率,如表4所示;同时进行分区统计,得到2005—2010年、2010—2015年屏障区各区县正向和逆向转换率并利用自然断点法进行分级,如图11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从2005—2015年,森林、草地、湿地生态系统的逆向转换率均大于正向转换率,这可能表示在2005—2015年北方防沙屏障带面临较为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退化等问题;而农田、城镇、荒漠及裸地生态系统正向转换率高于逆向转换率,表明生态防治等工程取得了一定进展,在2005—2015年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环境呈现稳定好转趋势。所有生态系统中,城镇和农田生态系统正向转换率明显高于其他生态系统,表明通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限制经济开发活动范围等政策对生态系统变化影响程度巨大。
从分布上来看(图11),2005—2010年正向转换程度高的地区集中分布在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和内蒙古防沙带的西部地区,此处也是退耕还林还草、三北防护林重点建设区域,而其他区域正向转换程度低。2010—2015年大部分区域正向转换程度高,然而塔里木防沙屏障带内的阿克苏市、阿合奇县、阿图什市、柯坪县、乌什县、拜城县,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内的德令哈市、天峻县以及内蒙古防沙屏障带内的镶黄旗环境改善状况较差;在研究时段内,北方防沙屏障带内生态系统逆向转换普遍较低、转换程度较高的地区零星分布,这类地区主要特点为经济开发力度较大、经济发展相对迅速,城镇化水平较高,故逆向转换程度较高。
2.3 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2.3.1类型尺度
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景观格局类型尺度的景观指数如表5所示。草地斑块数量最多,其余由多到少依次为森林、农田、荒漠、城镇、湿地、裸地。草地的边缘密度最大,其余由大到小依次为农田、荒漠、森林、裸地、湿地、城镇。斑块密度上来说,草地的斑块密度较高,其次为森林,城镇和荒漠基本持平,裸地密度最低。荒漠的平均斑块面积最高,其余由高到低依次为草地、裸地、农田、森林、湿地、城镇。草地与荒漠是主要生态系统景观类型,这两种生态系统类型所占比例超过64%。草地与农田的景观形状指数最大,其次是森林。

表3 2005—2015年北方防沙屏障带转移矩阵Tab.3 Transfer matrix of northern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in 2005—2015 km2

图7 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类型转换情况Fig.7 Ecosystem transfer in northern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图8 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类型转换情况Fig.8 Ecosystem transfer in Hexi Corridor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图9 内蒙古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类型转换情况Fig.9 Ecosystem transfer in Inner Mongolia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图10 塔里木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类型转换情况Fig.10 Ecosystem transfer in Tarim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表4 北方防沙屏障带各生态系统类型正/逆向转换率Tab.4 Forward/reverse conversion rate in northern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图11 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转换率分布示意图Fig.11 Distributions of conversion rate in northern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从表5可知,北方防沙屏障带内的荒漠景观所占比例减小的同时,平均斑块面积也在减小,而斑块数量、形状指数、边缘密度则在增加,而森林、草地的变化趋势与荒漠正好相反,这说明这10年间荒漠的面积在缩小的同时,大型的荒漠斑块逐渐被林、草地分割成多个斑块,使得荒漠破碎度增加。城镇的斑块数和斑块密度在2005—2015年间增幅较为明显,表明这个时期的城市化进程较为迅速,使得城镇的数量增加。农田大体呈现一个稳定的状态,说明农田生态系统在10年间变动较小。而湿地和裸地的景观比例、斑块数量、斑块密度等指数变化明显,2005—2015年呈减小趋势,表明湿地和裸地可能面临较大压力。
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内蒙古防沙屏障带、塔里木防沙屏障带内的生态系统景观格局在类型尺度的景观指数特征与北方防沙带的基本相同,但仍存在地区差异(图12~14)。
在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草地与荒漠是主要生态系统景观类型,这两种生态系统类型所占比例超过69%;内蒙古防沙屏障带内草地则是主要生态系统景观类型,所占比例超过40%;而在塔里木防沙屏障带荒漠是主要生态系统景观类型,所占比例超过42%。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塔里木防沙屏障带,草地的边缘密度最大,其余由大到小依次为荒漠、裸地、森林、农田、湿地、城镇。塔里木防沙屏障带内各生态系统的景观形状指数均最小,表明在塔里木防沙屏障带内各生态系统的景观形状相对较规则。在景观格局指数变化趋势上,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内森林所占比例在下降,而草地所占比例增加迅速。塔里木防沙屏障带内森林所占比例增加更为明显。

表5 景观格局指数Tab.5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图12 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景观格局指数Fig.12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in Hexi Corridor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图13 内蒙古防沙屏障带景观格局指数Fig.13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in Inner Mongolia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图14 塔里木防沙屏障带景观格局指数Fig.14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in Tarim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2.3.2景观尺度
从区域整体角度出发,在景观水平上选取利用斑块数、斑块密度、边界密度、平均斑块面积等8个指数对北方防沙屏障带地的景观格局特征及变化进
行了分析(表6)。结果显示:在研究时段内,斑块数量、斑块密度的变化大致同步,呈减少趋势,而平均斑块面积则呈先减少后增加趋势。边界密度指标直接反映了景观破碎化程度,可以看出10年间边界密度逐渐减小,即表示景观被边界割裂程度变低,说明北方防沙屏障带的生态过程活跃度有所减小。景观形状指数反映了斑块的复杂程度,形状指数越大,斑块形状就越不规则,曲折程度就越高,反之斑块形状越规则越平滑。2005—2015年间,景观形状指数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景观形状指数上升表明景观斑块形状不规则化增强,易受周围景观的影响,后一阶段景观形状指数下降,说明景观斑块形状趋于规则化。2005—2015年间蔓延度略有增加,说明景观破碎化程度减弱,聚集度变大,而景观破碎化降低,景观异质性略有减小。景观内各组分所占比例越均匀,均匀度越接近1。

表6 北方防沙带景观格局指数Tab.6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in northern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从分屏障带来看,在研究时段内,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内斑块的平均斑块面积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内蒙古防沙屏障带内的斑块数量在不断减少,形状指数却不断增大;塔里木防沙屏障带内的斑块数量、斑块密度、形状指数是所有防沙屏障中最小,却拥有最大的平均斑块面积,同时,塔里木防沙屏障带内斑块的斑块数量增加,蔓延度指数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表7)。

表7 北方防沙屏障带景观格局指数Tab.7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in northern sand control barrier belt
3 结论
(1)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系统类型主要以草地和荒漠为主。2010—2015年间生态系统整体呈稳定状态,屏障带内森林面积增幅明显,荒漠面积持续减少,10年间治沙效果明显;城镇面积增长迅速,表明城市化进程有所加快。从分屏障带来看,内蒙古防沙屏障带荒漠面积明显减少,塔里木防沙屏障带森林面积增长迅速,而河西走廊防沙屏障带草地面积明显增长。
(2)2005—2015年,森林、草地、湿地生态系统的逆向转换率均大于正向转换率,说明在此期间北方防沙屏障带面临较为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退化等问题;农田、城镇、荒漠及裸地生态系统正向转换率高于逆向转换率,表明生态改善工程取得了一定进展;城镇和农田生态系统正向转换率明显高于其他生态系统,说明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限制经济开发活动范围等政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大。2005—2015年北方防沙屏障带的生态环境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且2010—2015年间生态环境变好趋势优于2005—2010年间生态环境变好趋势。
(3)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可知,2005—2015年间,北方防沙屏障带生态总体向好,治沙效果明显,但局部仍面临较大的压力。在景观水平上,北方防沙屏障带斑块数量、斑块密度呈减少趋势,平均斑块面积呈现先减少、后增加趋势,景观形状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蔓延度略有增加;在类型水平上,荒漠景观整体呈现破碎化萎缩的趋势特征,森林、草地向形状简单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