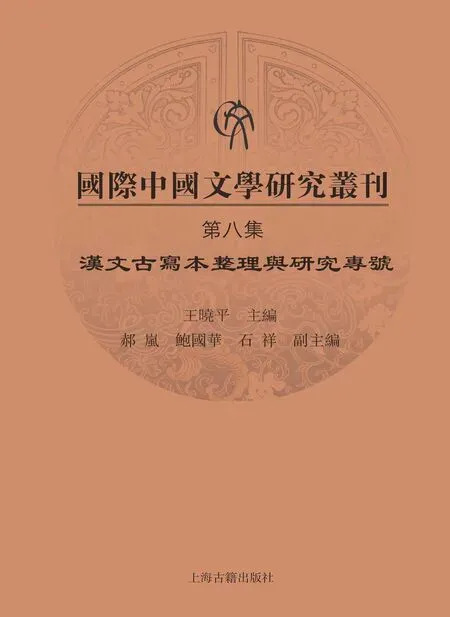“好玩”的學術與學術的“好玩”
曾艷兵
2003年,英國著名文學理論家伊格爾頓出版了一部名爲《理論之後》的書,他在書中開篇就宣佈:“文化理論的黄金時代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維-施特勞斯、阿爾都塞、巴特、福柯的開創性著作遠離我們有了幾十年。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爾·布迪厄、朱麗婭·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達、H.西克蘇、F.傑姆遜、E.賽義德早期的開創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從那時起可與那些開山鼻祖的雄心大志和新穎獨創相頡頏的著作寥寥無幾。他們有些人已經倒下。命運使得羅蘭·巴特喪生於巴黎的洗衣貨車之下,讓米歇爾·福柯感染了艾滋,命運召回了拉康、威廉斯、布迪厄,并把路易·阿爾都塞因謀殺妻子打發進精神病院。看來,上帝并非結構主義者。”如今,學術與理論一樣,似乎也進入了學術之後的時代。學術的黄金時代已經消失,學術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越來越遠。學術已變成一種純粹個人的技術層面上的操作,變得越來越面目猙獰、索然無味了。
伊格爾頓認爲,過去,活著的作家是不配成爲研究的對象的,人文科學研究的大多是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檢驗一項研究成果是否有價值和意義,其方法是看它是否無用、無聊,以及深奥的程度,“理論只不過是一群年輕幼稚、情感受阻的男人,在比較他們自己的多音節的長度而已”。這話説得雖然有些刻薄,但并非没有道理。放眼當今學術,要麽真的無用、無聊、無味、無趣;而那些有聊、有趣、有意味,還有讀者關注和閲讀的,大抵與學術無關。學術與趣味分道揚鑣久矣,難道就没有診治的可能和方法嗎?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天津師範大學的王曉平教授設計了一套叢書,并不希望就此徹底改變這種狀態,但至少讓人們覺得,學術其實還有另外一種做法: 學術是“好玩”的,“好玩”的也可以是學術的。王先生認爲:“中外文學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研究能有新高度、樣態、新滋味,并由此而贏得新讀者,是我們都樂見的。那種將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和跨文化現象量化、簡單化、標籤化的文字,恐怕很少有人真心愛讀。”因此,我們應該站在前賢的肩膀上做點什麽。於是,他便與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共同設計了“中外文學交流故事叢書”。該叢書寫人寫事,寫故事中的人,寫人的故事。用王先生的話説:“有人才會有故事,我們把這些故事講得有料(史料、資料)、有情、有味,有看頭,就要擺脱自恃高深的‘學報腔’。視野宜寬,材料宜富,叙事宜巧,道情宜精,議論宜深,炒舊飯自然不妙。”總之,叢書的寫作應當情理相彰,文情并茂,適當配以圖表。希望叢書的出版能够贏得國内那些真心愛文學的讀者,引起他們的關注和興趣。
當然,做這種事情其實有許多先例。1907年,魯迅完成《摩羅詩力説》一文寫作,該文最初發表於1908年2月和3月《河南》月刊第二號、第三號,署名令飛。這篇文章當初就不是僅僅寫給專家學者看的,而是寫給普羅大衆看的。如今,一百多年過去了,魯迅的這篇有關比較文學和外國文學的論文仍然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摩羅詩力説》在世界文學和中國本土文化語境的雙重背景中,以人類文明史和文化批判意識爲視角,站在西方近現代哲學的高度,以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系統評介了歐洲浪漫主義詩人,并對中國詩歌發出了時代的呐喊。這就使《摩羅詩力説》當之無愧成爲中國詩學現代轉型的開端和標誌。”比較而言,我們今天比較文學學者和外國文學學者撰寫的論文,當下就鮮有人閲讀,專業之外更是無人問津,何談現實意義、百年之後?
類似的情況中外皆然。早在1949年,蘇格蘭裔美國古典學家、評論家、文學史家吉爾伯特·海厄特出版了《古典傳統: 希臘-羅馬對西方文學的影響》(Gilbert Highet,The
Classical
Tradition
:Greek
and
Roman
Influences
on
Western
Literatur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一書,該書被認爲是“比較文學領域赫拉克勒斯式的壯舉,也是古典文化接受史領域的里程碑式著作”。該書主要勾勒了希臘語和拉丁語傳統影響西歐與美國文學的主要途徑、方式和意義。該書的第21章爲“學術的世紀”,所謂“學術的世紀”指的是19世紀。“從革命時代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那個世紀裏,古典學知識的傳播和深度都有所發展,對希臘和羅馬的認識從未像現在這麽深入;同時,比以往更多的人開始對希臘和羅馬有所瞭解……在整個世紀中,學者們對古代希臘-羅馬世界的發現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知識被整理成册,獲得它們變得愈發容易……在19世紀初,人們可能只需一室藏書便能掌握所有的古典學知識……但到了世界末,任何人都不再可能掌握希臘和羅馬的全部相關知識。他至多只能寄希望於理解學科基礎和關心研究發展的主要方向,他可以選擇在某些領域做到專長,通過它們來瞭解古典學的其他内容。”1873年和1876年謝里曼分别發現并挖掘了特洛亞和邁錫尼的遺址。此時,埋藏在埃及古老廢墟裏的紙草也被發現併發掘出來。這時學術研究的繁榮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與此同時,這個世紀學術發展的弊端已經初顯端倪,這首先體現在教學上。和19世紀的許多傑出人士一樣,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發現,糟糕的教學方法會扼殺最樂意接受優秀文學作品的年輕人對它的感情。尼古拉·穆雷·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對1879年紐約哥倫比亞學院古典學課程進行了描述: 大二第一學期研讀歐里庇德斯的《美狄亞》,學期結束時只讀了246行。教授過於强調語法和細枝末節,全不在意作品的意義和藝術特點。威廉·萊恩·菲爾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這樣描繪1883—1884年在耶魯學習古典文學的經歷:
我們的課堂大部分是乏味的,教學完全是機械的。院系像是受了詛咒,教學藝術像是長了爛瘡。許多教授只是讓學生回答事先佈置的問題。無論對研究還是學生,他們從未表現過任何真正的興趣。我記得,我們在一整年裏每週花三小時學習荷馬。老師從未改變過自己單調的套路,從未發表過見解,只是點名讓學生回答問題或分析文句,然後説“够了”,并給出分數。經過一整學年的這種令人無法忍受的課堂折磨後,在六月份的最後一次問答課上,我吃驚地聽見他説(雖然仍然没有任何感情):“荷馬的詩歌是有史以來人類頭腦的最偉大成果。下課。”於是我們走出教室,投入了陽光的懷抱。
一位古典文化的真正愛好者本森(E.F.Benson)對馬爾伯勒公學(Marlborough)如此評價:
這個體制多麽令人失望,它讓一門本質上是人性和美的課程失去了所有人性和美的元素,把一門所有人類語言中最靈動的語言(希臘語)變成了一系列代數方程。如果想象力先被點燃,這些枯燥的不規則變化學起來會多麽有趣……然而,在我學習希臘語的時候,老師的方法就好像讓學生們劈乾木柴,却希望借此教給他們阿提卡山坡上迎風蕭瑟的樹木的特徵。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如此介紹他在莫德林學院的導師瓦爾德格雷夫(Waldegrave):
我的導師……要求我們每天上午十點到十一點閲讀泰倫斯的喜劇。我在牛津大學得到的全部教益只不過是三到四部拉丁語戲劇;甚至對某部優美古典作品的研讀也變成了枯燥和機械的文本解讀,而不是安排成古今戲劇的比較。
老師的教學枯燥而機械,不願費力把喜劇當作藝術品加以分析。於是,吉本放棄了這些課程,他的導師對此却毫不關心。據説拜倫和雨果等在學習古典文學時總是抱怨一件事,即糟蹋了古典文學的是教學過程中對準確性的過度强調。譬如,當校長向學生們介紹一部最偉大的希臘悲劇時,他更多地是將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羅諾斯》當作一座不規則語法現象的寶庫。19世紀的時代精神强調紀律、體制、懲戒、辛勤工作和現實,其教育則强調精確、艱難和無趣等。另外,過度的專業化有時會導致老師和學生脱節。爲了解決這一問題,有些教授認爲,如果不能二者兼顧,自己有責任爲了教學而犧牲研究。當然,也有許多學生對教授的講課無法理解或心生厭惡,因爲他的學術生活所在的空間對於大多數學生而言高不可攀。
正如古典文學説到底是藝術還是科學一樣,人文科學究竟是人文還是科學?研究藝術需要品味和想象力,而不是所謂純粹的科學方法。研究人文至少應該有人文關懷,一味追求科學規則必將損害甚至扼殺人文關懷。古典文學教學必須具有純粹和科學的客觀性,這種理念毀掉了許多老師和許多好學生。人文教育必須標準化、模式化,乃至標新立異都成爲一律化的,這樣的創新自然也就岌岌可危了。如今的學術書籍很少有佳作,有的甚至故意讓讀者反感。讀不懂的程度似乎就意味著學問的深淺了。
科學方法和知識的擴張還導致了學術研究的碎片化,專業化的研究則導致廣大非專業人士對這些研究成果漠不關心,甚至連多看一眼的意願都没有了。大部分學者更喜歡小範圍地研究單個作家,或者單個作家的某些方面,或者社會和文學史的某個狹窄領域,或者晦澀、非主流和無人探索的話題。與此同時,許多重要的核心主題的工作却無人問津。學者們往往會選擇那些人們知之甚少的領域,這樣做更加安全。對於“原創研究”的重視愈演愈烈,以至於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博士生以自己和他人都不感興趣的東西爲主題發表論文,而日後他們自己也很少會重温這些論文。學者們拒絶或不屑於承認自己的工作與當代世界有關聯,他們自己造成了公衆的漠視。即便外面的世界洪水滔天,也與他的學術研究没有什麽關係。所謂躲進學術的諾亞方舟,管他冬夏與春秋。
當然,“好玩”的學術,就是我們争取做到讓學術有趣、有味、有意思,也有意義。但學術雖然也可以“好玩”,但“好玩”的并非就是學術。所以,我們不能爲了“好玩”而忘了學術,那樣就是本末倒置,南轅北轍了。學術可以“好玩”,自然是以非功利的目的從事學術思考和探討。當學術具有遊戲的意味時,它自然也就是“好玩”的了。18世紀德國著名美學家席勒説:“在人的各種狀態下正是遊戲,只有遊戲,才能使人達到完美并同時發展人的雙重天性。”“只有當人是充分意義上的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他遊戲的時候,他才是完全的人。”學術可以是遊戲,但遊戲并非就是學術。學術可以“好玩”,但如果純粹爲了“好玩”,那麽,最好還是離學術遠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