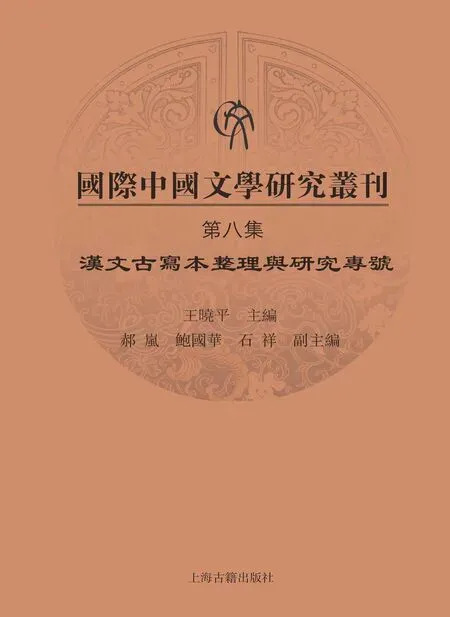泰戈爾的“中國”和中國的“泰戈爾”
黎躍進
文學、文化交流,以具體的人和事爲載體。説到泰戈爾與中國的關係,就繞不開他1924年的中國之行。1924年3月21日,泰戈爾率領的國際大學訪華團一行六人從印度加爾各答出發,走海路經東南亞,航向嚮往已久的中國。
早在1920年,泰戈爾遊歷美國。當時留學美國的馮友蘭拜訪他,兩人交談中泰戈爾表示“中國是幾千年的文明國家,爲我素來非常敬重。我之前去過日本,但没到過中國,至今甚爲遺憾。……然而我一定會要到中國去一次的”。1923年初,泰戈爾委派助手恩厚之,前來中國聯繫訪華事宜,得到中國學界的熱情回應和及時邀請,但幾經波折,直到一年後才成行。
泰戈爾經過海上漫長的航行,途中輾轉先後登陸緬甸、新加坡和香港,受到當地華僑華人的熱烈歡迎,一路都在感受中國文化。終於在4月12日上午9時15分,泰戈爾乘坐的日本客船“熱田丸”號緩緩駛入黄浦江匯山碼頭。高鼻朗目、鬚髮皆白、仙風道骨的泰翁早已興奮不已,靠在甲板欄杆上,觀賞浦江兩岸的風光。當輪船停穩,泰戈爾雙手合掌,向在碼頭前來迎接的上海各文化團體代表和社會名流微微欠身致禮。當泰戈爾走下輪船,踏上中國土地的時候,老人口中喃喃自語:“不知道是什麽緣故,到中國就像回到故鄉一樣。”
“回到故鄉”——這是一種怎樣的中國情結?這是對中國社會和文化長期關注、想象而積澱的心理認同,是一種内在認同的“精神故鄉”。隨著訪華期間對中國的實地考察和真切感受,泰戈爾曾滿懷深情地感嘆:“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國人!”
泰戈爾的這種中國情結和認知,首先來自家庭的薰陶。他的祖父是加爾各答著名的富商,與中國有貿易往來,從中國進口絲綢,將中國茶移植到阿薩姆邦。他的父親於1878年遊歷中國,帶回不少新奇的中國物件。少年時代的泰戈爾,就是從絲綢錦緞的華麗光澤與精美圖案、物品的工藝技術裏最早獲得的中國認知。其次是泰戈爾從中國古代典籍、文學作品翻譯的閲讀中理解中國文化。他在中國的演講中説:“我讀過你們一些詩集的翻譯,并且被你們的文學陶醉。它有中國特色,是我從其他國家文學中看不到的。”他不僅閲讀過李白、杜甫、蘇東坡這些唐宋詩人詩作的英譯,還讀過老子、孔子等思想家的著作譯本。
當然,1924年訪華,泰戈爾有了親歷中國的切身感受,以及和徐志摩、梁啓超、蔡元培、譚雲山、徐悲鴻等中國學者、詩人、藝術家的直接交往,對中國文化精神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
泰戈爾在1924年訪華的講演以及各類文學創作和論文中,經常談到中國,將他的“中國情結”加以情感化和期待性的表達。
泰戈爾的中國,是有著悠久文明,爲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中國。
他在訪華的演講中説:“你們在以往的時代中確實取得過驚人的進步。你們有過數種偉大的發明,有過被其他民族人民借用、仿效的發明。你們不曾無所作爲、得過且過。所有這些進步還從未曾使你們的生活蒙上過無足輕重的陰影。”“你們的文明是在基於精神信仰的社會生活中哺育出來的。你們是生活得最爲長久的民族,因爲你們有長達許多世紀的、被你們對善而不是對純粹力量的信仰所滋養的智慧。這爲你們産生了一個偉大的往昔。”
泰戈爾的中國,是勤奮、淳樸而偉大的中國。
1893年泰戈爾在長詩《大地》中有詩句:“文明古老的中國,日日勤奮工作”。1916年泰戈爾訪日,途經香港,見到一群在碼頭上卸貨的中國勞工。他們赤裸上身,展露强健的體魄,表現出男子漢的偉岸,運動的美、身體的美、勞動的美有機結合,體現了詩意與韵律的配合。詩人在讚賞中感嘆:“以人類最基本的愛美之心欣賞了這種從勞動中爆發出的歡樂和力量,我已完全信服,一個偉大民族的力量是由全國民衆共同積蓄的。爲達到理想境界而做的長期準備,在這裏的每一個勞動者身上得到了充分利用。千百年來,中國正是通過這種手段動員人民全身心地投入勞動和建設,把力量用在該用的地方,矢志於以豁達的民族精神去追求自由與幸福,爲未來描繪一張完美的藍圖。”他目睹中國勞動者如何堅定努力地工作,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淳樸而偉大的力量,預言中華民族一定會崛起。這不僅反映了泰戈爾寛闊的胸襟,更顯示了他世間罕有的智慧和遠見。
泰戈爾的中國,是充滿人情味、基於精神信仰、愛好和平的中國。
在散文《一個中國人的信》中,泰戈爾將中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對比,提出“中國的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是持久的、樸實的、自然形成的,是有道德秩序的有序的文明,是心中完全推崇孔子的文明,是道義約束的文明,不是只承認金錢關係的野蠻社會的文明。中國人禮貌謙遜、真誠無私地與他人相處,從骨子裏尊重道義和良知,享受大自然賦予的一切。中國的詩人和作家一直把人們的心靈引向人類生活的高雅情趣上。熱愛和平是中國人的本性。”在中國的演講中,泰戈爾從生態維度,論述中國文明的自然本性:“在一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生長著數不清的樹木,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繁茂翁鬱的古老森林。這片土地因爲長年累月的落花落葉而變得深厚、肥沃、豐饒。你們古老的文明就滋養了這片心靈的沃土。它那不斷的富於人性的輕觸,生氣盎然地影響了一切附屬於它的事物。假如這一文明不是特别地富於人性,假如它不是充滿了精神的活力,它就不會延續得如此長久。……我們這些來自另一國度的人在這一具有古老文明的國土上才會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我受到了極爲熱烈的歡迎,這使我感到你們特别富有人情味。”
一花引得百花开。之后,有孩子受此鼓舞,陆续成诗几首,有模有样;虽未必佳,却也可喜可贺。因为,这可是格律诗的雏形啊!
泰戈爾的中國,是友好、仁義、道德、講秩序的中國。
1927年7月,泰戈爾訪問東南亞,“大印度協會”舉行了一個歡送會。會上泰戈爾講話,其中談到幾年前訪華的情況:“我曾訪問過中國。我看到,從人種的角度分析,他們和我們完全不一樣。鼻子、眼睛、語言和舉止,我們和他們没有相同之處。但和他們待在一起,可以感受到親戚之間一種真情的紐帶,但這種紐帶,在與許多印度人接觸中却很難感受到了。”在論文《社會差異》中,泰戈爾寫到:“在中國,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丈夫妻子,鄰居街坊,國王臣民,祭司長老,人人都講仁義。不管外部發生什麽革命,不管誰登基當皇帝,仁義在中國内部以完整的體系密切聯繫著億萬群衆。仁義遭受打擊,中國立即感到死般的劇痛,并採取極厲害的手段進行自衛。那時誰能遏止它!什麽國王,什麽軍隊,都無能爲力!那時中華民族便幡然覺醒。”訪華時《在北京佛教寺廟裏的講話》中他説:“我深切地感到,中國確實有對秩序、對和平、對美的根深蒂固的熱愛,這使中國能諦聽有關印度對芸芸衆生的無限熱愛的詳述。”
泰戈爾的中國,是充滿詩意的、詩人輩出的中國。
作爲詩人,泰戈爾對中國傳統詩歌有很高的評價。20世紀20、30年代西方現代派詩歌傳入印度,引起詩壇“現代派”和“傳統派”展開論争。泰戈爾發表《現代詩歌》參與討論,文中他以四首中國詩(《山中問答》《秋浦歌》《夏日山中》《長干行》)爲例,分析詩歌的“現代性”問題。他得出結論:“從中國詩人李白寫詩算起,一千多年過去了,但可稱他爲現代詩人。他有一雙首次觀察過世界的眼睛。……英國詩人的現代特性,在中國詩的旁邊是站不住脚的。”
泰戈爾欣賞中國人用心靈去感知世界,主客觀融合的詩意化人生態度。1938年他致信阿米亞·賈格拉帕爾迪,“我們在往昔中重新發現今時,在其他時代的面前,判斷當下生存的價值。在古代一個破罐中,我們品嘗到人生之旅與昔時的愛的滋味。中國古代詩人的吟哦中,很容易看到人生旅途中每天行走的路上邁出的每一步,可我在其他國家的詩作中從未見到。……我談到的中國古詩,題材普通,但不膚淺,不加雕琢的真情實感毫不費力地表現出來,以樸實的眼睛觀察到的普通生活的美。”
泰戈爾以一個詩人的敏感,也看到中國社會的一些負面。如傳統中的女人裹脚,近代民族自尊教育的缺失,當時中國的落後、分裂、遭受列强壓迫的現實也出現在他的筆下。但整體上,泰戈爾對中國懷有特殊的深厚感情。他熱愛中國和中國文化,關心中國人民的命運。1881年,20歲的泰戈爾就在孟加拉文的雜誌《婆羅蒂》上,發表著名論文《在中國的死亡貿易》,嚴厲譴責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罪行。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争後,他多次以書信、電報、談話、詩篇等形式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暴行,聲援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鬥争。
異質文學、文化的交流和對話,總是雙向進行。泰戈爾的“中國”,是他對中國文學、文化接受、理解後的主體認同。泰戈爾是對20世紀中國文化和文學影響最大的外國作家之一,可以説他的思想和藝術參與了中國20世紀文化和文學的建構;其影響從20世紀初至今的百餘年裏一直持續不斷,還有越來越大的趨勢。一個異域作家能産生如此深刻的影響,可以概括爲“泰戈爾現象”。作爲深入研究的課題,這裏面包括泰戈爾爲何會有如此的影響,他的什麽東西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中國接受泰戈爾影響的過程中,本土文化起到了什麽樣的“過濾”作用,影響—接受的途徑是什麽等一系列問題,都有必要展開探討。
换個角度看,泰戈爾在20世紀中國傳播影響的過程中,中國的文化和現實要求構建了中國的“泰戈爾”。這個命題也包括許多問題域,如中國的泰戈爾是什麽樣的泰戈爾;中國的泰戈爾與印度的泰戈爾有何區别;中國的泰戈爾是怎樣形成的;中國社會的“期待視野”是怎樣的;在傳播過程中,主體的個體性(個人生命體驗、審美傾向個性化)具有怎樣的意義和作用等等。這裏我們不能對這些問題一一加以探討,只就中國翻譯界構建的“泰戈爾”略作展開。
中國對泰戈爾的譯介從20世紀初至今的一百餘年中,通過翻譯界對翻譯原作的選擇、重譯本的推出、譯者的介紹性文字和翻譯過程中歸化性表達,完成了中國譯界的“泰戈爾”建構。這個“泰戈爾”既是印度泰戈爾自身精神世界的部分呈現,又是中國現代文化“接受熒幕”中的泰戈爾。當然,不同時期的翻譯、不同的譯者理解的泰戈爾是有差異的。其實,把時間因素和接受主體個性納入考察視野,很難對中國譯界的“泰戈爾”做出本質化的界定。將問題擺在具體的歷史場域中做具體的分析,也許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這樣考察不同時期、不同接受群體,會看到20世紀中國的泰戈爾是多面的。
考察中國20世紀初至今一百餘年的泰戈爾譯介,中國譯界和學界不斷努力,從泰戈爾生平思想的介紹到文學、美學文本的研究性翻譯,從作品的局部編譯,到全集的完整翻譯,越來越系統、深入。而且從中可以看到,外國作家的譯介,是兩種文化的對話,是依託翻譯載體,在傳播中建構本土文化期待的“外國作家”。與中國三次泰戈爾譯介高潮相應,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中的三個泰戈爾:
第一個是維護東方傳統的保守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泰戈爾。對泰戈爾1924年訪華持褒貶不同態度者,都是把他當作東方傳統的捍衛者。這是中國譯介建構的結果。當時重要的翻譯家瞿世英認爲:“泰戈爾是以偉大的人格濡浸在印度精神裏面,盡力地表現東方思想……泰戈爾是個神秘主義者,説的話只可於言外去領會。”
第二個是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泰戈爾。在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文化語境下,泰戈爾的譯介作爲中國意識形態體現,傳達的就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時代精神。“這本詩集最突出的一點,編入了許多泰戈爾的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詩,這些詩顯示了泰戈爾的最偉大最受人民喜愛的一面。孟加拉本是印度民主運動和文藝復興運動的中心,在廣大人民渴求解放熱望自由的火海狂潮之中,泰戈爾感激奮發,拿起他的‘力透紙背’的神筆,寫出了熱情澎湃的歌頌祖國鼓舞人民的詩篇。”
第三個是東西方文化融合成功的實踐者泰戈爾。多元文化與改革開放的現實,人們力求全面理解、譯介泰戈爾。“他的全部作品構成印度文藝復興運動和民族獨立運動的一個重要歷史側面,對印度的社會生活和文藝運動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他的文學創作,不僅把印度民族文學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也爲世界文學寶庫增添了一份珍貴的遺産。……在對泰戈爾詩歌創作進行全面考察後,我認爲他的基本形象不是神秘主義宗教詩人,而是偉大的民族進步詩人。他的詩作不僅爲復興印度現代詩歌鋪平了道路,而且掀起了印度浪漫主義詩歌運動,奠定了印度詩歌與現實生活結合的美學基礎,同時在近現代世界詩壇産生重要的影響。”
這三個“泰戈爾”是中國一百餘年社會文化發展中,以譯介爲途徑而建構的“泰戈爾”。文學譯介,不是消極、被動地行爲;文學譯介是基於本土現實文化主動的,有目的性的選擇與建構。這是“異域作家本土化研究”的理論基礎與邏輯前提。
異域作家本土化建構的譯介學視角與方法,至少可以考慮: (1) 譯本的選擇;(2) 重譯本考察;(3) 譯者前言後記之類的文字;(4) 不同的翻譯群體的身份定位;(5) 譯者的個性化選擇;(6) 相似國家的泰戈爾譯介比較。
從“中國的泰戈爾”這個個案的探討,我們可以進一步拓展出“異域作家本土化研究”的新領域。這是一個有待理論闡發和展開研究實踐的領域,可以研究外國作家的中國化,如“中國的夏目漱石”、“中國的川端康成”、“中國的谷崎潤一郎”、“中國的莎士比亞”、“中國的歌德”、“中國的易卜生”、“中國的馬哈福兹”、“中國的索因卡”等等;也可以研究中國作家的異域化,如“印度的玄奘”、“日本的老舍”、“韓國的魯迅”、“美國的沈從文”、“歐洲的莫言”等等。
中外文學文化交流,是個無盡的學術寶庫。但開拓新的研究領域與空間,才是學術研究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