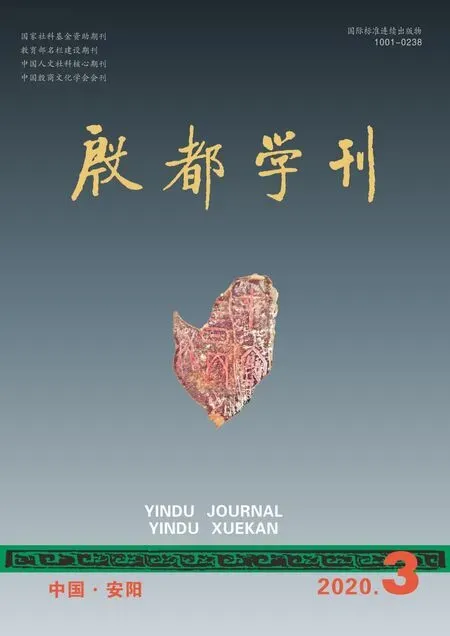利用楚简校读《左传》一则
——“陈公穿封戌”辨疑
付安莉
(1.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4;2.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天津 300222)
楚地战国简帛的发现,使人们亲见未经后世改动过的古书原貌,对古籍释读和古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上博楚简《申公臣灵王》所记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昭公八年“陈公穿封戌”[1]的故事多有雷同,为我们厘清相关史实提供了新的思路。简文主人公身份是学界讨论的焦点,陈佩芬、徐少华、周凤五、刘文强、陈伟、何有祖、凡国栋等诸多学者对此做了很好的研究(1)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马承源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徐少华:《上博简<申公臣灵王>及<平王与王子木>两篇疏证》,《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2008年;周凤五:《上博六<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新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58-67页;刘文强:《申公臣灵王王(二) —“遇於枥隧”》,《岭南学报复刊》,2016年第4期;陈伟、何有祖:《读<上博六>条记》,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2007年7月9日;凡国栋:《读<上博楚竹书六>记》,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2007年7月9日。,但学者们大多仅对读《左传》,未充分关注《史记》中“陈公”[2]的记载差异,因此该问题仍有探讨空间。笔者略陈管见,应用“二重证据法”对传世文献的疑误加以辨析,并探讨致误原因,若有失当之处,尚请方家不吝赐教。
为方便讨论,现将《申公臣灵王》篇整理者陈佩芬先生释文转写如下(采用宽式) :
吾于析述,申公子皇首皇子。王子围夺之,申公争之。王子围立为王,申公子皇见王。王曰:“申公忘夫析述之下乎?” 申公曰:“臣不知君王之将为君。如臣知君王之为君,臣将或至安。”王曰:“不穀以笑申公,是言弃之。今日,申公事不穀,必以是心。”申公坐拜,起答:“臣为君王臣,君王免之死,不以辰扶步 。何敢心之有?”[3]
将《左传》可与简文对读的内容转引如下: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五月,至于城麇。郑皇颉戍之,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戌囚皇颉,公子围与之争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请问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颉遇王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围,弗及。楚人以皇颉归。
《左传·昭公八年》:使穿封戌为陈公,曰:“城麇之役,不谄。”侍饮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对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礼,以息楚。”
一、简文“申公”不可读为“陈公”


表1 楚简地名专字“绅”字形表

∵A=B A=C
∴B=C(2)为方便阐述,上述各字分别以A、B、C字母符号代替。

二、《左传》“陈公穿封戌”应是“申公穿封戌”
既然简文“申公”不可读为“陈公”,那么“申公”其人究竟是谁呢?先来分析学界主要的两种观点:一是“申公巫臣说”恐不确。《左传·成公二年》“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遂奔晋,而因郄至,以臣于晋。晋人使为邢大夫。”申公巫臣于鲁成公二年(前589年)奔晋,为邢大夫,此为楚灵王(前540年—前529年在位)之事,巫臣此时已在晋,不可能继续任申公之职。二是“申公子亹说”亦不确。《国语·左史倚相儆申公子亹》开篇即载申公拒见倚相之原因为其“老耄”。“左史倚相廷见申公子,子不出,左史谤之,举伯以告。子怒而出,曰:‘女无亦谓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谤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见以交儆子。……’”[8]《礼记·曲礼上》云“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9]左史倚相与申公子亹故事发生在楚灵王在位时期,子亹此时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城麇争囚”事件发生于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推算可知申公子亹当时亦年近花甲,恐怕难以与壮年的公子围争囚,更不会有“抽戈逐王子圍,弗及”的结果。因此从申公年龄推算,“申公子亹说”亦不可信。
春秋时期,楚灭国置县,楚县的长官称县尹或县公,申公是楚申县之县公当无疑。虽然简文“申公”不可读为“陈公”,但简文情节与《左传》却颇为相似,文中主角到底是不是《左传》中的“陈公穿封戌”呢?需从《左传》与《史记》关于“陈公”记载差异说起。
《春秋》系传世文献关于此事记载如下:
《春秋·鲁昭公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
《左传·鲁昭公八年》:九月,楚公子弃疾帅师奉孙吴围陈,宋戴恶会之。冬十一月壬午,灭陈。 ……使穿封戌为陈公。
今按:有三点需特别注意。一是楚师灭陈之具体时间,经传相差整一月,甚怪;二是公子弃疾帅师灭陈,但灵王却封“仇人”穿封戌为陈公,甚怪;三是在传世文献中,穿封戌仅见于此故事。
《左传·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
《左传·昭公十三年》: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
今按:由“君陈、蔡”可推知公子弃疾先有陈而后有蔡,也就是说按《左传》逻辑弃疾为陈公当在昭公八年之后,十一年之前。为何穿封戌任陈公不足三年即改任弃疾?甚怪。杜预辨说“时穿封戌既死,弃疾并领陈事也”,但未提出证据。
《史记》系史书关于此事记载如下:
《陈杞世家》:三十四年,……四月,陈使使赴楚。楚灵王闻陈乱,乃杀陈使者,使公子弃疾发兵伐陈,陈君留奔郑。九月,楚围陈。十一月,灭陈。使弃疾为陈公。
《楚世家》:八年,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 十年,召蔡侯,醉而杀之。 使弃疾定蔡,因为陈蔡公。
《管蔡世家》:九年,陈司徒招弑其君哀公。楚使公子弃疾灭陈而有之。”“十二年,楚灵王以灵侯弑其父,诱蔡灵侯于申,伏甲饮之,醉而杀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围蔡。十一月,灭蔡,使弃疾为蔡公。
今按:《史记》记载公子弃疾灭陈被封为陈公,穿封戌未见。《史记》所载春秋之事多据《左传》,但此确有“陈公之异”,到底孰对孰错?王叔岷在《史记斠证》中多次提及史公当有所据,不必定依《左传》也。(3)参见王叔岷:《史记斠证》(卷三十六、卷四十),中华书局,2007年。《史记》载陈公为弃疾,未必无据。
《申公臣灵王》为楚人记载楚事,简文所记与《左传》多有雷同,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关于《史记》《左传》“陈公”之异,以《史记》为确,《左传》“陈公穿封戌”实为“申公穿封戌”。
理由一,左氏将“申公”误认为是“陈公”。
首先,从音理和辞例分析,“申公”被读为“陈公”的猜测,殆可成立。楚简地名专字“绅”,在传世文献中全部写作“申”。“申”书母真部,“陈”定母真部,二字韵母相同,声母为准旁纽关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皆有“申”“陈”二字的通假辞例。(4)未见地名与“陈”通假辞例。如《诗经·大雅·文王》“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10]《毛诗传笺通释》:“陈锡,即申锡之假借。”[11]上博楚竹书《容成氏》简53正云“武王素甲以申(5)简文“申”写作,非地名专字字形。(陈)于殷蒿(郊)。”[12]
其次,从古书流传的途径分析,无论是文本流传还是口耳相传都有可能导致“申”“陈”的异文或误读。《左传》的史料来源多是杂乱无章、记事记言的片段史料,[13]囿于先秦时代书写和传播条件的限制,这类材料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诸多字词表述的差异,出现假借字、异体字、误字误句。因通假造成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异文现象不胜枚举,“申”“陈”异文亦不足为怪。此外,口传材料也是古书的重要来源。口传的特点使得每个传播者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再加之传播者口音的复杂性等因素,就不可避免因“申”“陈”音近而产生混淆。
综上,根据“申”“陈”二字的古音关系,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材料中二字互通辞例,古书成书及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左氏或将“申公”误作“陈公”。
理由二,《左传》史料杂乱,内容分合无定。
李零在论述古书体例时曾指出“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性质”“《左传》应当也是利用这类(零散的篇章)材料,按鲁《春秋》编年整理而成的古书。”类似《申公臣灵王》这样的事语类材料,与后世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体例相似,被李零先生评价为“古代史书数量最大也最活跃的一种”[13]。这些事语类材料注重以事表人,以语申道,多不纪年。左氏为了编年,只能把完整事件人为割裂。顾颉刚曾云:“《左传》中有许多条是必不可编年的,为了硬要编年,致成削足适履之病。”[14]于是就存在这样的可能:左氏搜集到类似本简文《申公臣灵王》的故事原本,因“申”“陈”通假,认为故事主人公是陈公;误以为此故事与楚灭陈有关,故分置两段,分别编于襄公二十六年与昭公八年,所以才会出现《春秋》“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与《左传》“冬十一月壬午灭陈”的时间差异。
理由三,《左传》存在删减或增饰情节,人物代言之嫌。
在史料杂乱、出此入彼的背景下,古书的成书及之后的流传常有非常复杂的问题,古书与作为其史料的零散篇章,可能呈现两种关系,“一种是基本因循,一种是有所演绎”。[15]简文与《左传》关系当属后者。二书对相关事件的记载非常相似,这说明故事主体框架在上博简时代已经基本定型,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与故事主题关系不大的记言部分:伯州犁与郑囚“上下其手”的对话,《左传》有详细记载而简文未着一笔;简文详细记录了灵王与申公的对话,《左传》仅记穿封戌对灵王的批评之语。
钱钟书先生对于《左传》的这类记言早有质疑,在《管锥篇》有云:“吾国史籍工于记言者,莫先乎《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 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16]伯州犁与郑囚对话明显带有儒家“礼分华夷”的思想倾向,乃左氏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之语。宋人所著《毛诗李黄集解》亦评论此事云“若穿封戌与公子围争,安得为不吴不扬乎?安得为不告于讻乎?惟鲁之臣子皆重厚未尝有争忿之心,则其报功之际无有以所争之讼,告于治狱之官则治狱者不过断囚之轻。”[17]
陈地充当着楚国北进中原的桥头堡,数位楚王屡次发兵侵陈,足见其战略意义。据《左传》所载,灵王灭陈设县,却把如此重要的首任陈县县公之职委派给了曾经刺杀过他的穿封戌,这显然有违常理,亦不符合《左传》极力塑造的楚灵王暴虐无理的人物形象。不仅如此,穿封戌被封为陈公之后,毫无感恩之情,还在楚王宴会上叫嚣要誓死捍卫先君郏敖,杀死灵王这个弒君篡位之徒,这一情节更令人费解。对于灵王的回应和二人和解的过程,《申公臣灵王》有详细记载,但《左传》有意缺载,势必为表达其对灵王的一惯否定。
理由四,从当时地理和军事条件考察,“申公”更为合理。
春秋时,申县是楚国的北方重镇,亦是楚重要的兵源地之一,骁勇善战的申县之师,多为楚王出师、戍守之先驱。《左传·成公六年》有云:“(楚伐郑)晋栾书救郑,与楚师遭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师救蔡,御诸桑隧。”《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曰:“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有:“(僖)公以楚师伐齐,取榖……置桓公子雍于榖,易牙奉之以为鲁援。楚申公叔侯戍之。”申地临近郑地南门,此次侵郑之战,任用公子围和申县之师当属常理,楚简所记申公和公子围争囚是更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
三、结语
楚简中人名地名专字“绅”与“陈”无通假关系,《申公臣灵王》所载“申公”不能读为“陈公”。应用“二重证据法”对读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史记》《左传》所载“陈公”人物身份之差异,当以《左传》为误。《左传》所记 “陈公穿封戌”实为简文“申公”,左氏把申公事迹混淆到了陈公身上,以为此事与楚灵王灭陈相关,将故事分置两段编于不同年份,故造成《春秋》《左传》关于灭陈时间的记载差异。左氏为申明儒家义理,对故事情节有所增删、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