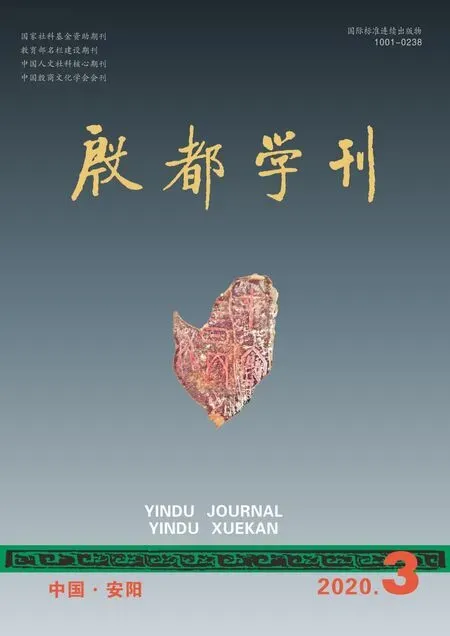论晚商的龟卜和信仰
谢炳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殷墟甲骨文以来,至今已足有120年的研究史了。甲骨卜辞是早期中国信仰文化的产物,在120年的甲骨文研究史中,关于商王朝信仰体系这一重要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1)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历史研究》1959年第9、10期;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谢济:《上帝崇拜在商代宗教信仰中的地位》,王宇信、宋镇豪主编《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宋镇豪,常耀华编纂:《百年甲骨学论著目》,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406-419页,等等。虽然学者对“帝”权、祖先神权的意见不一,但都承认甲骨卜辞真实地见证了早期中华的信仰知识。依据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对文化的看法,信仰是行为型文化和精神型文化的总和,[1]它对人们的行为有规范作用,对人们的精神起支柱作用。从殷墟卜辞看,王朝信仰在各个层面上整合了商代社会,是维系人间世界和鬼神世界正常运转的精神力量。而在“他们为什么那样做?”“他们为什么那样想?”这两个信仰的主要问题上,商代人的回答也可从甲骨卜辞中找到线索。现结合灵龟观念、由龟卜组成的占卜新体系、甲骨文所见商人主要信仰对象及其信仰逻辑展开探讨。
一、灵龟观念与龟卜的兴起
在古埃及文化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在仪式和精神层面维持世界运转的概念,而不断重复的仪式构成了保证文化一致性的基础和中坚力量。[2]商人与此相似,他们通过频繁的占卜仪式来推测鬼神的意志,此仪式与敬畏鬼神的文化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礼记·表记第三十二》云:“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3]卜筮的吉凶预示是王朝的行动指南,是王向大众发表演讲时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来源。殷墟卜辞作为商代信仰文化的文本,是随着占卜仪式而生成的。
学者的研究指出,“利用动物肩胛骨的颜色、裂纹等特征来预测未来,是人类普遍而古老的习俗。历史记载往往不区分冷卜(apyro-scapulimancy)和热卜(pyro-scapulimancy)。冷卜是使用被刮掉肉后自然状态下的骨头读取信息,热卜是灼烧骨头后读取裂纹。因此,尚不清楚商朝所见热卜所覆盖的文化区域的确切范围。然而,一般来说,欧洲、近东和北非用冷卜,北亚、中亚和北美用热卜。”[4]可以将占卜广义地定义为依靠物体、动物或其他现象作为神秘中介来揭示原本难以知晓的信息的任何判断性的或预言性的技术。[5]作为一种仪式实践,占卜经常被用作社会和政治权力的来源,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有助于保障社会持续运行。[6]中国的龟卜或骨卜,属于热卜的一种。这种仪式不始于商代。1962年发掘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现一些未经修整而有灼无钻的卜骨,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350年。[7]而在随后的北方龙山文化中,猪、牛、羊的肩胛骨被用于占卜的风气开始流行,并在与此密切联系的商代文化中有所发展。[8]而从考古学上看,龟卜盛行于商代晚期。
龟甲为什么被认定为占卜的神物呢?目前来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在占卜实践中,贞人发现了“灵龟”之兆的灵验性和确认了龟为吉祥物的地位。此可由传世文献对商代灵龟观念的记载进行逆推。《周易·颐》载:“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孔颖达《正义》云:“灵龟,谓神灵明鉴之龟兆,以喻己之明德也。”[9]此言龟能为人提供明察未来的预兆。《周易·损》载:“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孔颖达《正义》云:“龟者,决疑之物也。……马郑皆案《尔雅》云:‘十朋之龟者,一曰神龟,二曰灵龟,三曰摄龟,四曰宝龟,五曰文龟,六曰筮龟,七曰山龟,八曰泽龟,九曰水龟,十曰火龟。’”[10]此言不违背价值宝贵之龟的预兆,可得大吉。《周易·说卦》载:“离,……为龟。”孔颖达《正义》谓“取刚在外也”。[11]此言龟壳之坚硬。《周易·系辞下》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孔颖达《疏》云:“案《释诂》云:‘亹亹,勉也。’言天下万事,悉动而好生,皆勉勉营为,此蓍龟知其好恶得失,人则弃其恶而取其好,背其失而求其得,是‘成天下之亹亹’也。”[12]此言蓍、龟都是天生的神圣之物,运用它们,可以探索未来之事,可以获得远见,也就能判定天下的吉凶情况,成就天下勉力可为之事业,在这个能力方面,没有他物能超越它们。《大戴礼记·易本命》载:“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13]此言龟为列甲壳动物之首。《白虎通·蓍龟》:“干草枯骨,众多非一,独以蓍龟何?此天地之间寿考之物,故问之也。龟之为言,久也。蓍之为言,耆也。久,长意也。”[14]此言蓍龟长寿。《史记·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载:“记曰:‘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至千万。’”[15]此言名龟能给得主带来大财富。
上引从周代到汉代的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龟卜流行于商代晚期的原因。学者的研究指出,在中国食用动物的谱系中,龟没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也从不作为祭献之物;人们对它的崇拜,从大量文献记载看,主要还是与它特殊的骨相、鳞甲纹理和长久的寿命有关。[16]学者又进一步指出,龟因其有机体的宇宙性而为独一无二之动物——龟背拱如上天,龟腹平整,方如大地;和世寿不同,龟寿不见尽头,由此具备了形成一种信仰的要素,产生出了至高无上的龟卜学,用以开发神力,强化占卜效果。[17]腹甲对已经成体系和精细化的占卜传统是有益的,商代的这一传统为“小邦周”和周朝时期的占卜所吸收和继承,并可能反映出一种逐渐增强的象征体系,周代的占卜就几乎专用龟甲,这与龟长寿、力量以及来自较早的占卜实践产生的威望是相关联的。[18]
第二个原因是,占卜龟甲珍贵的来源以及商王朝对它的宝重。此可用考古学家皮波斯和李新伟的研究成果加以说明,也即社会上层获得遥远地方的物品和知识,是显示其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一个标志。皮波斯认为,“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的价值越高;从地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的价值越高”。[19]
专家早就指出,“迄今所知,史前食龟的地区大致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向南直抵南海之滨,向北及于海岱地区”,[20]而卜用龟应属产于河湖池沼之水龟。[21]专家又指出,“所以知殷代卜龟之多来自南方者”,一是因为“卜辞每言‘有来自南氏龟’(龟南氏)、‘西龟’(自西),知殷代之卜龟,盖由南方西方之长江流域而来”;二是“由专记龟甲来源之甲桥甲尾背甲诸刻辞,每言‘某人’‘某来’,知其由来之方式,为进贡”;三是“因殷代卜用之龟,据专家验之,多系南方种”。由此可推,“殷代与南方之长江流域或更以南,必已有繁盛之交通”。[22]殷商时虽然南北交通未必繁盛,因为依据皮波斯的学说,越是来之不易的远方神物越是值得宝重;但是南北交通网络的开拓,推进了来自远方的物质和知识的交流,应是符合商朝卜龟来源实情的。外国学者贝里(Berry)对刻有文字的龟甲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古生物学检查,发现了四种代表性龟种,即中华花龟(Ocadia sinensis)、中华草龟(Chinemys reevesi)、黄喉拟水龟(Mauremys mutica)以及Testudo emys龟。贝里的研究表明,中华花龟、中华草龟和黄喉拟水龟都是水生淡水龟,而现在只在中国南方发现了中华花龟和黄喉拟水龟,这一事实增强了龟甲来自南方的可能性;并且,独特的安阳陆龟(Testudo anyangensis)目前可在南洋和马来群岛见到。[23]这个研究无疑也增加了皮波斯学说的可信性。
据学者研究,约在公元前3500年,中国史前时代各地区间交流互动进入新的阶段,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24]江苏新沂花厅村(公元前3200-前2500年)文化遗址,可以找到在河南龙山文化里不见的殷商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特征,例如龟甲之使用早在花厅文化时已开始,作为随葬品,其用途虽还不能知晓,但经过制作过的龟甲应是有一定地位的;殷人用龟甲于占卜,一方面可说是原有占卜文化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可说是原有龟甲文化的扩大使用。[25]所以龟的知识应是从南方进入商王朝的知识体系之中的,并被贞人阶层创新性地运用于占卜,由此更新了占卜文化,并建立起了甲骨并用的占卜新体系。
二、商代的信仰体系
商王朝占卜体系的建立,是出于维护信仰世界和人间的正常运行而建立的。“通过观察,我们可以确定,占卜是大约公元前1250-前1046年间商朝晚期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26]“占卜甲骨上的文字见证了文字与权力的联系,此赋予了商代文字以特殊的力量”。[27]可以说,在占卜仪式中,晚商形成了甲骨文书写系统。晚商的信仰知识通过占卜、祭祀和甲骨文书写系统得以传播和保存至今。从甲骨卜辞看,商代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即天神、人鬼和地祇。天神由帝统率,人鬼是死去的祖先、名臣等的称谓,地祇包括山、川、土地神、四方神等神灵。商人为什么信仰这些鬼神呢?人间的幸福和鬼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从丰富的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哪些真实的线索来探索早期中华信仰体系呢?在先达研究的基础之上,试论述如下:
1.对帝的崇拜
商人还没有周代的“天命”观念。常玉芝说:“卜辞和金文中,殷人把天神称作‘上帝’或‘帝’,而绝不称作‘天’,卜辞中的‘天’字都不是神称,而是表示大的意思,如‘大邑商’,又称‘天邑商’,‘大乙’,又称‘天乙’等。”[28]但商人已有“帝命”的观念,所以贞人关注帝的动向。那么,帝在商人信仰的知识结构中位置如何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商人是怎样认识帝之能力的。在商人看来,帝对人间有着如下影响:
(1)下令打雷,如“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帝其于生一月令雷”(《合集》14127正),意即“卜问帝到了今年第十三月下令打雷。帝在将到来的一月下令打雷”;
(2)下令降雨,如“贞今二月帝不其令雨”(《合集》14135正)、“品,贞今三月帝令多雨”(《合集》14136),意即“卜问今年二月帝将不会下令降雨”、“贞人品,卜问今年三月帝将下令多次降雨”;

从上文可知,帝有下达控制天气之命令的权力,有伤害人间的能力,有帮不帮助商人的决定权,有同不同意惩罚某人或某方国的权力,等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帝有终结某一个邑国的权力。于省吾说:“总起来说,甲骨文的帝是否终绝兹邑,实际上是指商邦的存亡言之。到了商代末期和西周,才明显的以帝和邦国的寿命相连为言。这就不难看出商末和西周时代天命观的发生和发展的由来。”[32]也即,到了武丁之时,商人已经有了“帝有终结殷邑”的认识和忧虑。但值得指出的是,西周之时的“天命”观还未发生。杜勇说:“殷人尊帝不尊天,这在殷墟卜辞中反映得至为明显。”[33]商人也是尊天的,他们自称“天邑商”可作为一个例证;但说商人尊帝是可信的,因为在殷人看来,帝是主宰天的至上神。

2.对死去的祖先和名臣的敬畏
王国维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他在甲骨卜辞中发现“王亥”一名,并与《山海经》《竹书纪年》等传世文献相印证,得出“王亥为殷之先公”的结论。[34]此后学者对商人死去的祖先和名臣展开了细致的考察,但很少涉及商人敬畏祖先和名臣的原因,所以本文尝试给予分析。从甲骨卜辞看,商王敬畏死去的祖先和名臣的主要原因可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


3.对地祇的敬畏



综上所述,商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包括了天神、人鬼和地祇三大部分,他们敬畏这些神灵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神灵有着伤害人间和决定人间幸福的能力,帝甚至有着终结商邑的权力。
三、商代信仰的思想逻辑
商代信仰的形成是基于什么思想逻辑呢?通过这种逻辑基础,它对当时的人们的思想行为有着什么样的深刻影响和作用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思想逻辑。

又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在商人的信仰文化里,死去的祖先、臣子等人是通过作祟、作害等伤害人间的手段来引起人间关注的。在他们看来,人间的祸根和不幸皆因鬼神而起,这个思想认识使商人长年累月地以占卜的方式检测鬼神的意见,而不留意最需关爱的人间。所以帝辛认为他的王权来自神授,人间是无法夺走的。《尚书·商书·西伯戡黎》载:“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格人元龟,罔敢告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40]由此可见,在帝辛看来,王权的获得和丧失由神决定,人间没有话语权。帝辛对信仰的认识正是商代的信仰知识的体现。不论是从甲骨卜辞看,还是从《周易》《尚书》《诗经》等传世文献看,商王都不能突破这个信仰知识的界限。由此可见,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人信仰知识对当时人们的行为有着指向意义。
第二,在商人信仰文化里,人死后依然会按照他们的意愿影响人间,在幕后控制着人间的幸福。这实质上表明,已死的商人祖先对人间的留恋;再进一步来说,人间的美好和死去世界的不美好,是死去的人留恋人世的主因。以此认识为思想基础,商人形成了关注此生幸福的信仰体系。罗素说:“巴比伦的宗教与埃及的宗教不同,它更关心的是现世的繁荣而不是来世的幸福。巫术、卜筮和占星术虽然并不是巴比伦所特有的,然而在这里却比在其他地方更为发达,并且主要地是通过巴比伦它们才在古代的后期获得了它们的地位。”[41]早期中华的信仰知识与巴比伦的有类似之处,不论是商人对帝命的关注,还是对人鬼和地祇的隆重祭祀,都是为了获得此生的平安和幸福。这就可能意味着,在商人看来,来世幸不幸福是未知数,他们对此怀有深深的恐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死后的世界并无幸福可言,所以人鬼频繁地干涉人间事务,通过伤害人间的方式引起尘世的关注和祭祀。
人鬼频繁地作害作祟实质上是留恋人世的体现,也由此反衬出人间的繁华和美好。如果我的这一认识合理的话,商人的信仰文化对当时和后世就有重要的影响,就很好解释为何追求长生不死的道教的发生问题,也能很好解释强调生死轮回的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人们今生积善,是希望来生投胎人间,获得更美好的生活),因为这个信仰的认识基础在商代已经成立。若不是有着“死后世界是不美好的”的认识,贵族会使用人间大量的贵重物品来陪葬吗?商王会使用周祭的仪式为祖先定期贡献祭品吗?(12)关于周祭制度,可参考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一个主要原因是,希望死后继续生时的荣华富贵,生者希望死者继续享受生时的高级待遇。此对儒家、墨家的鬼神观、后世道教的发生和佛教的本土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总之,商人信仰体系成立的逻辑基础,主要建立在两个认识之上,一是认为人间的祸根和不幸多因鬼神而起,所以他们过分地关注鬼神,以商王为中心的贵族阶层还未将目光转向更需关爱的尘世;二是认为人间是美好的而死后的世界是不美好的,此是商人的信仰关注现世生活的两个重要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