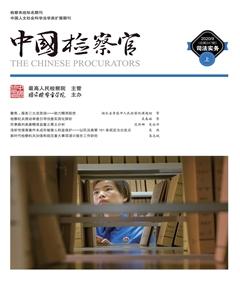论我国减刑制度之立法完善
马楠
摘 要:当前,我国减刑制度存在一些不足,在实体条件上,减刑制度比较片面,未充分考虑减刑对社会的影响和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在程序上,减刑制度比较封闭,罪犯诉讼权利缺乏救济,监督程序设计不足。建议在实体法上进一步完善减刑的实体条件,将社会效果纳入减刑的实体条件,将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作为减刑的必要条件;在程序法上增设被害人意见调查程序、上诉抗诉程序和减刑撤销程序,保障实体法的实施。
关键词:减刑 社会效果 财产性判项 监督程序
从法律规定看,我国减刑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减刑制度是指刑法第78条第1款规定的减刑制度,即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符合法定条件,经法定程序,减轻原判刑罚的制度。广义的减刑制度还包括刑法第50条规定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本文讨论的减刑制度限于狭义范围。
一、我国减刑制度应实现的价值功能
笔者认为,对于减刑制度,立法和司法应实现至少两方面的价值功能。
第一,维护法治权威,保障刑罚执行。刑罚不仅可以惩罚犯罪分子,让被害人感受到法律对自身权益的保护,还能对有犯罪意图的人起到震慑作用,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刑事诉讼法构建了审判程序,以公开公正的程序保障实体法的正确实施,确定被告人应受的刑罚。生效判决确定的刑罚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是维护法治权威、实现刑罚预防犯罪功能的关键环节。减刑制度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其实体条件、程序设置存在不足,生效判决确定的刑罚和实际执行的刑罚不匹配,刑罚的预防犯罪功能乃至司法权威就会大打折扣。只有在定罪量刑時的犯罪情节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才能依照与定罪量刑程序同样公开公正的减刑程序改变生效判决确定的刑罚。科学严谨的减刑制度有利于保障实现刑罚功能作用,进而维护司法权威。
第二,对罪犯进行有效改造,输出守法公民。减刑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对犯罪份子进行改造,向社会输出合格的守法公民。审判制度依据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出判决,确定刑罚。通过减刑制度,可以促使罪犯主动降低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其自身的人身危险性,促进其改造。例如,在刑罚执行期间,罪犯通过自身的劳动所得或者由其家人对被害方进行赔偿,履行生效判决中的财产性判项,获得被害方一定程度的谅解,可以认定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所降低,通过减刑制度对罪犯给予鼓励和肯定。再如,罪犯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可以认定其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同样可以通过减刑制度进行鼓励和肯定。
二、我国减刑制度在实体和程序方面存在的不足
对比减刑制度应实现的功能作用,在减刑制度的设计上,笔者认为还存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不足。
(一)减刑的实体条件比较片面
1.未充分考虑减刑对社会的影响。按照刑法第78条第1款的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相关司法解释对刑法规定进行细化,要求办理减刑案件要综合考察罪犯犯罪的性质和具体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等因素,并明确“确有悔改表现”要同时具备四个要件:一是认罪悔罪;二是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三是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四是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根据上述规定,作为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狱,依法提请减刑的主要依据是罪犯犯罪、判决情况以及对罪犯在监狱内的劳动、学习、遵守监规监纪等情况进行考察的结果,其中罪犯服刑期间的表现是判断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主要标准。而罪犯减刑后提前释放回归社会,可能对被害方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未列入减刑实体条件。可以说,目前减刑的实体条件更关注罪犯的狱内表现,对减刑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缺乏足够重视。
2.未充分考虑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第3款、《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7条第1款、第9条第1款、第11条和《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定》第1条的规定,仅对于依照刑法分则第8章贪污贿赂罪判处刑罚的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一般不予减刑。对于其他类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虽规定从严掌握,并具体规定了较一般情况更加严格的减刑起始时间、减刑幅度、两次减刑之间的间隔时间等,但仍较为笼统,而且没有不予减刑的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财产性判项的强制执行力不足,罪犯履行财产性判项的积极性较差,减刑实体条件失之过宽。
(二)减刑的程序设计比较封闭
与定罪量刑程序比较,减刑程序较为封闭,主要在刑罚执行机关和与之相对应的法院、检察院之间进行,罪犯诉讼权利缺乏救济,监督程序设计不足。
1.罪犯权利缺乏救济。程序法具有保护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功能。在定罪量刑程序中,刑事诉讼法为被告人设计了上诉制度,对于被告人不服第一审判决的,允许提出上诉,通过两审终审制度保证被告人得到公正处理。而减刑程序直接影响罪犯实际执行的刑期,对罪犯实体权利的影响不亚于定罪量刑程序。但刑事诉讼法仅将减刑程序作为刑罚执行程序的一部分,与定罪量刑程序相比过于单薄。由于减刑程序中缺乏上诉程序,罪犯不服法院不予减刑裁定的,无法通过上诉程序维护自身权益,不符合诉讼程序的一般原则,不利于维护罪犯的诉讼权利。
2.监督程序设计不足。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54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第20条的规定,法院作出减刑裁定后,应当在7日内送达同级检察院,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法院减刑裁定不当的,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20日以内,依法向作出减刑裁定的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法院应当在收到意见后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在1个月内作出裁定。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审理减刑案件的法律监督限于同级监督。虽然实践中不乏成功监督的案例,但同级监督的力度仍弱于上级监督。在定罪量刑程序中,检察机关认为法院裁判确有错误的,可以通过抗诉程序提请上一级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减刑制度中缺乏相类似的程序设计。
三、完善我国减刑制度的建议及法律条文设计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升,减刑制度具备了进一步完善的条件。笔者结合办案实际,对减刑制度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完善进行框架性研究。
(一)实体上进一步完善减刑条件
1.将社会效果纳入减刑实体条件。就个体而言,罪犯得到减刑将对被害人造成直接影响,并且会辐射扩散到被害人所处社会群体。就整体而言,如果减刑制度不完善,不完整服刑比例不合理[1],容易造成被害人乃至社会群众对法律的轻视和不信任。因此,建议将社会效果纳入减刑实体条件,将刑法第78条第1款修改为:“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且提前释放后,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不致对被害人的工作、生活、心理造成负面影响的,可以减刑。”
2.将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作为减刑的必要条件。财产性判项是法院裁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履行情况反映了罪犯的认罪悔罪态度,也关系到被犯罪侵害社会关系的修复。对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财产性判项的罪犯,无论何种犯罪,均应认定为没有悔改表现,不能减刑。判断是否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的证据标准,要符合常情、常理和常识。例如,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应当退赔而未退赔,且未说明财产去向的,即可认定为不积极履行财产性判项。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财产性判项履行的规定,作为第78条之一:“对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罪犯,不予减刑。”
(二)程序上进一步完善有关规定
1.增设被害人意见调查程序。在量刑程序中,被害人谅解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对罪犯的减刑,同样应将被害人意见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在法院对刑事案件作出裁判前,应征询被害人意见,询问被害人是否需要对被告人服刑期间的减刑发表意见。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应征询其近亲属的意见。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表示需要发表意见的,刑罚执行机关、相应法院在提请减刑前、裁定减刑前,均应征求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是否同意减刑的意见,作为减刑的必要条件之一。建立被害人意见调查制度,有利于促进罪犯更加重视被害方的感受,反省自身犯罪行为对被害方乃至社会造成的损害,真正认罪悔罪,同时有利于促进罪犯积极赔偿被害方损失,让被害方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被害人意见调查程序,作为第275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作出裁判前,应就被害人是否需要对被告人服刑期间的减刑发表意见,征求被害人的意见,并在判决书、裁定书中注明。被害人已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应征求被害人近亲属意见。(第二款)罪犯服刑期间,刑罚执行机关拟提请减刑的,对于原判决书、裁定书中注明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要求发表意见的,应征求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对罪犯能否减刑的意见,将被害人或其近親属同意该罪犯减刑作为提请减刑的必要条件。(第三款)人民法院审理减刑案件,拟作出同意减刑裁定的,对于原判决书、裁定书中注明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要求发表意见的,应征求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对罪犯能否减刑的意见,将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同意该罪犯减刑作为作出同意减刑裁定的必要条件。”
2.增设上诉抗诉程序。建议参考刑事审判的第二审程序建立针对减刑裁定的上诉抗诉程序。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上诉程序,作为第276条:“罪犯对人民法院不同意减刑的裁定不服的,或对人民法院裁定减刑的幅度有异议的,可以参照本法第三编第三章第二审程序的有关规定提出上诉。”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274条,增设抗诉程序,作为第277条:“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减刑案件裁定,可以参照本法第三编第三章第二审程序的有关规定提出抗诉。”
3.增设减刑撤销程序。减刑制度的作用之一在于鼓励罪犯真正认罪悔罪,以守法公民的身份回归社会。如果罪犯经减刑提前出狱后,原判刑期届满前,再次犯罪,说明罪犯在减刑时仍有再犯罪危险,实质上不符合减刑条件。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减刑撤销程序,作为第278条:“罪犯经减刑提前释放,在原判刑期到期日之前再次犯罪的,应当撤销其减刑裁定,将原判刑期的未服刑期与所犯新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注释:
[1]广东省2014年-2017年减刑率分别为37.31%、40.81%、45.62%、32.07%,参见杨智明:《省政协常委王晓华:依法逐步提高广东监狱服刑人员适用假释比例》,南方网http://law.southcn.com/c/2019-01/27/content_184976572.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7月11日。上述减刑率是否合理需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