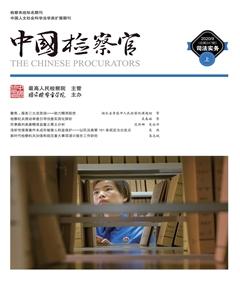浅析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权益保护
吴燕
摘 要:民法典总则第191条规定了受性侵未成年人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从时效制度方面强化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但在实践中,该法条适用仍存在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赔偿难、举证难、保护难等方面。有必要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延长或者取消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追诉时效。
关键词:性侵未成年人 诉讼时效 精神损害赔偿 民法典第191条
新颁布的民法典总则第191条规定了受到性侵害的未成年人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這条规定沿袭了民法总则第191条的规定,内容没有变化。其立法本意主要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囿于传统观念,不少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不想、不敢或不知如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待受害人成年后寻求法律救济时,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了更好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民法典对诉讼时效的起算进行了特别规制。如何理解并适用民法典的这条规定?笔者结合司法实践谈一些粗浅思考。
一、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
早在2009年,上海市检察机关部分基层院就开始探索将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纳入未检部门受案范围。2016年上海市检察院检委会正式发文,明确将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案件交由未检部门集中归口办理。从近几年办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情况看,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案件占比高。2019年,上海未检部门受理审查逮捕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共220件246人,审查起诉191件211人。在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案件中,性侵害案件占总数的60%以上。
第二,幼童占一定比例。在上海市未检部门2019年受理审查起诉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14岁以下的被害儿童占67%,其中6岁以下幼童占8%。
第三,熟人作案多且隐秘性强。根据统计,2018年公开报道的317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例中,熟人作案210起,占比66.25%,明确表述性侵者多次作案的有124起,占总数的39.11%。[1]这不仅说明此类案件的隐蔽性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反复、多次作案的情况严重。
第四,案发距作案时的时间间隔较长。有的案件因未成年人受到恐吓或出于害羞心理,不敢或不愿告知家长、老师等成年人。有些家长在得知侵害事件发生后,出于“顾及家庭”“保全名节”等考虑,要么选择不报案要么很长时间后才报案。
第五,证据相对弱。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特别是幼童的表达能力、认知程度有限,且易受他人诱导,加之犯罪嫌疑人多拒不认罪、痕迹物证缺乏,因而案件存疑不捕率相对较高。例如,上海市未检部门2019年办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审查决定不捕的占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人身权利不捕案件总数的87%。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以上特点,给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造成了困难。
二、检察机关对受性侵未成年人支持起诉的实践
2012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独立机构的检察院,一般应实行捕、诉、监(法律监督)、防(犯罪预防)一体化工作模式。其中法律监督涵盖民事诉讼监督,这一规定为未检部门通过监督手段维护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打下基础。2017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决定在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2020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会议上指出,“检察机关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原则上可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统一集中办理。”基于此,检察机关未检部门在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可以通过履行民事检察职能,如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启动撤销监护权,或者通过支持起诉帮助未成年被害人获得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实现对未成年人全面综合的司法保护。
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此项规定也为检察机关行使支持起诉权提供了法律依据,上海检察机关通过个案办理积极开展了相关探索。典型案例如下:
2017年8月至10月期间,上海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聘用的书法班老师廖某借教学指导之机,猥亵程某等4名学生。2018年3月,长宁区法院一审判决廖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5年内禁止从事教育及相关工作。廖某被追究刑事责任后,4名被害儿童家长又向长宁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培训机构赔偿精神损害,并向长宁区检察院提出支持起诉申请。
长宁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4名申请人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儿童,在被告处学习期间受到猥亵犯罪侵害,导致心理创伤,被告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4名申请人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同时,4名申请人均系不满9周岁的儿童,相对于被告公司属于弱势群体,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有利于监督案件依法公正审理,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长宁区检察院决定支持起诉,并于2019年1月17日向长宁区法院送达“支持起诉书”。决定支持起诉后,长宁区检察院积极向4名原告提供法律意见,引导其采取有效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是考虑到被告过错行为系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长宁区检察院建议4名原告向法院提起教育机构责任之诉,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二是建议4名原告从被告对廖某的教学资质与教学经历审核、教学活动日常监管等方面着手,收集证明被告存在过错的相关证据。
长宁区法院不公开合并审理该案,长宁区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起诉。最终,经二审法院调解,原被告双方于2019年6月达成协议,原审被告分别给付程某等4人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4万元并当场赔礼道歉。
三、对民法典第191条的适用理解
结合立法背景和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该条文:
第一,本条从时效制度方面强化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符合立法逻辑。民法典第128条是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民事权利特殊保护的原则性规定。第191条不仅是对第128条规定的具体贯彻,也体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第二,本条规定的是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如果是刑事犯罪的追诉时效,仍应适用刑法第87条的规定,即犯罪经过法定期限不再追诉,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第三,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在年满18周岁之前,其法定代理人也可以代为行使请求权,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受害人在年满18周岁之后对相关处理不满意要求再次处理的,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2]
第四,本条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自未成年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其具体适用应当依照民法典第188条关于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即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3年。此外,如果符合民法典第194条、第195条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情形的,也应当依法适用。
四、民法典第191条的适用困境及完善建议
(一)适用困境
民法典第191条规定在促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实际适用过程中仍然面临较大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赔偿难。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性侵意见》)第31条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因被性侵害而造成的人身损害,为进行康复治疗所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从赔偿范围看,虽然该司法解释明确未成年人因性侵遭受人身损害可以提出赔偿请求,但赔偿范围仅限于为进行康复治疗所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实际费用。《性侵意见》的规定主要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8条的规定,即:“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因遭受性侵要求赔偿损失的,精神损害赔偿并不包括在内。但事实上,性侵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身体损伤的同时,对其造成的精神伤害往往更为严重,一些心理创伤可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不仅影响其交友观、婚恋观,实践中有的被害人还因严重的心理问题自伤、自残、甚至自杀。但是赔偿范围的局限性使得受性侵未成年人实际上得到的赔偿少之又少,根本无法弥补其精神上受到的伤害。
从民法典及相关解释来看,当事人可以就侵权行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第1183条第1款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第10条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各地相继出台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如安徽省规定数额“不高于8万元”,江苏省明确“一般不宜超过5万元”,北京市对最为严重的情形规定“一般不得超过本市城镇职工上年平均工作的10倍”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7月下发《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当在受害人主张的范围内酌定。……至于具体的数额除了要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的手段、方式,受害人的损害程度,侵权行为的社会影响等因素外,还应当与当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相适应……考虑就目前上海市实际生活水平而言,精神损害赔偿额以一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为宜(上海人均GDP的二倍)……当然如果加害行为特别恶劣,受害人的损害程度特别严重或者社会影响特别大,需要提高赔偿额的话,也可以适当提高,但为谨慎和统一起见,判决前须报高院民庭复核。”该《意见》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额“一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其计算依据是括号中注明的“上海人均GDP的二倍”,1999年上海人均GDP约2万余元,人均GDP的二倍差不多就是5万元。而2019年上海人均GDP已达15.6万元,前文列举的长宁区程某等4人与被告上海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4名原告分别向法院提出3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申请,基本符合2019年上海人均GDP二倍的实际,但法院最终判决原审被告分别给付4人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4万元,没有超出1999年《意见》规定的5万元限额。
2.举证难。《性侵意见》规定的合理费用是“因被性侵害而造成的人身损害,为进行康复治疗所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等”。该费用应当包含用于治疗性侵害造成的精神损害或者心理疾病产生的实际费用,但是实践中未成年被害人或其家人要么不知道求助心理医生,要么讳疾忌医拒绝接受心理治疗,要么无力垫付较高的心理治疗费用,真正接受精神或者心理治疗的寥寥无几。此外,有的受害人由于缺乏证据留存意识,当年看病的医疗费收据都已经丢失,以至于无法向法院主张权利。
从取证能力看,前文所述上海检察机关受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67%是14岁以下的被害儿童。这些孩子基本没有获取证据的能力,而性侵案件本身就存在客观证物少、言词证据多,直接证据少、間接证据多等特点,作为公权力机关的公检法尚且存在取证难的问题,何况未成年人?特别是要在被性侵多年满18周岁以后再去请求损害赔偿,不仅要冒着“名誉风险”,还要通过更为困难的举证来主张权利,基本上空有诉权,所以实践中极少有被性侵的未成年人在成年后依据第191条的规定进行维权。
3.保护难。从立法情况看,目前性侵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途径是提起侵权之诉。侵权行为一般是轻微违法行为,一旦被告人的侵权行为严重到构成犯罪,被害人只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申请损害赔偿但并不能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即便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人民法院也不予受理,原因在于被告人已经受到刑罚制裁。但对被告人的刑罚处罚是否能够等同于受害人得到的精神抚慰?立法是否应该更多地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去检视“惩罚与补偿”的有效落实?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此外,无论是精神损害赔偿还是物质损失赔偿都存在被告是否具有赔偿能力的问题,未来可能存在的执行难问题也给受性侵未成年人的保护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如遇被告人无力赔偿的情况,被害人还可以通过申请司法救助获得一定的补偿。
从追诉时效看,性侵案件被害人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訴讼获得有限的经济补偿,并借助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帮助自己获得赔偿,前文列举的长宁区检察院支持起诉案,就是由检察机关辅助被害人将刑事证据转换为民事证据,这大大降低了未成年人的维权难度。公权力介入民事诉讼是以形式上的不平等追求实质上的平等,不仅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优先保护,也是实现国家监护的有效途径。但检察机关介入的前提是案件尚在追诉时效内,一旦过了追诉时效,被害人只能面临独自维权的窘境。因为我国刑法第88条规定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只有两种:一是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二是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在域外,韩国的一些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借鉴:2011年10月28日,韩国国会高票通过了《性侵害防治修正案》(又名《熔炉法》)。《熔炉法》不仅提高了性侵未成年人罪犯的刑期,还规定性侵女身障者或不满13岁的幼童,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废除公诉期,即取消了追诉时效。
(二)完善建议
1.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取消侵权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固定最高限额。如可将上海《意见》 “精神损害赔偿额以一般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为宜”修改为“精神损害赔偿额以一般最高不超过当年上海人均GDP的二倍为宜”。
2.借鉴国外做法,建议延长或者取消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追诉时效。如可在刑法第88条中增加一款:性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等。
注释:
[1]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会:《“女童保护”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98646877_99996733,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1日。
[2]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