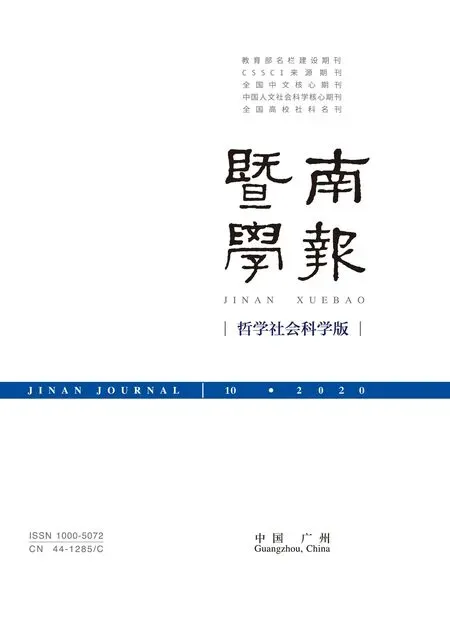孙犁:中国乡村人道主义作家
贺仲明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作家。他曾经是抗战时期很有影响的革命作家,但始终没有进入文学中心。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具有政治和文学双重耀眼履历的孙犁,却长期任职于一家地方报纸的副刊,与主流文学界相远离。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孙犁的文学地位,他是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文学中少见的能够被文学史和读者大众都认可的作家之一。孙犁的为人和为文,与他深厚的乡村文化滋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最具个性的创作思想和审美特色,都具有中国乡村文化的深深烙印。
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将“人”放在重要位置、表达对“人”深切关怀的作家不多,孙犁是很突出的一位。这既体现在其创作内容上,也投射在其艺术特征上,同时更贯穿于其整个创作生涯中——无论是早期的战争书写,还是晚期的回忆散文,都具有如此的特征。具体说,孙犁创作有如下表现:
其一,以“人”为创作出发点。“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1)《孙犁文集》(补订版)(第5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页。孙犁的创作包括战争、政治运动等多个题材,这些题材都属于宏大题材,与个人的距离相对较远,但孙犁却很特别地没有集中书写战争和时代政治本身,而是将目光落到其中的个人上,从“人”的角度来思考和写作。比如他写抗日战争,就较少书写战争的大背景,也很少进行具体的战场描写,而是关注战争中的普通人生活,书写他们在战争中的个人情感,以及战争带给他们的伤痛。孙犁写政治运动也一样。如《秋千》《铁木前传》等作品写土改运动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前者以土改工作队员角度写农村土改运动,但其中心却不在如何开展政治运动的过程,而是聚焦于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孩身上,关注她的心灵在运动中受到的戕害。后者虽然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持明确的肯定态度,但其对运动本身同样着墨甚少,重点放在写两个与运动关系不大的农民黎老东和傅老刚的私人关系,以及九儿与六儿、小满儿等几个青年之间的感情纠葛,致力于思考人的心灵如何被财物所异化(六儿),以及政治对情感世界的影响(小满儿和九儿),其立足点都可归结为人性和人情。
“文革”后,经历了政治劫难的孙犁创作了一系列以“文革”等政治运动为中心的散文和小说。这类作品是当时的“时文”,许多与孙犁经历相似的老作家都有这类创作。但孙犁的作品颇为与众不同。他很少直接书写政治运动细节,也很少联系大的政治背景去思考运动本身,而是始终将视野集中在自己和身边朋友、同事在运动中的遭遇和表现上。他写得最多、也是他对这场政治运动感受最深的,是人情的冷暖和人心的难测,还有对人生无法把握的偶然性的感叹。在回忆一些与政治关系颇深的故人时(如《芸斋小说》中之《王婉》等),孙犁很少去追究他们的政治行为,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其人品和人格的揭示,以及对其命运的慨叹上。也就是说,孙犁回顾这场政治运动,思考的核心并非政治,而是人性。这就如孙犁对“革命”所做的人性化理解:“过去之革命,为发扬人之优良品质;今日之‘革命’,乃利用人之卑劣自私。”(2)《孙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也如他表述的对“文革”最深的体会:“深深有感于人与人关系的恶劣变化,所以,即使遇到一个歌舞演员的宽厚,也就像在沙漠跋涉中,遇到一处清泉,在恶梦缠绕时,听到一声鸡唱。感激之情,就非同一般了。”(3)孙犁:《删去的文字》,《晚华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其二,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孙犁的作品从人出发,有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揭示(特别是晚年的创作),但最中心的内容还是传达对人现实和心灵世界的关怀,特别是对生活中的不幸者和弱者的悲悯和同情。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政治中,老百姓、女性和小孩都是天然的弱者,孙犁作品写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些人。通过书写战争和政治带给人们的各种苦难,揭示和否定战争、政治的非人性性质,表达对不幸者的同情、关怀,以及无奈和悲悯。比如《“藏”》《荷花淀》《嘱咐》《风云初记》等战争题材作品,都书写了战争给无数个家庭带来骨肉分离的伤害。战争让女性无法平静地生儿育女,儿童无法健康幸福地成长,甚至还要遭遇伤痛和死亡;而晚年的《芸斋小说》和诸多散文则关注了多位被时代政治所播弄的女性和文人的命运,在慨叹人生无常的同时,更有对人生的悲凉感和无奈感。
孙犁的人文关怀,虽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限制,但在很大程度上对阶级、地位、性别等外在因素进行了超越,直接进入到人的个体本身。比如,《秋千》等作品所关注的就是非劳动阶级的子女,《铁木前传》中塑造的小满儿和《风云初记》中塑造的李佩钟,更是对阶级身份的冒险性挑战——要知道,在孙犁书写的时代,阶级身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也是长期笼罩在很多人头上的巨大政治阴影。事实上,孙犁也因此而多次受到批评。这两个女性都受家庭出身所累,生活充满困厄,内心孤独而无助,但孙犁对她们的叙述惋惜与赞赏并存,蕴含着强烈的同情和关怀情感。此外,在晚年回顾往事的散文中,孙犁也常常记叙那些被生活所摧残和伤害的弱者,表达追忆和叹惋之情。对于那些曾经的政治风云人物,孙犁很少计较个人恩怨,在其落魄之后,从无借机讽喻之意,而是长怀惋惜之心。
其三,对人性美和善的执著关注。这一点,学术界已经有非常广泛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言。只是想对晚年孙犁创作风格与之的关系略做阐述。政治运动的残酷“洗礼”对晚年孙犁的文学风格有较大的改变,其中已经较少有对人性美好的讴歌,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慨叹和思考。包括在一些时候,孙犁还表达了对生活热情的丧失,并放弃了他曾经最钟爱的小说创作:“这种东西(虚伪和罪恶)太多了, 它们排挤、压抑, 直至销毁我头脑中固有的, 真善美的思想和感情。……它受的伤太重了, 它要休养生息, 它要重新思考, 它要观察气候, 它要审视周围。……假如我把这些感受写成小说, 那将是另一种面貌, 另一种风格。我不愿意改变我原来的风格, 因此, 我暂时决定不写小说。”(4)《孙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64 页。然而我以为,这种表现不能说明孙犁丧失了热爱美善之心,而恰恰相反。他之所以强烈反感现实,是因为他依然有所期待;他之所以拒绝妥协,是因为他始终有所坚守。历经劫难而痴心不改,正体现了孙犁对人性美关注之执著和深切。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是密切关联的。孙犁以人为中心、对人关怀的思想特点,对其艺术个性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或者说,其思想和艺术之间相互呼应,艺术特点也构成了孙犁文学对人关怀思想内涵的一部分。
其一,情感真诚的抒情艺术。
孙犁文学作品较多抒情,其中既有对战争中胜利和美好人性的赞美性抒怀,也有对牺牲者的感伤和悲悯,还有对个人命运被时代政治所严重影响的深切感怀。战争小说的表现很多,这里不再赘举。政治运动方面,如《铁木前传》笼罩全篇的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如《芸斋小说》对各种被时代政治所播弄者的强烈叹惋,都传达着作者对人生的感喟。这些抒情,有时候直抒胸臆,语重心长,有时候则如饱经世故老人看透世事的人情冷暖,但共同的特点就是真诚坦率。其战争小说如《琴和箫》对两个被战争戕害小生命的叹惋,以及《嘱咐》对水生夫妻深情的歌吟,都细致真切,如诉心声。而其晚年作品更是彻底地袒露自己的真实生活和内心世界,包括其再婚往事,包括对年轻美丽女性的眷恋之情,都无所避讳,细致道出。让人感觉到其无所防范、无所隐匿的真诚赤子之心。
其二,细腻立体的人物形象。
孙犁小说创作还有一个突出特点是人物塑造。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塑造的水生、小满儿、李佩钟等人物非常形象生动,是很有生命力的文学形象。这与孙犁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特点有直接关系。因为孙犁的创作重点不在宏观的社会政治,较少书写大的现实场面,而是落脚于个人,注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这些人物的主体精神揭示得比较充分。此外,因为孙犁关注人,所以他的作品多从人物出发来观察和展示生活,人物得到多侧面、多角度的展现,而很少简单化和脸谱化地处理,人物性格也就往往具有多面性和立体化的特点。前面所谈的小满儿、李佩钟、九儿等主要人物形象不说,即使是《风云初记》塑造高疤、俗儿这样的反面人物,也同样有对其情感面的一定正面书写。
除了艺术创作特点,孙犁的文学观也体现出其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特点。孙犁是一个受五四文学影响的新文学作家,但他的文学接受观与主流观点不大一样。具体说,就是他很重视老百姓的接受,认可大众化的文学观。所以,孙犁对另一个特别重视农民接受的作家赵树理创作有很高的评价:“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我在冀中区读到他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我当即感到他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5)孙犁:《谈赵树理》,《天津日报》,1979年1月4日。而且,在对文学与读者关系的看法上也与赵树理相似:“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倒是多接受了一些西洋的东西,这当然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有总的关联,而且也不是徒然的。但是这样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损失,它使文学局限在少数知识青年圈子里,和广大劳动人民失去了联系。”(6)孙犁:《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遗产》,《孙犁文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页。并将自己的文学价值与农民读者的评价密切结合在一起:“看看是否有愧于天理良心,是否有愧于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7)《孙犁文集》(补订版)(第5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72页。
二
孙犁对人关注的创作,使他在抗战时期就与其他同类作家形成了显著的差别,成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8)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并受到批判和冷落,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孙犁。包括在经历了漫长的创作间断期,特别是十年“文革”的艰难遭遇后,孙犁也依然保持了这一个性。这说明孙犁的这一特征源于其内心深刻的思想文化,是其人格精神的结晶。从最外在和最直观的层面上,它可以溯源于孙犁的人格和个性,缘于孙犁秉性的善良和敏感。但是,任何个人都既是个体的,又同时是时代的。孙犁的个性气质与其生活和文化环境有着深刻而内在的关系,具体说,就是中国的乡村生活和文化。
童年是一个人成长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对于作家这样心智敏感的人更是如此。孙犁的童年在河北农村度过,他的家庭和周围环境对他的成长影响至深。孙犁家虽然在农村,但家境也算小康,生活环境比较优裕。他的父亲是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行为儒雅,母亲也非常善良,性格平和。因为孙犁童年时身体不太强健,家人对他也有更多关爱,特别是母亲对他的照顾非常细心周到,孙犁对母亲的感情也特别深,性格上也敏感,喜静不喜动。此外,孙犁所在的乡村民风比较平和、安静,能让孙犁充分感受到乡村的温馨、宁静和美好。
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孙犁一直保存着对乡村生活的美好记忆。后来的生活中,他始终以乡村文化为心理指归,并始终在心灵上怀着对乡村的强烈感情,对城市生活怀着拒绝和厌恶的心理。“我每天都在思念农村,在那里,人与人的间隔大,关系会好得多。”(9)孙犁:《老荒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10)孙犁:《答吴泰昌问》,《孙犁文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49页。与此同时,他也一直保持着对父母亲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乡村和农民的关怀之情。孙犁的日记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他去看电影,正好碰上新闻片中播放农村的灾情,结果,孙犁顿时心生感触,写下了这样的心情:“难过不在于他们把我拉回灾难的农村生活里去,难过我同他们虽然共过一个长时期的忧患,但是今天我的生活已经提高了,而他们还不能,并且是短时间还不能过到类似我今天的生活。”(11)金梅:《孙犁自叙》,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
对乡村的强烈情感认同,自然会投射到价值观上。也就是说,乡村社会滋养了孙犁的心灵,其朴素人文和道德观念也会对孙犁的人格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家庭的影响最为深刻。(12)参见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特别是因为父亲家庭出身不好,新中国成立后多受打击,孙犁对家人命运非常牵挂,也自然将这种感情延及到文化态度中。孙犁的父亲乡土文化观念很重,母亲也同样持朴素的乡村道德观念。母亲对孙犁的启蒙教导“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对孙犁思想影响很深,到晚年还记在心中。(13)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168页。孙犁一生中有多次做官的机会,他都主动放弃,甘于做一个普通编辑,显示出这种文化教育影响之深。而孙犁一辈子为人谦和,从来都是将自己视作身份普通的人,并以平等态度待人,也可看出这种文化的影响。评论家阎纲对孙犁有这样的评价:“孙犁写他的人物,特别写他笔下的人民,关系是平等的。不但平等,而且不惜站在人民之下,眼睛朝上看人民,人民比他高。”(14)阎纲:《孙犁的艺术——在〈河北文学〉关于“荷花淀”流派座谈会上的发言》,《孙犁作品评论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98页。评论家鲍昌也对孙犁的思想有这样的评价:“孙犁作品中‘善’的内核,是带有普通人们(主要是农民)的思想特色的。它表现为农民式的质朴、仁爱乃至农民式的乐观幽默,干脆说,它具有醇厚的农民的人情味。”(15)鲍昌:《中国文坛上需要这个流派》,《河北文学》1981年第3期。这既是孙犁的为文,也是孙犁的为人,是其人格和文化的积淀结果。
按照西方学者希尔斯的说法,中国的乡村文化属于“小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它既有自己朴素的、更切合自然和生活方式的文化特点,又与儒家文化的“大传统”有一定联系。特别是在乡村文化的上层——乡绅社会中,儒家思想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孙犁的家庭属于乡村中比较富庶的家庭,他的父亲又属于乡村知识分子群体,因此,孙犁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接受的文化影响中,自然会有较多乡村儒家思想的因素。这一点,结合孙犁文学作品对“人”的关怀特点可以理解得更为准确。也就是说,前述孙犁作品的“人文关怀”特点,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有内在的联系。从孙犁对弱者的关爱中可以看到孔子“仁者爱人”和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子;从孙犁对美善的特别执著中,更可以看到孟子“性本善”观念的影响。
在乡村文化中,朴素的乡村道德和儒家文化本就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所以,对孙犁所接受的乡村文化因素也没有必要辨析具体的归属。而且,孙犁文学中的思想观念也不仅仅是来自于中国,西方现代思想因素也是绝对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孙犁从读书起,就接受过现代文化教育,之后的学习和工作也都与新文学、外国文学有密切的联系。他曾经这样说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离乡背井……我的破书包里,还总是带着一本书,准备休息时阅读。我带过《毁灭》《呐喊》《彷徨》,也带过《楚辞》和线装的《孟子》。”(16)《孙犁文集》(补订版)(第7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中外作家之中,我喜爱的太多了。举其对我的作品有明显影响者。短篇小说:普希金、契诃夫、鲁迅。长篇小说:曹雪芹、果戈里、屠格涅夫。”(17)《孙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并且,孙犁还明确表达过对西方人道主义文学的推崇:“我幼年学习文学,爱好真的东西,追求美的东西,追求善的东西”,“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18)《孙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可以说,孙犁以“人”为中心的文学不是单一和狭窄文化的产物,而是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的丰富结合。
正因为这样,孙犁的小说中表现出强烈的“人文”色彩,从中可以看到与西方文化的“人道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但又与之不完全一致,而是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它体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乡村文化的深刻关联,是以乡村文化为精神主导和核心。具体说,孙犁文学的人道主义具有这样的思想特征:
其一,较强的民族国家意识。西方文学的人道主义往往以个人为中心,孙犁《铁木前传》等作品也有对个性的张扬,但在更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其战争小说中,都是以民族国家意识为中心,个性意识被服从或结合到民族国家思想之下。表现之一是将个人遭遇与民族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以“保卫家园”为中心,赋予民族战争以正当性和合理性,将战争歌颂与“人”的主题统一起来。《嘱咐·纪念》中的这段话是形象的表述:“我不禁心里一震。原来在深深的夜晚,有这么些母亲和孩子,把他们的信心,放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当作了保护人。我觉得肩头加上了很重的东西,……”(19)《孙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表现之二是对“军民鱼水情”情感的演绎,将人性与民族国家(集体)感情融合起来。如《嘱咐》中写水生对父亲和妻子、家乡的深厚亲情;《碑》《蒿儿梁》写老百姓与战士之间如同家人一般的牵挂、伤心和牺牲。《女人们》写女孩脱下棉衣盖给伤员的细节,更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我只是把那满留着姑娘的体温的棉袄替顾林盖上,我只是觉得身边这女人的动作,是幼年自己病倒了时,服侍自己的妈妈和姐姐有过的。”(20)《孙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页。而在《浇园》中,孙犁更将民族国家情感与最基本的人性——两性情感做了结合。作品中,乡村女性香菊与伤员战士李丹的感情,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伤员和护理者之间的感情,而是有了男女之间的情愫。但是,作品并没有让个人情感突破集体感情。“革命”的理性是两人感情的统率者,他们始终没有逾越“革命战士”和“拥军农民”的政治身份。
其二,较浓郁的中国传统伦理色彩。西方人道主义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但孙犁作品却是个性解放与传统伦理的杂糅。孙犁作品尽管塑造了很多优秀女性,但她们的家庭基本上都是以男性为主导。这既是现实的反映,也折射出孙犁的思想观念。所以,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具有中国文化的忠贞、勤劳、爱家等传统美德。比如《荷花淀》《“藏”》等作品在谈到女性时,都特别提到贞洁的意义——以至于有学者对孙犁作品思想的现代性有所质疑。(21)逄增玉:《重读〈荷花淀〉》,《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包括孙犁作品中最富有个性、具有突破传统伦理色彩的人物形象,如《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村歌》中的双眉,《风云初记》中的李佩钟等形象,虽然作者赋予了她们追求自由的个性,但也始终没有超越道德的范围。或者说,在这些形象上,既有突破时代文化限制的勇气和力量,也有民间文化的自由和生动,同时还有儒家伦理思想的制约。
当然,尽管孙犁作品的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文学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孙犁定位为一个优秀的人道主义作家。因为虽然“人道主义”这个词缘于西方文化,但并不意味着它只能存在于西方文化中。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因素,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和表现发生一定的变化是正常甚至是必需的。只要具备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基本核心——也就是对人性的关怀和关注,以人为中心来进行创作,就可以理解为人道主义文学。考虑到孙犁的思想资源最主要是来自于中国乡村,所以,对孙犁最恰当的界定也许是“中国乡村人道主义作家”。
三
无论是从文学价值本身,还是从文学史的意义,孙犁的中国乡村人道主义写作都有着非常突出的意义。
首先,它深化了新文学的人性关怀书写,特别是拓展和深化了战争文学的思想内涵。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没有人道主义思想内涵,但长期的专制文化却阻碍了其生长和发展。这也导致中国传统文学严重缺乏深刻人性关怀的作品。特别是古代战争文学,多从胜负、道德、社会等角度来书写,对人的价值则是严重忽略甚至是反人性。(22)例如学术界对《三国演义》非人性的战争观念已经有深入的揭示和批判。参见颜翔林:《第一批判:〈三国演义〉的美学批判》,《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新文学兴起后,情况有所改观,但传统思维还是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作家们的思维,其战争文学的品质和高度依然存在较大缺陷。对此,孙犁创作显示了自己的显著突破。他对战争中人性人情的关注,对牺牲者的悲悯和同情,都揭示了战争的反人性特征,诠释了对战争本质的认识,从而对中国现代战争小说品质作了很好的提升。同样,孙犁晚年从人道角度反思“文革”的作品,也拓展了同类题材创作的思想范畴,显示出在时代文学中的超拔位置。确实,在今天看,那些过于贴近时代来看问题的文学作品,容易获得时代效应,但局限性也往往会很大。孙犁从“人”角度出发的冷静旁观,虽然难以进入时代潮流,但在时过境迁之后,更能看到其独特视角背后的深度意义。
从美学意义看,孙犁小说同样魅力突出。典型如其战争小说。虽然如一些批评家所说,它们存在着战争场景书写过少、战争严酷性展示不足等缺陷,但它们从人的角度出发,细微深切地关注人的心灵,并蕴含着真诚的同情、关怀和悲悯,呈现出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是一种具有强烈个性化的艺术风格,也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如果我们不苛求所有的战争文学都具有一致性的思想艺术特征,而是认可文学的魅力往往在于个性和创新,那么,孙犁战争小说就绝对具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这就像质朴简单的民歌,可能永远成不了洪钟大吕,也没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含量,但其价值魅力永远都会存在。
其次,从文学史角度看,孙犁创作的意义更为突出。由于中国传统文学缺乏优秀的人道主义文学传统,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创作一直非常匮乏。即使偶尔出现人道主义文学作品,其思想资源也基本上来自西方文化。从早期许地山的《命命鸟》,到80年代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人啊,人!》等,基本上都是如此。所以,尽管这些作品有自己的价值,但由于它们以西方思想资源为立足点,就很难真正与中国大众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也难以在中国土地上扎下深根。相比之下,孙犁能够立足于中国乡村文化,对中国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拓展,而且又以开放的姿态融入西方现代思想精神,因此孙犁的思想既朴实自然,也更富生活性,具有更强的感染力。可以说,孙犁的中国乡村人道主义思想不只是对时代精神有大胆的突破,而且具有更广泛的方法性意义。
比如孙犁对战争的思考。与现代西方的人道主义战争小说不同的是,孙犁小说不是简单地反战,而是对战争有所赞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人道主义相悖,但实际上,这并不影响孙犁整体上否定战争的思想。他之所以肯定战争,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自我的卫护,其目的就是为了赶出侵略者并最终消灭战争、获得和平。他之所以歌颂战争中的美和善,目的是以之反衬战争的残酷和反人性。这一思想,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意识,也就是具有明确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战争进行否定的思想。所以,孙犁在作品中非常自觉地将自己和民族国家融为一体:“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23)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晚华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0页。此外,在文学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孙犁具有中国传统哲学内涵的人生思考:“只有寒冷的人,才贪婪地追求一些温暖,知道别人的冷的感觉;只有病弱不幸的人,才贪婪地拼着这个生命去追求健康、幸福;……只有从幼小在冷淡里长成的人,他才能爬上树梢吹起口琴。”(24)《芦花荡·邢兰》,《孙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孙犁的这种思想观念,包括其所表现的人生观,可能不一定完全符合现代标准,但却是真正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色。
当然,孙犁的人道主义书写并不完美,而是存在不小的遗憾。其一,思想深度的有所欠缺。这主要表现在受时代阶级等政治限制较多,未能充分体现出以“人”为中心的本质,对中国乡村文化的朴素人道主义精神挖掘和体现也不够充分。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复杂,其中既有封闭保守、愚昧自私的一面,也不乏善良淳朴、道义真诚。在后者中就蕴含有丰富而质朴的人道主义因素。孙犁对之有所展现,但内涵还比较单薄狭窄,政治局限性较大。比如《秋千》,是一篇从人性角度审视政治运动的优秀作品,但作品的关怀主题——对大绢的同情还是被限定在其祖父身份的前提上。也就是说,正如作品中的议论:“正月里,只有剥削过人的家庭,不得欢乐。”(25)《孙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只有在最终证明大绢祖父并非真正地主身份的前提上,作品才能充分表示对她的同情。再如《铁木前传》对小满儿生活的展示也过于简单,她的身份、家庭与乡村伦理以及政治伦理之间究竟构成什么样的冲突,以及有什么复杂性,作品都语焉不详。这些方面对作品的思想深度显然有很大的制约。其二,人性的表现较为单纯,没有充分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孙犁小说很少有悲剧性作品,也很少营造剧烈的矛盾冲突,让人物在矛盾中接受“洗礼”。而且,由于作品的篇幅都比较短,人物的活动未得到充分展开,特别是人物内心世界展示得很不够。所以,孙犁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固然很具个性,但深层精神却比较模糊,社会历史的内涵更为缺乏,给人以意犹未尽的感觉。其三,孙犁的作品质量不够齐整。真正比较深入表现人性关怀的作品只有《铁木前传》、《琴和箫》和《白洋淀纪事》中的部分篇章。与此同时,孙犁也有部分作品沉陷于时代流俗中。
对于自己创作上的这些缺憾,孙犁并非没有意识到。晚年孙犁对《琴和箫》的重新认识就体现出这一点。《琴和箫》是孙犁为数不多的直接叙述战争死亡的悲剧性作品,艺术水准也很高。但很长一段时间中,孙犁都没有将它收入作品集中,文学界也几乎将它遗忘。但在生命的晚年,孙犁重新谈到了这篇作品,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由此还感慨:“真正的激情,就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所流露的激情,恐怕是构成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26)孙犁:《〈琴和箫〉后记》,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145页。虽然只是对一部作品的反思,但折射的却是孙犁对文学深度意识的自觉。
而且,孙犁也曾经进行过自我突破的创作尝试。这就是孙犁唯一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这部作品采用了将个人故事融入大的战争背景中展开的结构方式,试图将人物命运与时代环境结合起来,并营构了众多的人物和宏大的战争环境,意图实现“战争史诗”的效果。然而,就总体来说,作品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还伤害到了孙犁一贯的以“人”为中心的创作特色。最突出的是没有将人物塑造与时代展示很好地统一,时代风云没有融入人物的性格发展和命运之中,而且由于人物活动空间受到侵占,反而影响了人物形象的清晰度和完整性。比如春儿和芒种两个中心人物形象呈现开头鲜活、后面却模糊的特点,就是因为他们只在作品开头部分有重点描述,之后就混杂于一般大众中,很少有机会独立表现。同样,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李佩钟也只是零星地点缀在作品中,致使形象个性没有充分突出。(27)贺仲明:《文体·传统·政治——论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1期。
之所以如此,也许部分可以归咎于孙犁的性格气质。孙犁的性格比较柔弱,审美气质偏于柔美而不是壮美,因此他不习惯于构造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也难以承载丰富宏大的社会历史含量。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时代限制,在于“人”的主题与时代要求之间的内在冲突。无论是《铁木前传》还是《风云初记》,都存在着人的关怀主题与时代政治主题之间冲突的巨大可能性。如果孙犁真的在作品中深入展开对小满儿、李佩钟等形象的书写,就必然会与时代政治的要求产生割裂。在这个意义上说,孙犁的创作局限中铭刻着时代的深深烙印。而且,时代的烙印不只是影响到孙犁作品,还对孙犁整个创作生命和人生道路都有伤害。像《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都存在难以正常终篇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而孙犁在50年代严重神经衰弱,无法继续写作,也是这种冲突的结果。
然而,不管怎么说,孙犁既有的成就已足以让他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卓越的身影。也许他还不能与世界一流作家们相比,但在他的时代却已经是独树一帜,即使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他也能够以其人道主义思想特色而赢得不朽的位置。并且我相信,正如人性的魅力永远不灭,孙犁的作品也肯定会超越时代,进入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