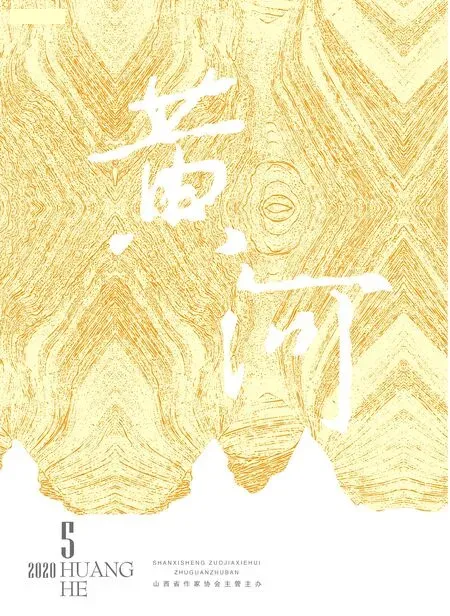按摩师
麦子杨
1
樊思明十七岁那年,因为一场突如奇来的眼疾,整个人被拽进黑暗,绝望中挣扎十年,他用一双手夺回了光明,成为这座城市首席按摩师。
三十岁的时候,樊思明按摩治疗机构已开了三间分店。
樊思明从来都把自己当作身体健全的选手,他在爱情的角逐中不接受低就缺陷。家人和亲朋戚友,介绍了许多身残志坚的姑娘给他,樊思明都断然拒绝。迫于家人压力,偶有见面的,他也是墨镜始终不摘,一言不发地制造相亲的尴尬,致使姑娘的家人疑问,他除了瞎眼不会还是哑巴吧?
除了奶奶,没有人能叫思明去相亲。奶奶临终,拉着孙子的手说:“我知道你想找一个健全的爱人。 ”樊思明点头。奶奶接着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健全的孩子。 ”樊思明用力点头。奶奶“上山”后,樊思明站在山腰上奶奶的坟前,轻叹:知我者,泥土里了。
樊思明对自己是健全人的信念来自奶奶。奶奶说,自己年轻时也有过短暂失明,父亲用治病招亲的办法,最后引出十万大山里的思明的爷爷。思明的爷爷用针灸和按摩治好了奶奶,迎娶了这位如花似玉的海边姑娘。思明的爷爷出身于一个老中医世家,悬壶济世,眼中只有病人,解放后奶奶活了八十八岁,七十八岁时患白内障,医院免费治愈。五年之后,也就是八十三岁的时候,奶奶瞎了,就像是年轻时的那次短暂失明再次袭来。这回没了爷爷,奶奶就在黑暗中与思明相依为命五年,最后留给孙子两句话,“上山”享福去了。
奶奶对思明的感情,差不多是用沉默的黑暗来表达的。樊思明告诉过家人和朋友,我有另一个世界,在黑暗中找不到光明,就在黑暗中看清黑暗。
如果不是奶奶最后的五年眼疾重患,眼角膜是要给思明的,至于思明接不接受,那是另一回事。
奶奶临终那句话,不是凭空而来,她知道思明一直以来把自己当作健全人,他的信念不仅来自她的经历,更来自他对自己的拯救。思明翻毛了无数本盲文医学书籍,直到再也摸不到自己的指纹。以前,他的指纹是十只螺,算命先生说十螺命丑。怎么丑?算命先生不说,只说是书上这样说的。
奶奶走了,樊思明很奇怪自己变得一身轻松,全身长起了羽毛似的,这使他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2
立夏那天下午,樊思明的第四家按摩治疗分店陈经理打来电话,说一位客人点名要樊思明来按摩。第四分店新开在远离市区的滨海旅游区,陈经理是一个中年妇女,小儿麻痹症患者,是樊思明手把手带出来的高徒之一。
她什么问题?
一个乳房有增生囊肿。
樊思明沉吟片刻,说那我跑一趟吧。
这两年,樊思明沉浸于书房和实验室,很少打理利润越来越可观的分店们。他正取得一些令他窃喜的成果,多年来他给自己的眼部神经和穴位针灸、按摩,已从两眼一抹黑到现在一丝感光,就像一台老式照相机,从镜头前的黑幕到机腔里面放下感光底片。樊思明坚信自己不久就能冲洗出一个光明世界来。
滨海旅游区的分店就开在大海对面。这天退潮,樊思明细听潮声,知道海水已退身很远,但他眼前感光地“看到”退潮后,海滩上留下一枚玉脂贝。好像在樊思明的黑房里,定格了的底片,让他冲洗显影。
他“看到”了她的轮廓。她说的一句你好,像是借大海的嘴,潮声一样问候按摩师。
贝壳是大海的小嘴巴。
她明显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想不到按摩师这样年轻英俊,身材修长潇洒却饱含忧郁。她心想,可惜了。
她自报了姓氏。
樊思明没有摘下墨镜,说,请坐。
你怎么知道我还站着?
樊思明不想接她的话茬儿,逗她开心,尽管这可能会调顺她的内分泌。
樊思明例行公事地问,你,什么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你才有问题!她突然气汹汹地嚷道。
樊思明愣了一愣,搁在双膝的双手回应地暗笑了一笑。他听到自己的指关节发出笑声。他向她倾了倾上身,她窘困地手抚胸口说,我是这个有点……
樊思明不禁皱了皱眉头,你左乳出现硬块,按摩治疗一个月无效,要求全额退款?
她看见他神经质地搓了搓双手。
她说,或者,你能妙手回春。
好吧,你请——
他指了指侧边的更衣室。
她愣了一下,脱口而出,樊医生,你看不见的……
樊思明怔了一怔,他不是告诉过她,自己感觉得到吗?他背过身去坐回自己的办公椅,听到她窸窸窣窣换上按摩服。
对不起,你先起来。
还坐在办公椅里的樊思明“看见”她躺上按摩治疗床,提醒她。
我们还不能开始吗?她坐了起来。
是的,我要先了解你的病情。
陈经理不是告诉你了吗?
但我要了解你的病灶,她没告诉我这个。
我没有告诉过她,也不准备告诉你。
樊思明说你最好配合治疗。
她不快地抚着胸口说,我这儿有硬块。
心中块垒。他喃喃自语。
是胸。
心胸。他进一步肯定。望着她说,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这是我的私生活。
如果是由此引起的话——
她默不作声。
他说你现在还可以要求全额退款。
樊医生,我真的很痛苦。
心疼……
是的。她美丽的面容闻声枯萎成一朵死珊瑚。
海风在窗外温柔地哨过。
我跑遍公立大医院了,他们诊断是良性肿瘤,我第一时间拒绝手术,第一时间想到你的按摩治疗。他们把你传得可神了……
谢谢你信任,他接住说。
但你的那些规范科学按摩治疗套餐,一个月了还是不见效。
她见樊思明一动不动木然的表情,垂下柳眉问,真的非说不可吗?
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按摩师扬起脸庞。
但我有一个条件。
我不会侵犯你的隐私。按摩师说,我看不见,但眼中只有病人。
好的。她说,樊医生,我们能一边治疗一边说吗?
胸中块垒形成很漫长了吗?
当然,那是一个心路历程……
这个我不感兴趣。按摩师有点烦,这个聪明的女人。
我真的不知打哪说起,要不,你问我答?
按摩师点点头,问,发现硬块的时间?
四个多月前。
是什么形成的?
这个我正要问你呢!
硬块开始有几个?现在有没有增加?
你摸。
按摩师无动于衷。她兀地把这个主动性的邀请弹出,反倒有些困窘,两手相绞,她想自己如此放肆,是欺负他这个残疾人了。
她下床从沙发上拿过挎包来,说樊医生,我把我的病历记录念给你听吧,你就听诊我,行不?
她想中医的“望问闻听切”,莫非就是如此的“听”?望是望不到了,先问和闻,后听和切吧。
樊思明仔细听完了她的病历,问还有片吗?
你——她欲言又止。
我能听得见。按摩师说,你对着灯光,把看到的告诉我。
她就举起那张报纸大小的X光片,看着片子中的乳房,回答他的问题。她想,可惜X光片没有发明盲文图像的。
结合你对片子的描述和病历的诊断,你现在的确可以放心的是没有患上乳腺癌,我只是说现在。
是的,那些大医院的主治医师也告诉我这个,但有可能病变……
一切皆有可能。
樊医生,我服了很多药物都没效果,他们告诉我试试中医按摩疗法。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的胸中块垒是不是增多和增大了。
她心一沉。
你躺下。
她上床躺下。
樊思明在身后的热水龙头下冲洗双手,擦干,在烘热机下烘热,像手术医生一样,把双手升到胸前。
她解开胸前的纽扣,一对硕大的乳房挺胸而出。她红着脸提醒说,左胸。说着,双手护在双乳前,准备腾出手来引导他。
按摩师准确地将右手按在她左乳房上。
她有点紧张,乳房告诉她,有陌生人从你打开的房门进来了。
请你放松。樊思明让她心宽,说不然会变成僵尸的。
她扑哧声一笑,就温柔了。
他的五指环绕在她的乳峰下,按向她的膻中穴、乳根穴和太冲穴。
她感到他的手指向自己的房间探索,像海底珊瑚虫爬行。决心选择他按摩治疗,最重要的当然是他的按摩术,但她心里想到的,还有他的看不见给予她的安全感。这当口她发现自己的窗帘也掀得太开了,就收了收拢衣襟,将右乳房遮挡好。还没容她再多想,他就收手上来,又在热水龙头洗起手来,擦干,烘热。她感到有点莫名的郁闷,但随即想,我是病人。
你胸中三团硬块没有增多,但增大了。
啊!真的?怪不得这几晚隐隐作疼,樊医生,那怎么办?
针灸按摩再配以药敷。
他们约好明天开始第一疗程,地点就在此地。
3
在得知她没有装过硅胶、没有使用过丰乳器、没有服用过隆胸药物等之后,樊思明对第一疗程充满信心。
第一疗程的第一天。阴天,浊浪排空,惊涛裂岸,这片海的东头是一个古老的丁字形港口,挤满避风的渔船,渔船桅杆顶的风向标,仿若一尾大鳝肚,能把整个大海的风装进肚里平息。
为了缓解紧张心情,她向他亮出左乳时说,台风在这儿登陆。
不是正面袭击。樊思明侧着身子,依旧是洗手、擦干、烘热。
她看到他拉开一个精美的鳄鱼皮包,一只扁平的不锈钢盒露出来,戴着墨镜的他拈起一支银针。
她失措地左护右乳,右挡左胸,惊问针灸?
针灸。他说,左手在她的右掌中接过大白兔一样蹦跳的左乳,食指和大拇指轻轻搂着,找准按住了大白兔双耳一般的乳腺穴位,右手的银针在她毫不知觉中插进去。他重新拈另一支短银针时,她才惊呼乳前竖立着的银针。他插了三针,针尖在她里面转动,他侧耳倾听。海风隔着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呼进来。
热。三分钟后她说。
他侧身坐回办公椅上,点点头。扎了针后,他为她掩好衣服,只让银针像挺拔的松针种在胸前。
麻。十分钟后她说。
他点头。他没看她一眼,尽管她不怕他看。他看不见,看不见松针随山峰起伏。
辣。十五分钟后她满脸酡红,光洁的额头沁起一层汗珠。
他将一本盲文医学杂志搁上办公桌,站起身来,说这就对了。他没有正面对着她,说,你枕边有毛巾,可以擦汗。
她不敢叫他帮忙。
他给她拔针,开内服和泡浸的药水、敷药的膏药,都是中药和中成药,他说睡前泡浸、按摩,一天早中晚三次。
她穿衣服,动作缓慢。她今天穿的是一条银花白点镂空低领旗袍,她不知道穿给谁看。她挽着披肩长发问,下次什么时候来?
药用完就来。
中草药一共七小包。
用完药她准时再到第四分店。这天风和日丽,樊思明刚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打的从机场直奔海边。她已在候诊室了。她招呼他,他只点了点头,径直上楼,她尾随。
她更衣躺上按摩治疗床时,他还在整理从外地开学术会议带回来的一沓资料。
情况如何?樊思明总是头也不抬地问话。
没见如何,只是晚上失眠得更难熬了。她侧过身来说。
他有点意外地扬了扬浓眉,停止整理,去洗手、擦干、烘热,她捧出左乳,像奉献细软,低眉看着这坨不争气的肉,气鼓鼓的好像在等他来招安消气。樊思明没有碰到过她气嘴般的乳头,她的块垒在乳房里面,他依旧是轻轻按压了几下她的左乳中部,说疼吗?
有点。
他使点劲。
她张嘴就喊疼。
他松手,说疼就好,块垒没有消解。
她着急地说,以前按它没那么疼的。
因为针灸和用药了。樊思明皱了皱眉头说,可以肯定的是,块垒没有继续增大,但也没有消解,你在第一疗程没有积极配合。
她委屈地说,我按时服药、泡浸和敷药了的。
按摩了吗?
我自摩。说完,她也笑了。
樊思明说这不行。
那我还找你们陈经理按摩吧。
不行。樊思明坐回办公椅子里问,你先生呢?
与他何干?她在床上腾地坐起来。
樊思明说,你先躺下。
她躺下,盯着他。他看不见她眼眶里淌出一串泪珠,但他能听到泪珠的碎落,再次提醒她枕边有毛巾。
她用毛巾抹去泪珠,闻到海边太阳的味道,有点咸,但新鲜。她不禁深埋在毛巾里闻下去。
他沉默起来。第一疗程他开给她的中药里,是掺进一些助性粉末的,在稍微增加她体内酮体素和荷尔蒙的同时,让她的血管承载性爱的动力,配以病人本身具有的生理需求,她的胸中块垒没有理由不出现消融瓦解的迹象。
对不起,我答应过边治疗边跟你说的。她说请原谅我的失态,我不知道你扎针后给我的这些药还需要那样的药引。
樊思明皱眉道,这不是很正常的药引吗?
她长叹一声,你不了解这个药引霉潮的世界。
樊思明把一本小巧的盲文会议笔记本打开又悄悄合上,打心眼儿说我略有所闻。
她拨了拨垂至面颊的长发,喑哑地说,这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不说也罢。
她心想,以你不用开眼的神医之术,追本溯源,知道下什么药,也自明了我的病根了。
他真的不愿施以援手?
她想到援手,手?就盯向他的手,发怔的她想得到的就是这双手,按摩师的手,白皙有力,有肉骨感,深蓝色的血管像一条条江河溪流,汇聚手背海洋深处,力拔山兮气盖世,蕴藏着神秘的魔力。她忽然想起,黑暗的世界才跳动海洋之心。她无声地对他说:“他不是千手观音,他顾不过来啊! ”
樊思明有时庆幸自己眼不见为净,否则现在就会看到面前这个风韵怨妇了。但他莫名地有点心疼,长吁口气,平复下来。不能删除的就隐藏起来吧,他在墨镜后阖紧眼睛,让外面冷场。
没别的办法了吗樊医生?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办法是你不愿试才上我这儿来的。
切除左乳房?
樊思明在办公椅里点点头。
不!绝不!
我也是这样想的。樊思明心底里思忖道,握了握拳头。他感觉看到了她的惶恐。他抬起头来问,你们——多久不按摩了?
很久了,很久有多久,我也忘了很久。
樊思明想一双没有爱抚的乳房是易结块垒恶化成乳腺癌的。他想不必这样对她说,她会明白的。她在按摩师的冷场中,咬了咬嘴唇说,就算我找陈经理按摩也是不行的。
是的,你缺少雄性……樊思明突然说,只有你先生能给你……
只有?
樊思明不禁抬起头来,听到她一声冷笑。
他从办公椅里站起身来,拉开米色窗帘。二楼这间按摩治疗室宽敞洁白,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后面是销声的大海,浪花在沙岸上昙花一现,海鸥不时张开翅膀丈量沧海,发出完成海量工作的尖叫。海浪后面是看不出航向的一字形排开的龙头渔船,这些大多是摸螺船,今年花蛤螺在浅海海底堆积如山,老渔民说这证明今年的海势不好。果然是螺多鱼少。预言。妄断。臆测。谶语。生活的海洋也是弱肉强食。
她央求道,樊医生,可以进行第二疗程了吗?
樊思明无言地回转身来,去洗手、擦干、烘热,他仿佛闻到一缕香气,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气体。他镇定地拉开那个精美的鳄鱼皮包,一只扁平的不锈钢盒露出来,戴着墨镜的他拈起一支银针,准确地把她的左乳握满掌心。
还是三针吗?
平躺着的她仰头问。
是的。按摩师捻着闪亮的银针,在她乳房里顺时针捻动,他好像通过银针,触摸到她更深的心室,那是一个本来美丽现在却病变的世界。触摸有时比看见更有力量。一种暗物质的作用力,一个隐蔽的掩体,一股秘而不宣的潜流。他的指力劲道十足,只有他的指端了解他在暗中加速使劲,悄悄转动的速度偷偷加快,银针像时针看不出的缓慢转动,一点点地探索深入,从秒针缩成分针再短成时针。她的乳房丰满挺拔硕大,他仿佛在耐心劝说她的乳房把长长的银针吞进去,排掉潴留的水钠,与主人一起运算这道神秘的消融化解术。
她依旧喊起那三个程序的字眼:热、麻、辣。
一刻钟之后,他拔了针问她感觉如何,她说更热更麻更辣!
你歇一会。他在帮银针消毒时,好像对银针说。
她透明一样平躺在按摩治疗床上,看着他收拾好针灸工具,用一双一抓准的手抓中草药。她皱起柳眉问樊医生,还配那些药给我吗?
第二剂要恶补。他把药送到她面前。
她侧身而卧,盯着他的目光犹如要射穿他的墨镜,说,你最好给我配一副药引。
她接药的双手不是握,而是攥住了他的双手。他要挣脱是能挣脱开的,但他没有想到她的手会瞬间长刺,倒钩的刺,咬入肉里不撒手。她把他的双手按在左胸口上。
樊医生,你能治好我。
他动也不动。
“我不怕死,怕丢了乳房。 ”
她感觉到他的手的脉门在狂跳,血管里的血要破壁。她害怕地捏牢他的手,按在左乳上顺时针抚摸,一波接一波,一轮又一轮,是满月的潮涨,惊涛骇浪。她涨得通红的脸庞告诉自己身体像海边的火烧云,可惜他没看见,但他能感觉得到,他俩已经感觉到左乳越来越大,他的手越来越从屈从到顺从,按摩语言从晦涩到流畅,小河潺潺吟唱,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运动起按摩章法。她将自己的发现耳语给他,见他不语,就赌气地掏出右乳说,不信,你看一下另一个。
我看不见。
她回过神来,悄声地说,你可以用手看。
樊思明的右手轻轻地“看”起她的右乳房,他的指端好像是眼睛,贴得亲近地“看”。她索性把障碍全部清除,苦恼地问,是不是那边有三块肿瘤,所以显得肿大?
是的。樊思明有点气喘。他俩都听出来了。
樊医生,请放松,这样疗效会更好。她反客为主,颤抖地说,紧闭双眼,长长的睫毛像松针在雪中低垂。
按摩师倏地收手,就像他的双手从一盆火炭中抽出来。
他洗手、擦干、烘热。
她盈眶热泪,滴下来就会发出响声。她没有发现他洗手的水是冷水。
隔天来,按时服药。说完,他走出按摩治疗室。打开门时,一匹浪头炸进来。
4
隔天的按摩治疗进展顺利,到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时候,樊思明告诉她肿块瘦身了。
真的吗?她悲喜交集,敞着怀,顾不得羞怯地在床上跪起来,要拥抱她的按摩师。
樊思明按着她的肩头说,但病根还没除掉,后天,我们开始第三疗程。樊思明发现自己按住她肩头的手有点哆嗦。
第三个疗程开始的头天,这个海滨城市刮起夏季第五号热带风暴信号,在她到达按摩治疗室时形成威力强大的台风。一身无袖深蓝色连衣裙的她感到有点冷,怀抱双臂,高跟水晶鞋敲击厚地毯发出橐橐声,一个猫步闪上楼来。
站在二楼窗前的他盯着一辆宝马驶离,他听到了车来去和车门开关的声音。他转身问上楼来的她,要不要冲个热水澡暖和一下?
她说,谢谢。
诊治室后面的居室内含一个浴霸,她淋在热水里还能闻得他身上的本草味道,她有点贪婪地多淋了一阵。
她出来的时候,他说洗的时间长了点,但这个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请你擦干身子才出来。
她慌乱地啊了一声。她是披着浴巾当着他的面擦身子的。她想擦干身子直接套上按摩服,反正他看不见。
樊思明还是一副墨镜,侧身对她。今天没有拉上窗帘,台风把这座城市昼夜颠倒,外面黑云压顶并和骇浪共舞,只有治疗按摩床头有一支高挑的银色落地灯。灯光如伞,仿佛让他俩躲在世外。
他依旧拉开那个精美的鳄鱼皮包,那只扁平的不锈钢盒露了出来。他拈起一支银针。
三支银针在海天泼洒进来的墨香中闪烁,像三尾飓风中飞翔的银鱼,腾跃在沙丘般的胸乳上。他正想像以前一样扎了针离开,她扣住他的腕,犹豫着央求,我们能说说话吗?
他回过头来。
她冷不丁儿努着嘴唇贴上他的手心,好像要用吻来回报按摩师。但他们之间,隔着三尾正在风浪中飞翔的银鱼。唇印变成的花瓣,绽放在他的手心,他会再让花瓣落到她乳房上。
他们就这样用手说话。手只有在这当口,在南方的海边,有台风的日子,像鸟,是海鸥,飞在水里,像鱼,两尾带电的蒲鱼,游在空气中。
按摩师为她拔银针时晚了一会,他说不会影响疗效。拔了针,她能贴得他更近了。她的按摩服已滑落臀部,她痉挛着说更热更麻更辣了。
台风是从下半晚过去的。每年这座滨海城市都要遭受来自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飓风袭击,但这座城市躲在一个海湾里,飓风来到这儿变得温和多了,与这座滨城擦肩而过,荡涤酷暑。
想看看我吗?她说,他们都说我是美人鱼。
她的按摩师却发出可气的鼾声。
5
第三疗程是最后一个决定性的疗程,特别漫长,漫长到好像为了拖延出院时间。她把本应办理治愈手续的手握紧他的手,熨上自己的左胸,说你帮我消除了心中块垒,却把另一块垒留在了里面。
他说,我是医生。
我永远是你的病人。
病人永远可以选择更高明的医生,医生只能等来病人。
你想溜?她淘气地笑着,把他的手啮得生疼。
他忍着,药引做不了菜。
她说,药引肯定不是我的菜,但有时是毒药,也是解药。
我成了你的病人?他冷冷地反问。
这回我是医生,你听我的。她不容争辩。
他仍是动也不动地皱紧眉川。
为什么是吧?她帮他问出来,悄声说,我整个人,都是你的药引。
他的这个“药引”,把他这个按摩师引导得越来越远,他和她外出时间越来越多,她说是“出诊”。他们郊游、垂钓、烧烤、爬山、游泳,甚至还短途去了另一城。他俩戴着情侣墨镜,她顺理成章地与他十指相扣,说我愿意做你的导盲犬。
思明每一次疗程完后都说你痊愈了,放心离开你的按摩师吧。
她微笑地回一句,我怕复发,我喜欢你的奶奶。
思明一愣,看来,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好的医生。她是真的喜欢他奶奶。但思明还没等到她的复发,这天就突然遇见了这个送她上门按摩治疗的男人。
那魁梧的男人看见戴墨镜的按摩师,一点也不意外,照旧抽烟,只是微微一笑。他看见按摩师愣了一愣。
这天是思明与她相约按摩的日子,思明有事来迟了一步。她刚上楼。思明仿佛还看见她的白玉兰裙摆飘逸在旋转楼梯口。
来一支。魁梧的男人对按摩师说。
思明不抽烟的,但接过了一支。
谢谢你,按摩师。魁梧的男人掏出打火机凑过来,给按摩师打着火。每次我没空送她来,就让司机送,真的谢谢你,果然是首席按摩师,一流,绝活,技术活啊,手到病除。医者仁心,救了她和我们全家。
思明一笑,谢谢,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不了,我没这个能耐。魁梧的男人自嘲地撇了撇大嘴巴。
思明手指有点颤抖,举起烟又垂下。
海风从他俩中间穿过。
魁梧的男人看在眼里,倚着宝马的身子,喷出一口浓烟,眯起双眼皮的大眼睛,突然咳了一声,说按摩师,我还要额外谢你,你使我决定了一项投资。嗯,那就是仿真人,比充气娃娃更智能,我刚签了一批最新代的宝贝,按摩师你猜怎么着?哈哈,它们会人脸识别。
按摩师的双手被抽了筋似的颓下来,香烟落进草地里。
她倚在二楼的窗口,俯视这两个男人,心想他看得见以后,手就不能集中了,可惜了一个按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