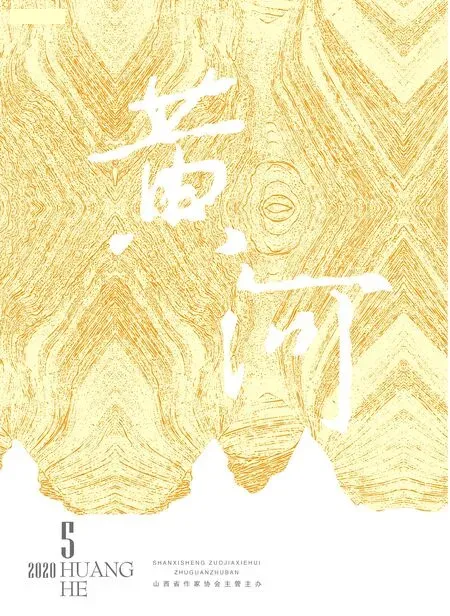这一门人
毕星星
关于门
乡村人家聚族而居,一个村子大多就是一个家族。年代久了,难免有杂姓人家迁居进来,也有杂姓后来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村的主要姓氏。一般来说,一个村子的人口主要还是老早占据这个地方休养生息那一家姓氏的多村子的大姓叫主姓。再多了,就是杂姓。像我们高头村,毕姓人家占多数。史家说先祖是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早年封在此地,后世子子孙孙就都姓毕。毕姓是个小姓,但在我们老家县份,足可以排到前十。一个古老的姓氏,在它的源地,总归还是有粗壮的根脉。
村里除了说这一族人,乡亲们更多说这一门人。门这个叫法,比家庭大,比宗族小,特指家族某一支。一门的大小远近,也不甚确定,可大可小,可远可近。有时候专指血脉较近的本家,有时候也就宽泛一些,追溯得远了,旁系或者较远的旁系也能包括进来,说这一门。反正都是一个街巷的同姓血亲,分得那么清楚也没必要。
我的家族往上溯,我只能说出高祖的名字。巷里说起我们这一门人,一般说是曾祖一辈,我的曾祖毕昌河,宗族一共有兄弟十人。
经历分家析产,一族几家分为十个门户。
我们家族的辈分排列,我知道的五辈,按照彦、士、昌、庭、迺排列,分别是天祖、高祖、曾祖、祖父、父辈,这一门人,昌字辈的,我的曾祖一辈,大小曾祖一共十人。
我家长门,辈辈长门。父亲辈分小,在村庄像个人样的都是他的长辈,有些就是细碎的娃娃。巷子里没人叫他叔爷什么的,大人小孩都叫他“老拖”。拖是方言,老拖就是老大的意思。也有叫他“大哥”的,那是比他辈分高年纪又小的年轻一代。他就是人家的侄子辈或者孙子辈,人家怎么称呼他?在村里,叫一声大哥就是礼貌。看到三五岁十来岁的娃娃管一个老人叫大哥,别扭吧?这就是乡村辈分排序的力量。
我的这十个曾祖,按排行我得叫二老爷,三老爷等等。村里年轻人,比我大一辈的多,他们要叫二爷,三爷,以此类推到十爷。大部分年轻一辈都这么叫,二爷三爷到十爷,也就成了特指的身份。一说二爷,三爷,村里都知道说的是哪一个。
大爷,方言叫拖牙,二爷,方言叫日牙,三爷四爷等等,就叫三牙四牙,一直到十牙。大爷到十爷,这一门,在村里确是一支可观的人丁,一支不可小看的亲族队伍。
今年9月里我曾回村里去,和同辈的伙伴聊起这十门人家的来龙去脉。
一片菜地,种辣椒,村里都叫秦椒。高头村的秦椒远近闻名,辣椒不是炸辣,香味醇厚,香辣,又不刺激肠胃。色泽鲜红,飘锅,所以,用于羊肉泡馍的大饭锅最好,撒一把,立刻泛起一片红。在锅面上载沉载浮,诱人眼神,你不由得要停下脚步,买主来了。
高头村的辣椒特产,和村里的土质有关。这一片都叫垆土地,和沙土地不同,含胶泥。奇怪的是,也就高头这一块是垆土地,一旦走出高头村地界,就是另一种土质。上天圈住了这样一个小岛,与众不同。
高头村人稠地窄,分地以后,各家各户地块都小,田里庄稼也就成了一绺一绺的,我在永孩的秦椒地一边摘辣椒一边聊。秦椒已经开始成熟,有青青角,也有酱色的,全红了的。一绺地,三行秦椒,摇摇曳曳,田野里飘着青禾的香气。
永孩这一家人在村里很有声望。他爸在村里上一辈人都叫犬娃,小名。民国时代阎锡山整顿村务,犬娃当过编村村长。卸任村长以后,依然热心村里社事。大家信任他,有关村里公益,还是习惯找他。家风影响,永孩在村里也是一个热心家族事务的人物。理清宗族脉络,和永孩说,最合适不过。
日光下,碧绿菜畦里,南瓜很随便地躺着。豆角鼓爆了身子,芫荽正旺,贴着地皮,清香味儿一阵一阵冲过来。
永孩说,这一支,一共十门。
上溯
巷子里都不记得大爷和二爷,他们早去世了,只有“二虐”还在。“虐”是我们当地对祖母的称呼,叫“虐”不太准,后音更接近“窝”。当地人叫转了口,都这样。这个发音,当地其实接近于“娘”,近年也有学者探讨,说这个音其实是“女娲”二字的连拼,运城这个地方,有好多远古的文化遗留,我们邻县就有后土祠,专门拜祭女娲娘娘的地方。也许这个叫法,就是女娲那里来的。
二虐和我家邻居。她没有男丁,我在孩童时,二虐常常抱着我,大一点,二虐就带着我。夏天夜里,我们会铺一领凉席,躺在院子里,二虐会给我念“小星星,亮晶晶”一类歌谣。如果有蝎子嘶嘶嘶窜过,二虐惊恐地抱起我,看着那个高举尾巴的爬虫飞快溜过去,才平静下来。浮云飘过遮了月亮又露出来,二虐会给我念叨一些戏文。她爱看戏,会说很多戏里的故事。二虐最喜欢说一句戏文,“做官不知民受苦”,她还会变着各种乱弹腔调来哼哼这一句词儿。
有那么一个秋夜,少年的我突然来了兴致,看着二虐在旁,就学了一句她的“做官不知民受苦”,二虐却没有呼应我。她止住我,感叹地说,唉,做民不知官艰难哪!
“做官不知民受苦”,“做民不知官艰难”,这是我最早接受的社会学启蒙教育。一个农妇对那时官民关系的通达理解。
二虐只有一个女儿,嫁到邻村。为了养老,女儿的一个女儿,又过继回本村,给一个人家做了女儿,离二虐门户不远。
最后一次看到二虐,是八十年代,她去看女儿回来,满脸苦相,大概得了难看的病,照面也顾不上和我说句话。不久,二虐就去世了。
三爷早夭,没有后人,巷子里也就不咋有人提起。
四爷就住在我家隔壁,和二爷二虐一个院子。民国年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农村两家合住一个院子的很多,哪像现在,村里盖房子都是独门独户独家院。
四爷房子窄小破旧,儿子两口住北房,他只好和四虐挤在伙房里。做饭住人,苇箔泥糊的顶棚烟熏火燎,早已经黑得油亮。一到吃饭揭锅,水汽蒸腾,只能在雾里摸索。柴火灶,炕上睡人,脚地做饭,屋里常是满满当当、乱七八糟。
我打小就记得,四爷的儿子在太原重型机械厂当工人,应该是五十年代出去的。四爷四虐去世以后,他就不怎么回来看,村里和他联系也不多。我调到太原工作以后,过几年曾经把老母亲接来住。老人很寂寞,没人说个话拉拉家常。我就想到了四爷的儿子,他在村里长大,和母亲说一说村里的事情,聊得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邀请他过来。他也说了过来,几次联系,却不见动静。终于等到腊月快除夕了,我再联系,邀请他过年一定全家过来,在我这里吃饺子,我们一门两家热热闹闹在太原过一个团圆年。他那时已经退休,在一家私家厂子里帮工。我们殷切地期望着等待,过了初三,我再联系他,家里人说他初二就去上班了,厂子里没人看门。我终于明白了,他有三个儿子,一大家子人,他想多一点收入,过年也闲不着。于是告诉母亲他来不了,一家人都觉得没滋没味的。
四爷四虐去世早,儿子在太原也不怎么回来,他们的院子早早就空起。一个本家兄弟给看着。偶尔住一下。房子老旧,他也不修,老院子就七扭八歪,渐渐只留下一个空架架。路过的都说,家里没人就是这个样子。
五爷
巷子里也不怎么提起五爷,他的寿数也不算高。不过五爷有后人,传到孙子这一辈,迺鹤,迺荣,都是村里的能人。
人多说三岁看老。迺鹤少时聪明,上书房时,捣蛋不好好学,功课却从来拉不下。书房里的小学生都贪玩,迺鹤就带着他们和先生躲猫猫。先生来了,一个一个装模作样念书,先生一走,立刻掀翻桌椅大闹天宫。小迺鹤敢站上课桌,掏出小鸡鸡朝着先生的站台撒上一泡尿。年轻时候,他也是吃喝浪荡,不像个正经庄稼人。
“七七事变”以后,全面抗战爆发。在山西,阎锡山的晋绥军和中共领导的牺盟会都积极活动组织抗战。牺盟会就在稷王山一带活动,村子里来了宣传队宣传国难,号召抗战。日本人已经开到高头村,见天往峨嵋岭上开炮。父亲本来胆小怕事,这一回也被亡国灭种的威胁激发起来,参加了牺盟会的培训班,回来就在村里土墙上到处贴标语呼吁抗日,一支抗敌演剧队路过村子,他找到长官要送大哥去当小演员。最后还是因为孩子年纪太小没有入队。不过可以看出,在民族危亡时刻,我们一家的抗日热情被激发了。
不几天日本人就进了高头村,他们来村里指认中国兵,不知怎么稀里糊涂地就指到了迺鹤。日本人把他捆住,按在条凳上灌辣椒水。灌满了,站上一个日本兵,肚皮上一踩,那血一样鲜红的辣椒水就从嘴里鼻孔里喷射出来。日本人把他带回羊驮寺据点。
都以为迺鹤这一回小命不保。一年后,他却回来了,一点事没有。听他说,抓走以后,日本人把他关在南杨姚军营,让他当马夫,喂军马。仗着聪明,迺鹤很快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日语,能和日本人对话。由此搭上了日本军队的金翻译,二人混得厮熟。有了这一手,他没怎么受罪。在南杨姚日本人这里,迺鹤大致呆了三年。
1942 年阎锡山军队抓兵,迺鹤被抓。在吉县接受培训期间,加入同志会,成为阎部铁军基干。以后迺鹤主要混迹在阎军,担任过61 军71 师216 团5 连政卫工作员,抗战胜利后,任阎军汾南地方团队二团机炮连特派员。解放初识字人少,当地安排他在临猗县第一高小管理总务,很快就因为贪污公款被判刑,三年监狱坐满,回村当了农民。村里看他有文化,安排他到民校当教员,扫文盲。迺鹤利用这个机会,多次诱奸女学生,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
村里至今都在传说迺鹤诱奸环环的故事。环环是前巷一家的女子,上了民校,很快就被迺鹤闹大肚子。闺女本来已经许了人家,人家一看,立马退婚。这个时候环环肚子越来越大,娘家眼看瞒不住,只好急匆匆给找了个人家出嫁,那头家穷,也顾不了这些。环环出嫁时上马,家家都站到巷里看热闹,这时环环肚子已经很明显地大了。奉子成婚,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环环生下这个孩子,一眼看出就像迺鹤。皮黑,方脸盘,一直到老,高头人都知道那是谁的种。前些年这个儿子都五十岁了,跑一趟客车,高头有一站。每当过站,高头人还会指着后影,议论说,你看那个迺鹤的眉眼!
迺鹤坐了班房,回到村里照样威风不倒。他先后当过大队的计统股长、生产股长。生产大队就是一个村子里的股长,当然不算国家干部,可是在农村实物过手,有实权。大跃进中间迺鹤因为贪污盗窃,懒于劳动被拔了白旗,1959 年以后就只能在三小队当记工员,兼会计。三年困难时期,迺鹤利用这个身份,伙同队长保管,偷盗库房粮油。迺鹤肥头大耳,游手好闲,成天骑个自行车转来转去,号称检查工作,从不下地劳动。
饥荒威胁每一家人,那时上地干活私拿偷拿很普遍,谁家没有饥饿的老人孩子,吃一口是一口。我父亲胆小,不敢动。黑更半夜悄悄摸到菜地,偷拿两苗白菜,白天一家子煮了吃一顿菜汤。不料迺鹤闻着了风,半夜尾随父亲外出,在菜地当场抓住父亲。迺鹤得意洋洋号称人赃俱获,第二天组织全村开大会,责令父亲检讨。每天民兵把在巷口,像这样被迺鹤抓住偷拿的社员太多了。家口等着救急,叼一口也许就是救命。迺鹤如此不仁不义,乡里少见,却是没人敢惹他。那时小队吃食堂,队干权力大得很,谁要是不听话,喊一声,“把他的饭止了! ”“今晌午不能领饭! ”你就得饿着。
迺鹤横行霸道欺压良善,终于激起众怒。“四清”运动之前,社员们已经开始秘密串联,写好帖子按上手印告状。四清运动一开始,查账清理,落实贪污盗窃数额定罪。矛头所向,迺鹤人人喊打。批斗会上,迺鹤多次被架上条凳,蹬翻摔下,跌得鼻青脸肿。
批斗大会群情激昂,挨整的乡亲纷纷撺掇父亲上台,动口也动手。父亲没有说话,背地里他说,总是一家人,算了。
四清运动结束,迺鹤戴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迺鹤戴了帽子,受了管制,在村里,那叫“王八是啥他是啥”,从此没了威风。在乡亲们的冷眼里,迺鹤郁闷气结,活到八十年代初就去世了。也就六十岁。
五爷有两个儿子,迺鹤,迺荣。迺荣在五十年代当过乡长。 1960年前后是高头村的支书。四清以后下台。四清清查,迺荣只有一些多吃多占,在那个年代不算什么。他的下台,无疑和庇护其兄迺鹤有关。
七爷
六爷和我家亲近。不过他死得早,我没有什么印象。
七爷我就记得了。我小的时候,好一些的人家,大门口都有一溜上马圪台。门口砌成一道斜坡,一条一条青石就坡摆上。七爷经常坐在对门的石头圪台上,和人聊天说闲话。他小腿上长着一块牛皮癣,时常要撩起裤管,伸手上下抓挠。巷里人都知道他这个毛病。
七爷是穷家,出了名的穷。他和儿子都靠常年给财主扛活,才能有吃穿。他是典型的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乡村的无产阶级。土改以后,七爷才分了一处住房,全家总算有了个住人的院子。说是院子,也就是村里富户的一处马坊,有平常人家的半个院子大,土墙土屋,窄矮黑暗。灶火是黄泥涂的,出出进进的门也就是土墙一扇柴门,歪歪扭扭斜靠着,能挡住鸡狗。本来么,人家财主原来就是喂牲口的地方。这还算有个窝,天晓得他们一家原来怎么住。
在村里,七爷行侠仗义,好打抱不平。有恶人欺负谁家,七爷会出头说理。有争斗,七爷会主持公道。他不怕事,不怕打架。敢上手,有大规模的械斗,七爷提上家伙就走。村里的恶棍烂人,见七爷都惧怕,让着他。一门之内谁要是仗势欺人,七爷会找上门去,打起来他也不怕。
七爷有两个儿子,庆祥,都祥,都是一把力气的汉子。站在那里顶天立地,七爷的门风就硬气。庆祥更是健壮挺拔,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出门到县城走一走,谁见了都惊讶,这哪里像个庄稼户的孩子。
谁也想不到庆祥这样一个漂亮公子,却和北坡一代的土匪地痞扯到了一起。他家穷得干打干,出门却是好吃喝好赌钱。一把玩跌了,跟上杀人越货,渐渐心狠手辣起来。晋南那年月时不时有八路军游击队出没,各村里中共领导的地下村长,农会也在悄悄活动。两军对垒,激烈残酷。庆祥参加了反共复仇暗杀团,一到夜色降临,这伙匪徒立刻流窜出没,绑架活埋,刀砍斧剁,残忍杀戮那些乡村红色政权的领头人,积极分子。猗氏县东好几处惨案都和庆祥有关。夜色里残忍在进行,村庄连环遭到夜袭,打头的是一个英俊后生,做活儿残酷潇洒。一副漂亮面孔里,暗藏着一副嗜血成性的手段,这是村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也已经注意到了庆祥这只黑手,猗氏县城解放以后,武工队俘获了他们。
庆祥死得很惨。村里有看到的说,处决的时候,一群拿枪带刀的包围了一个圈,你捅一刀,庆祥就倒向另一边。对面再捅一刀,庆祥又倒过来。庆祥倒下,又被提起推过来。翻过几个来回,庆祥浑身成了血窟窿,被扔进庄门头前的一眼枯井里埋了。庆祥撒播的仇恨终于回报了自己,他双手沾满血债,村里也没人敢埋他。这样暴毙,也不好进祖坟,就那么荒野里埋了算了。
庆祥死了,这样一个穷家,都祥也娶不起媳妇,庆祥老婆就和都祥过到了一起。小叔子嫂过在一起,乡下常见。
都祥两口子生了七八个孩子,在村里,数得着的多子多孙户。
都祥爱做农活,在村里有名的能吃苦。担粪,他挑大筐,装满。翻松的地里拉小平车,一步一个深深的脚窝。浇园,熬到半夜,一个一个没精打采,都祥不这样,地头引水过来,回了畦口子,他跑到地块另一头,身子躺在小路上,脚伸到玉茭畦里,水来了,冷水一激,打个愣子醒了,起来接着看水,折腾一夜。第二天,和他一起做夜工的累得七倒八歪,都祥照样上工。到三路里给队里拉石灰,三四十里路,黎明起来,赶到石灰厂装满,拉起小平车一路小跑,随行的天黑了才能到家,都祥还要赶回去下午出工。都祥没有累过,没有垮过,在队里是一个铁人。
农业社实行大寨评工,最高一天十分工,都祥永远是标杆,十分。小伙子也就九分五。谁要是能评上九分九,那就是特别能干了。和都祥只差那么一点点!
都祥实受,都祥苦干,没说的。谁又能想到,都祥的一世英名,到了“四清”给拆穿。
都祥在队里当仓库保管。 “四清”揭发定案,都祥伙同迺鹤等人,开仓偷盗队里粮食,食油,折价260多元。除了队长,就数他偷得多了。
村里有人就说风凉话。我就说哩,大家都饿得前心贴后心,那家伙哪里有那么大的劲头!
多数人还是原谅了他,家里那么多张口等吃饭的,不偷,七大八小吃什么?
“四清”以后,都祥被撤了职,又成了社员。农村小队干部,本来也没有什么,他依旧卖力,依旧苦干。抓革命促生产,每当要论促生产,都祥还是劳模,还是榜样。
一场新的分田分地,让都祥的苦干失去了任何意义。 1980 年代初,全国实行土地承包,土地重新回到各家各户。地是你的,给你自己干。你卖力也罢,偷懒也罢,谁管你,你在自己的土地上卖力,还能给你个什么荣誉?当然,你愿意偷懒,愿意少收点。
在我看来,都祥就是一架劳动机器。民国时代,他给财主当长工,是出了名的好雇工。合作化以后,在集体地里受苦,他从不惜力气。八十年代又分地,我们村地少,都祥名下的地根本不够他操弄,村里有一家跑运输发了家的,愿意把地交给都祥耕种,讲好每年多少地租,都祥于是又租了一份地,春种秋收,交了租金,留下余粮。崭新的时代来了,都祥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身份。
都祥完全不再做活,是在世纪之初。他老了,一点也干不动了。
都祥养了一头牛,每天牵着出去放牛。
农村耕种,家家都知道叫机器来,牛,不是杀了,就是卖了。
高头村,养着农业社留下的最后一头牛。
都祥照样牵着牛出去遛弯。牛也老了。这已经不是为耕田拉车,它是都祥养的宠物。
都祥的牛,一直养到死。
都祥牵着牛,缓慢地从田野走过,夕阳照亮了一身金灿灿的大黄牛。那是七爷这个家,固执地支撑着的一个逐渐黯淡下去的理想。
九爷
八爷九爷是嫡亲弟兄俩。
兄弟两个40 多亩地,一起伙着做,伙着吃。土改了,四十亩地,划成富农。
九爷的儿子叫恩娃,解放以后,恩娃一提这事,就捶胸顿足,仰天长叹,我爸和我爹就是不分家嘛,要是分了家,一家20 亩地,还能划成地主富农?嗨!一副悔青肠子的样子。
一家人分了九爷的老院子,要翻盖房子,拆墙。听说挖出一罐罐银货。这家人当然不说,村里只是传得厉害。事过不久,九爷就疯了。随后,八爷九爷相跟着殁了。
恩娃在村里,当然憋屈得很,做事左右不是,说话也低声下气。他会唱几句戏文,到了野地里,看看没人,才能吼一嗓子。
那一年村里排老戏,一出戏叫《庚娘传》,里面有个不吃劲的角色,老苍头,没有多少戏份。实在找不下人,就把恩娃拉上。农村闹戏,就是庄稼户自家热闹,唱的怎么样不要紧。大家也就找个乐子。可不管怎么说,唱戏登台,也是个出头露脸的机会。乡村剧团的演员,也是村里的公众人物。逢年过节,是乡村的关注中心。
大幕拉开,没有出台,恩娃就在边幕后面唱:
荒乱年众百姓出逃流离——
恩娃的嗓门,苍老粗放,就是冒了。台下友好的哄笑,横嗓子啊。
唱戏,是恩娃少有的露脸机会。
这出戏,庚娘报仇,手刃强徒时有一段唱:
气得人一阵阵黑血往上潮,
杀人的贼子你死期到,
我忙把宝刀抽出鞘,
照贼人的头上砍一刀。
恩娃没有多少戏份,别人唱,他也跟着学,庚娘这几句,恩娃就唱熟了,有了兴致就来一段。
不久就有人反映,恩娃唱这个,暗藏着自家的心思,是对贫农翻身的刻骨仇恨,是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有人还引用报纸的高调,上纲这是贫下中农和地主阶级谁占领舞台的问题。恩娃一时很尴尬,戏,不能唱了。
好在正月的热闹也过去了,恩娃又回到小队,做他的农活。卸去油彩,洗去铅华,恩娃失望地走下舞台。恩娃给队里赶车,戏文不能唱了,笑话也不敢说,坐在车辕上闷闷不乐。
农家都习惯吃两顿饭。早饭在九十点。也是一天早饭,母亲看着饭还有一会,对我说,你去给到地里拢些草,喂猪。提上那个猪笼筐子。
我家有一个筐子,平时都叫猪笼。说它大,可以装下一头卧着的猪。同样的大筐,一般都是圆的,粗柳条编成,插一个圆木绊。我家的猪笼是长方的,四四方方,筐绊也是竹编,好几绺拼成,编工很是细致。也是庄稼户的家具,可就显得很精致。婚嫁行礼什么的,装一些轻巧的行装,看起来很飘洒。
我挎了猪笼,跑到小队菜地。这一块菜地,我已经看过了,知道长了一片马齿苋。我把猪笼放在路边上,自己一个人进地去拔草。马齿苋好多,一会儿就拔好一堆,我看猪笼差不多能装满了。这个时候,我看到恩娃赶车,从河埝子那边上了路。马车的铁轱辘骨碌碌从地头碾过,我也没有在意。抱了野菜回到地头路边上,才看到,猪笼被碾扁了。一道车辙从猪笼中间碾过,竹编已经碾折了,筐绊也歪歪扭扭倒在一边。一件漂亮的竹筐,成了一个瘸着拐着的残废。
大车只要稍微向外打一下,就能绕过猪笼。停下车,叫我去拿开也行。
正在饭时,四野空荡荡无人,恩娃就是故意的。碾坏一件村里少见的工艺品,他心里大概很有点报复社会的快意。
我抱了猪笼和猪草,哭着回家,给父母说了。一边说,一边忍不住大哭。
父亲很是生气,拉着我,要找恩娃说理。叫他赔,净是欺负小娃!
母亲也气得不轻,父亲拉我要出门,她还是挡住了。
她说,算了吧。你看恩娃,一天就没有个开怀大笑的时候。就是欺负一下小娃,他能开心一下。不要争竞了,算了吧。
恩娃果然开心。下午出门,他见了我,背过脸偷偷地笑。
十爷
十爷最小,和父亲年岁差不多,我就记得多了。
十爷身强力壮,在巷子里强横,不服人,好争胜。翻了脸,敢吵,也敢打。巷子里一般没人惹他。
十爷最瞧不起软蛋,认怂。偏偏父亲从小寡母养大,受欺负,在巷子里,就是个软人,受点气,受就受了,和谁也不竞争。你打我?我不惹你你打我?你骂我?你骂我我又不疼。你吐我一脸唾沫,擦擦一会儿就干了。十爷就最看不起父亲。
十爷和我家隔一家相邻,十爷咋看父亲都不顺眼,整天横挑鼻子竖挑眼,父亲做什么都不对,做什么都怂包。在他看来,父亲这个软蛋,就是族人的耻辱,有事没事就教训父亲一番。他辈分大,父亲也不好说什么。
两家连畔种地,就少不了磕磕绊绊。十爷动不动就起事,站在地头大骂,父亲一声不敢吭气。骂得兴起,他扑过来,动了拳脚。这个时候,七爷不让了。七爷本来就好打抱不平,想不到本家还这么欺负自家人。村里这个时候,只有七爷敢出面为父亲抱屈说话。他跳脚大骂十爷贼坯子你敢动手?打起来,七爷也不是善茬儿。当然,对着七爷,十爷也就不敢动手。
七爷怒气不息,这么长年累月欺负人,多会儿是个完?他拉了父亲,要去找官府说理。当天晚上,他们爷孙套了一驾马车,连夜赶到峨嵋岭根下的七专署去告状。马车在夜里圪圪当当摇晃着,爷孙两人满以为国民政府会给人民做主,谁知道抗战中间,七专署忽摇忽摇,连自己都不知道哪一天就没了,哪里还有心思管什么民间吵闹。
十爷于是更加凶恶。一个月以后,在田间地头,十爷又来寻衅,父亲忍不住争辩几句,十爷架住父亲的一双胳膊,劈头盖脸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他高大强壮,父亲毫无还手之力。
打完了,十爷撂下一句话:这才是捎信儿哩,看我今黑了怎么收拾你!
一个人再软蛋也受不了这个,绵善的父亲终于动了火气。当天晚上,父亲在家里,翻出一杆苦叉,我们那里装载麦捆子专用的,挑起捆好的麦子,装到大车上载回去。一个长长的木把子,顶头安一个铁叉。父亲怒火中烧,他在静静地等待一个人,等待他破门挑衅。如果是那样,一杆钢叉将飞快地射出去,一场血光之灾在小院里迸溅。
父亲平静地给大哥嘱咐后事,家里预感到一场横祸就在眼前,全家都紧张得发抖。
父亲手持钢叉,期待流血,一洗屈辱。
没有。那一个晚上平静地过去。十爷没有呼号侵入。
往后好几年,父亲和大哥一旦托付家事,就是嘱咐大哥报仇。
父亲说,你要记住昌贵这个恶人,欺负了我多少年。你还小,长大了,要替我出了这一口气。
大哥那是也就十六七岁,傻傻地站在一旁,哪里明白父辈痛说不怎么革命的家史。家仇村仇这些东西,在这些革命青年看来,都叫小气。他们关心的是解放天下。
但是这个报仇,还就在不经意中间一步一步走来了。
运城解放,大哥在正在晋南中学读高中,解放军多么需要念书的年轻人,大哥旋即参军,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
打土匪,护送干部,大哥率领一车人,往山窝窝里开。车上就他一个军人,胸前一支冲锋枪。一进大山,枪声四起,人们都吓得蹲下。车里颠簸,人群像装满车的土豆一样撞来撞去。大哥知道自己不能怕,他站在车厢前沿,把着抢,迎风屹立。到了安全地带,一车干部都在夸奖,一个20 岁的小兵,怎么就一点不害怕?大哥后来对我说,咋不害怕?我硬是腿肚子打战!
大哥他们挟胜利之师的威风接管成都,他和他的战友们,经常穿着国民党军队缴获的黄呢子军大衣,在街上,晾晒那一份威风和自豪。
天下甫定,组织上安排大哥进了文化单位当个小领导。大哥执教,教授他的马列主义,中共党史。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大学教授啊,前三十年的大学教授啊,收入不是一般的高。大哥就不断接济家里。
大哥通过邮政给家里汇款。
每当大哥来了汇款,大队的高音喇叭会广播,起孩家的,快到大队取汇款条子,带上章子。带上章子。有时也喊,北庄的老拖,老拖,到大队来,带上章子。人们也知道,父亲是去取钱。
前三十年的农村,日子多么艰难,仰仗着大哥的接济,除了强令吃食堂那几年,我们家没有受过多大苦。二三月青黄不接,全村人都在挨饿,我们也不够吃,就去黑市买高价粮。冬天全是玉米面窝窝头,我们家不吃粗粮。最多也就白面搀和玉米面。平时隔一阵买点猪肉,偶尔也尝一尝点心。在村里,那个年月吃穿不受屈,老拖家,高头村头一份。
十爷家里孩子多,吃喝就艰难。春天了,要来我家借粮。分下小麦不够吃,愿意到我家,二折一,一斤小麦换二斤玉茭。偶尔,也借个三块两块钱零花。来了客人,借一茶缸白面,擀面条。炒菜,借一个调羹匙的油。那时候,不来客人,谁家炒菜舍得放油啊?倒了油,慢慢地走,哆哆嗦嗦端回去。隔几天来还油,一小勺倒进油瓶子,瓶子口儿小,洒到瓶子外沿,流下一道油渍,连忙用食指抹了,收到嘴里吸溜吸溜咂吮干净。那个时候的人家,穷气得不怕人笑话。
不知道父亲遇上这个场面,心里有没有解恨的感觉。这个儿子为他争了气。
十爷对父亲凶狠异常,可是这个十虐不管这个,十爷吼不吼,老人家对我家一直来来往往。她和母亲,更是多年交好,有来有往,亲不见怪。
十爷和我家的冤仇,终于也有化解的时候。
我高中毕业,“文革”了,大学不办了,只好窝在家里,当农民,做庄稼。
在农村,我也到了找对象的时候,十虐这个农妇以非凡的眼光选中了我,她要给我介绍一个姑娘。
十虐的女儿嫁到邻村,女儿有个小姑子,运城师范毕业,教小学。十虐就去提亲。人家嫌我没有工作,架不住十虐苦口婆心,明以大义,十虐以她的阅尽沧桑的人生经历,断定我不会窝在农村。这门亲事就这样说下来了。
我的媳妇儿,就是十虐女儿的小姑子。
一个姑奶奶辈分的,我开始叫人家嫂子。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农村这种娶过来嫁过去的人家,常有。
两家于是成了亲戚。这大概也算乡间的和亲外交,最大的矛盾,只有靠联姻才能化解。
十爷见了我家人,还是不怎么说话,不过脸上没了仇气,僵着的皱纹开始松绽。
村里排戏,演《沙家浜》,一日主演出了事,就让我顶刁德一上场。
十爷不爱看戏,村里唱戏从来不去台子底下。这一天,十爷收拾好站在了台子前头。
看见的人们就指着十爷,悄悄说,那两家好了。
我哪里会演戏,就是个背台词。乡亲们看了都说,不沾弦,不沾弦,好好的一出戏,就是那个刁德一搅坏了。
十爷就说,呃,不能这么说。就没有登过台,头一回么。
旁边立刻有人就撇嘴,看人家,到底是亲戚么。
念书
我们这一门人,在村里评价较高。说聪明了,会说,那一门人,灵醒。说能干了,会说,那一门人,利索。说自信,就说,那一门人,走路都和别人不一样。说的是有心气,精气神儿足。这一门人硬气在哪里?在村庄,有什么特别之处?靠什么,这一门人门户不倒,支撑了一二百年?我多年想来想去,不得要领。
村庄人家院子大,一般留着大车门,进车,偏院喂养牲口。门楣上,一般都有砖雕或者墨写的匾额,这个铭言,写“耕读传家”的居多。说明在庄户人家看来,一农耕,一读书,是农家立家的两大支柱。作务庄稼不用说了,要靠这个养活家人,传衍子孙。读书呢,就是庄稼人的更高追求了,活得体面,活得明白。我们这一门人都教导孩子上学。祖父民初考进北京国立法政大学,是民国时代第一代大学生。往后传,民国时代都读过私塾。迺鹤读过六年私塾,解放初参加工作,简历填写的初中。那时的文盲很多,小学毕业就很了不起,中学生是大宝贝。冷面杀手庆祥,劳力苦干的都祥,都进过私塾。我父亲打小起,读过三年私塾。到了民国后期,我家大哥读到晋南高中,在方圆,那是创了学历新高。后人必须念书,这是这一门人恪守的家规。
我小的时候去迺鹤家,常见他躺在一架躺椅上读书。就那种葛优躺,一颠一颠的,优哉游哉。庄户人家,读书,只能是一种雅好。五十年代,村庄还能容忍。迺鹤身边,经常放置着《古文观止》一类古典,也有新文明小说,比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他喜欢看这些谴责小说。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号,叫“旭昭”。迺鹤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过手捧一卷书,立马把他和一般的庄稼人区别开来。
解放初的乡村,文盲很多,读书人很少。读书才能了解外边的世界,读书才能具备管理众人的能力。列宁也说,一个文盲不可能带领大家建设社会主义。乡村干部,还是要从识字人中间挑选。高头村从土改到合作化,人民公社,村干部还是挑选识字人。
劳动养活自己,读书提高自己,在乡村也是这样。读书才能实现向社会高层流动,即便困在乡村,也会跻身于乡村权力的顶层。我们这一门人,迺鹤迺荣都祥等人,多年担任村干部,在乡村地位都比较高。他们发挥了领头作用,这个家族,自然分享了他们政治地位的优越感。至于大哥由此进入军队文官系统,成为新政权标举的学术专家,也是时所必然。
究竟是什么维持着一个家族的百年兴衰?除了强大的传统力量,乡村世界也自有一套朴素的民间道义和乡村伦理,维持着乡村社会生生不息平稳运行。民间的善良,正直,公平,美好的原则恒久不变。比方说勤劳,节俭,亲近大地,赞美劳动,讨厌懒惰讨厌贪心讨厌奸诈;比方乐于助人,悲悯情怀,反对残害,反对流血,反对损人利己等等。家族相处求和能忍,斗则两伤。庆祥的残忍,落了报应。迺鹤损公肥私,受到惩戒。都祥劳作不止受人尊敬,偷盗公粮同样为人不齿。至于我家和十爷两家,纠纷打斗终于握手言和,也是乡村土地绵延不绝的天道人心,冤仇宜解不宜结。
乡村的纷争乃至家族内斗,更多与个人德行有关,按照阶级阶层的解释未免牵强。贫穷并不天然生长美德,邪恶也不见得都和富裕有关。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变迁,善恶正邪时代而表现不同,人心的差异和对立并没有多大改变。
迺鹤迺荣都是中农,他们多年担任村干部,是乡村红色政权领头人。庆祥都祥贫农,庆祥参加暗杀团血手残杀八路军村干部。我家中农,大哥却是为数不多的参军解放大西南的战士,我们村里唯一的离休高干。五爷和我家都是中农,迺鹤下手狠整父亲,凶狠又下流,并不因为同一个阶级而手软,给迺鹤带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更像是贴一个标签,贪污偷盗这种刑事犯罪,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容忍,地主并非都是红头发绿眼睛,恩娃的小耍弄,可恶又可怜。
几个后人
庆祥的儿子叫养孩,养孩青少年时期,在村里是出了名的顽劣。
少年上小学,养孩爬墙上房,掏鸟窝,挑马蜂,偷到地里摘瓜打枣,掏空西瓜瓤子拉屎,村里家家说起来挺头疼,又没有办法。养孩逃学,跑到娘娘庙打翻神像,搬了八百罗汉的小泥塑到课堂上摆成一个队列。老子暴毙,毕竟是一个没人管教的孩子,能说什么。
青年时代的养孩,更是没人敢惹。他身板高大,筋骨强壮,是村里有名的大力气。在村里一伙年轻人打赌,经常比赛扛车辕,扛石头,养孩没人能敌。看戏到戏台子底下打架,在巷子里大凡有个争执,就骂就打,整个一个煞神,谁敢惹他。
养孩40岁以后,可像是变了个人。人到中年,懂事多了。他带头在村里做善事,孝敬老人,帮扶贫困。地里活做不动了,养孩会帮你。屋里需要提水扛粮食,养孩胳膊夹了就走,有的是力气。村里的公益事业,比方修路呀,出勤杂工呀,养孩不含糊。红白喜事,养孩带头操持。办得多了,养孩成了公认的执事社首,谁家的孩子不孝顺,养孩会上门做工作,劝说老人,也督促小辈不要越外。养孩变得这样通情达理,村子里觉得惊诧莫名。感叹一番,又只有归结为天道难违。
养孩这样出众,村里就选他当了队长。
养孩当队长那几年,地已经分了,劳动不用组织了,收入也是各家管各家。队长的职责,主要就是一些公共摊派啦,调解纠纷啦,家庭矛盾啦,养孩和气耐心,说合周旋,倒像个碎嘴婆娘。
养孩中年以后最大的一个心愿,是要给死去的父亲找一个女人。
山西这边有一个民间习俗,夫妻死后合葬,男人死后若是单身,要找一个单身女人合葬。其实配冥婚这种习俗好像其他地方也有,不奇怪。按说养孩父母双全。可是庆祥死后,母亲跟了二爸,将来要和都祥合葬,庆祥肯定要落单。作为儿子,养孩不忍。
养孩按照习俗,在这一带为父亲找寻单身亡故的女人。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人们同情养孩的孝心,不再计较庆祥的革命反革命。总归是他爸,孤魂野鬼,怪可怜的。
40 多年过去, 庆祥的遗骨早已不见踪影,原址就在庄门前,具体地点谁能确指呢。
养孩说,找不到,就在原来那一片地块,铲一锹土,埋了算了。
这个迁坟,没有骨殖,更像是一个仪式。
养孩先后谈说过几个,有嫌庆祥年纪大了,养孩就再三解释,人死了变鬼就不长了,鬼还有年纪吗?死时多大,永远多大。也有的女人的孩子不满意,嫌弃庆祥挨刀暴毙,命中犯凶,总归不太顺利。
养孩总以为此事可以从长计议,不料10多年过后,商品经济大潮,任什么都涨价,价格飙升,一副女人尸骨要三万五万,一直到十万八万,这简直就是买卖婚姻,比人间要彩礼厉害多了。好在生产队墓地不收费,不然的话,简直比找对象再婚还厉害。
这个价格,严重挫伤了养孩的积极性,此事也就暂且放下。
养孩也老了,不能下地了。运城有家公司,找他给人家看门,活儿不重,每月能有一份收入,他就去了。
时间不长,养孩煤气中毒,大脑受了损害,一阵清楚一阵糊涂。养孩,就成了一个废人。
几年以后,养孩病死了。
养孩的晚年,村人都说好。和睦邻里,孝敬老人,尤其是还惦记着给死去的父亲合婚。养孩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哪怕那人是一个恶魔。
乡间总有一些东西,不为社会变迁所动,那就是亘古不变的人伦。
走进新时期以后,十爷一家发家致富起步较早。
十爷一家,长久为穷困折磨,有一年春节贴对联,十爷的儿子发狠,贴上“挖掉穷根栽富根”一联,足见心有郁结。“文革”甫一结束,他家就开始思谋开放搞活。十爷的儿子和长孙承包了一辆车跑运输,给一个工地拉水,一天挣40块钱。那时的40元,是普通干部一月的工资。几年功夫家财巨万,1980 年代初发家光荣,万元户光荣,十爷属于第一批光荣起来的人家。我们村里第一栋两层小楼,是十爷家的小院。养汽车,住小楼,十爷是村里率先富起来的人家。
家境小康,十爷的孙辈先后进大学学医,分配到省城人民医院当医生。十爷的儿子也已经老态龙钟,近年搬到了省城,跟着孩子养老。
我家大哥先期落户成都,我的两个孩子也先后落到北京上海,早年的长门人去屋空,只留下孤零零一座老宅盘踞在巷口,顽强地告诉你,这一家人后人依然一路逶迤,老根苍劲虬曲。
四爷的儿子前些年回了一趟家,把他的院子转让给看门的本家侄子。随后不久,他就在太原去世。
这三家原来都在巷底,挨门挨户,眼看都已经是人去屋空。今年清明,十爷的孙子回去上老坟,我也回去祭祖,我们在巷子里遇上,同在省城见一面也很难,在先人坟地见着,感叹一番,心里不是味儿。我们和村里就这样维持一种联系,不绝如缕,如悬一丝。回头再看四爷的家,那就算是从高头村的土地上完全抹去了。
养孩死了以后,村民重新选举,养孩的弟弟养增当队长,这时叫居民组长了。
我们这一门人,在村里依然算个望族。不过这些年,家族家门这回事已经不再有人提起。
这一族人的辈分,只排到“迺”字,后人有了孩子,起名字再也不排辈分。在省城曾经有一次聚会,一席人谁为尊长,谁排在后,辈分已经不是排序的依据。大家嬉笑一番,推一个年长的在上就罢了。
起名字不止是没了家族辈分的观念,对于名字的严正堂皇,也不讲究了。过去孩童有乳名,入学要有学名,成人之后有大名,做官要有官名。我的父亲一介农民,按照辈分起了正规名字,请教书先生起了表字,他自己又循名思义起了大号。我们家,有堂号。父亲一生以字行世,多年来我们误以字为名,竟也不知他的名字。至于起一个乳名稀里糊涂叫到老,周围更比比皆是。认真落实张狗娃书记的指示,接受李丑子县长的领导,这样的名字不仅有损自家尊严,也是对家族的亵渎轻慢。
家门家道在衰落,不可遏止。
在社会这个大的共同体里,人们很少想到家族家门这个小单元。
人们越来越以个人的身份融入社会,家门,一点一点黯淡下去。
我们一族的老家谱,修自晚清,追溯到明代。由家谱得知“世居猗郡高头村”,民国时代宗族活动多,家谱不时拿出来翻检,再后来,宗族活动受到打击,家庙渐渐废弃塌毁,家谱也不知所终。多年以前,不肖子孙竟然将它卖给了来村里收废纸的,也是命不该绝,有新的后人又收买回来。由此纸上一脉不绝如缕。数年以前,我曾动议重修家谱,响应者寥寥。农村日渐荒凉,年轻力壮的外出打工,留守的栽种果树,挣钱,盖房子,娶媳妇,过不好的要过好,过好了的要攀比。上几辈先人手里的事情,谁还在乎记录下来呢?
在村里,翻检前三代的事情,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家族的历史一片混沌,一家一门的事情呢,听起来更加迷惑。
天道轮回,万物有生复灭。恩娃的隔阂,迺鹤的仇隙,七爷的侠义,庆祥的打杀,都祥的劳苦,十爷的凶悍,在时光里一天一天化于无形。
劳动,创造,生活,奋斗,生存,挣扎,恩与仇,善与恶,合作计较……这一门人形形色色,林林总总,日渐模糊。大地上的事情,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