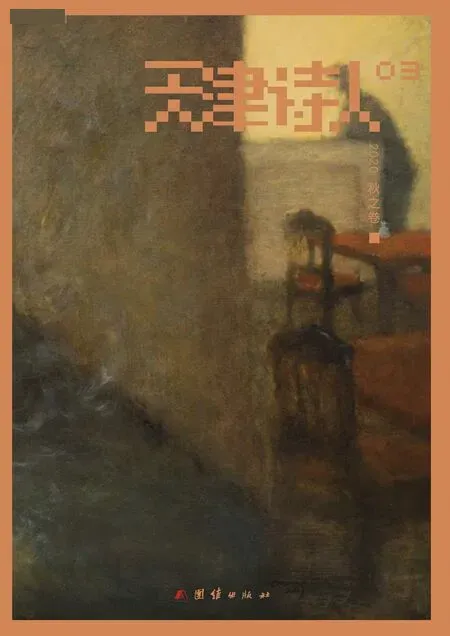诗缘蒙古国
北塔
我有幸两度去蒙古国参加世界诗人大会,期间颇有些特殊的经历、有趣的花絮、影响我文学生涯的要事。现在扼要回顾一下。
一.2006年,第一次参加世界诗人大会结识杨允达先生和蒙都友先生
蒙古国是中国的邻国,曾经还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从少年时代起,就从内心里喜欢大漠孤烟、草原骏马,也间接知道蒙古国比内蒙古保留了更多更原汁原味的蒙古文化、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原始文化、萨满教文化,一直想去瞧一瞧,但始终没有机会。
直到2006年,蒙古国中央政府文化部等机构举办第26届世界诗人大会。
时任世诗会秘书长(现任会长)杨允达先生给我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了邀请函。我向单位领导请示,领导因为不了解世诗会,有点拿不准是否批准我参加境外组织举办的会议。诗歌向来被认为是意识形态中最敏感最有潜在危险的领域。我灵机一动,把八路军出身的老党员诗人雁翼先生搬出来,他们才放心放行。
我的本家、黑龙江诗人徐宝山先生来京,他酷爱诗歌和旅游,于是相约同去。我提议,我们俩去的时候坐国际列车,从北京到莫斯科有一趟列车途径乌兰巴托,一路上可以饱览草原大漠风光。我们还看到了各种各样大团的草、大群的羊,牧民骑的马,还有悠然在水洼边饮水的野马,在空中学飞的雏鹰。这些恐怕在内蒙古的草原上都不容易见到,更别说在北京了。我深有感触,有诗为证。有时我想,假如我不是坐火车去的,就很难看到此物此景,也就可能不会有此诗。因为我的诗歌的发生都必跟我的所见所闻等亲身经验有关。
他们安排我参加了大会的多个重要环节。比如,大会的研讨会。我被安排宣读提前提交给他们的英文论文,是关于诗歌中的时间意识的。这是我诗歌写作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的第一部中英文诗集的名字就叫《正在锈蚀的时针》。大会期间有多场朗诵会,但最重要的是“成吉思汗主题”朗诵会。我之前提交给大会的诗作名为《成吉思汗的额头》,写的是蒙古包,因为蒙古包内的门楣上一般都有成吉思汗画像,就好像这画像是蒙古包的额头。组办方专门印制了一部成吉思汗主题的诗集。一共收入了80多首诗,我的作品也被收入其中。我原来以为他们会把我们的诗翻译为蒙文,但翻开书一看,都是俄文字母。
我直截了当地问蒙都友先生,为何不翻译为蒙文。他说,我看到的不是俄文,而是用俄文字母拼写的新蒙文,没有古蒙文的影子;所以习惯看古蒙文的我会望字母生义。
整整800年前,即1206年,是成吉思汗建立蒙古王国(汗国)的年份。有了蒙古汗国才有后来的蒙古帝国。蒙古国政府于2006年在世界各地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世诗会是在他们本土举办的非常特殊而重要的一 场。
蒙古国政府之所以用诗歌这个媒介、世诗会这个平台组织如此重大的国家级纪念活动。我认为有三个比较内在的原 因。
1,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能歌善舞,许多人是天生的诗人;诗人在他们人口中的比例大于别的民族。游牧民族的一个习性是自由散漫。他们在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如此,到了都市里操办国际会议也是如此。有一位蒙古诗人,穿着蒙古袍,脖子上挂着酒囊,一边聊天读诗一边喝酒。诗人,我认为,就是整个人类中的游牧民族,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是牧民式的,他们的创作思维的根本特点就是游牧式,他们灵感的马总是逐语词的水草而居。这已经为德勒兹等当代许多文艺理论家所津津乐道。从蒙古回来后,我写了篇随笔《当诗人遇上游牧民族》。两者相遇如同兄弟相见,于诗是好事;但于诗事未必灵光,游牧民族和诗人都不是做事的好手,两者“沆瀣一气”,恐怕要坏事。果然,大会期间有几场活动,比原计划晚一两个小时开始竟然是常态。但无论怎么样,游牧民族对诗人是亲切友好的,对诗事是热情支持的。
2,蒙古民族还保留着原始宗教信仰。而诗歌是巫术,诗人是巫师。我曾专门写文章,谈诗巫合一话题。在原始社会,或者说在原始宗教被信奉的地方,这是通例。蒙古虽然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宗教在他们国民的生活中依然占有一定分量。蒙古的宗教主要是喇嘛教和萨满教(史书上也称作“珊蛮教”)。萨满教是原始崇拜。在成吉思汗时期,这是他们全民族的信仰。比如,元太祖铁木真出身于蒙古贵族,信奉的是萨满教。他身边有大萨满照顾族人的精神生活,相当于“国师”,被称为“通天巫”(或称“阔阔楚”)。从世祖忽必烈开始,采取宗教多元化政策,奉藏传佛教八思巴、道教真人丘处机为国师;从此,萨满教与外来新教(主要是佛教)就有了尖锐的斗争,其结果是:八思巴向忽必烈及其王后、王子等多人灌顶,佛教取代了萨满教在宫廷里的地位。但佛教的影响仅限于上层统治阶级,中下层大多数信奉的仍然是萨满教。目前,蒙古族信仰萨满教的人虽然已经不多,但在社会各个层面都还有认同的。萨满教中的神职人员是巫师。有一位巫师还参加了我们的诗会,还在深夜的戈壁滩上给我们做了一场特别的法事。此人身材非常魁梧,把做法事的错综复杂的行头全部穿戴整齐之后,显得更加伟岸,真乃“神汉”也。我意料之中的是:此人是诗人。让我惊奇的是:此人的英语相当好,能说会写。他时常代表蒙古宗教人士到国外参加交流。他还送了我一本他自己的薄薄的英文诗集呢。正是萨满教的遗风让蒙古人的心灵诗意浓郁。我根据那次法事中的亲身感受,写了一首诗,即《子夜萨满》。
3,蒙古族的领袖都被认为是诗人,或者至少是具有诗人的气质。大会组委会编的关于成吉思汗主题的诗集中,打头的是成吉思汗的一段讲话。原来他们从历史书上摘录一段成吉思汗的誓师演讲,当做了诗歌。我同意他们的这一做法。想象当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东征西讨,他的阵前演说必定特别激情昂扬、鼓舞士气、深入人心,语言也相当讲究,比如用排比句,很有气势和节奏感。这些不就是诗歌的特征吗?这样的话语真正起到了极大的“诗可以群”的功能。只不过,成吉思汗的诗歌纯然是口头的,由别人记录下来的。但是,口头诗也是诗啊,《诗经》里的大部分诗都是口头的呢。再说,人家蒙古族的很多诗歌就是口耳相传的,不是一定要先写下来,相互传阅,再拿去进行所谓的朗诵。直到今天可能还是如此。因此,在蒙古族人的心目中,成吉思汗是一位诗人。
2006年时的总统恩赫巴亚尔先生在从政前是诗人、翻译家,曾在苏联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文学院和英国利兹大学(Leeds)修学,曾长期在蒙古作家协会翻译局工作,翻译了许多文学作品。蒙都友先生是他的挚友。在他的支持下,蒙都友牵头于2005年成立了蒙古诗歌文化院并出任院长,可以看作是为2006年的大会做组织准备。蒙都友领衔操办第26届大会,显然也是恩赫巴亚尔大力支持的结果。恩赫巴亚尔对诗歌的支持不是做官样文章,而是出于内心的喜爱甚至尊重。比如,他不仅全程参加了大会开幕式,而且在开幕式当天还请所有与会嘉宾参加由他主持的晚宴(相当于国宴)。
蒙古这次诗会对我个人的诗歌生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之前我跟世诗会的关系是间接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直接参加。感觉非常丰富新鲜美好。主办方竭力安排当地最有特色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最精彩的景观展现给大家。比如,蒙古国家乐团特地在国家剧院举办了一场以马头琴为主的音乐会。正式的大型那达慕已经在8月份举办过了,但是在戈壁滩,当地政府又组织了一场小型那达慕,摔跤、骑马、射箭等基本项目都有,还让我们品尝了老阿妈现场做的各类奶制品。我还借了一匹马,在无边的草原上放肆地骑了一回。我们还专程去1206年时蒙古汗国的首都赫尔哈林考察怀古,那是成吉思汗势力的发祥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是漠北的政治中心。
参会的各国诗人都非常热情友善,尤其是拉美的诗人一路说笑高歌。我一下子交了好多外国诗友,其中有几位后来一直有联系。当然,最最重要的是我结识了我一生的贵人杨允达先生。他是常住法国的著名爱国华侨。他年少时是台湾世诗会创立者之一、著名前辈诗人钟鼎文先生的高足,到2006年已经担任了12年世诗会秘书长。由于时任会长、印度大法官诗人莫汉先生已经年老体弱(我亲眼见他走路都需要人搀扶),会务基本上都由杨老操持,连大会开幕式都由他宣布。由于去蒙古之前,我俩已经通了多封邮件,所以一见如故。我打心眼里敬重他,他对我也比较赏识,把我介绍给他的许多老朋友,让我第一次参会就混了个脸熟,为我以后在世诗会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蒙古诗会结束之后,他来北京看他儿子(当时在英国石油公司驻京办工作),我请他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2008年,他在墨西哥第28届大会上当选会长。我见证了那个辉煌时刻,从此他对我栽培有加、鼓励不断,使得我有机会为世诗会、为中外诗歌交流力尽绵薄。
蒙都友先生是蒙古著名诗人、小说家,非常朴实能干。我很敬重他。他能听懂一些英语,但几乎不会说。大会结束嘉宾返程,他亲自在车场跟大家一一道别,还跟我来了个大大的拥抱。后来,通过他的秘书,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们在世诗会执行委员会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为后来的中蒙诗歌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2017年,我率团参加第37届世诗会并跟蒙都友先生一起操办中蒙诗歌交流会
时隔11年之后,蒙都友先生再度操办世诗会,即第37届。
2006年,我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世诗会;这回,我组织了20多人的代表团。加之人多,由于上次火车旅行时我对浪费时间刻骨铭心,这回我决定整团都飞进飞出。机票并不比车票贵,而时间可以省下一天一夜。
有一个安排让我们受宠若惊、啧啧赞叹。大会的后半场由乌兰巴托转到东戈壁省举行。我们是乘坐火车专列去的。火车是老旧的绿皮车,但里面是普尔曼式的,大部分两人一间,少数四人一间,挺安静、舒适。火车上只有与会的诗人嘉宾和工作人员,没有其他乘客。到东戈壁省首府的火车站之后,我们全体下车,转乘汽车前往戈壁滩。专列就停在那里,要等到第三天我们结束戈壁滩上的活动之后,再乘坐它原路返回乌兰巴托,每人乘坐的车厢来回都相同。
当然,最值得我们称道并铭记的是在我的提前请求下,在蒙都友先生的亲自过问下,2017年8月22日,在蒙古国家图书馆举行了中蒙诗歌交流会。这可能不是史上第一次,但是至今规格最高的一次。出席的蒙方嘉宾有蒙古作协主席、秘书长等,还有一些著名的诗人、学者。双方诗人或朗诵或发言,气氛融洽,秩序井然。担任翻译的是我的老朋友、蒙古国赫赫有名的诗人、翻译家森哈达先生和一位在蒙古国立大学留学的中国女学者。蒙都友先生年老体弱,而且操持大会极为忙碌,非常疲惫,但还是坚持出席并致辞。他说:“中蒙两国为邻国,没有距离。中国著名诗人北塔先生一直努力于中蒙诗歌交流,做了很多事,这次交流会便是他的功劳。中国诗人们来蒙古参会,认识了许多蒙古朋友,希望能够有所收获。从13世纪起蒙古就翻译李白、杜甫的诗歌。我很庆幸中蒙之间的诗歌翻译传统悠久,我们一定要珍惜并继续发扬这个传统。希望在座的蒙古诗人,明年到中国去参加下一届世界诗人大会。另外,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分享大家在戈壁篝火晚会上写的诗。我们打算把大家的诗放到蒙古国媒体上传播”。
我以中国诗歌代表团团长身份致了答谢辞,介绍了代表团的情况,并概括了我多年来阅读蒙古诗歌的主要印象:浓郁而强烈的抒情性、舒缓而高亢的音乐性。我们向蒙古国作协、蒙都友和哈达等人赠送了团礼,包括大唐开元通宝纪念币和陕西著名书法家刘文西先生的书法作品“永恒之火,诗意蒙古”。
按照惯例,在第37届闭幕式上,第38届主办方的代表应该接旗。之前,第38届由中国贵州省、遵义市和绥阳县三级政府申办,大会执委会也集体投票同意。由于这些年我国政府官员出国不容易,贵州主办方委托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代为接旗。我请我们办事处秘书长梅尔女士跟我一起上台承接。然后,我用英文即席发表了几分钟的接办演讲,算是热情洋溢、真诚恳切,所以赚取了各国诗人的热烈掌声。我脸上挂着笑容,内心却感到了压力。这将是在我国首次举办世诗会,万事开头难,在中国举办类似的会议,谈何容易?不过,在梅尔女士的不懈努力下,在贵州各级领导开明开放有魄力的鼎力支持下,几经周折,最终在2018年10月,我们举办了世诗会历史上品质最高的一届大会,与会诗人纷纷翘起大拇指。我感到特别欣慰,就好像一位母亲经过10月怀胎,终于见到健健康康的孩子出世一样。要知道,这是杨老半个世纪的崇高心愿——要在祖国举办一届,我们这些晚辈经过差不多10年的努力,终于帮他老人家完成了这个宏愿,而且完成得近乎完美。老先生也连声赞美!而我始终记得,中国贵州的第38届是从蒙古的第37届闭幕式上开始的,所以感谢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