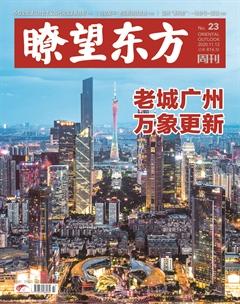世贸枢纽越千年
骆晓昀

广州南沙港码头
2008年5月,《广州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广州建城史的报道《明年才该是广州建城2222周年?》,引起广泛热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公元元年的统计方式,一年之差引得市民、专家各抒己见。
上世纪80年代,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了各色“进口商品”:非洲象牙、红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银盒等等。这些几乎与城同生的“物证”,揭示了广州这座古都,延续了2000多年商脉的起点。
在全世界所有的城市中,唯有广州是保持千年不衰的商业型城市。“一年之差”对于老城历史不过沧海一粟,而365天时光之于这座活力迸发的城市则能创造太多的果实。
秦时古都,帆影点点,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千年商脉,源远流长,广州在全球城市发展史中创造了奇迹。
山水江海间的世界商贸枢纽
从世界版图上看,广州正好位于太平洋西岸生产性地带的枢纽位置,连接中国腹地和东南亚。
以广州为中心画圆,可以发现众多竞争力强大的全球城市都在不远处。往北,北京、上海、首尔、东京;往南,香港、深圳、新加坡、吉隆坡;往西,孟买、迪拜。

广州十三行繁华胜景
作为中国陆地版图与东西方大动脉距离最近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广州自然而然成为东西方交流一大中心。
历史的答案,借由自然之笔挥就。广州的选择,就在山水江海之间。
自古广州就有独到的“地理优势”: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三条大江奔流在崇山峻岭之间,它们在下游交汇,冲积出了珠江三角洲。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设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广州由此正式开始了行政区划建制,被纳入秦中央集权制国家版图。此后,广州始终承担着历代对外通商口岸的重大使命,从未间断。
每年冬季风自北而南从大陆吹向海洋,每年夏季风又自南而北从海洋吹向陆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借助季风的力量,在海面上南来北往,广州成为他们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大航海时代,欧洲的帆船为了中国的茶叶不远万里:从欧洲到达南印度,再从南印度到达东南亚诸岛,最后再等待一年一次的季风从东南亚到达中国大陆,珠江口就是这条路线上最佳避风港。
商船到达珠江内港,可以直接通过水路从海珠一带装卸货,广州城内有完整的货运产业链,能将全国的货物集中到广州码头内,并将国外货物运送到全国。从成本、效益和风险角度看,广州都是大航海时代中国最优选的商业城市。
可以说,广州站立在珠三角甚至是中国南方最佳的地理位置。地缘优势是建城两千多年历史的广州一直保持长久不衰的重要财富密码。
帆影不绝的海上丝绸之路
公元785年的一天,今广州黄埔港附近的南海神庙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祭祀典礼:受唐德宗派遣、即将出使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的宦官杨良瑶登上海船。他带着勇毅神情,剪下一缕头发,祭祀海神,祈求万里波澄。
后来,航行万里的杨良瑶果然一路平安,履行使命后如期返朝。而他从广州启程的远洋航行比郑和下西洋早了近千年。
比杨良瑶远航再早近千年之前,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也曾派出使者,带领一支船队,从当时被称番禺的广州等地出发,沿着民间已开辟的航线,前往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和南亚的印度半岛诸国进行贸易活动。
《晋书》载广州“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梁书》又载“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一个热闹喧哗的贸易大港形象跃然纸上。
彼时的广州,作为南越国曾经的国都,已是南海北岸的主要港口和舶来品集散中心。《史记》称番禺“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
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和交往进一步发展。《晋书》载广州“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齐书》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梁书》又载“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一个热闹喧哗的贸易大港形象跃然紙上。
曾远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东晋高僧法显在其所著《佛国记》中描述了一条著名的“丝路航线”:从印度恒河口出发,至印度洋,驶经马六甲海峡,随后由马六甲海峡进入爪哇海,再由爪哇海进入南海,最后抵达广州。
史料记载,当时这条航线上,来来往往尽是来自中国、波斯、天竺和扶南(中南半岛古国)的船舶。船舶“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法显去天竺取经,就是从这条海路回国的。
唐朝从广州启航的“通海夷道”贯穿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1.4万公里的航线堪称中古世界之最,广州也由此成为唐朝最大的贸易中心与南海交通枢纽之一。
武则天时期,“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天宝九年(公元750),鉴真和尚北归途经广州时,见到“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欧洲人)、赤蛮(阿拉伯人)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美国汉学家谢爱华(E.H.Schafer)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
宋元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航线进一步向纵深扩展,拉丁美洲、欧洲、非洲都曾留下中国船队的足迹,元代同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达到了140多个。远洋航线的扩展大大促进了广州内外港码头的建设。当时,广州海运的外码头有扶胥和屯门两大古港,内码头有光塔和兰湖里,各码头商船如织,热闹非凡。
明代广州已开辟了四通八达的海运航线,实现了广州与世界的海上运输“外循环”以及与内地运输的“内循环”。当时每年举办两次集市贸易——“定期市”,分别于1月和6月,外国船只满载各国特产进港,在划定的市舶区交易,与今天的广交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乾隆年间,清廷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只允许外商在广州一处通商。所有进出口贸易必须经过广州十三行行商,由此产生了许多富可敌国的行商,进一步巩固了广州的繁荣地位。
时光荏苒,历史兴衰,但海运始终不断,广州港口的船影始终不绝。千年商都,在一次次扬帆远航中连接起中国与世界。
优化营商绵延千年
据2019年7月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对外通报称,目前,广州全市共有在住外国人约8.34万人。按国籍分,前十位为韩国、日本、美国、印度、也门、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泰国、英国。“洋人聚集”是广州自古以来的“国际化特色”。
广州有许多老街巷,仙羊街(今海珠中路)、仙邻巷、擢甲里(至今仍在),它们的名字全部来自阿拉伯语音译。“仙羊”意为“送别”,“仙邻”意为“登岸”,“擢甲”意为“小巷”……在一千多年前的大唐盛世,这里是珠江边繁华的码头,也是天下闻名的蕃坊所在地,聚集了十万“老外”。
早在南朝萧梁时期,南海诸国商人就“久停广州,往来求利”。久而久之,广州就聚集了为数众多的外国侨民,形成了“与夷人杂处”,“与海中蕃夷、四方商贾杂居”的国际化特色。
唐朝还诞生了一个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官职,市舶使。广州是唐代唯一设立市舶使的港口城市。当时的市舶使肩负奏报、检查、款待、征税、收市、进奉、立法职责。从职责上看,这就是海关雏形。
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下令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任命潘美、尹崇珂同知广州兼市舶司。彼时,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处于全盛时期。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朝政府本着“理财从政,莫先法令;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创法讲求,以获厚利”的立法思想,颁布了《市舶条例》。这是中国最早的涉外经济立法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成文法规之一。
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蕃商(外商),是当时市舶司官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当有蕃商来华或离开,市舶司官员都要设宴招待,对成绩突出者还授予官职,以示褒奖。
在宋代广州贸易经营中,不单外商,华商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天禧三年(1019)九月,供备库使侍其旭曰:“广州多蕃汉大商……”而宋代广州市舶司就经常发舶往南洋诸国进行贸易活动。
当时每年举办两次集市贸易——“ 定期市”,分别于1 月和6 月,外国船只满载各国特产进港,在划定的市舶区交易,与今天的广交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明朝初年鼓励对外贸易。永乐三年,重新建置了福建﹑广东﹑浙江市舶司,并且较唐宋元三代更趋完善,建造了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驿馆,其中以广州的“怀远驿”为最大,驿舍多达120余间。
从兴建外国商人居住的区域,到设置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再到出台相应法规,在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一步步推动着契约精神产生和规则意识的确立,营商环境不断得到优化,同时也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一口通商的百年机遇
中国历史上有一段“閉关锁国”的时期,却成就了广州的空前繁荣。
明中叶后,倭害日甚严重,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明政府罢除市舶,关闭口岸,停止对外贸易,实行锁国政策。但是这一政策给明政府自身财政和社会经济带来许多问题,于是万历年间,又让广州作为唯一港口进行对外贸易。
清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英国商人多次违反清政府禁例,并有“移市入浙”趋势,企图直接打开中国丝茶产区的市场。乾隆首先下令增加浙海关税收,以抵制外国商船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回广东。增税无果后,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海关,仅留粤海关对外通商。
从此,广州独享85年的对外贸易特权。
一口通商后,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广州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从世界商贸的角度看,一口通商是一种贸易上的束缚,但客观上却造就了明清时期的广州成为中西贸易中心,以及令世人瞩目的广州经济文化辉煌时代。
仅1749到1838年之间,就有5390多艘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美利坚、英国、法兰西、普鲁士、瑞典、智利、墨西哥等的商船到这里来进行贸易。直到1820年,中国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广州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口、国际贸易大港、大都会,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
在广州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建起了一幢幢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的夷馆。商馆朝南而建,由东至西面江排列。华丽的西式建筑上悬挂着各国国旗,俨然世界商务博览会。
1830年,英商在英国下院听证会上表示,广州是世界上通商条件最好的口岸之一。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方便。
当时,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乾隆初年,每年十三行的海外贸易关税收入,除支付军饷、衙役差饷所需之外,尚有盈余50多万两银元上缴朝廷。
1850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直到1875年仍列第七。
十三行行商中,有两个最显赫的家族——潘家和伍家,常以非凡的胆色涉足前人未尝之境地。作为经常参与国际商圈活动的行商,潘振承更是第一个接受外国汇票以作支付手段,足足比汇票在华普遍使用早了五十年。
2001年,《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曾选出在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十三行行商伍秉鉴是中国入选的6人之一。
伍秉鉴还利用手中的大量资金储备在境外进行着前人不敢想象的投资,涉足美国的保险业,买美国证券,可以说代表了广州现代金融业的萌芽。

广州地铁海上丝绸之路风格的站厅
1822年,一场大火烧透了广州十三行街,致四千万两白银化为乌有,史称“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南京条约》结束了十三行一口通商的历史。
盛极一时的十三行虽然衰落,但广州商人的眼光与胆略,以及创造新业态新事物的精神永远留在了城市血脉之中。
千年传承的城市精神
作为唯一一座千年商都,广州的地理环境、地缘优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两千多年来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张力、对外贸易所带来的从容、淡定、开放、包容精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难得的“规则意识”。正是因为把“规则意识”转化为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降低了广州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带来了商业的持续繁荣。
广州市工业与信息化局综合与政策法规处(审批管理处)处长王玉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当千年商都遇到了互联网,遇到了数字经济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广州其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广州精神则是应对挑战的最大原动力。”
什么是广州的城市精神?
一切似乎從2000多年前的开拓者那儿就有了答案的端倪,向海而生的广州人特质鲜明。
因为做了一千年生意,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道路上始终兴致勃勃,他们是务实的、有功利心又有契约精神的;因为开放了一千年,看惯潮起潮落,来的都可以是合作伙伴,任何人任何文化都能在广州得到包容甚至欣赏的目光,甚至广州话里的英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单词音译就有数百个之多;一千年面对南海和印度洋、太平洋的风雨、汹涌波涛,涉鲸波,战恶浪,都是平常事,市场充满风险,稍不留心就可能血本无归,但那不过是另一个风浪,扬起风帆再出发就是。
不管岁月如何变迁,走进历史新方位的广东始终有“走在前列”的底气。摸准时代脉搏,明确湾区定位,携手新老广州人,引领周边城市群,一起发展做大。
广州人爱说“来了的,就是广州人”。而做一个广州人就要奋斗有为,就像那首《广州仔》歌谣里唱的:“这里的风光,你我的依归,常常地为她着迷。光阴似箭,碌碌无为,我哋觉得失礼。”
(实习生吴梓溢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