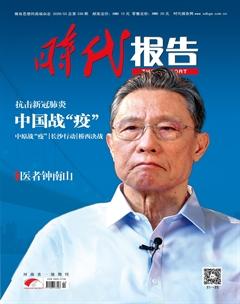王秀仙老人的初心
肖根胜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他值得骄傲的事儿。
王秀仙老人骄傲的是自己的党龄、婚龄与共和国华诞同龄。
1949年3月初,河南省委发出渡江支前工作指示,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到28万人的郏县,有3148名适龄青年应征入伍,超额完成省定任务,受到省军区嘉奖。在总结表彰这次组织青年参军的活动中,19岁的王秀仙入了党。郏县解放之初,土匪活动猖獗,虽然党员身份不能公开,面对党旗举举手,她心里仍像燃了一把火,热乎乎的。
10月1日那天,身为小赵庄村农会主席的父亲让她喊一些妇女到县城“南大坑”(郏县县城的集市、集会场所)参加庆祝大会。庆祝建国,万民欢腾,彩旗猎猎,鼓乐齐鸣。正在看热闹的一个街坊嫂子指了指迎面而来的一位穿着粗布上衣、脸上泛着红光的小伙子。她只看了一眼就羞得低下了头。走出会场后嫂子介绍,小伙子叫黄殿卿,在冢头烟行当相公(会计)。数月后,他俩结为伉俪,成了夫妻。
结婚后第三天的晚上,村里管事儿的杨勋、郭振海、蒋朝娃三个人来到家里。杨勋一本正经地问:“听说你是党员?”
秀仙以为他们是来看新媳妇、闹新房的,没想到说起正经事儿,她没有再隐瞒,就说:“是哩。”
“当时咋说哩?”
她想也没想就说:“没咋说。我大字不识几个,说哩就是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多做好事儿,有工作干到前头。”
……
2019年的12月初,我专程拜访即将走上耆寿殿堂的老党员王秀仙老人。虽然经历了去年一年的疾病折磨,老人仍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言行不失往日的敦厚、朴实、爽朗、风趣。在谈到70年前这段经历时,老人很风趣地笑着说:“那可能就是俺这一代人的‘初心了!”
听到耄耋老人说出“初心”,我等不由放声大笑,由衷地敬佩老人的睿气和明智,为这样一位农村老党员的精神、情怀敬叹、点赞!
殿卿媳妇是个党员
“殿卿媳妇是个党员。”
这消息犹如热油锅里放入水豆腐,噼噼啪啪响后还要冒一阵子热气泡。“党员”在当时的乡村是很新鲜、很令人钦羡的事。黄家娶个新媳妇竟是党员!
知情的人说:她爹是小赵庄的农会主席,也是党员。
也有人说:哪个村都有党员,也没听说过老党员的黄花大闺女是党员……
在当时,农村女党员确实少。现在黄家娶来个党员媳妇,不让人议论不正常。街坊邻居、乡里乡亲都在看这个党员有啥能耐、有哪些与众不同。
先看到的当然是她的言行举止。
她的长相是老天爷送的。眉清目秀,脸颊的酒窝像两朵盛开的菊花。见人不笑不说话,说话又很有分寸。这分寸是娘家父母教的。
秀仙的父亲是位德高望重的小乡绅。土改开始就被选为村农会主席。母亲出身于大家旺族,虽知书不多,却以达礼出名,人缘颇好。平时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秀仙懂事明理,勤俭贤惠。出嫁前,母亲把孝敬公婆、尊敬邻里、慈爱兄妹、多干少说等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礼数嘱咐一遍又一遍。其实,受这种家教的姑娘多了,而到婆家后能执守、能奉行、能在生活中开花结果的并不多,更多的可能还是个人的德性秉性特性使然。
殿卿家住在村西头,门口不远是一眼半个村子人用了几辈子的吃水井。秀仙出入来往路过井边,看见年长一点的婶婶、嫂嫂在井上打水,她就走上井台:“让我来吧。”春寒料峭,井台结冰,她帮上年纪的把水桶提到井台下,送到家门口。刚过门的新媳妇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把水桶送到手上了才问你是谁家的?
农历三月十八,郏县县城古刹大会。秀仙和娘家嫂子一起赶会回来给公公婆婆买了两个锅盔。从村西口到家门口有半里路,一个锅盔给了哭着找爹娘的小男孩,另一个给了急着去县城给女儿看病的隔壁嫂子。
细微之处见人品。大屯村很快又有了说法:殿卿娶了个好媳妇!
秀仙到婆家后参加的第一个会议、领受的第一项任务是推销政府公债。
1949年,中共“三大战役”相继告捷,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为了克服日益严峻的经济困难,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陈云效法在东北发行公债的成功做法,在已经解放的广大区域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本次公债的发行主要对象是城市工商企业、工商户。发行方式是自愿购买,不得强行摊派。郏县28万人基本全是农民,只能把任务分配到各乡村。
中秋节前全县开始发动,秀仙结婚前娘家那个村已基本完成任务,到了婆家以后才知道大屯村的任务一多半没完成。腊月二十三是农村的小年,这天上午农会的几个人在村公所开会,传达区里要求,必须在年前完成任务。
室外寒风刺骨,屋内冷风嗖嗖,几个人的心里咋也热不起来,而且凉得没底。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村民家家戶户都有了土地,不巧的是这年秋季中原地区涝灾严重,郏县城东沿汝河一带近十万亩秋作物颗粒无收。农民越冬过年的生活都不宽裕,这个时候要完成国债发行任务难度可想而知。农会主席杨勋把会议精神讲完,你看我,我瞅你,半天没人吱声。5个人4杆烟袋,满屋子烟雾腾腾,好像要从呛人的旱烟里吸出办法来。杨勋憋不住了,抬头问秀仙:“殿卿家,说说你的意见?”
初来乍到的新媳妇,只有听的份儿、干的份儿,今天的会上她的想法是——“哑巴进庙,多磕头少说话”,没想到主席点住她的将。秀仙就是秀仙,既然主席点名了,也不能把第一腔唱噎住:“我看只有咱几个先带头,然后再分包几户做工作。政府布置的任务,砸锅卖铁也得完成!……”
杨勋忽地抬起头,没想到刚过门的新媳妇说话这么硬气实在,要不是个晚辈女流,他可能当即就把烟袋递过去送她吸几口。
“中!中!别的门没有,就按殿卿家说的办。先自己带头,再亲戚朋友……”
“二十三,祭灶官。”秀仙打算在祭过灶神吃饺子时把买公债的事给公公婆婆说一下。媳妇与姑娘不一样,在娘家父母和俩哥宠着她,基本上是她想要办的事说出来就八九不离十。现在是媳妇了,一切得听公婆的。没有公婆做主支持,她这个头儿不好带。
她意想不到的是饺子没包好,殿卿回来了。临年靠节,自己的丈夫在烟行当会计非常忙,此时突然回来必定有要事。一问才知道,俩人一个事儿:买公债。
殿卿的烟行虽然没有被政府没收,事实上已完全由政府主导。他们这些有职人员有薪俸,买公债首当其冲。他结了婚成了家,这等大事自然要向新媳妇报告。
秀仙一听就笑了。自己夫君知事明理,这等大事没有落人后边,她表态也很实在:“中,冇啥说哩,支持政府买公债,咱不能落后!”
话好说,可是说了后心里不轻松。
殿卿在单位买了公债,家里再带头买公债,咋给公婆说?
船到码头要装货,事到临头没退路。还得说!
公公祭过灶神,婆婆煮熟饺子,捞出锅一排四碗,坐下要动筷子发现少了一碗,转眼又不见了媳妇。正待要问,秀仙进屋了,看着公公的脸说:“我晌午在俺娘那儿吃过了,那一碗我端给俺哥吃了。”
一句话让公公黄玉坤心里热乎乎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这媳妇真理解爹的心。
“爹!今天过小年,殿卿也回来了,一家儿人怪高兴,我得跟您说个事儿!”
黄玉坤心里的热劲儿还没退,听见媳妇客客气气地“说事儿”,没加思索:“自己一家儿人,有啥就说。”
“我这快人快语您二老也看到了,说错了别生气。”秀仙见公婆的脸都带着喜色认真地看着她,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想好的话直溜溜抖了出来:“来大屯半个多月,都知道了我是党员,没有给您争啥光哩,就领回来了任务。咱村的公债任务冇完成,上级要俺带头买。”
儿子娶了一个如花似玉、懂事明理的媳妇,想不到还是个党员,不少人竖指称慕,仰脸高看。为这事儿老两口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听说媳妇要带头买公债,俩人相互看一眼异口同声地说:“中!中!买吧,买吧!”
公公婆婆大字不识一个,既不知公债为何物,也不知道公债值多少钱,只为贤惠知理的媳妇让他们心里“快活”、面子好看,一边点头,一边应承。
“我想买两份。”
公公不点头了,但仍是“中、中”。
玉坤不知道买一份要多少钱,更不知道两份买起买不起,他心里没有太大的底,虽然不再点头,也没有再多想,他还在兴奋中。
事情在公婆的高兴之中商定了。第二天,秀仙用自己的私房钱买了几份串门点心后才给婆婆说:“让殿卿陪我趁早把村里的几家近族和亲戚走一遍。”叔伯爷儿们、老亲旧眷见新媳妇上门,喜出望外,乐不可支。说起公债,家家支持。十几份公债一天推销完。
锋芒初试,一举功成。小屯村一个星期超额完成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任务,受到区领导的表扬,秀仙在城东区有了点名气。
名气往往就是影响力,就是号召力。名气是一种无形的资源,但这种资源的取得需要用心投入,更需要精心维护,维护了才能不断放大,才能在人生的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当年开始到1958年,全县先后又推销过5次公债,每一次秀仙都走在前头。
1951年的春节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化春节。城乡百姓看着年戏、放着鞭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没多久全县组织开展“郏县号”战斗机捐献活动。
动镰割麦前的一个晚上,秀仙出去开会回来得很晚。第二天早上,婆婆起床走到简易的厨房时,见秀仙已在动手和面做早饭。不知是出于婆婆的关心,还是女性的敏感,一眼看见媳妇手脖上的银镯子不见了,便问:“镯子咋没有戴?”
“捐了!捐给政府买飞机打美帝。”秀仙直言不讳。
“那也不能把恁娘陪送的镯子捐了呀?”
“手镯戴不戴无所谓,美帝打过来了事儿就大了!”
婆婆也不知道说的“美帝打过来”究竟是啥意思。只是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媳妇不戴副镯子有点怪“那个”的。
“要捐也是把我那一副捐了,咋也不能把恁娘陪送的首饰捐了!”
“我捐了是带头……”
党员带头,静水自流。没几天全村掀起捐献高潮,有钱的敲锣打鼓带头捐,没有钱的几分几毛地捐,十斤玉米,五斤高粱,两个鸡蛋……保家卫国,踊跃捐献。全县至7月底捐款19.1亿元(旧币),再次走在许昌专区的前列。
这个同志不简单
说这话的人是郏县县长贾传卿。
贾传卿是土生土长的郏县干部,他的最大特点是当县长不像县长。去许昌地委开会——“粗布鞋、粗布衣,戴个草帽黑兮兮”,门卫硬是不让他进会场。下乡去黄道山区,在一个大坡前遇一拉煤车的农民,他二话没说把布衫脱了搭在肩上,从坡底推到一里多长的坡顶。拉煤老汉握住他的手,半天挤出一句话:你可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弟”。这个“老弟”是郟县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县长(1956-1968),也是用两只脚走遍全县所有行政村的县长。王秀仙就是他用双脚行走大地中认识的一位农民党员。
1955年麦收时节的一天上午,艳阳高照,热浪翻滚,县城以东四里营村公路边的麦场上人欢马叫,热火朝天。碾场的、上垛的,放磙的、扬场的,一派喜获丰收的景象。
时近晌午,从公路边走下来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年龄小点的像个机关干部,走上前问道:“这里有区干部没有?”
“有!”站在树下像是刚扬场下来休息的年轻人指了指不远处挥着木锨扬场的妇女说。
“你喊一下,就说贾县长来了。”
中年人看看周围好像没哪个像“县长”,只有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穿戴相差无几的人,两手推着自行车在向场内察看着。年轻人听说县长到了,虽然没有看见县长,还是急走几步到扬场的妇女跟前喊:“社长!贾县长来了!”
这社长就是王秀仙。去年年底她被民主选举为一区大屯初级社(辖四个村)的副社长兼妇联主任,按党支部分工她分包四里营村。她听到声音刚放下手中的木锨,机关小青年已陪着那位农民模样打扮的人走到跟前了。
小青年上前介绍:“这是贾县长。”
贾县长微笑着应了一声:“我是贾传卿。”
两个人都是一惊。秀仙惊的是,他咋会是县长?听说新上任的县长朴素,没想到朴素得与干活的社员一模一样。
贾县长惊的是,这么一个水灵灵大闺女一样的女干部竟然会打略扬场。
说着话他们已来到场边的一棵泡桐树下。贾县长两个脚跟蹲着一块烂砖头,问了一遍收割、收打、收成、抢种情况,好像还没有忘记他的那一“惊”:“你一个女同志还会扬场?”
“庄稼活儿,不会干了饿肚子……”她还没有这样给县长对过话,只是这个土得掉渣的县长也没有让她怎么害怕。与往常一样不卑不亢地答道。
“不简单!”贾县长黑黑的瘦脸,平时笑得不多,微笑时又不易被人看出来,扬了一下脸,称赞道。这是县长第一次夸她“不简单”。
这时已围上来几个看热闹的人。站在县长一边的那个青年人不断示意他们不要嚷嚷。其中一个听到县长夸社长不简单,就憋不住了:“俺这社长放磙、垛垛、扬场啥都会,比爷儿们还厉害!”
豫剧《朝阳沟》栓保爹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那是一句客气的宽心话。其实不少庄稼活必须学,而且还要认真学。有些农活有的人干一辈子也不见得能干好。麦秸上垛、圆垛、长垛、大垛、小垛,没有技术堆不起来,垛不齐修不圆。麦子碾好后,扬场打略,把麦粒从麦糠里分离出来,没有技术、没有窍门,干着急也分不开、扬不净。农村麦场上,上垛扬场的往往是上了年纪的人。一般年轻人对这种农活白着急,干瞪眼,望场兴叹。年轻媳妇王秀仙对农村庄稼活事事通,样样会,不少干部群众内心佩服,无比赞赏。
人们常说,聪明人一拨三转,糊涂人捧打不回。说穿了这是悟性的差异。
秀仙在娘家上有身强力壮的父母,一般农活不靠儿女们。另有大小二位兄长,下力活还轮不到她。父亲的掌上珠,母亲的小棉袄,家里租种地主家七八亩地,让她干体力活的机会很少。自打懂事起,父亲犁地她往地里送饭;哥哥收麦打场,她去场里送茶水。去得早了站在地头看,父亲、兄长吃饭休息时好奇地动手学几把。没有干几下就像模像样,颇得父兄赞许。结婚到大屯黄家,公公婆婆把她当成鲜花、宝贝,虽然争强好胜,但她动手干农活的机会仍然不多。可她见活就干,啥活都会。这种个性和聪慧的呈现只能理解为悟性。有了这种悟性,她的言行举止往往会异于常人,会让你不得不服气。
不过,秀仙让人服气的不仅仅是她的悟性,还有她那种热情、干劲和毅力。
初任副社长兼妇联主任,秀仙感到最大的难处是不识字。自開始有扫盲班,她心里暗暗卯上了劲。白天不管干活有多累,晚上必须去扫盲班学文化。婆婆带孩子累一天,晚上她抱着吃奶的孩子去扫盲。刮风天去,下雨天去,附近村里她去,堂街五区在汝河南七八里地办班她也去。近了走路去,远了老公公给她找个小毛驴骑着。风雨无阻,乐此不疲。这种执着,让不少扫盲老师心热,三里五村的不少文盲妇女心也热了,劲也足了,纷纷跟着区长学文化,长见识,开眼界,一时扫盲成风。
“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理想口号激励了“大跃进”年代的无数国人,但苦的可能就是最基层那些党员干部。
1958年下半年,全国大炼钢铁掀起高潮。全县要建一大十小钢铁厂,还要10万人修水库,几万人深翻土地,城西北到景家洼修铁道,城东往襄县修公路。全县干部群众吃着“人民公社”组建后的“大锅饭”,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这跑步的路上,王秀仙身为党员,听话带头,无怨无悔。
公爹先去修老虎洞水库,又去钢铁厂炼铁。大伯黄勋上了水库工地。身为村干部的秀仙两大任务要带头:一是深翻土地,二是淘铁砂。深翻土地的任务她可以晚上干,大不了天天晚上不睡觉,连轴转,难的是汝河淘铁砂。
出伏牛山流经郏县的北汝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明清时期在县域东南水流较缓的河段曾有航运之利,以后数百年来,年年防汛,岁岁遭灾,两岸百姓流离失所,叫苦连天。就是这样一条灾害频仍的汝河,突然被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飓风吹得雷动山响,旌旗翻飞。不知是哪位有文化的领导受“金沙江淘金”的启发,在黄道的江山、鏊子山找不到铁矿石的无奈之下,决定从汝河河沙里淘铁砂。
北汝河发源地的山体基本上是由含铁量极低的火成岩、变质岩构成,而且经过100公里的跌宕冲涮,已细如米粒,风吹而动,水动而走。听说要到汝河淘铁砂,在河边居住了千百年的农人笑得把饭喷出老远。
一纸荒唐令,苦了数万人。汝河沿岸各村动员,能走得动路的男男女女全部下河涮砂淘砂。干部不行动,说啥没有用。王秀仙脱下外衣,挽起裤腿,带头下入没膝深的水中。
立冬过后,中原大地寒风阵阵,汝河水寒冷刺骨。一天上午,西北风刮得让人喘不过气。河岸上走下来几位县里督战的领导,走在前那位领导,一脸的精明厚道,微笑着向大家示意。身边一位瘦高个的年轻人介绍:这是咱们县委代理书记武松根同志。当大家仰脸看这位“代理书记”时,他已弯下腰在看河堤边几个人裂着血口子的腿。他用右手按了按一个壮年男子的小腿肚,问:“疼不疼?”
“不疼。”
“裂这么多血口子,不疼?”
“在水里泡时间长,没感觉了。”
武松根心情有些沉重。问:“干几天了?”
“半月了。”那人答道。
“一天能涮多少?”
这人有点聪明,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没立即回答,而是看了看在水里弯着腰正涮砂的妇女,伸手指了指说:“她知道。”
武书记走到水边,那妇女已从深水里走过来。没等开口,就听领导说:“你是这个区的妇联主任?听说你们一区深翻土地在全县得了个第一,这边涮铁砂啥样?”
“不中!这河沙里含铁砂很少。”
“一个人一天涮多少?”
“从早到晚不停干也就二三斤。”
“从上报的数字和你们炼的铁块看,可不是几斤呀!”
“那铁里面有他们家里的破锅、烂锨、门搭铃。”全是一五一十的大实话。
武松根到郏县代理书记有半年时间,对县情和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尽管已有初步了解,面对着众人,他也是多看少说不表态。他听出秀仙的“大实话”,尤其面对这样的女同志,他无法表明态度,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沉思片刻,变了话题:“你天天这样下水?”
“不下去干会中……”秀仙说着低下了头。
武松根早已看到她腿上浸着血的一道道口子,像蒸过火又放凉的红芯红薯。立即激起矜悯心情:“女同志还是尽量不要长时间站到冷水里。”
“没事!习惯了!”秀仙答道。
对于秀仙说“没事”两个字,这位山西高平籍的武书记,不知对这句中原土话听懂没听懂,至少他没有听出秀仙说这话的实质。这是她不服输、不畏难的刚强性格惯常性表达。也正是她这倔强性格,前几天经期到了仍不露声色,违背常理地拿着簸箕连续三天站在冷水里带领大家淘铁砂。河岸上有不少轻一些的活儿、不沾冷水的活,作为女区长完全可以适当选择,她却没有。那是挑肥拣瘦,是特权思想,她不可能那样做。也正是她这不服输的性格,勇于带头的作法,几年后的初冬时节村东南堰洼池一带麦地积水排涝时,她在一两尺深的冷水里挥锹改水,例假的鲜血顺着大腿流到地上,漂在水里,周围的人劝解无效,她硬是站在冷水里坚持一个多小时,直到大水退去。还是她这不畏难、不服人,到粮店交余粮带头扛口袋、抬麻袋,与其他村比干劲、争速度,一下子累得月经失调,腰肌劳损。她的妇科病早已暴露,来例假时疼得两条腿站不稳,三天例假期,一星期身上不干净。妇科病愈来愈严重,婆婆提醒,妹妹督促,男人劝说,她没有时间休息,顾不上就医,小病拖成大病,直到1975年不得不去郑州做了子宫全切手术……
武书记听了秀仙“没事”的表态,对她的工作给予肯定,感到放心,对她的身体倒表示担心。鼓励安慰一番,离开前对同行的几个同志说:“这个同志不简单!”
武松根书记也称赞秀仙“不简单”。秀仙心里已没有了第一次受到县领导称赞时的高兴和欣慰,更多的是郁闷和委屈。一位基层干部,一个农民党员,对党的号召、政府的任务,她唯一的选择就是服从,就是带头,就是落实,有无奈只能憋着,有委屈必须忍着。即使这样她还是记住了这位书记的聪颖和善良。正是有了这一次的深刻记忆,几年后,已成为专政对象的武松根被批斗得走投无路、命悬一线时,她勇冒风险,临危出手,救了书记一条命。
我啥时候都说实话
“大食堂”开始的第二年,小麦长势良好,夏粮喜获丰收。只是因多数男劳力上水利工地,靠女劳力收割,进度缓慢。眼看大田小麦已过成熟期,秀仙分包的四里营村比其他村收割快一些,也僅仅是一多半。她急得头上冒火,七窍生烟。
一天上午,秀仙正在二组收场,乡通讯员骑自行车来通知,要她立马到乡里参加紧急会议。
早上一碗红薯汤的热量早跑到九霄云外了,走几步路都眼冒金星,还要立马去开会!抢打抢种,雷打不动,一句话就得动!她有些怨气!
生气归生气,大步流星的风格不变。书记开的是小会,却是紧会。
上午县里召开夏季产量汇报会,王集乡报的最低,受到县领导批评。书记陈炳聚从县城走到乡里,懊恼之气还在脸上弥漫。秀仙和已先期到达的几个人,都是上报产量较低的村干部。
书记先讲当前的形势:全国夏粮丰收,嵖岈山公社亩产3500多斤;再传达会议精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全县多数村的产量都超千斤……要求各位村干部紧跟形势,报清产量。
几个人一头雾水,面面相觑。人老几百辈子耕田种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谁都知道,这亩产千斤是咋产出来的?后来就有了“麦杆像秫秆,麦籽像鸡蛋,红薯一亩二十万”的顺口溜。这是后来的戏言,在当时还是让不少人畏难、无奈。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烟鬼不停地吸烟,不吸烟的没事找事也装模做样地撕块旧报纸学着卷,试着吸。陈书记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不停地提醒:说吧!说吧!问了五六遍仍没有人应声,他火了:“关键时候都哑巴了!”指了指八里营的贾支书:“你先说!”
贾支书抬头看了看没吱声,低下头继续吸烟。
书记可能觉得女人胆子小,好说话。扭脸指了指坐在门口的秀仙:“秀仙,四里营报多少?”
“……三百斤。”
“人家三千斤,你们三百斤。上午有些乡报一千斤还挨批评哩,你这三百斤能过关?!”
“一亩地能打多少小麦咱都知道,我只能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你也不能报三百斤!”
“三百斤已虚报了,我啥时候都说实话。”
“不中!”
“不中,我不干……”
不欢而散。
身在江湖不由己。
农村生农村长的陈炳聚书记绝对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小麦。“高产放卫星”,他不放就过不了这个关。逼着各村干部虚报产量,那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与难堪。
不与领导保持一致是从政的第一大忌,秀仙没有被处理,只是没过多久她的工作分工有了调整。
三个月后,全县推行“三院”(敬老院、保健院、幼儿院)合一,王秀仙调整分工当上了“院长”。接到通知后,他哈哈一笑走马上任。
人们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其实说发光不是黄金价值,而是黄金的物理属性。黄金丢在垃圾池里,其他垃圾经高温处理成了肥料、废渣,而黄金仍然是黄金。人,亦如此。一个有责任感、事业心、有德行、有良心的人,不会因工种的调整、单位的变化而改变初衷,改变秉性,改变其正直、善良、无私、奉公的率性。王秀仙任院长时间不久,即把她的性格展示得墨黑纸白,一清二楚。
敬老院运行的关键是粮食。她先抓住这个“牛鼻子”,一子儿走活全局。
以前三个院天天派人到各村各队各组收粮食,收面粉。干部看见就躲,要不就是百般推辞。秀仙上任后,亲自出面,恭敬拜见,说情论理,巧妙安排,加之她的人品、人缘、人格魅力,每到一处把道理讲得不拿粮食就感觉是缺德丢人,没良心。拿到粮食她自己背,亲自扛,背得汗流浃背,扛得尘土飞扬,队组干部为之感动,佩服信服。“以后再收粮食早点说一声,俺给你送去……”
大眼瞪小眼,老少傻了眼。当然是黄殿卿先开腔:“咋啦!”
“咱大小是个干部,是党员,不能让人家说闲话。贫下中农的好孩子多了,让他们去上吧!”
就这样,眼巴巴的看着把读高中的机会放弃了。大儿子为此哭了好几次。
秀仙大字没识几个,道理懂得一个多,什么事儿都想得通,讲得明,让人信服。轮到做自己儿子的思想工作她更没有绕远:“过罢年可以去当兵。到部队大学校里学军事,学文化,武装思想,接受锻炼,一辈子都有好处……”
第二年春天,大儿子应征入伍。不巧的是“路走对了、门进错了”,老大去了成都军区独立师,被分配到海拔四千多米的甘孜州理塘县执行剿匪任务。和平年代,这样的军差让你自己选择都困难,恰恰被黄家大儿子领受了。知道自己的孙子去高原上打土匪,从来没有埋怨过儿媳的婆婆这一次有些坐不住了,提起这件事就伤心,哭得成了个泪人。
秀仙自有一番道理:“既然去当兵,就是让他接受锻炼,增长见识。蜜罐里不能炼铁,温罐水不能养鱼。和平时期再苦也苦不到哪儿,再险也险不过战争年代的攻城拔寨。有这样的锻炼,不愁给咱黄家培养一个有能耐的接班人。”
一年后孙子寄回来了立功喜报,两年后得到孙子入党的消息,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大孙子退伍参加工作后表现优秀,又被企业推荐上了大学。婆婆再次从内心服气了不识字的媳妇胸装大千世界、看透世事百态。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國。大屯村支书、主任因派性影响,长期坐不到一起。为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秀仙千方百计、百计千方,紧撮合、细劝说一直无法调解。乡党委不得不下决心“大换血”调班子。乡领导一致的看法是支部书记首选王秀仙。组织委员、主管书记三番几次谈话,秀仙咋也不答应,理由是不识字、不懂政策,妇道人家不方便……
党委书记赵德运是一位有魄力有眼光的明星书记,上任三年第一次遇到拒不受军令、硬不接支书的党员,不得不亲自出马。如果是其他任何人,赵书记绝对没有这般好脾气。王秀仙是全乡出了名的妇女干部,他要屈尊下驾,当面听听意见。
秀仙还是那几句话:不识字、不懂政策,家庭负担重……
“这我全知道,都理解,但你是党员!”赵书记亮出了“撒手锏”。
无言以对,她只能应允。但话还得说:“我是党员,我听党委安排。当干部、干工作要凭个良心。不识字、水平不高,我凭良心干。干好是我的本意,干不好、干错了党委就罢免我……”
铿锵有力,字字入心。每个字都像一个铅球,落地一个坑。
秀仙上任遇到的另一件大事是:好人好马上“三线”。
那年,她的小儿子已进入乡高中二年级学习,秋季开学前给男人殿卿商量:
“三线工地要上人,让老二去吧!”
“他才十五岁,太小了吧!”
“小啥!多少老革命都十几岁入伍,一二十岁带兵打仗。年轻孩子在于锻炼。舞阳工地也不远,全省组织十万建设大军,郏县是丁学敏书记带队,咱还有啥说哩!”
1970年11月初,二儿子随郏县民工团奔赴“平舞”(平顶山舞阳钢铁基地)会战工地,他是8600多人的郏县民工团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干得最好的民工之一。第二年在工地上入党,是全团最早入党的小青年儿。两年后平舞工程结束,二儿子回到郏县先后在供销社、县政府工作,政绩突出,人品优良,被提拔到县级领导岗位从政多年,在当地颇有声望。当年“三线”工地的锤炼,锻就了他健行致远、广受赞扬的人生。
大屯村有了“文革”的派性病根,加之紧邻城区,七姓八家,姓杂人众,秀仙的党支部书记干得极不省心。但她一招治百病:善待他人,遇事带头,严格律己。
1972年,农村开始为住房特别困难的群众批划宅基地,秀仙家三代8口人,是理所当然的批划对象。但她把自己家放在第二批。批划一开始就出现划新不交旧的棘手问题。秀仙家新宅基地上的房子盖好,搬过家没出一星期就组织人拆除老房子。婆婆是老观念,金窝银窝,不如祖传的老窝。提出“恁住新房子,我住老房子不中?”秀仙直爽爽地说:建新宅扒旧房咱得带头!
在王秀仙的心里,率先带头永远是第一原则,第一坚守。这个原则,工作中时时遵循,事事坚持,在家里更没有商量的余地。
“七五·八”舞阳县水灾,政府安排给灾区捐衣捐被,送烙馍。秀仙不仅把孩子的衣服捐了好几件,又把准备给二儿子结婚的新被子捐了。为这事,婆婆几天不高兴。全村群众每人给灾区贡献一斤二两烙馍,秀仙白天深入各家各户动员催促,晚上和婆婆点着油灯炕馍。婆婆见全部是用好面(麦子面),担心地问:“好面用完了咱吃啥?”
“咱从明天开始吃玉米面红薯面。人家是救命,咱是过日子。咱吃了填坑,人家吃了传名……”
婆婆烙的馍有点小。秀仙慌了:“不中!不中,咱烙的小了咋说人家。还有几家自己吃饭有困难,咋再让他们完任务,咱多烙点……”
婆婆问:“烙多大?”
“要比咱平时吃的都大,可着鏊子恁大。”
秀仙生性是那种大气人。说到“大”字时语音格外重,好像是只此一言就让你入心入脑。只是不管轻不管重,媳妇说了都执行——婆婆知道媳妇的为人,更理解媳妇这支书当得不容易。
理解万岁!说的就是万事理解第一。一个家庭的互相理解更是如此。
您说的话在理,俺听您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县委号召在全县大力发展新党员。王秀仙根据自己对村里年轻人的了解,推荐本组一位比自己年龄小两岁的周姓小伙子加入了党组织,一年后小周娶了邻村一位山眉水眼、风致不凡的女子为妻。媳妇的性格是心直口快,十几年间相继生了6个子女,50多岁那年不听人劝告又生了第7胎。孩子多,难处多,矛盾也多。艰难困苦是理性和温柔性格最直接的杀手。漂漂亮亮的媳妇最后成了村里有名的“不敢惹”。家住村西头,骂男人、骂孩子的声音在村东头可以听见。孩子在外面打架,她不教训自己的孩子,而是拉着孩子到对方家里争吵对骂。她养的母猪不上圈,糟蹋了邻居家的玉米,邻居找上门时她说:“猪没有人听话,你有本事去摆话摆话(土话,教育教导的意思)它……”周的大哥知书达理,在外村学校教书,妯娌俩吵架如喝凉水,实在没法一起生活,早早地搬出老宅,躲避是非……
就这样一位人见人怕的“不敢惹”,后来与王秀仙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有一次,秀仙去周家通知开党员会,正遇两口吵架。起因是没有人家借给她织布机用,男人埋怨了几句,她不仅不听,反而骂骂咧咧把浆洗好的织线扔了一地。秀仙进屋拾起扔在地上的线团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能老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我拿回去给你织织,过几天你去取……”
周家媳妇裁剪衣裳不在行,秀仙拿过来:我给你剪。当时她已有4个孩子,秀仙见只做了两件,即把自己二儿子和女儿穿过的衣服找出来送给她。周家孩子多,经常吃不饱饭,秀仙下地干活常走她家门口过,只要遇到他家孩子哭了,就带到家里,让他们吃点喝点,有时还会“再给恁哥带一个”……
没有人帮你我帮你,没有人理你我主动亲近你。即是坚冰一块,有了热有了温暖也可以被融化。周家的媳妇与秀仙常来常往,性格逐步改变,为人处世循规守礼。周家的儿子辈诚实劳动,勤俭持家,个个日子过得顺风顺水。孙子辈知理好学,有当兵的、入党的,还有两个在政府部门工作干得颇有成就。
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而难断的家务事还必须有人去断。在大屯村,难断的家务事就少不了秀仙老人。
村东头四组一户姓徐的,两个媳妇经常吵架。有一次,两个人嫌婆婆劝架不公竟把婆婆打一顿。秀仙第一次遇到媳妇打婆婆的大不敬事儿,陪徐家婆婆到卫生所包扎处理后,把兩个媳妇叫到一起,先从婆婆开说:首先是你教子无方,处事不当。打父母伤天害理,三岁孩子都明白。俩媳妇也不是那种不通道理的人……批评婆婆的话,让媳妇听得心里发热、发怵,然后先用“放大镜”找媳妇的优点、能耐,后又借古喻今,讲人伦纲常,明鼓励,暗批评,情真意切,鞭辟入里。人间烟火、人情事理谁都懂。不懂的人,你能说出道理她就听你的,就买你的账。两个媳妇内心服气了这个“村干部”:“伯母,您说话在理,俺听您的。”
两人说出了内心话,只有内心话才能言出行随,自觉执守。她俩后来都成了受村民称赞的好媳妇。
大屯村历史上没出过什么名人,“文革”期间倒出了两个全县闻名的人物:一个是“河造总”在王集乡的总指挥,一位是“二七公社”“7·26”的王集乡掌门人。武斗时都抱过机枪,拿过手榴弹。王秀仙开始是不左不右的“中间派”,担任支部书记以后是批斗对象。“中间派”时两厢劝阻,成为“斗争对象”时自己做自己的检讨,双方都不伤害。担任支书之前支书与主任坐不到一起。支书召集会议不通知主任,秀仙接到通知后就特意去找主任:蒋支书让我通知你去开会。主任在乡里开会回来传达精神安排工作,又不通知支书到场。秀仙参加时会专门到支书家里:李主任让喊你去商量一下当前工作。单独和哪一个在一起的时候,把没有捅破“窗户纸”的隔阂和没有沟通形成的误解、猜忌,挑明点破,依理劝说。有时也依着年长几岁的优势,该批评的批评,能鼓励的鼓励几句。有时把不好扯清的责任自己多承担些,甚至再检讨几句。为缓和两人的矛盾,有两次特意把会议地点安排在自己家里,商量过工作,让儿子备上几个菜,摆上两瓶酒。古道热肠,苦口婆心。热情似火,真心一片。
人心都是肉长的。肉长的心自然可以被焐热、被感化。何况他们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利害冲突,没有个人之间的恩怨仇恨。特殊年代形成的非理性思维狂热性行为,在人们的思想回归理性以后完全可以走向理智,走向阳光。大屯村经过秀仙任支部书记几年后,上级党委政府和本村群众最担心最痛恨的派性遗毒被烈火一样的热情、水晶一般的真诚消解、消弭,清刷、清洗,成了全县知名的富裕村、和谐村。
2002年秋季,72岁的秀仙老人坚辞了村内所有职务。新上任的村支书恳求说:“您是村里的压舱石、主心骨,关键时候,有棘手难题您还得支持,还得出手。”
秀仙还是报以几十年常挂在脸上的微笑:“不当干部了,还是党员。啥时候都听党支部的话。”
常言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精明透彻的秀仙老人对常言古训了然于心,无奈于乡村两级领导的敬仰尊崇,村里有了难断难解难处难理的破事烂事,常常会请教于她,请她出面调解,到场融通。因为只有她,才能言出人随,人到事成。
“言出人随,人到事成。”是大屯村党员干部、社员群众对秀仙老人几十年工作的基本评价。我作为比较熟悉她的晚辈,对这一评价既认可又感动。但我内心一直在思考的是,一位农村农民党员何以能让一个村的百姓几十年始终如一地追随她、敬服她!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到了贝多芬的名言:“那些立身扬名、出类拔萃的,他们凭借的力量是德行。”
德行是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骨子里、洋溢在言行中的力量。秀仙老人就是靠着她的德行在影响人、温暖人、感召人。她的德行,大屯村的男男女女看得见,十里八村的群众口口相传,耳熟能详。
不能让人家吃亏
王秀仙与黄殿卿结婚前,除在“南大坑”经街坊嫂子介绍见过一面,再没有碰过面,而且对殿卿家里的人丁、宅院、地亩一无所知。成亲过门几天后才知道殿卿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黄勋。
黄勋比殿卿大了十来岁,他是那种忠诚老实、干活不惜力、办事不太麻利的好人。两位老人为他没少操心,却一直没能成个家,快40岁了还与父母一起生活。一家有一家的难处。老人一时也没有啥好主意。
秀仙是精明通透之人,结婚到黄家没几天很快看出了问题。有一天,殿卿在家工休,趁中午和公公婆婆围坐在院里石桌前吃饭时说:“俺哥要是回来吃饭就好了。”
老公公黄玉坤闻听此言,像初春听到了雷声。筷子将要送到嘴边的面条忽然停止了,两眼盯住媳妇看着,直出了几口气才把面条又送到嘴里。一年多来他焦心的事不好说出口,今天竟从刚过门的媳妇嘴里说出来,心里的块垒郁结被一语道破。更重要的是从媳妇这小小的举动,他黄玉坤认定了“娶个好媳妇,一贤兴三辈”的好兆头,看到了他黄家一门兴旺发达的光明前景。他没有喝酒心里却醉了,那是甜蜜,是温暖。遗憾的是老人家没有躲过1960年的天灾人祸,没能看到自秀仙到了黄家以后的儿孙贤良、家族兴旺。
公爹去世那年66岁,病得说话的力气已没有了。拉住大儿子黄勋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咱家有了殿卿媳妇,我对你也就放心了……”
没有多久,公爹去世。让公爹没想到的是,他说这话时,媳妇秀仙就在他床头的一边站着。他这句临终遗言,成了秀仙几十年铭记于心的亲命嘱托,忠贞不渝的坚守,使黄勋这个无儿无女的光棍汉享受了家的温暖,快乐生活几十年。
我去拜望秀仙老人那天正遇她的大儿子在家。有幸听他介绍母亲几十年如一日赡养大伯的一些往事。
“我记得母亲交代我最早最多的两句话就是‘把饭给你大伯端去‘去喊你大伯回来吃饭。俺爷去世时我已十来岁了,正好可以端碗送饭。我们家的饭做好第一碗饭一定是给大伯的。前些年,母亲一直操心想给大伯成个家,平时把大伯穿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母亲特别勤劳,白天开会、干活,晚上纺花织布。织好布做衣裳,首先是给奶奶做,给大伯做。有一次,借住在我们家的雷达排吴排长休假回来带了一罐湖南米酒,中午喝酒时大伯犁地没有回来,母亲把我叫到一边交代:‘给你大伯留点尝尝。我从部队退伍带回来一顶皮帽子、一双毛皮鞋,母亲安排:‘帽子你爹戴,毛皮鞋给你大伯穿。
“大伯曾给我说过,爷爷去世那一年,其实他也得了病,母亲悄悄卖掉父亲的自行车和几只老母鸡,换钱给他治病。病稍好一点就把他接到四里营敬老院。‘没有恁娘,我早跟你爷一块埋地下了。
“我大伯从小患有‘疝气,成年以后仍治不好,母亲四处打听偏方,到处找专科医生。大伯这种男性病,一般女人都没法插嘴过问,我母亲为了大伯的健康,不计较忌讳,不怕别人耻笑。70年代家里经济非常困难,为了减轻大伯的病痛折磨,她找俺舅、俺姨好几家亲戚借钱,陪着大伯到郑州铁路医院做手术。当时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为了不影响父亲和我们弟兄俩的工作,母亲不让俺仨人请假,她在医院给大伯端水端饭,左右伺候,不知情的人感到匪夷所思。母亲是个正常的人,却做出了让不少人难以想象的事。惊世骇俗,感天动地。
“1992年母亲还担任着村党支部书记,92岁的奶奶患脑中风一病不起,需要有人床前服侍。母亲给我们宣布,侍候照料公公婆婆是儿女媳妇们的事。我只要在一天,能走得动,你奶奶的事你们就不用管。每天喂药喂饭、擦洗穿戴一律不让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近前。两年后,81岁的大伯也瘫在床上了。母亲找到乡党委主要领导硬是把职务给辞了,全天候照顾两个吃饭喝水全靠人喂的老人。这时母亲已经66岁,我们几个商量轮流照顾奶奶和大伯。母亲一听挺不高兴:‘照顾好恁大伯是恁爷交给我的任务,我不能昧了良心让祖宗骂我。当时我岳母80多岁,身体不好,二弟的岳母快90岁了,也是只有弟媳一个女儿。母亲明确要求:‘老大家、老二家,你们回去照顾好你们自己的爹娘,不要给咱姓黄的丢脸。有个星期天我们回来看老人,母亲开着玩笑说:‘看看恁奶奶恁大伯受没受委屈,评价一下我这个老保姆合格不合格!敬人得寿,行孝有福。我长寿百岁,给你们添麻烦了可不要埋怨我……我们都笑了,两个媳妇和我妹妹笑得流出了眼泪。
“我奶奶在床上躺了五年多,96岁去世。大伯有两年生活不能自理,去世那年85岁。两个人去世时,脸上没愁容,身上没褥疮。97年、98年相继送走两位老人。四世同堂送高寿的奶奶,母亲亲自张罗,把丧事办成了喜事。第二年大伯去世。热情似火、刚强得眼里常常冒火的母亲从来不流泪,大伯咽气时她流泪了:‘俺哥没儿没女,辛辛苦苦一辈子。老了应该享享福,他却早早地走了,走得早是俺没有侍候好……弟媳妇精心服侍照顾大伯多年,乡里乡亲都称赞不已,她却还在伤心、在落泪、在自责。在场的几个人都眼热心动掉了泪。
“安葬大伯时,母亲给我和老二交代:‘恁大伯没有儿女,咱要把他的丧事办得体面些,让大伯黄泉之下没遗憾,不抱怨,高高兴兴,无忧无虑……
“安葬大伯那天,村上来了很多人。应该说,来了那么多人,吊孝送葬的很少,多数是来看看母亲善如命重、孝比天大的高风亮节的。母亲几十年做事低调,生活简朴,在大伯的后事处理上却少有的高调,甚至有点铺张。全家人都理解母亲的心情,看热闹的很多人被感动。不少人都说,黄勋上辈子烧了高香,遇上王秀仙这样的弟媳妇,比有儿有女的人还有福……”
家庭爱是根,做人善为本。秀仙老人用爱注塑了家道,扬起了家风。在几十年的任职和生活中,她又用善良在百姓中展示了她的胸襟,她的慈心,她的厚德和崇高。
王秀仙没有担任支部书记之前,有一次丈夫殿卿托熟人从食品厂买了一斤多猪皮上刮下来的似油非油、医学上称为淋巴类的筋膜,黑糊糊、腥兮兮的。秀仙用热水泡几遍沥干后在热锅里熬了半碗油。在当时这可是宝贝!用这种油炒萝卜丝足以香飘半条街。
平时秀仙家门口常有附近几个人蹲在一起吃饭聊天,形成一个小饭市。有一天生产队分了几个萝卜,秀仙早上用猪油炒了一些,两大盘萝卜丝,自己家留一盘,另一盘端到门口,饭市上吃饭的几个人,人人有份,每人一筷头(两根筷子夹一下)。在“一年红薯半年粮”的年月,用油炒菜是多少人家的奢望,能吃猪油炒萝卜丝的人实在不多。这一筷头萝卜丝让几个人嚼了又嚼,舍不得咽下,香味直浸肺腑。这样的萝卜丝,常在这儿吃饭的几个邻居后来又吃过几次。秀仙家门口的饭市也不断发展,成了村里的一道景观。
村东头三队有个徐次会,无儿无女只身一人。有個生存能力很一般的侄儿无力赡养他。秀仙从副支书到支书,基本把徐次会当一个本家兄弟照顾。给婆婆、大伯擀面片时多做一碗,儿女们在家让儿女送,儿女不在家她从村西头跑到村东头,送到徐次会的床前。碰上烙或蒸好一点的馍,就包上几个送过去。下雨天担心他的房子漏水,黑更半夜打着伞再去看一看。郑州住院做手术回来的第二天她去看望徐次会发现老人病了,当晚吃过饭,婆婆和大伯在院子里乘凉发现不见了秀仙,等好长一会儿才回来,婆婆担心她刚做过手术,身体虚弱不能多跑路。问后才知道她去给徐次会送药,顺便把家里的温水瓶也送给了他。大伯听后不大高兴地说:这事让我去不是也中!秀仙说了一句当时大伯可能听得不太懂的话,“中是中,我送与你送不一样!”
三队有个五保户刘玉化,比秀仙年长一辈,年龄和大哥黄勋相差无几。晚年后隔三差五找大伯说话(即唠嗑),中午了秀仙就安排他和大伯一起在家吃饭。他有病有事不找别人,只找一个人,就是“殿卿家”。有一次殿卿从城里回来买了两个火烧,秀仙看到后交代:咱娘咱哥想吃“火烧”不难,这俩馍你送给玉化叔吧!刘玉化80多岁去世,咽气前给他的一个亲戚说:“我这后二十多年的命是殿卿家给我续的!”
八九十年代,郏县烟草公司仓库边正对着去大屯的岔路口有个理发店。店主是大屯人,叫石刚岭。他开始理发就有一个小小的报恩愿望——大屯黄家理发不收钱。问其究竟,答曰:我的命是黄家给的。
然而,他的图报愿望却一直没有实现。
石刚岭在家排行老二,比秀仙老人的小儿子晚一个多月出生。也算刚岭命运不济,因母亲身体不好,出生后就没奶吃,饿肚子。婴儿求生的哭声急坏了石家老小。在当时的农村,能想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别人的奶吃。打听到村西头殿卿家刚添个小孩,只是觉得不一家不一姓,何况人家是村干部,平时只是见过面,话也没说过几句。奶奶怀揣着哭了两天的孙子,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找到刚出满月的王秀仙,进门一句话没说完,秀仙双手接过声音已哭得沙哑的小刚岭,即刻就把奶头送进了他嘴里。刚岭的奶奶流着泪说:殿卿家,我想给你跪下……
一份不太充裕的饭食两个孩子吃,襁褓中的黄家老二本来就吃得不太饱,现在则是半饥半饱,也常常用啼哭诉苦。秀仙让就婆婆嚼点红薯、嚼点馍喂儿子,“只要不饿着就中。”秀仙中午常在家,刚岭奶奶中午把孙子抱去吃奶,秀仙如果不太忙,就到村东头的刚岭家去喂奶。有几次秀仙外出中午不回来,临走前就把奶挤到小碗里给刚岭存着。刚岭自有记忆起就听奶奶和母亲说,你是吃秀仙奶奶的奶水成人的。刚岭成人了,有用了,他要用自己的劳动报答秀仙奶奶的恩德。偏偏秀仙奶奶不是那种施恩图报的人。得知剛岭理发不收钱,特意对家人说:“理发这种小生意挣个钱不容易,不收钱咱就不能去。”
刚岭两个多月没见到隔壁烟草局院子里上班的黄殿卿去理发,经了解才知道了个中原委。一天他来到秀仙奶奶家,声大腔高地说:“奶奶,我给您提意见来了。”
秀仙老人没怎么在意。谁知刚岭一开口说得挺严肃,而且还动了感情:“奶奶,是您给了我这条命,这一辈子都报答不完。我就这么大本事,只能给您家里人理个发,你却不让。你是不把我当成人吧!你给我个报答的机会不中?”泪如泉涌,哭声号啕。
秀仙老人劝说:“我生两男一女,给几个孩子喂过奶我也记不清了。能有几个孩子吃吃我的奶,那是缘份,是我的福气。一个人做点好事、积点德、行点善,老是记到心里挂在嘴上,那有啥意思!你帮我,我帮你才是好乡亲。你只要心里有我这奶奶就中……”
从此以后,黄家的大人孩子又都去刚岭的店里理发,秀仙老人却定有原则:不能让刚领白干,不收钱就给他的店里送些东西,不能占他们的便宜,不能让人家吃亏……
“不能让人家吃亏”,这是一位做了几十年好事的老人的处世原则。
有70年党龄的王秀仙老人,当了50年村干部、6届县人大代表,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强国富民、惠及千家万户的壮举,她能做的就是给门口吃饭的乡亲搛一筷头猪油炒萝卜丝,给五保户送几包药、送一碗面片,给没奶吃的婴儿喂几口奶……大屯百姓不忘她,大屯群众敬重她,周围不少人敬仰她……
拜望老人回来的路上,我想到了花丛中、田野里、树林、路边的小草:不与鲜花争芬香,不与树木争高低,把绿色献给人间,而且绿叶永远向着太阳。
大地处处有小草,绿色让世界更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