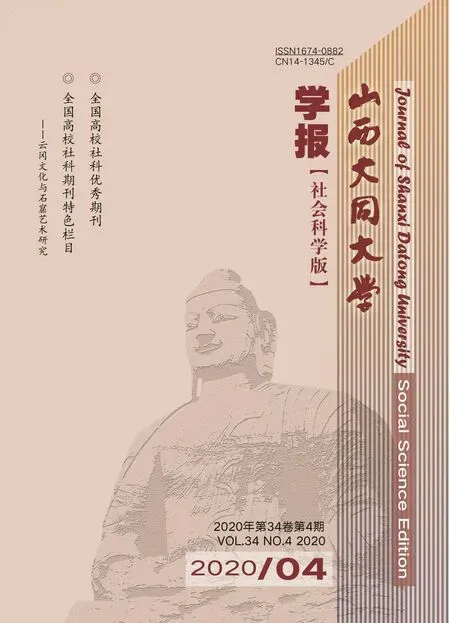先秦诸子文艺思想及其现代性
万志全
(河池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河池 546300)
处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先秦诸子文艺思想较为丰富。其中,儒家文艺思想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指导性文艺思想,这在某些方面得益于孔子、孟子和荀子文艺思想的博大精深,使得后世儒家从作者到读者、从创作到批评、从审美到功利等方面都能纵横捭阖;道家文艺思想之所以能够对后世文艺创作有着较大的启迪意义,主要得益于老子和庄子能跳出文艺谈文艺,从而启发了后世文艺理论与创作着意追求灵动性与玄妙性;墨家、法家文艺思想虽不如孔孟荀或老庄丰富,但也不乏闪光点,也能给后世提供某些论域和论据,能启发后世文艺思想推陈出新。而若用当今之眼光来衡量先秦诸子,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文艺思想都契合当今之现代性,并对当今的文艺思想与创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先秦诸子文艺思想的主旨:艺以载道
先秦诸子虽然不常论及文艺,但他们的思想、言行、实践与创作中却暗含一些文艺思想。其中,儒家与道家就文艺的主题、创作、欣赏、功用与文艺修养等方面阐发了较为丰富的理论见解,墨家与法家对文艺言之甚少,但也论及文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比如墨家提出艺术的普及性问题,法家对艺术的实用性与艺术内涵问题进行了探讨,这给后世文艺思想与文艺创作以启迪与智慧。
(一)儒家文艺思想的主旨:艺以辅政助德 在文艺思想方面,先秦儒家重视艺术,热爱艺术,倡导发挥艺术的社会效用,关注艺术的普及性以及艺术对于人性修养的积极功用。
孔子的文艺思想。孔子是艺术评论与鉴赏的通才,从他对“《诗》、《韶》《武》乐、绘事”的评论中,可知他在文学、音乐、绘画等方面皆有独到的见解。在文学评论与鉴赏方面,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1](P172)“诗”(即《诗经》)是一个人说话文雅、言之有据的根本,因此,世人必须重视《诗经》的学习与理解;而学了《诗经》以后,有何帮助与启迪呢?答曰:“思无邪。”[1](P9)除了让学诗者的思想和行为变得纯洁无邪以外,《诗经》还具备一些社会功用,《论语·阳货》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P177)这里的“兴”是抒发感情、培养意志与情操,“观”是了解社会与习俗,“群”是团结合作、增进友谊,“怨”是怨刺不平、直言切谏。孔子认为,《诗经》可以教育子女更好地尊敬父母,把父母赡养得更为舒心,可以帮助臣子更好地尊重君主、更忠诚地服务君主,可以帮助学诗者知晓动植物的名称。而关于诗歌情绪的表达,孔子认为应以适度为佳,《论语·八佾》云:“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P26)正如《关雎》这首诗在情绪表达时既能透露出欢乐的情绪,又不至于过度高兴,既能表达哀愁的情绪,又不至于过度伤心。孔子醉心于音乐鉴赏,《论语·述而》有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P65)当他听到舜帝时代的祭祀乐曲《韶》时,竟然陶醉得三个月内吃肉都觉得没有滋味,他又对《韶》与《武》作了比较:《论语·八佾》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P29)又可以看出他对音乐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关注,他认为在形式美的基础上,还应保证其内容美;如果内容不美,则应极力反对,《论语·卫灵公》云:“放郑声……郑声淫。”[1](P157)虽然郑声的形式新鲜活泼、热情奔放,但孔子觉得它们过分地表达男欢女爱,超越了“文质彬彬”所规定的含蓄范围,且又不合礼教,有伤风化,故而应予放弃。在绘画评论与鉴赏方面,《论语·八佾》中载:当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的回答是:“绘事后素。”[1](P22)子夏是想问老师“含笑的样子恰到好处,美丽的眼睛左右流盼,素服上染了绚丽的色彩”应如何理解,孔子却告诉弟子“先要把素描(白描)的底子打好,然后才能涂上绚丽的色彩”。由此可见,孔子对于诗歌、音乐、绘画都强调内容与形式兼美,亦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1](P55-56),虽然这句话本是孔子对君子内外兼修所提出的具体性要求,但也可用于文艺创作者,那就是要求创作者既能确保艺术作品内容的纯正无邪,又应要求作品的形式文采斐然,只有做到“文质彬彬”,才能成为艺坛之“君子”。另外,孔子还特别重视艺术对于修养的帮助效用。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1](P77)他认为,诗歌、音乐等艺术可以帮助君子修养出完美的人格。故此可知,孔子认为艺术不但有愉悦身心的效用,也有道德修养的效用。
孟子的文艺思想。首先,对于如何理解《诗经》,孟子认为应该“以意逆志”。《孟子·万章章句上》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2](P215)这就要求欣赏者应尽量超越文字和词语的限制来理解诗的本意。为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欣赏者还应知人论世,与作者为友,《孟子·万章章句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P251)只有结合作者的经历和心境来理解作品,才能把握作品的精髓。其次,统治者在进行艺术欣赏时,应该“与民同乐”。《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2](P3)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不会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百姓的痛苦之上。毕竟百姓与统治者一样,都有着相同的审美喜好。《孟子·告子章句上》云“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2](P261)正因为人人都有着相同的美食爱好、音乐偏好、美色喜好,所以统治者不应置百姓的审美需求于不顾而去单独享乐。最后,对于艺术创作者而言,为能创作具有艺术感召力的作品,创作者应在人格修养上做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章句上》),[2](P62)亦即用仁义道德涵养自己,时刻积累浩然正气,并让其蓬勃生长、永不衰竭。倘能如此,则就能使得正气完满,从而为创作高雅的艺术作品做好充足的准备。
荀子的文艺思想。首先,关于审美享乐。荀子认为,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其审美官能都一样:《荀子·荣辱》云“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3](P63)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追求美色、美声、美味、美嗅、美的安逸乃人之常情:《荀子·王霸》云“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3](P211)正因为有许许多多可以带给人以美感的物质,故而人的口鼻耳目与身体之所需可得到充分的满足:《荀子·礼论》云“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3](P346-347)其次,关于文艺经典。荀子认为圣人是整理与传播文艺经典的关键性人物:《荀子·儒效》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3](P133)文艺经典是圣人阐发思想主张的媒介,而圣人的思想主张又是天下思想之核心枢纽,历代帝王的思想也在此得以统一规整。再次,关于音乐审美。荀子认为音乐能带给人快乐,这是人的性情所天然喜欢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荀子·乐论》)[3](P379)由于人的天性是寻求快乐,而音乐不但带给人快乐,而且可愉悦性情,尤其是高雅的音乐还可使人发扬善心、祛除邪气,因此,不管是地位高贵的君子,还是地位低下的小人,都喜欢带给他们快乐的音乐:“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故乐者,治人之盛者也。”(《荀子·乐论》)[3](P382)君子用音乐来修道,小人用音乐来满足情欲,但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进而言之,治国之圣人若能用它来移风易俗,则可使天下之人皆来归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荀子·乐论》)[3](P381)故此可曰,音乐是天下大同之利器,是中和人性之纲纪,是调和性情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乐论》)[3](P380)最后,关于人格修养。荀子认为,人的天性是清白无染的,而道德修养又是人应该努力实践的,若能将道德修养添加于清白无染的天性上,必将成为道德圣人:“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3](P366)由此可见,先秦儒家追求的道德是一种“躬身内求”的主体性道德,他们特别看重艺术的个体修身价值。[1]因此,那些有志于求道的君子若想成为圣人,就应朝着“全粹之美”的方向努力迈进:“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荀子·劝学》)[3](P18-19)只有学问全面,道德纯粹,才能修炼出理想的人格。
(二)道家文艺思想的主旨:艺以合道 相对于儒家而言,道家更提倡艺术化生存,更愿意把自然当作艺术来欣赏,并对艺术家和艺术想象有着超拔的要求。
老子的文艺思想。老子认为,不同层次的人在理解与实践“道”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做法,但不管怎样,“道”的美却是不变的:“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老子·四十一章》)[5](P228-229)不管是上士、中士,还是下士,不管他们怎么对待“道”,“道”的美就像是空谷,你很难把握它,尤其是它的质真(本质纯真)、大白(高洁廉明)、大方(伟大的方正)、大器(伟大的器皿)、大音(伟大的音乐)、大象(伟大的形象)等美学属性是若隐若现的,是需要认真体验的。因此,老子提倡一种“与道合一”的艺术化生存(虚静无为、无知无欲、回归婴儿、与世无争),来体验“道”之美。他要求人们把大自然当成艺术品来欣赏(比如对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大自然),尽管大自然没有具体的声音和形象,但却能发出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呈现世界上最伟大的形象。而对于艺术,从表面看,老子是否定艺术的;[6]若从深层看,他对人为的艺术与享乐持反对态度:“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十二章》)[5](P106)老子认为,向内的无欲的“腹”是人的,而非向外的逐欲的“目”。因此,只有涵养虚静无欲的心性,才能从感官享乐中挣脱出来,达到“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老子·二十三章》)[5](P157)的“与道合一”之艺术化生存境界。另外,“见素抱朴”(《老子·十九章》)[5](P136)、“涤除玄鉴”(《老子·十章》)[5](P96)等思想,亦可视为老子对艺术创作者“抛弃功利,纯任自然”心境的特别要求。
庄子的文艺思想。庄子倡导人们在开展艺术想象之际应“虚静“、“物化”、“得意忘言”,这有利于创作者进入心无杂念、与艺术形象合而为一的,超越语言限制的深层感悟状态。至于如何达到“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庄子·天道》)[7](P340)的虚静状态,庄子认为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心斋”(《庄子·人间世》)、“坐忘”(《庄子·大宗师》)。关于“物化”,庄子介绍了“庄周梦蝶”的亲身经历;关于“得意忘言”,庄子列举了“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7](P725)庄子对于“得意忘言”的敏锐观察与探析,揭示了世界的无限宏富与人类的有限认识水平之间的矛盾,揭示了人的思维活动与语言表达能力之间的矛盾,并为弥补其间差距、驰骋思维想象和文辞挥洒力量开拓疆域。[8]
(三)墨家文艺思想的主旨:艺不与政相争 关于文艺,墨子认为统治者应该“非乐”。墨子提出非乐问题的出发点,是对当时统治者奢侈腐败行为的强烈不满和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9]《墨子·非乐上》曰:“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10](P273-274)他反对统治者不顾苍生之生计而追求个人享乐,为此他喊出“为乐,非也”的口号。墨子进一步指出“非乐”的原因,“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灸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上》)[10](P274)因此,墨子非乐,否定的是那种独自享乐、不顾百姓生计的超前享乐,若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君主能够恪行与民同乐的审美原则,可见,墨子是并不反对统治者开展艺术享乐的。
(四)法家文艺思想的主旨:艺以实用至上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讲求艺术的内在实用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11](P266)墨子话语直白而不动听,韩非子为其进行辩护。韩非子认为艺术的内在实用性高于并超越外在的形式美,否则就会造成外在的形式美超过内在实用美的“买椟还珠”似的尴尬局面。因此,韩非子特别重视艺术作品的内在涵养:“和氏之壁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韩非子·解老》)[11](P133)这里的“质美”即要求“首先应该让内在的内容和意义美起来”,如果内在的质不美,那外在的形式无论有多美,都是枉费心机、适得其反的。
综上所述,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论及文艺生活、文艺创作、文艺欣赏、文艺功用、文艺教化、艺术化生存等诸多方面。他们直言不讳,坦诚己见。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偏颇,但其智慧却给后人以启迪。因此,在文艺思想的开拓性方面,先秦诸子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淹没的。
二、先秦诸子文艺思想“反思性、批判性、超越性”特色契合于艺术的现代性
关于现代性的定义可能不下几十种。[12]英国的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一种社会生活或社会组织模式。[13](P1)德国的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它指的首先是这样一个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和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因此置身其中的人们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和标准。从实证的观点看,现代性是以个人的自由为特征的。[14](P25)法国的福柯认为,现代性指的是一种态度,即思想和感觉、行为和举止的方式;[14](P29)在启蒙的时代,其态度构成一种特殊的哲学气质,即批判的精神。[14](P35)以上是西方思想界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若将现代性概念运用到文艺上来,福柯的解说应该更为契合些。而在笔者看来,“文艺思想的现代性”是指文艺思想“运用现代性眼光,对当前文艺及其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性反思与深刻批判,并引领同时代文艺超越现有思路方法和社会禁锢,以全新面貌走向未来”的一种属性。文艺思想的现代性至少包含着“反思性、批判性、超越性”等特质。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文艺思想具有“反思性、批判性、超越性”等特质,那它就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如果该文艺思想不具有“反思性、批判性与超越性”等特质,那它就不具有现代性。而令人惊叹的是,现代性的这些特质其实早在先秦诸子文艺思想那里即已暗露端倪。
首先,在反思性方面,道家关于审美享乐对自然人性的戕害有着深刻的认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5](P106)老子明确反对审美享乐,庄子也认为包括文艺在内的人为的东西是不美的,是应制止的:“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庄子·胠箧》)[7](P259)那些人为的东西只会纵容人们去刻意追求享乐,让人们失去质朴无欲的天性。庄子还认为“天地有大美不言”(《庄子·知北游》),故此我们应该“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7](P563),以求在虚静无欲中臻达道德与美的最高境界:“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7](P337)
其次,在批判性方面,墨子对统治者一味地审美享乐有着深刻的批判。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为乐,非也”的批判。首先是“为乐”不符合万民之利:“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墨子·非乐上》)[10](P274)其次是“为乐”无助于社会治理:“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墨子·非乐上》)[10](P276)最后是“为乐”会使得百姓像君主一样聃于荒淫, 荒废劳作:“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墨子·非乐上》)[10](P277)
最后,在超越性方面,墨家要求统治者应超越个人享乐,在民众已然安居乐业之后再去享乐。这种观点得到了儒家亚圣孟子的发扬:“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2](P3)孟子以周文王为例,认为周文王虽然建造了“灵台、灵沼”等高台深池,但由于与民同乐,故而获得了真正的快乐。荀子则要求君子应该超越现有状态的局限,向着知识全面、德性纯粹的“全粹之人”方向努力迈进。而庄子在“梓庆为锯”、“佝偻承蜩”等寓言故事中谈到梓庆“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佝偻丈人“不以万物易蜩之翼”(《庄子·达生》)[7](P472),其实也是间接地向艺术创作者发出超越当前功利的号召。
那么,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为何能暗含文艺的现代性呢?主要是因为现代性其实是每个时代的文艺思想应有之属性。通常情况下,那些能够健康发展的文艺思想其实都是“对人性反思、对社会批判、对自我超越”的,都具备“对文艺主题的反思、对主流思想的批判、对文艺现状的超越”等现代性特质。因此,先秦诸子身处学术思想发展的“黄金时代”,其文艺思想当然也是反思、批判与超越的。而由于封建治理的逐步牢固,先秦诸子之后的文艺思想较大程度地沾染了政治因素和官方观念,因而其“反思性、批判性、超越性”或多或少地丧失,虽然在魏晋风度和元曲创作中略有伸张,但大部分时期都处于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境况;而现当代文艺思潮乘着西学东渐之风,又刻意主张起文艺应该富有现代性,这便使人猛然想起先秦诸子。原来先秦诸子早就带着“现代性”傲立华夏两千余年了。
三、先秦诸子文艺思想现代性的当代启示:忘我、客观、实用、高雅
正因为先秦诸子文艺思想暗含着现代性,故而对当代艺术发展有着一定的启示效用。首先,在艺术修养方面,我们应该培养先秦诸子那种全然忘我的精神境界,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庄子·齐物论》云:“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7](P33)其次,在艺术创作方面,我们应“虚静”、“物化”、“得意忘言”,全然融入到艺术想象中去,以求达到“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庄子·天道》)[7](P340)的“天乐”境界。第三,在艺术接受方面,文艺欣赏者应该“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地追求客观,将文艺作品与艺术创作者放到其时代背景中、客观而全面地考察之,而非“六经注我”式的随意解读文艺作品。第四,在艺术的功用性与普及性方面,艺术创作者也应追求尽善尽美,不“以文害用”,能“与民同乐”,不去创造那些贵族式的、小众的文艺去娱乐少数人,尽量从有助于世的实用角度创造艺术精品。最后,在将艺术运用到生活方面,文艺创作者也应努力实践,争做高雅的“全粹之人”,为创作高雅的、典型的艺术精品而竭诚奉献、呕心沥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