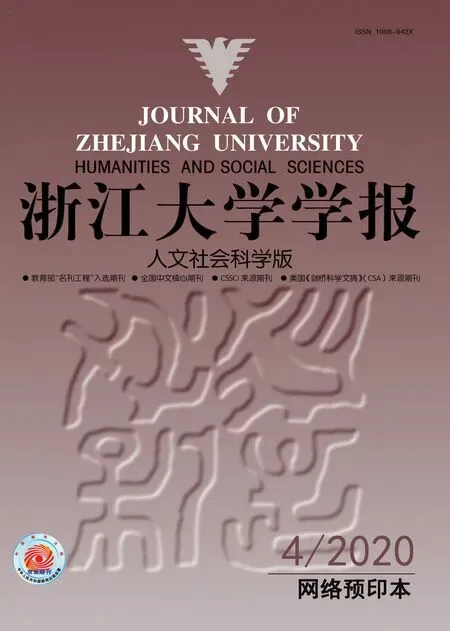理想主义的限度与超越
——基于马克思对《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自我评价的考察
刘同舫 佘梅溪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青年马克思于1836年10月初到柏林大学时依然保持理想主义的思想底色,一年之后却实现了从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向黑格尔哲学的转变,这一重大的思想转变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以文学创作为主,而文学作品与学术研究之间在话语体系上存在较大差异,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缺少学术研究的学理性和严谨性。从马克思这一时期的诗歌和剧本等文学作品中,我们无法寻找到马克思理想主义实质性变化的踪迹:诗歌创作的主旋律是“纯理想主义”[1]6的,并未实现对理想主义的超越,其折射出的理想主义变动非常细微;剧本被马克思认定为“不成功”的作品,其篇幅仅有一幕,且内容并未直接涉及黑格尔哲学及理想主义转向。然而,在这一时期唯一的一篇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中,马克思揭示了理想主义限度的表现形式,追溯了理想主义限度的浪漫主义根源,先后摒弃了康德、费希特抽象的理想主义,转向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实现了对理想主义限度的实质性超越。本文以马克思对小说的自我评价“理想主义渗透”[1]12为分析起点,试图阐明该小说虽具有理想主义的表现形式,但并未局限于抽象的理想层面,其内容落脚于非理想主义的现实因素,内含马克思的理想主义思想纠葛的独特见解。通过文本形式的选择,剖析马克思早期的理想主义转变,进而厘清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想主义的传承和超越,有助于发掘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明晰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过程。
一、 “理想主义渗透”: 马克思对小说的自我评价
马克思对《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的自我评价是“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1]12。对其中“渗透”一词的理解,将直接影响对小说中理想主义把握的准确度。“渗透”一词比较微妙,它有两种不同程度的释义:一种是“渗入、透过”;另一种是“逐渐进入”。结合理想主义特质审视小说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自我评价中所说的“渗透”更贴合后一种释义,即理想主义虽然渗入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却并未彻底渗入其内容。
《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的非现实性、抽象性特征,表明理想主义已然渗入它的文本形式。首先,小说在章目形式上结构混乱,背离现实叙事的客观需要,存在理想主义的非现实性特征。小说共计10 000多字,自第10章开篇至第48章收尾,仅有24章,中间存在大量缺章;各章篇幅不平衡,部分章字数多达2 000余字,而部分章却仅有几句话,无序散漫,失之规整,同现实事件的演进不尽契合。其次,小说采用符号化形式塑造主要人物,具有理想主义的抽象性特征。小说以人物的名字为基线揭示人物的内在特性。例如,默腾(Merten)与马特(Martel)发音相似,而Martel在历史上有“锤子”之意,所以,默腾的出场动作就是击打费利克斯;玛格达莱娜(Magdalene)被视为仙女,就在于德语“Magdalene”与“抹大拉的马利亚”即耶稣忠实的女性门徒的名字拼写一致。抽象的符号化描述虽然在形式上丰富了人物的象征意义,但在实质上却剥离了人物的现实存在,以致小说人物的具体形象与现实发生割裂,在内容上呈现出理想主义的非现实性。
尽管理想主义已渗入小说形式并对其内容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小说因其内容的现实性“抵御”了理想主义的彻底“渗入”。一方面,小说的环境背景具有现实色彩。小说对自然环境描写着墨甚少,而对社会现实环境描写格外丰满。如小说中描述道:“我内心深处感到激动,我端详着天地万物、自己的内心和上述这二十五塔勒(这三个词包含着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实体啊!它们无所不在,它们发出的声响宛如仙乐,它们使人想起末日审判和国库)”[2]807;“爱司已成了一切近代法学的基础”[2]822(扑克牌中“爱司”的德文“Aβ”与拉丁文的“As”即“金钱”发音相近);“他们远远地坐着,使执政者和平民之间保留一定的空隙”[2]823;“他是怀着迷信的崇敬心来侍候这条狗的,它在桌旁的座位是最雅致的”[2]824;等等。小说描述了“二十五塔勒”对人的吸引,刻画出金钱致人癫狂的状态;强调“爱司”的法学地位,揭露社会中的物质崇拜;展现不同阶级的日常生活,批判无处不在的阶级压迫;神化狗的存在,讥讽封建迷信……使现实的“光束”透过理想主义形式,让小说呈现出现实主义的黑色幽默性和深刻讽刺性。另一方面,小说内容的展开依托现实依据。默腾与德语“Martel”(锤子)谐音,他的所作所为均与现实的锤子及其基本功能存在一定的必然联系,如小说中写道,默腾的手掌在触碰费利克斯时让“费利克斯确实相信他受到了锤子的抚爱”[2]810。狗与圣使徒博尼法齐乌斯同名,以致它的失踪使“大家都被罩在一片漆黑中,接着一个充满不祥之兆的、急风暴雨的夜晚降临了”[2]824,如同圣使徒消失一般引发令人胆战心惊的轩然大波。主人公“我”的观点和行为具有明显的解释信息、推进情节的作用,增强了现实在小说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虽具有理想主义的表现形式,但内容却落脚于非理想主义的现实存在。理想主义只达到渗入小说表层的程度,这是马克思曾经坚持的理想主义对意欲表达现实的小说创作产生影响的结果。马克思思想深处的理想主义纠葛充分表现在小说形式的理想主义同内容的非理想主义的冲突中,其矛盾心理与复杂情感加大了小说创作的难度,马克思自身也承认这篇“幽默小说”是“勉强”写出的。马克思在小说创作中的思想冲突使其进一步察觉到理想主义“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奔放的思路的纯形式艺术”[1]12。其理想主义思想遭遇非理想主义的现实冲击,马克思正是在现实冲击下展开了对理想主义的反思性理解。
二、 马克思的理解: 何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渗透”了的小说《斯考尔皮昂和弗利克斯》不同于“纯理想主义”的诗歌,它以现实为航标,运用理想主义形式呈现现实内容,表明马克思曾经坚持的理想主义发生动摇,势必导致他对理想主义及其现实意义的理解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马克思利用小说的现世性(1)现世性是指文本是客观存在于世界中的现象,投射并构成现实世界。小说能够实现理想主义要素与现实要素的共存,其所展示的虚构幻想不等同于应然的理想存在,幻想看似与现实对立,实则是扭曲的现实。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萨义德就曾指出:“文本是现世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事件,而且即便是在文本似乎否认这一点时,仍然是它们在其中被发现并得到释义的社会世态、人类生活和历史生活各阶段(moments)的一部分。”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页。特质,结合现实理解理想主义,从三个方面剖析理想主义限度的表现。首先,马克思披露理想主义之理想对人的创造物——财富的侵占。小说第10章从现实的物质生活出发,指出财富由凡人创造,但“凡人的权力不能享有这笔钱,只有那统治天宇的最高权力”[2]807,即理想的上帝才有资格享有。其次,揭示理想主义之理想对现实的人的侵占。小说第19章写道,“我们看到远处宏伟高尚的、光芒四射的思想,我们预感到着了魔的痛苦”[2]810。理想本应是现实所趋向的模范,但理想主义之理想只能带给现实人类被操纵的痛苦。再次,揭露理想主义之理想的存在基础与现实对立。马克思在小说第39章指出,理想存在的合理性源于神圣权力,但神圣权力存在的基础并非现实,而是幻想。理想一旦离开幻想的遮掩,内在的虚无性便暴露无遗。即使理想依凭幻想获得存在,它本身对现实的脱离也必然造成理想的非现实性,致使其与现实对立乃至割裂。因此,理想主义中理想的生成和存在均与现实处于对立且无法弥合的矛盾状态。
理想主义是有限度的存在,而其限度的产生根源与浪漫主义密切关联。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求学期间曾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而理想主义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带有浪漫主义的种种痕迹,因而他在小说中不自觉地从浪漫主义视角探寻理想主义限度的根源及其解决方案。一是揭示理想主义的本体是源于浪漫主义的抽象的普遍精神。小说描写最高权力统治宇宙的状态时认为,作为理想主义本体的最高权力只是虚构故事中的角色,看似涵盖现实万物,却并不具有现实支撑,反倒以抽象的普遍精神为存在形态。“在本体意义上说,浪漫主义始作俑于万物的一(oneness)。这种普遍的一在自然的多样性中展现自身,并作为精神——神圣的精神拂过万物。”[3]6理想主义的本体渊源是抽象的普遍精神而非现实世界,这势必造成理想与现实既相互脱离又彼此对立的外在关系。二是揭示理想主义合理化自身存在的方式的抽象性。理想主义采取了同浪漫主义一致的生成路径:“实在的第一范畴是生成。生成被认为是一种流动”[3]64,通过抽象生成的方式将世界存在的根源归于抽象自身,证实自身存在的现实意义。鉴于此,马克思通过小说表达对理想主义生成路径合理性的否定态度。在小说中,如流动的河水一般普通平常的双眼的灵魂是“蓝色染匠”[2]809,“蓝色染匠”(Blaufärber)在德文中有“撒谎者”之意。斯考尔皮昂和默腾受到神圣存在的影响,但未发生具有创造性意义的生成,“正像一个胚胎尚未挣脱世间关系而形成一种特殊形状那样,他俩身体各部分的联结力在一片正在膨胀的混沌状态中也完全松散了,结果是他俩的鼻子跌落在肚脐上,而脑袋掉在地上”[2]821。无论抽象的普遍精神采取何种形式的发展演变,都属于思辨的逻辑,而逻辑的严密性不能改变其抽象本质,抽象逻辑创造的仍是虚假现实。马克思利用熟识的浪漫主义视角剖析理想主义如何通过抽象性本体与抽象性生成,构建起非现实的、抽象的理想世界,意识到理想主义非现实的抽象本质,决定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是理想主义的固有限度[2]7。
在认识理想主义的限度和质疑理想主义的合理性的基础上,马克思重新审视理想主义的意义,将理想主义从意欲表达的思想内容转变为表达思想的手段。他运用理想主义惯用的象征手法,但摒弃了这一手法的虚构性质,将象征改造为辅助理解现实的工具。默腾象征拥有锤子般权力的统治者,斯考尔皮昂象征蝎子般狠毒的统治阶级,玛格达莱娜象征无批判思想的卫道女等,马克思通过赋予象征以现实内容,基本否定了理想主义试图构建的具有欺骗性质的存在。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结合现实因素,利用理想主义抽象逻辑推演的优势,表达自身对现实发展演进的理解。在小说第21章中,马克思推演默腾(Merten)一家可能是战神玛尔斯(Mars)的后代:“Mars的第二格为Martis,希腊语中的第四格为Martin,由此而得出Mertin和Merten”[2]811,且职业为裁缝的“默腾”与能够实施暴力的工具“锤子”谐音,“战神的技艺同裁缝的技艺相像之处就是截裁,因为他截手裁脚,截掉人间的幸福”[2]811。默腾的儿子名叫斯考尔皮昂(Scorpion),“Scorpion”这个词的本义是“蝎子”,蝎子是“一种能用眼光杀害人的有毒动物,它所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它的目光能摧残破坏——这是对战争的绝妙讽喻,战争的目光是致命的,战争的后果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内部出血、再也无法治愈的斑斑伤痕”[2]811-812。继而依据默腾的信仰、社会文化演变、当地风俗习惯、民族血统等综合要素再次确证推演的合理性。马克思将理想主义象征表达与现实因素相融合,将抽象逻辑推演与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在创作“理想主义渗透”了的小说中实现对现实的分析反思,比较客观地肯定了理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担当现实表达工具的基本功能。
三、 马克思对理想主义限度的超越
在小说的逻辑展开中,马克思逐渐表现出对康德和费希特式理想主义的抵触,反倒对黑格尔逻辑学式的现实主义较为青睐,这鲜明地体现出批判现实的创作旨趣和深入历史的现实精神在马克思此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从抽象中把握的现实,小说同样内含对黑格尔被理想主义同化的虚假现实的批判,这进一步凸显出马克思以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为特征的、对理想主义限度的实质性超越。
马克思通过对康德理想主义中理性认识之断裂的指认,否定实践理性的能力,摒弃了康德的理想主义。马克思在小说第19章中直接描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断裂状态,“我们喜爱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万木葱茏的世界,我们看到远处宏伟高尚的、光芒四射的思想”[2]810。“万木葱茏的世界”代指康德的现象界,而现象界是物自体展露于世人面前的形式,世人在现象界中能够认知模糊、不真切的物自体,但是“一旦我们认出它们,它们就像美丽、优雅、欢乐三女神一样,羞怯地畏缩后退”[2]810。物自体在康德理想主义中是理性认识能力无法直接把握的存在,所以现象界显现的并非物自体本身,只是看似触手可及的镜花水月。马克思对康德理性认识的描述并非意在表达认同,而是力图展开批判。他系统批判了康德理想主义割裂现象界与物自体的目的,即开发实践理性以形成能够指导人类进行科学判断、实施合理行为、建构理想世界、获得不受认识形式限制的自由理想领域的绝对命令(2)康德的理想主义试图通过割裂现象界与物自体明确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界限,为信仰留有余地,实现对实践理性的开发,让实践理性的道德意志形成绝对命令。。小说第27章引用《新约全书》中“山羊置于左,绵羊置于右”的典故以探讨“左右问题”。山羊与绵羊在《新约全书》中代表拥有不同信仰的人,左或右是人选择不同信仰的结果。马克思对“左右问题”的探讨看似在研判信仰问题,实则是探寻人对理想性存在的选择。他指出“左”与“右”“不过是两个相对的概念”[2]816,否认了确切的理想性存在,直接取消了康德理想主义的追求目标。即使理想真实存在,现实根基薄弱的人类实践理性也不能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绝对命令,无法做出获取理想性存在的正确判断。“如果靡菲斯特斐勒司在这时出现,我就会变成浮士德,因为很清楚,我们大家都是浮士德,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个方向是右,哪个方向是左……”[2]817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康德理想主义所导向的理想是与现实相对立的虚幻假象,康德对实践理性的开发也难以实现理想并解决理想主义的限度问题。
面对康德理想主义内部明显的断裂,马克思曾试图从费希特的思想中寻求化解断裂的理论支撑。他肯定费希特思想的“绝对自我内部存在非我”这一具有辩证关系的观点,在小说中发出“啊!我是自己的替身”[2]828的感叹,以表明他对自我与非我之同一性观点的把握。但是,马克思所欣赏的仅限于费希特的辩证关系,他并不认可费希特为了弥合康德理想主义的内部断裂而创造“绝对自我”的解决方案(3)费希特发展了康德的理想主义,他认为物自体是自我设定的非我,将物自体与现象界统一于绝对自我的辩证运动,通过强调人的自我意识的实践创造能力弥合康德理想主义内部割裂的缺陷。。马克思认为,“绝对自我”实现统一的基础是彻底的主观性,纯主观的“绝对自我”不能够创造任何现实存在,主观性基础将导致客观现实更加遥远,依然无法打破理想主义限度的对立性桎梏。于是,马克思转而试图在现实的生活中找寻人的存在依据,展示人的现实生活对人之存在的影响。他在小说中将人的生活描述为圆形的竞技场,“在我们摔倒在沙地上,角斗士即生活把我们杀掉之前,我们一直绕着圈子奔跑,寻找它的左右两边”[2]817。圆圈中左右的位置根据人的奔跑不断发生变化,人的现实活动能够打破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状态,超越理想主义设定的理想性存在。马克思通过将现实因素引入反思理想主义,促使自我走出主观世界,走向现实的生活世界,超越费希特“绝对自我”的狭隘性。他反思的基础已然扎根于现实,彻底否定理想主义中抽象理想的存在,形成了基于现实的批判意识。
为了彻底解决理想与现实对立的问题,青年马克思继续探寻协调理想与现实关系的理论道路。他欣赏黑格尔将历史、社会等现实因素与理想辩证融合于一体,运用辩证思维调和理想主义内部对立的高明之举。但随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入理解,马克思察觉到黑格尔哲学在实现自身圆满的同时,也暴露了绝对圆满外部的现实缺陷,即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社会是被理想主义同化的虚假现实,不具备解决理想与现实对立问题的可行性和发展性。他立足现实的历史发展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虚假现实,找寻到一条由现实走向理想的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了对理想主义限度的超越。
第一,否定黑格尔理想主义中虚假现实的归宿——以意志为根据的国家。小说在第27章结尾呼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救世主”[2]817。于是,第28章的开篇出现了一位国家官僚的代表恩格尔伯特。恩格尔伯特像一条干瘪的蜥蜴,有着骇人的高颧骨,火红的鼻子,嗓音嘈杂含混,讲话逻辑混乱还结巴,认为“鸽子的眼睛是最聪慧的,他本人虽然不是鸽子,但至少对于理智来说他是个聋子”[2]819。在西方,蜥蜴是权力、邪恶的象征,红色是暴力的象征,而鸽子的眼睛就是红色的,且在德文中“Taube”(鸽子)与“Tauber”(聋子)发音相近。究其旨意,在于抨击黑格尔的救世主是依靠邪恶权力和暴力爬上统治地位的小丑,否定黑格尔理想主义的国家观,即国家是人的目的及最高义务,人能够在维护国家中获得理想性存在(4)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人“在世上行进的神”,“国家的基础就是作为意志来自我实现的理性的权力”,是理想主义中理想性存在的现实形态,服务于理想主义的普遍精神(理性)。维护国家就是遵循理性的发展,而理性与人的发展具有统一性,因此,人能够在维护国家中实现自我。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8页。。
第二,批判黑格尔哲学中国家的现实统治形式即长子继承制的理想主义本质。马克思在小说第29章中剖析了长子继承制,揭示出缺少现实存在合理性的国家的维权奥秘。他嘲讽“长子继承权是贵族政体的小浴室”[2]820,直指长子继承制作为国家展现理性力量的现实形式,是在封闭的理想主义普遍精神保护下的国家制度。长子继承制尽管在形式上赋予长子绝对的权力,保障了权力接续的稳定性,但这种封闭式的维护只能起到短暂的效果,且对人的现实创造能力造成实质性的摧毁,在给“一家的长子镀上一层银”的同时也给整个政体“印上一层愁苦的浪漫主义惨淡色彩”[2]820。长子继承制看似是保障国家长期稳定存在的现实制度样态,实则是逃避现实、陈旧迂腐的表征,它以抽象普遍精神构筑的密闭体系将统治阶级与现实历史发展隔绝,创造虚假现实的抽象永恒,以致“当今之世是写不出叙事史诗的”[2]820-821,结果只能是理想主义的虚假现实与历史发展的现实之间发生彻底的断裂,无法走向真正的理想。
第三,探究国家现实的历史发展,理清现实走向理想的基本路径。马克思追溯国家的历史渊源,解析影响其发展的现实因素,以历史发展的现实取代理想主义抽象普遍精神的逻辑发展的“现实”。他以裁缝出身的默腾为例剖析“默腾国家机构”[2]823的发展史。一方面,马克思详尽推敲默腾的民族血统,将他认定为战神的后代;另一方面,马克思探究默腾早期的财富积累,将他描述为法兰克王国的奠基人克洛维的马裤裁制者,且因克洛维穿了此条马裤赢得普瓦捷会战的胜利而获得两百金币的奖赏,最终建立起自己的“默腾国家机构”。马克思笔下默腾发家的因素包含民族、劳动、暴力以及资本等,他指出人的现实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构成最初的资本积累,并借助暴力与劳动分工产生阶级,最终构建了暴力机器——国家。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否定黑格尔哲学中普遍精神发展的动力内核,而且较为真切地揭示出资本、暴力和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内在规律。
第四,打破理想主义的抽象性,在现实劳动中探寻理想存在。马克思认为,个人可以通过劳动争取理想的生活,但个人一旦凌驾于他人权利之上,便会失去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小说宣扬了那些“普通的人,即没有长子继承权的人,得跟生活的急流搏斗,投身波涛澎湃的大海,在幽深的海底夺取普罗米修斯右手中的明珠”[2]820。相反,默腾却因实施贪婪的掠夺、锤子般的暴力而使自己在那只与圣使徒同名的狗患病时落入无人相助的孤立境地。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发现蕴藏在人民群众内部的现实力量,认识到人的活动能够推动现实走向理想进而打破理想主义限度。
总之,马克思批判理想主义的起点是以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在现实的历史维度中认清自己实际情况的自我反思。他运用文学的表达方式,在自由创作中反思自我、反思先哲、感知现实、认知理想,跳出先哲构建的理想主义世界,追溯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渊源,在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一致性的生成方式中认识到理想主义的限度,形成了独立的基于现实的批判意识,完成了对理想主义所构建的虚假现实的实质性超越。马克思摒弃康德、费希特抽象的理想主义,转向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继承,是其独立的现实批判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这种基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成为其不断突破超越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