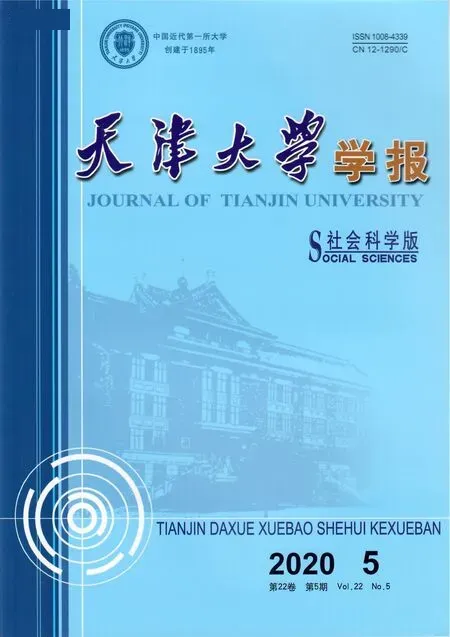顾颉刚的考古实物思想及古迹古物考察述论
封 磊
(延安大学历史学院, 延安 716000)
顾颉刚(1893—1980)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现代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目前,学界对顾先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学术活动等方面[1]。顾先生因古史辨伪而知名,但不影响他对考古实物资料的重视。有学者指出,在顾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实地考察也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顾先生对考古实物资料的重视与实地考察的结合,成为顾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学术生涯中颇为重要的学术活动[2]。但是,目前已有研究多局限于顾先生的史料学思想[3],而对顾先生的考古实物思想渊源及其产生的学术背景却语焉不详,对顾先生在考古思想驱使下的古迹古物调查活动却多有忽略。
一、重视考古实物的思想渊源
顾先生作为书斋式的经史学者,注重从考古学上重视实物资料与田野调查,始于在北京大学求学和从事古史研究。此处的实物是指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尤其是近代甲骨文发现以来被学界普遍关注的以考古发掘物为主的出土材料。
1918年发轫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使受传统经史教育的顾颉刚的思想发生转变,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发出的“到民间去”的口号所体现的对民间资料所抱持的民主与科学态度。受此影响,顾先生将史料分为三种:实物、记载与传说。这三种史料“都有可用的和不可用的,也有不可用于此而可用于彼的”[4]。大体上,实物是直接史料,记载和传说是间接史料。顾先生毕竟是以分析经史文献见长的学者,但这不影响他对实物资料的重视,并肯定用实物材料解决古史问题是“正当的方法”;同时,顾先生对当时“颇有尊遗作品而轻载记的趋向”没有盲从或偏执一端,而是另辟蹊径,力图通过对古书等文献材料的考证辨伪和对考古实物资料的参证来构建现代中国的科学史学:古代的实物材料固然直接出于古人,文献记载的材料也并非尽出于后人;如果说文献记载的材料多伪作且难以考定,那么如何保证实物材料纯粹无伪作而容易考定呢?“若是多信一点遗作品,少信一点载记,这是很应该的;若说惟有遗作品为可信而载记可以不理,便未免偏心了”[5]。可见,在顾先生看来,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材料具有平等的价值,应同时并重,并具有互补、互证的关系。
此外,顾先生还认为,自己的古史辨伪工作是为将来重建古史做准备,而重建古史的根本出路在于考古学,即寄望于地下实物资料的发掘。1920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步之际,顾先生以一个传统的经史学者,以地下实物重建古史的卓识,是难能可贵和颇具预见性的。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顾先生对考古实物作为史料是极为重视并积极提倡和实践的。
顾先生重视考古实物的思想,源于在北大求学期间深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与胡适倡导的科学地“整理国故”的影响,成为顾先生重视考古实物思想的学术渊源。
在回顾自己早期的学术经历时,顾先生认为自己的学术导师是王国维而非胡适:“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6]。他曾两次拜访王国维,还写信欲拜师门下,愿“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7]。虽然顾先生曾承认自己的古史思想受胡适、钱玄同的影响较大,但这种影响在早年尚属引导性的“启发和帮助”。因此,从顾先生本人的学术立场来看,王国维才是他真正的学术导师。正是在接触王国维及其著作后,顾先生感叹自己“学问的根柢打得太差了,考古学的素养也太缺乏了”,意识到“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这条路是大路”[6]44。从而激发其对考古学、古器物学的学习及对甲骨文、金文等出土实物的重视、研读和运用。1920年代,顾先生对古器物学产生极大兴趣,曾编辑“古器文书目”,将“研究古器物学”列入其研究古史的计划,还欲厘定传世古器的时代,使之与经籍相印证。在《顾颉刚读书笔记》中也常见他对“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如在《古人日用器物当作考定》的笔记中:“予常欲据地下发现之实物,及各时代之图画,加以经史中之记载,将古人衣、食、住、行、娱乐、武事各项考定出来”[8]。据《整理古籍目的在批判接受》记载:“将来地下发掘工作一定大发达,也必须将古书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实物和书籍记载相印证,从两重证据法上作确实的考定”[8]249-250。
不惟如此,顾先生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还提出利用民俗学、民族学实物资料研究和佐证古史的观点。如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的自序中写道:“既可用了考古学的成绩作信史的建设,又可用了民俗学的方法作神话和传说的建设。”[6]1-2认为研究经学“除经书以外,还要读‘子书’等,并看甲骨文、金文,看地下出来的材料,更要研究现代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古代的社会现象已没有了,但在某些少数民族的生活中还存在着”[9]。这说明顾先生还将民族学、民俗学的方法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相结合,将中原地区汉族的文献记载与边缘地区的民族文献、实物遗存进行参证、互证,这无疑是对“二重证据法”的创新与发展。这种思想对现今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的发展也颇具指导意义。
此外,顾先生重视考古实物的思想还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是胡适倡导的科学地“整理国故”的影响。1922年,北大成立研究所国学门。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史科系的学者发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要求扩充“国学”的研究范围与资料来源,并列出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风俗史等10项内容作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系统[10]。这与其说是一份“国学宣言”,毋宁说是一份打破以往以儒家经典为圭臬的主流学术模式,以平等的、科学的眼光看待其他研究领域和材料。可以说,这是一份向现代社会科学进军的纲领性的指导文件。国学门成立后,又将“歌谣征集处”(后改为“歌谣研究会”)改隶其下,下设编辑室、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等机构,发行《歌谣周刊》。而在1918年,顾先生就因率先响应刘半农等人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而“以搜集歌谣出了名”,成为“研究歌谣的专家”[11],刘半农就此称赞顾先生:“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11]23。
不得不说,胡适倡导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实是以西方的社会科学来解释和研究中国文化,这对顾先生一直运用“故事的眼光”来研究历史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的方法实施于各种材料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结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因此,“整理国故”成为顾先生学术生涯中一次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的转向。可以说,《宣言》对科学方法的号召及对各种材料(包括地下与地上)的平视态度,是对顾先生早已开始的学术思索与田野实践的契合与肯定,因而在这段时间,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成为顾先生用力最多、成绩最显著的学术事业。可以说,顾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践行《宣言》的号召,成为“把口头的主义作事实的研究”[6]34的第一人。
在实际研究中,顾先生也自觉地号召、利用传世或考古新发现的实物以印证或考辨古史。1926年,顾先生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撰写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提到:“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研究学问的人只该问这是不是一件事实……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古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12]可见,顾先生已经将民间地上的实物资料与传统的经史典籍置于同等地位,平等的看待实物遗存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同年,顾先生到厦门大学任职,在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撰写的《缘起》一文认为:“学问应以实物为对象,书本不过是实物的记录”,“掘地看古人的生活”是“求真”之途[7]238。在厦门期间,顾先生还与陈万里数次前往泉州访古调查[13]。1927年在为中山大学创立的《民俗》周刊作《发刊词》一文,顾先生认为到实地搜罗资料,挖掘民众的历史,可以“建设全民众的历史”[14]。可见,顾先生对实物资料的理解已经包含地上与地下,并充分肯定实物资料在研究历史时的重要作用。
顾先生重视考古实物在古史研究中的价值,并将考古实物尤其是将民间实物资料以平等的眼光纳入古史研究,成为他重视考古学与实地考察的学术动因。而从现代史料学的角度来看,则包含着几点颇值思索的意义。其一,顾先生以古史辨伪声名鹊起,以“古书论古书”为研究取径,在方法论上不免陷于唯书论的窠臼,顾先生正是从辨别史料真伪的角度来实现建立“信史”的鹄的,最终目标是确立确信的史料与史学规范,与现代西方版本校勘学或历史文献学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一点对于处在新旧杂陈、学术嬗递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尤显思想的超前和闪光之处。其二,顾先生以疑古辨伪为古史研究的抓手,看似在破除以往矢信不疑的新、旧史料,但又借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以证伪达到证实的目的而将考古实物纳入古史辨伪中,无疑具有史料学上的创新意义。其三,顾先生受胡适科学地“整理国故”的感召,将以往“不入流品”[15]的民间实物材料纳入经史研究,并重视对考古实物资料的考察与搜集,是将理论思索与实践运用紧密结合的体现,也使顾先生从书斋式的经史学家开始步入民间,走入社会,为之后开展的广泛的社会活动与边疆民族史地研究开启闸门。可以说,重视实物资料与实地考察一直贯穿顾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并将这一治学精神延续至1930年代在北平的学术事业中,成为顾先生在北大安定的环境下热衷于古迹古物的考察活动的思想渊薮。
二、古迹古物考察活动
1930年之前,顾先生主要从事古史辨伪研究,学术追求主要在于“求真”而非致用,“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还主张“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6]22。因而,1920年代先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执教期间,顾先生多专注于对歌谣文本等实物资料的收集与研究活动。而进入1930年代后,据《顾颉刚年谱》记载,顾先生从事古籍、古物等实物的搜集,以及亲身参与的实地考察或带有游览性质的活动共40次,如此密集的考察活动发端于1931年的一次考古旅行。
1929年底,顾先生告别在南方“如沸如羹”[16]的人事纠葛,执教于燕京大学。燕大安稳平静的生活与融洽的人际关系,为顾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成为顾先生学术生涯中学术成果最集中、最高产、最快速的时期。期间顾先生接连撰写七十余万字的论文,将十多年来积蓄心间的学术思考进行系统阐发。由于研读“用力过猛”,患上“怔忡病”,“一构思、一动笔,心旌动摇,好像要跳出腔子似的”[17],于是以考察各地的古迹古物状况为名义,与容庚、郑德坤、林悦明等人组成“燕大考古旅行团”,在1931年的四五月间,实地调查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等地的古迹古物,是为辛未访古。现以辛未访古为例,将顾先生在1930—1945年集中进行古迹古物调查活动的主要作为概述如下。
1.调查、搜集古代文物与文献
1931年,顾先生组织燕京大学考古旅行团的目标,一是为燕大图书馆与博物馆搜购文物;二是调查历史文化遗存的损失及现状[16]。顾先生等人一行,重点调查、搜集清代著名辨伪学者崔述的遗物与旧稿[18]。除此之外,顾先生还在文献搜集方面收获颇丰[16]。
2.展示、出版古迹古物考察纪录
1931年访古考察结束后,“与旅行同人编此行所摄照片目录,在校举办照片展览会”[14]216-217,并将此行记录写成《旅行后的悲哀》,以呼吁国人重视和保护古迹文物。此外,同行的郑德坤将考察收集的文物整理陈列,郑德坤还将各地见闻笔记写成英文报告,被其师洪业选入《燕京学报附录》,成为郑德坤用英文写作考古文物报告的开始,并为其以后开展田野工作和文物整理陈列奠定学术基础[19]。1935年顾先生任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时,组织吴世昌、张江裁带队调查北平古迹,以大小庙宇为重点,分别编著《北平岁时志》《北平史迹丛书》《北平庙宇通检》等书籍,后均由北平研究院出版。
3.开设古迹古物调查课程,开展实地考察与实习活动
为“养成学生自动搜集材料的兴趣,俾所学不受书本限制”,顾先生于1936年9月到1937年6月在燕大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14]262课程,每两个星期的周六下午,带学生到他事先选定的古建筑或重要古遗址所在地,或在北京城内,或在城外近郊,进行实地考察实习活动[20],该课程还吸引清华大学师生加入。全面抗战爆发后,1940年该课程还开设到了西迁至成都的齐鲁大学。不得不说,此时的顾先生已认识到古史研究与教育教学的活动中,应配合实物实地考察的方法,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这在当时是一种颇为超前的教学思想。现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作为当时受顾先生亲炙的学生之一,就表示顾先生的古迹古物实地调查思想与课程设置对自己历史教学与实地考察的史学方法产生了重要启示[21]。除此之外,这一创新性的课程思想与实践还是顾先生欲将古迹古物调查活动进行学术化、理论化、专门化与实践化的学术愿景的体现。
4.呼吁重视与保护古迹
其实早在1922年,顾先生在考察苏州保圣寺后,就撰文呼吁保护保圣寺唐代塑像。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专批一万元作为保护资金,使之得以成功保护[22]。1931年的实地考察古迹古物活动,顾先生在叹服先民之遗产“祖宗贻我之厚如此,拜倒于其下”的同时,更是对古迹文物在当时所遭受的急剧破坏,深表“及我之身将沦胥以铺”的恐惧心理,甚至表示“我宁毕世不见出土之古物,以待太平之世我曾孙玄孙之发掘,不顾其今日显现而明日澌灭”的愤懑情绪。因此,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对古迹文物的保护:“至于破坏之后如何保存,各种材料如何整理,则更为国人应负之使命,此文亦可为此种工作之前奏曲也”[16]。
或许由于其之前从事民俗研究的缘故,其对民间生活的状态略有认知,但也只局限于书本或文献资料,与真实的民间生活还存在相当距离。但1931年的访古考察除使其在亲眼目睹先民遗产堪忧的状况,感叹古迹古物在当时受到的剧烈破坏外,更重要的是看到“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后给予思想上的深刻触动,远非从事民俗学研究期间的肤浅体会。以致回到北平后,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与乡民贫困破败的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23],“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但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14]216。这次古迹古物考察中对底层民众生活的亲身感受,使顾先生“读书不求致用”的学术追求开始岔出另一条支线,使其学术重心由之前纯粹的学术研究转移至实地调查活动及社会活动中,以开展民众教育事业,促进民众觉醒。可以说,正是这次考古旅行,成为顾先生学术思想及其学术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如1947年,顾先生准备撰写自传,在拟定的“自传计划”中,“河南访古”和“第二度访古旅行”分别被列成小节的题目[17]3,足见这两次实地考察活动的影响之大。晚年时,顾先生在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与人生历程时,还曾多次提起和承认这次旅行对改变自己学术生涯的影响[23]69。总之,正是这次古迹古物考察旅行,成为顾先生学术生涯由“求真”转向“致用”的转折性的事件。
虽然现在较难评估顾先生的古迹古物考察活动的考古学价值或学术意义,但若将考察活动置于顾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来看,古迹古物考察活动也是顾先生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源于对考古学的倚重及对实物资料的重视,传统经史出身的顾先生为古史研究的需要,身体力行的进行实物搜集与实地考察,体现出严谨的治学精神。其二,顾先生毕竟是以传统经史文献分析见长的学者,若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调查方法与考古学的知识体系来评定其效果与意义,恐未必公允。顾先生持续进行的古迹古物考察活动,最大的价值在于他对始终以现代科学精神与严谨治学态度重建古史,以发扬和延续民族文化遗产。其三,还应从当时的学术环境来检讨。20世纪初至20年代,社会调查方法引介至中国,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社会调查更形成了一个高潮,大批学者、个人、团体、政府等就当时的社会焦点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与调查报告的撰写,可谓是“目光向下”的学术转型。这种“眼光向下”的学术事业其实是与现代民族国家在知识、文化、学术上的建构关联与共的[24]。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顾先生以“现代科学”的标准给予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的质问与考证,以建立科学可信的中国学术,这是顾先生最重要的贡献所在[25]。
三、结 语
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正如罗志田指出的,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纷涌踏来之际与影响之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学术分科趋势与潮流[26]。同时,新文化运动将科学作为两大基本的价值目标之一来追求,科学性成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这两大主题导致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以分科为基准来认识和研究中国学问,成为学人所遵循的主流取向,而以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学科化大约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此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27]。
考古学即是这一学术潮流中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20年代,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古史学者愈益认识到考古学及其实物材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价值,特别是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以及王国维在运用甲骨文、金文等实物材料方面取得学界公认的成就,为史学界运用实物等材料研究中国古史树立了榜样。而顾先生开始从事古史研究时,正值中国史学研究开始脱离传统经史研究的藩篱而逐渐走上现代分科、专科治研的轨道,也是国内史学界充分肯定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学者运用考古实物材料考证古史的成绩,并希望通过对考古实物材料的运用来建立中国新古史学的殷切之望。正是这一学术期待,对顾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对考古实物颇为重视与积极践行产生了深刻影响。
顾先生早年因古史辨伪而骤得大名,以致欲将古史研究作为终身之业。后又响应新文化运动中的“到民间去”的号召,从纯经史的考据考辨转向具有田野调查性质的歌谣收集和整理运动中,由此开启民俗研究的学术事业。在此过程中,顾先生意识到民间资料对古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但他并非只是对古史进行“破”的“反动”,更重要的是“立”的建设。正如顾先生对自己从事古史考辨的期待那样,“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尽“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可走,而我所走的路是审查书本上的史料”[28],而“立”的抓手即是考古学。正是这种分科治学的潮流,以及顾先生对中国史学科学化的孜孜追求,使他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做出很大贡献,也对顾先生后续的古史研究影响颇深。在抗战前夕,顾先生还与容庚一起搜罗甲骨文著作,已备古史研究之需。在《顾颉刚日记》中,顾先生读甲骨文、金文及相关著作的记载也有很多,至新中国成立后,伴随考古事业的发展,顾先生一直颇为注重出土材料。如1979年5月15日记载:“看《中华文史论丛》十辑。抄李平心《保卣铭新释》一页”;5月19日记载:“看曾宪通《试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29]等。
从此意义上来说,顾先生倡导并践行的古史辨伪是从对文献的考古上着手的,而这种“文献考古”的方法,所秉持的正是对史料的考证辨伪与史学研究的求真求实的科学审慎的精神,故而有必要打破传统史学的思维惯性,以平等、怀疑、科学的视角看待作为史料的考古实物资料。因此,顾先生源于对史学求真目标的追求以及对考古实物的重视,进而引发对古迹古物和实地考察的重视,直接促成顾先生在1930年代热衷于考古与访古的实地考察活动。此外,若从顾颉刚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来看,也正是在这次古迹古物考察过程中对民间社会的真实状况的体察,对顾先生学术理路的第三次转换产生了直接作用,即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从事边疆史地研究及边疆民族考察活动,并在1930—1940年代的边疆史地研究的多重学术场域中发挥了结点的作用[30]。
最后,笔者着重强调的是,顾先生在动荡不定的时局中能从书斋走向民间,从城市走向乡村,从内地走入边疆并转向边疆民族史地研究,固然有着时局的影响,但其重视实地考察及其身体力行却是导源于1930年代的古迹古物考察的系列活动。顾先生治学生涯中的“到民间去”、“到田野去”、“到边疆区”的三次转变,是留给笔者继续研究的课题。笔者拟另辟专文,以探讨顾先生学术生涯的三次转向及其背后更深层的学术、时局、国家等多元交织互动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