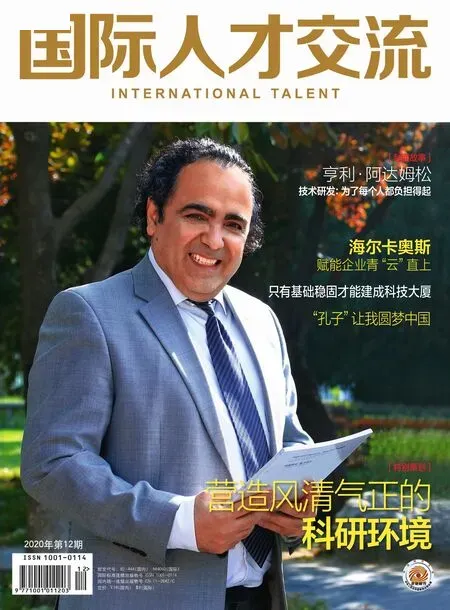12名外国专家谈如何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
文/徐家伟 杨艳
为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科研作风和学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2020年在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司的指导下,科技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开展了科研作风学风专题研究,并于11月在河北省科技厅、南京市科技局的支持下先后在两地召开外国专家座谈会。通过座谈、调研和访谈,本刊整理了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法国、丹麦、韩国、日本、古巴等近30位外国专家关于科研诚信、科研生态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下为观点摘编:

杰伊·西格尔(美国/瑞士)
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唐立(澳大利亚)
南京大学宜兴环保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萨万(加拿大)
西湖大学讲席教授,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保罗·博若思(英国/美国)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关于科研诚信和学术氛围
杰伊·西格尔认为,中国有很好的学术机构和大量学术人才,但是没有把现有的资源转换成更好的学术环境。因为中国有论资排辈的传统,这种传统会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但却不利于学术和科研创新。很多中国的科研人员到国外才更能感受到科研的自由,但是回到国内却必须要做一些上面安排的学术研究工作。
唐立认为,中国学术界发表期刊论文的压力太大了,很多期刊收到了很多来自中国学生、教职工提交的论文。很多论文和学术期刊的作者名单特别长,但实际上影响力很小。建议将工作重点放在那些扎扎实实做事情的人,而不是关注论文发表的数量。论文作者名单尽量短一些,影响力和意义更加深远一些。世界上很多大学正在发生改变。比如,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现在要求要更加关注论文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萨万认为,中国的博士生和其他学生都非常勤奋,未来都希望能够成为科学家。但是那些最好的学生,他们理想总是去清华、北大,这毫无疑问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前往最高的学府。但是我觉得在高中甚至更早的教育阶段,应该更好地引导中国的学生了解什么是科研,引导他们决定今后是去一所好大学还是去走科研道路。他认为,诚信是我们生活的基础。要尽早开设科学道德伦理课程,通过一些简单的以身作则的方式言传身教,比如在发表期刊论文的时候,不能抄袭,让学生接受关于科研伦理和道德价值观的学习,强化诚信的价值观。
保罗·博若思认为,要改变唯学历观,职业技能的认证水平应该远远大于对学历学位重视的程度。
波涛认为,激发创造力要凭本事吃饭,而非凭学历职称和职位吃饭。专家说话要实事求是。要尊重小人物和他们的观点。
罗杰威认为,博士生培养周期长、毕业程序复杂,目前的评估系统“一刀切”。博士生超过四年的培养周期拖延了他们投入科研行业的进程。而且博士生毕业资格审核制度过于严格,很多非常优秀的学生在最后的盲审中得到不太客观公正的结果,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在中国找到很好的工作。另外,以发核心期刊为毕业考核条件其实是很好的指标,但是这些核心期刊选择文章时考虑的具体因素让导师和学生难以把握。

波涛(英国)
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罗杰威(意大利)
意大利米兰理工学院建筑与环境科学系研究博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原一浩(日本)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特聘专家

法国巴黎矿业大学博士,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特聘专家
关于基础科学和激发创新
中原一浩认为,中国要消除学历偏重主义,杜绝填鸭式学习,要培养更多具有自由构思创意能力的人才;思维和工作模式不能受局限,要提出自己的想法开展研究讨论,否则很难创造出更多具有建设性的成果。提高多视角和独立创新想法能力,培养想象力丰富的人,建立多元化的人才梯队,以激发原始创新。
尤古塔纳·贝努利认为,创新是一种心态。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国的企业,管理结构非常强大。这种垂直形态的管理很好地适应了日常工作,但不适合创新。创新必须依靠最好的专家和工程师,因此需要鼓励、激发专家和工程师的创新行为,让经理和领导者了解这种创建过程的复杂性,为科研人员提供自由、宽容的工作环境,并给予他们充足的时间。
罗伯茨认为,要支持科学家们开展交流、提出新想法,也要给予这些科研人员一定的自由度,让他们自由地思考。要基于他们的成就进行鼓励,使他们不再害怕创新。我们不应该以发表论文的数量去衡量一个科研人员的成就,而是要看他所做的科研实验的质量以及影响度有多大。
林钟城认为,未来是属于数学的,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都离不开高等数学。中日韩三国学生数学水平与欧美相比要高很多,但东方人在真实世界当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很弱。所以大学教育需要以更具有创新性的方法去思考如何来教授数学。
关于人才培育和国际交流
杰伊·西格尔认为,要真正促进科技发展、社会进步,需要年轻人的力量,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支持青年科研工作者努力创新。
保罗·博若思认为,不要盲目地追随一些科学家。把外国顶级的科学家引到国内没有问题,但也不要忘记那些年轻的研究人员,在他们未来五六十岁时要指望他们开展科研工作。
尤古塔纳·贝努利认为,一方面,中国应该给更多的欧洲和美国学生提供来中国学习的机会,尤其是博士生的研究项目,建设国际友好的校园是关键;另一方面,还要推动更多的中国科研人员、工程师在国外学习先进经验、技术,因为他们需要直接参与这些创新集群,以了解和掌握技术的核心。这是中国进行高效创新的关键点。必须确保中国学生、工程师和专家在学有所成后能够回到中国,给他们相应的位置、待遇和物质条件。
行政事业单位掌握着重要的公共权力,当其公共权力为落实到位,在日常工作中出现违法违纪行为,产生的后果也会非常严重。我国曾曾出现过诸多的风险事件,所带来的影响和危害性也有目共睹。很显然,对于风险事件的评估能力与评估意识还相对缺乏。
彼得·腾森认为,要建立不同的通道、机制吸引学术型人才和创业型人才。目前,我们有非常多的政策支持了一些国内的人才以及来自海外的华人华侨,但是针对纯外籍人才,目前现行的政策还有待优化。

罗伯茨(美国/澳大利亚)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林钟城 (韩国/加拿大)
杭州坤慕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浙江大学工程学院兼职教授

彼得·腾森(美国/爱尔兰)
英国全球技术创新联盟创始人,南京腾森国际技术转移中心CEO

谢尔盖(俄罗斯)
俄罗斯原子能建设出口公司驻中国(连云港)代表处主任
萨万认为,如果中国有意将外国的人才长期吸引到中国来,一定要考虑这些人才配偶的就业机会以及子女的教育问题,还要考虑到如何以西方的方式对他们的子女进行教育和培训。
要让大学、研究机构和产业界去签署备忘录和合作协议,通过加强合作来吸引国际人才。中国的人才应该在中国开展创新,没有必要跑到国外,以防人才的流失。要鼓励中国的高校与国外的高校开展合作,开展双学位教育,组织和主办一些竞赛、比赛,为这些创新人才和高等人才提供激励政策,鼓励他们充分挖掘自己的创新潜力。要进行跨学科合作,这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研究人员以及科学家们开展合作,通过跨学科和跨组织的合作促进创新。
谢尔盖认为,中国需要尽量多地参与到国际论坛、项目、展览、研讨会等活动中去。要在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建立紧密联系,每年组织留学生交换项目,欢迎更多的外国大学生来华学习,派遣更多的中国学生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去邻国学习。
波涛认为,大公司细分多,出来的人并不见得有全局观,小公司不一定比大公司弱。科技人才交流合作不光要找带头人,还要找能做事的人。所谓“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只有能做事的人才知道细节。
关于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
中原一浩认为,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产学官”合作模式,联合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对各自擅长的研究领域分别提供必要的研究资源与丰富的开发经验,通过共同研究机制实现共同目标。在政府的支持下邀请外国专家,除了建立、磨炼自己的技术机制以外,还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国内各领域优秀人才交流。扩大网络知识、技术、信息共享平台,创造更多合作环境,推动科学技术进步。
保罗·博若思认为,政府要给初创企业创造一些安全的空间。比如,对研发的资助和根据国际标准保护知识产权。可以借鉴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一些项目,尤其是那些追求创新的小公司。第一个阶段叫概念发展阶段(SPIR)。这个阶段的项目风险度比较低,它的资金补贴的周期是6个月到1年的时间,一旦这个想法得到了验证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能够获得资金的周期会更长一些,资金量也会大得多。很多企业正是从这样的补贴项目中受益的。
彼得·腾森认为,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一是政府借鉴国外开放式创新模式,采用包括像类似于美国SPIR机制来鼓励更多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研究模式;二是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剥离出孵化公司和知识产权授权职能;三是鼓励政府更多地和企业合作,应对更多社会性挑战。
波涛认为,中国必须要在各领域建设自己的平台。有了平台,才能制造出更加高端的产品,产业转型升级就会大大加快。平台是个面不是一个点。国家光靠项目论文,难以形成规模,无法成为真正的生产力。不能“唯论文”,“面”
和“点”的关系要靠政府来引导,无法依靠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