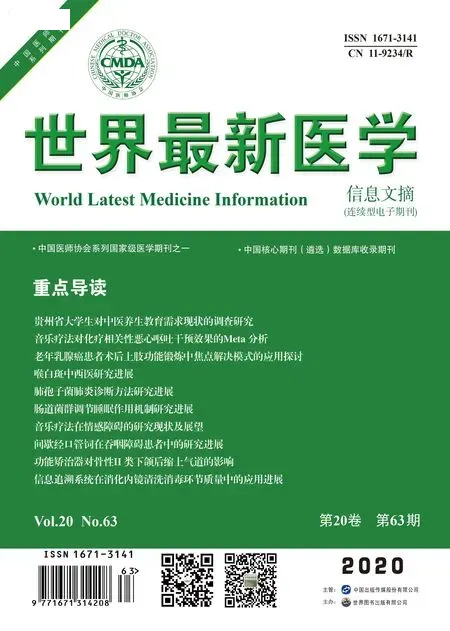浅析妇科病脏腑辨证特点
张若 ,王晓昕 ,汪小瑞
(1.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 成都;2.绵阳市妇幼保健院,四川 绵阳)
1 中医妇科辨证特点
脏腑辨证是妇科主要的辨证方法,五脏均与妇科疾病关系密切。刘完素提出“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从厥阴论之;天癸已绝,乃属太阴经也”[1]。这成为后世医家主张妇人少年治肾,中年治肝,老年治脾的立论根据,妇科疾病辨证均责之“肝、脾、肾”三脏,治疗上也是从“疏肝、健脾、补肾”三法。近代医家以《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女子生理论述为基础,治疗妇科疾病亦均从“肝、脾、肾”入手,而偏废“心、肺”。华占福教授及郑启仲教授首先注意到这种情况,并论述了“肺”在妇科疾病辨证中的重要意义[2][3]。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提出“心-肾-胞宫轴”理论,在治疗妇科疾病中尤其重视“宁心安神、补肾宁心、清心滋肾”,在辨证中将“心”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但从“肺”论治妇科病目前仍少有提及,至今未将“肺”这一脏腑功能纳入妇科病脏腑辨证体系。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2 妇科疾病脏腑辨证演变
2.1 两汉时期
《黄帝内经》初步奠定了中医妇科理论基础。《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4]。初步阐明了女子的生理变化,也将“肾”机能失调作为妇科疾病的主要病因病机。《素问·阴阳别论》:“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5]。”《素问·评热病论》指出:“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6]。”后世医家宗此以心脾失调,气上迫肺为闭经病因病机。《内经》中关于妇科疾病的论述未言及肺。《金匮要略》:“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在上,呕吐涎唾,久成肺痈,形体损分……”[7]。提到寒伤经络,经水绝断及久成肺痈。两汉时期,对于妇科病因病机的认识主要为“心、脾、肾”机能失调,对于闭经的认识为胞脉闭,心气不通,肺气上逆。
2.2 隋唐时期
《诸病源候论》中论及月经病均以“冲任脉损,少阴心经虚损”为主要病机。如“妇人月水不调,由劳伤气血……损手太阳、少阴之经也……此二经为表里,主上为乳汁,下为月水[8]。”“月水来腹痛候、月水不断候、月水不通候、带下候”等均言手太阳小肠及手少阴心经受损。在月经病及带下病中强调了“心”的重要性。《千金方》云:“女子月经不通,总不出二脉为病,冲脉紧附于肝,而能疏摄厥阴肝者,又在中土脾经[9]。”孙思邈认为月经病当责之肝脾,不孕则因“肾气弱”,以补肾为要。隋唐时期妇科脏腑辨证以“心、肝、脾、肾”为主,但言及“肝脾肾”者多,言及“心”者少。
2.3 宋金元时期
金元四大家中刘完素提出“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从厥阴论之;天癸已绝,乃属太阴经也”。这一论述对后世辨证论治妇科疾病产生重要影响。陈自明则以肝脾为重点,认为“妇人以血为本”,“男子调其气,女子调其血”,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肝主藏血,主疏泻。脾健则气血生化有源,肝疏则经水自调。朱丹溪提出“痰”致病的学术观点,治疗妇科疾病提倡和胃化痰。李东垣强调心火及胃火灼阴,导致血枯经闭,提出补血泻火的治法。这一时期初步形成“肝脾肾”辨证为主的特点[10]。
2.4 明清时期
张景岳调经尤重脾肾,《景岳全书》:“故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资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知斯二者,则尽善矣[11]。”傅青主认为“经本于肾”,“经水出诸肾”,着重强调了“肾”在调经中的地位。而叶天士提出“女子以肝为先天”[12]。秦天一认为叶天士调经首重肝,次重脾胃。“今观叶先生案,奇经八脉,固属扼要,其次最重调肝,因女子以肝为先天。阴性凝结,易于怫郁,郁则气滞血亦滞。木病必妨土,故次重脾胃。”明清医家已独重“肝脾肾”。
3 妇科病脏腑辨证特点及形成原因
3.1 特点
隋唐以前妇科病脏腑辨证主要关注“心、脾、肾”,妇科疾病病因病机为心脾两虚、脾肾两虚,心脉功能异常。隋唐以后,“心”脏在脏腑辨证中的地位下降,“肝”脏的地位逐步上升。自古以来在妇科病中论及“肺”脏的都很少,仅见“经行鼻衄”和“血枯经闭”两个疾病。张景岳首次提及这一现象。《景岳全书》:“是固心脾肝肾四脏之病,而独于肺脏多不言及,不知血之行与不行,无不由气[13]。”明清时期医家开始独重“肝脾肾”,张景岳调经之要在补脾肾,傅青主独重肾,叶天士首重肝。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一致影响至今,妇科脏腑辨证也独重“肝、脾、肾”。
3.2 原因
笔者认为形成这种辨证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对《内经》中涉及女性生理条文的认识变化。隋唐以前医家以《素问·上古天真论》中的“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和《素问·阴阳别论》:“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为理论基础来阐释妇科疾病。故重视“心、脾、肾”三脏。隋唐以后医家以《灵枢·五音五味》:“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14]。陈自明、张景岳都以此为基础认为女子以血为主,叶天士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以肝为先天,此后“肝”取代“心”成为主要脏腑。其次,在论述妇科疾病时将“肺”的机能归于“肝、脾”,“心”的机能归于“肝”,因为肺主气,脾为气血之源,补肺多以补脾代,而肺的行气功能多被肝的疏泻功能所取代。如薛立斋说“肺气虚不能行血,治疗之法补脾胃”。再如妇科大家刘奉五先生治疗闭经的“瓜石汤”,药物组方中瓜蒌、麦冬、玄参均为走肺之品,只言气宽胸滋胃而独不言肺,未免太过偏颇。心主血,肝藏血,故经常会把心的功能统一于肝,故在后世心的地位被肝代替。
4 辨证偏颇的影响
辨证独重“肝脾肾”而轻“心肺”产生了一些影响。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内经》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补脾胃可使肺气旺,气虚之失可以补脾代补肺,但肺主治节,主散经之功能脾胃不能代替。心主血的功能可以归于肝,但心主神明之功能肝不可代替。对于脏腑辨证之偏颇影响中药组方,国医大师夏桂成重视心,强调补肾宁心,镇心安神的意义。不重肺则不会瓜蒌此等宽胸行气之品。缺乏这些认识,在治疗妇科疾病时仅仅囿于“疏肝、健脾、补肾”三法,往往不能收全功。
5 心、肺论治妇科疾病
现代中医名家逐步认识到这种辨证偏颇,并开始逐步完善妇科疾病心肺辨证体系。国医大师夏桂成尤重妇科疾病从心论治,并提出“心-肾-胞宫”轴理论。中医妇科名家尤昭玲教授从心论治“经前漏红、早孕胎漏、经行腹痛、崩漏”等。经前漏红尤氏常用莲子心配石斛、合欢皮等清心安神之品,早孕胎漏则用莲子心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宁心安神之品[15]。《医学正传》:“崩漏不止之证,先因心火亢盛,于是血脉泛溢,以致肝实而不纳血,出纳之道遂废”[16]。尤氏治崩漏常用莲子心、石斛、合欢皮、珍珠母等镇心药物。目前也有医家从肺论治月经病、带下病及妊娠病,主要涉及“闭经、妊娠恶阻、子肿、转胞”等。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息贲者,死不能医。”为闭经从肺论治的理论基础,现代医家从补肺益阴角度来论治妇科生殖器结核致月经不行者收到一定效果。绝经前后诸证多谓“肾虚为病”,但仅从肾论治往往效果并不满意,薛立斋言肾水当藉肺金为母,金水相生,补肾当配合补肺。现代医家从肺肾同治出发,创立加味三才饮,搭配使用润肺滋肾药物,收到较好效果[17]。经行吐衄中医辨证主要为阴虚肺燥和肝经郁火证,遣药组方也以从肺论治为主。《妇人大全良方》:“妇人带下……伤于太阴肺经色如白涕[18]。”薛立斋言白带下是肺虚,当用补中益气汤补益肺气。当代妇科大家刘云鹏从肺论治妊娠恶阻,应用清燥救肺汤清肺润肺,肺气和则恶阻止,与大多数医家的思路不同。 “血病即是火病,水病即是气病,治血者必调气”,“气生于肾而主于肺”,“气为血之母”,治气当治肺。以上均可见,妇科疾病从心、肺论治有一定临床意义,但从“肝、脾、肾”三脏出发并不能涵盖所有妇科疾病。
6 结语
脏腑辨证是中医重要的辨证方法之一。仲景讲“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笔者通过对古代经典的回顾,粗浅的讨论了中医妇科辨证特点及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希望能对临床工作有所裨益。总体来看妇科辨证独重“肝脾肾”的现象出现在明清,“心肺”功能多归之“肝脾”,至国医大师夏桂成“心-肾-胞宫轴”理论提出,才重新将心的地位提升起来。在这种辨证偏向中我们忽视了心肺的一些功能,比如“心主神明”、“肺主治节”,也影响了我们遣方用药。临床上论治妇科疾病时当兼顾五脏,不可偏废,如此方可保证疗效,使患者最大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