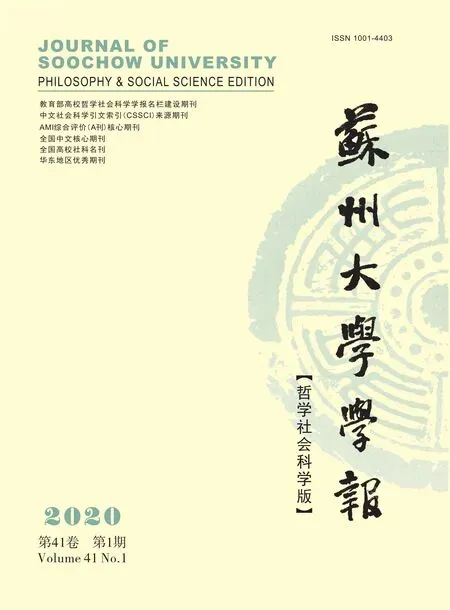论儒道的“道隐”及其历史前源
沈思芹 钱宗武
(1.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2.徐州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隐逸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种特殊的精神行为,隐逸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隐逸行为多为隐居不仕,遁匿山林。隐逸文化的追求目标多为内心的平和、生活的简朴。隐逸是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态度,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隐逸行为催生隐逸文化,各种方式的隐逸行为和各种形态的隐逸文化,反映了各种各样的隐逸思想。轴心时代产生的儒家、道家都有隐逸思想,均可称为“道隐”。儒家道隐与道家道隐既相互联系,又彼此有别。同时,这两种隐逸均非中国隐逸文化之源,而是隐逸文化之流。
一、儒家之道隐:人道之隐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隐逸有过不少叙述。诸如: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1]77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1]95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1]106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1]158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162-163
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1]173
综上所论可知,孔子不仅承认“隐逸”的正当性,而且予以高度重视,甚至将“隐居”与“行义”等量齐观,将“辟世”作为评判“贤者”的标准之一。这是因为孔子所主张的隐逸本质上是一种“道隐”,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的。在孔子看来,个人的出露行藏并不取决于自己的意志,而是取决于天下是否有道。
何为“道”?三代之制,周公之礼。孔子曾在《论语·八佾》中作过表述:“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65“道”的内容,反映于孔子参加一次鲁国年终祭典后的一番感叹,不仅表达了儒家社会历史观和礼乐观,也反映了“道”的实践内容。孔子的这一番感叹见之于《礼记·礼运》: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2]1413-1414
可知,“道”就是公天下的大同。公天下的大同是人为的结果,因而,“道”是人之道。“道”的实行也是人为的结果。孔子也有表述。
《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东汉王肃注:“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2]2518朱熹注:“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1]167
道之大小取决于弘道者才能的大小。人能够弘大道义,道义是不能弘大人的。
《礼记·中庸》:“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1]23
由此可见,孔子明确指出行道是人为的结果。道不能排斥人,人为道而排斥人就不是行道,也不可以行道。
“大道既隐”,怎么办呢?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隐逸与出仕是儒家面对不同政治形势时采取的两种不同态度。政治清明、天下有道时就出仕为官,政治黑暗、天下无道时就隐逸避世,而这两种态度归根结底都是“道”的实现。《论语·季氏》:“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一句话道出孔子隐逸思想的真谛,即隐居也罢,出仕也罢,都是为了完成志向,实现治道。如果时局许可,当然要积极出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时局混乱,则应当暂时隐退,怀抱志向等待时机。
天下无道政治黑暗时为什么要选择隐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当个人理想与时局格格不入之时,如果不能及时隐遁,难免招致重大挫折。据《荀子·宥坐篇》记载,孔子曾对此有过精辟分析:
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而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曰:“由!居!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句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3]526-527
一个人能否实现其政治抱负,不仅仅受主观因素影响,还受到客观条件制约。忠言逆耳,有时不仅不能为上所用,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因此,当政治黑暗、人主昏聩之时,贤者应当采取隐逸的办法以保全自身,在隐逸期间不断修炼自身,相时而动:“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由此可见,虽然“隐”本来是儒者在政治黑暗时躲避乱政、保全自身的一时退让,但奋发进取的儒者在“隐”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积累学问、锻炼才干、培养德行(博学、深谋、修身、端行),最终落脚点仍在于等候时机,为治世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看,“隐逸”连接着儒家“内圣”(修身)与“外王”(治国平天下)两大理想,隐逸的过程既是“内圣”的过程,也是“外王”的准备期。事实上,《荀子·宥坐》这段论述正是《论语·季氏》“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绝佳演绎。邢昺早已指出:“‘隐居以求其志’者,谓隐遁幽居,以求遂其己志也。‘行义以达其道’者,谓好行义事,以达其仁道也。”“志”是侧重于个体层面的理想、价值,而道则是侧重于社会层面的理想、价值。“隐居”是修己内圣的过程;“行义”则是治世外王的过程。如此看来,孔子所谓的隐逸可谓名副其实的“道隐”。儒家“道隐”绝非摒除世俗所扰,视功名富贵如粪土,追求潇洒、超脱、恬淡自如,而是一种手段式的待时之隐,其背后支撑仍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道精神。儒家的“道隐”是人道之隐,“隐”是为了“显”,“逸”是为了“达”。“隐逸”是手段,是策略;“显达”是目的,是理想。
孔子之后,“道隐”观念被孟子和荀子所继承。尽管《孟子》中没有对“道隐”观念的明确表述,但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著名观点实与“道隐”精神相一致。孟子在《尽心上》有一段深刻的论述:
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351
士人处于“达”(得志)的状态时就可以“泽加于民”,也就是出仕为政,治国平天下;而处于“穷”(不得志)的状态时就“修身”完善自己,而不论何种状态,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是道,是义。据此,孟子此言实与道隐精神一脉相承。
荀子“道隐”观念见于《荀子·儒效篇》:
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呜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3]117-118
这段话是荀子对秦昭王“儒无益于人之国”观念的回应。秦国自孝公时期商鞅变法,至昭王时已历三世四王。在这一时期,秦国君主专制之势已成,同时也逐渐对六国拥有绝对优势。在临近“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荀子试图将“儒”融合进“秦法”体系之中,尤其表彰儒家隐者对“道”的执着追求,指出儒者不论在朝或在野都始终坚守“道”,对国家、对君主忠心耿耿。他宣称“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其实是将“道隐”吸纳到国家统治秩序之中,而此“道”即“社稷之大义”,亦即忠道。荀子之“道”与孔子之“道”一脉相承,只是荀子之“道”更加突出个体对国家意志的服务与服从,并且从国家统治的角度阐释了“道隐”的政治意义。
二、道家之道隐:天道之隐
有学者认为儒家隐逸重“道”,道家隐逸则重“形”。但事实上“形”不能脱离“实”而单独存在。“形”必须有所承载。就精神实质而言,道家的“隐”其实也是一种“道隐”,是“道”的寄托。
道家源远流长,代有家派,诸如,黄老之学、老庄之学、杨朱之学、玄学、心学。其中,老庄之学是道家的主流,庄子又是老庄之集大成,上承老子,下启心学。道家对隐逸的系统论述见于《庄子》。诸如:
啮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4]96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4]603-604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之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4] 605
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今寄去则不乐。由是观之,虽乐,未尝不荒也。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4]558
庄子呼唤人们从世俗功名利禄的价值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返朴归真,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在他看来,世俗社会是一个充满局限的、格调低微的世界,理想中的世界则是与日月同在的无限自由世界。而隐逸就是脱离世俗社会、返归本性、实现自由的不二途径。就此而言,庄子的隐逸背后同样有着“道”作为行动理据,只是这种道不是儒家积极入世的人道(社会之道),而是超然物外的天道(自然之道)。事实上,对于这一分野,《庄子》中就已有明确的表述:
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4]401
《庄子》天道观与儒家人道观针锋相对。“天道”与“人道”仿佛君主与臣子的关系。入世者对政治功名孜孜以求,使自己身心俱疲;不如抛却世俗价值观念,追求个体生命精神的充盈和自由。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道德经》就是由《道经》和《德经》构成,《道经》理所当然会多次论及“道”。根据王中江先生的研究《道德经》的“道”有五个义项[5]11,“道”指自然客观规律是道家的主要概念,“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思想。《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中气以为和。”[6]233
“道”生成气,“道”生成自然万物。冯友兰先生说:“这里说的有三种气:冲气、阴气、阳气。我认为所谓冲气就是一,阴阳是二,三在先秦是多数的意思。二生三就是说,有了阴阳,很多的东西就生出来了。那么冲气究竟是哪一种气呢?照后来《淮南子》所讲的宇宙发生的程序说,在还没有天地的时候,有一种混沌未分的气,后来这种气起了分化,轻清的气上浮为天,重浊的气下沉为地,这就是天地之始。轻清的气就是阳气,重浊的气就是阴气。在阴阳二气开始分化而还没有完全分化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中的气就叫做冲气。‘冲’是道的一种性质,‘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四章)。这种尚未完全分化的气,与道相差不多,所以叫冲气。也叫做一。”[7]41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6]169
郭店楚简本《道德经》甲本这一段文字为:“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8]3
王弼注:“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9]65
王弼注《老子》一贯以“自然”为“万物”的“自然”,“万物以自然为性”,“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指称“客体”(如自然界),而是指称事物的“存在方式”和“状态”。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即“无状之状”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自然。
在道家隐逸论述体系中,“道生万物”“道法自然”,道家的隐逸思想内涵是尊重生命,尊重自然,追求独立和自由。《周易》:“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遁世(逃世)的原因是遁世者具有“独立不惧”的人格。庄子追求“不为物役”和不为“圣人之知”所役。当然,实现人格的独立和自由,还不是庄子隐逸思想的全部,更重要的内容是体会人与自然的同源同德,进而通于自然之道,达到绝弃名利(无我、无名、无功)、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这种物我两忘的人生境界,可以使人超越名利之上、有无之上,而实现生命的自然久长。儒家隐逸思想是政治价值化的隐逸思想,较之老庄隐逸思想精神层次有所不同。不过,在文人理想通过政治方能最终得以实现的政治中心化的时代,实用理性兴盛,儒家的隐逸思想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尽管道家与儒家隐逸的内涵不尽相同,但道家隐逸同样也是一种“道隐”,并且道家隐逸主张的出发点也与儒家有惊人的相似性:
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4]554-555
与孔子相同,庄子隐逸观的产生同样源于道之不行。“隐”本非人主动的追求,而是由于人的主张与时局不合。在这种情况下,隐逸成为圣贤唯一的命运选择。因为“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此时即使并未退居山林,由于其理想、主张不为世所容,事实上与“隐”的状态并无二致。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形隐”并非道家隐逸的必然要求,道家隐逸本质上仍然是“德隐”“道隐”,认为“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孔子主张隐逸是求志修身的过程,而庄子主张隐逸是“深根宁极而待”的过程。“深根宁极”是道家增进个体修为的方式。可见与儒家相同,道家也将隐逸视为个体修行之机会。
可以认为,道家与儒家的隐逸都是“道隐”,且二者结构具有相似性。其不同处则主要在于,儒家之“道”乃人道,道家之“道”乃天道。同时,道家之道最初也是针对社会而非个体提出。在《庄子·缮性》的描述中,上古社会是一个“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的“至一”的、“自然”的社会,此时物我混一,自无显隐之别。后来经历神农、黄帝、唐尧、虞舜之世,“德下衰”而“世与道交相丧”,最终沦落至“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的地步,方才有显隐之别。如此看来,虽然道家更多关注个体生命之隐,但道家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却始于社会。就社会层面而言,“隐”对于“显”实乃一种反动,其中始终贯彻着道家至一、自然的社会理想(天道)。这更加确证了道家隐逸的实质是天道之隐。
三、两种“道隐”的历史前源
学界大多认为隐逸起源于先秦儒家或道家。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而从上文分析可知,先秦时期儒家、道家的隐逸思想已经相当成熟,因此不太可能是隐逸的最早发轫。历史文献的梳理可知儒家与道家隐逸思想可能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渊源。
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就有踪迹可寻,诸如: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1]102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1]173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1]182-183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185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1]234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1]355
天地不知,善桀纣,杀贤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舆避世,箕子佯狂;田常为乱,阖闾擅强。为恶得福,善者有殃。[3]553-554
《论语》《孟子》《荀子》中,记载了吴太伯、齐太公、箕子、微子、伯夷、叔齐等著名隐者,这些隐者都得到儒家的表彰和赞许。此外,这些隐者均是殷末周初时人,在正史中都有记载,事迹主要见于《史记·殷本纪》《周本纪》《齐太公世家》《宋微子世家》和《伯夷列传》。而其中宋微子的隐逸始末更可追溯至《尚书·微子》。
据《史记》的《殷本纪》和《宋微子世家》记载,殷末国君纣王受在位时,统治黑暗,不务国政,淫佚奢侈,使得民不聊生,微子多次进谏,纣王都不听。等到因周西伯姬昌修行德政,国势强盛,微子担忧灾祸降临殷朝,便又来奉告纣王。纣王却说:“我生有命,决定于天,周西伯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于是微子估计纣王最终不能接受劝谏,打算以死相争或逃亡出走,拿不定主意,便去询问父师和少师。父师建议微子远遁荒野,从而殷商灭亡以后,还有人能够祭祀殷商先王先公。史官记录微子和父师、少师的问答,是为《尚书·微子》: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厎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
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隮,若之何其?”
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乂雠敛,召敌雠不怠。罪合于一, 多瘠罔诏。
“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隮。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遯。”[2]177-178
微子首先分析殷道德沦丧、法度崩坏的种种乱象,指出殷商行将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微子提出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我其发出狂”,一是“吾家耄逊于荒”。狂,《史记·宋微子世家》引作“往”。据孙诒让说,“我其发出往”意谓“我其废弃而出亡”。“吾家耄逊于荒”,《史记·宋微子世家》引作“吾家保于丧”[10]1607,意谓在丧乱中居家自守(1)“荒”音义皆从“亡”,故《史记》作“丧”。下文云“天毒降灾荒殷邦”,“荒”即“荒乱”“丧乱”之谓,是本篇“荒”确有作“丧”解之例。。这两种行为其实都属于隐逸的范畴,第一种即远遁世外,是比较彻底的隐逸;第二种则是在天下丧乱时去国守家,对于国而言亦可谓隐逸。微子讨论隐逸主要基于两点,其一是对乱政的愤懑,这一点后来即发展为儒家“有道”“无道”之说;其二则是基于血缘的宗法观念:保全家的目的主要在于延续殷商宗嗣。微子最终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他去国暂隐而并未彻底与世隔绝。史载武王克殷后,“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10]1610。的确,如欲延续宗嗣,必须与新生王朝合作以求宗庙之存。
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宋微子世家》时基本引用了《尚书·微子》的全部内容,但也作了一定改写。主要有以下两点:
1.《尚书·微子》“今殷民乃攘窃神祗之牺牷牲用以容”后的内容不见于《史记·宋微子世家》,而以“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10]1607代之,并且交代此事最终结果是微子“遂亡”。《尚书》经文中,父师仅仅是主张自己“死国”而微子、箕子应当出逃,并没有深入论述原因;而《史记》中,父师(太师)分别对“死国”与“去国”两种不同态度作不同分析,指出“死国”或“去国”取决于国能否“得治”。如果能以身死换得国之治平,则当死国;如果不能,则当去国。
2.采录《尚书·微子》文后叙述箕子、比干事迹,之后又补叙微子事迹: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10]1610
《史记》补叙之文强调微子远遁合于君臣之义。
综合以上两点,可见《史记》在引述《尚书·微子》的同时更加突出微子隐遁的行动理据,强调微子之隐合乎儒家之道;而在微子事迹中间插叙箕子、比干事迹,则是基于孔子“殷有三仁”说的历史建构。《史记》的历史观是儒家的历史观。儒家主张道隐,因此《史记》在叙述历史时尤其注重对“道隐”观念的阐发。而另一方面,《尚书》等经典本即经过儒家整编,而经典整编乃是经书“经典化”过程的开始。经书经典化的过程也就是儒学化的过程,在整编过程中,儒家学者势必凸显其合乎儒家观点的元素,删减背戾儒家观点的内容。《尚书》的整编是儒家试图将历史经典化的一次努力;而司马迁据《尚书》等经籍写作《史记》,则是历史经典化的又一次努力。从《尚书·微子》到《史记·宋微子世家》,我们可以窥见儒家“道隐”思想建构的历史过程。
除了微子,殷周之际还有其他几位著名隐士。
箕子。《周易》和《尚书》中提及箕子,但叙述极简。《史记·宋微子世家》云: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10]1609
据《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认为“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而箕子则认为“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因此没有选择去国,而是“隐而鼓琴以自悲”,采取了与微子不同的隐逸方式。据前文分析,文中所载微子、箕子对道义的剖析可能是出于后代历史叙述者的敷衍,是儒家学者对于微子和箕子不同行为方式做出的儒学解释。君主昏聩,臣子数谏,已尽君臣之道,这种情况下微子选择去国,在君臣关系方面固然无可指摘;但是这一行为依然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孔子谓殷有三仁,但微子和箕子究竟谁的行为更合理?这可以视为儒家后学对“道隐”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云: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10]1445
吴太伯和仲雍为了使“立长”“立贤”两种王位继承制度并行不悖,同时也避免使其父周太王陷于不义,故选择奔荆蛮而祝发文身。其行为符合儒家忠孝观。
齐太公。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吕望事周的故事版本流传各异,其中一种认为其为海滨处士。而其年老时“以渔钓奸周西伯”的事迹则应当属实。倘若吕望确实曾为处士,则其隐逸可谓待时之隐的典型。
伯夷和叔齐。据《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有过两次“隐”的行为。其一是为推贤及维护父命而隐,与吴太伯之相类: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10]2123
其二是为忠孝仁义之道而隐:
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10]2123
伯夷、叔齐先是为让国而隐,是源于对“推贤让能”传统的维护及对父命的尊重、服从。其后拒绝与新生周王朝合作,而隐于首阳山,亦是出于君臣父子之谊。这些均为儒家所表彰。
由此可见,箕子、微子、齐太公、吴太伯、伯夷、叔齐,他们的隐逸都属于儒家“道隐”范畴,反映了儒家忠孝仁义的各个侧面,为儒家极力推重;然而,道家对于这些隐者的态度却比较复杂。一方面是持批评态度,诸如:
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4] 232
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4]323
而最为著名的当属《庄子·秋水》,庄子设计河伯和海神对话的情景方式,借用“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的话题,论述小大之辩,揭示事物的复杂性和认知的差异性。先写“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时,黄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再写河伯“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极写北海之大,“东面而视,不见水端”。波涛激荡,心由境生,愧悔不已。
北海海神“未尝以此自多”,谆谆与之“语于道者”:“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河伯仍然有惑:“然则何贵于道邪?”北海海神指出:“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4] 561-564庄子借海神之口批评伯夷自多,阐明万物浑然等齐,取消一切对立差别,无大无小,顺物自化,返归自然。庄子论述的道自是天道自然之道。
另一方面,庄子对伯夷却又持褒奖态度。《庄子·让王》记载“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周武王使周公旦以“加富二等,就官一列”与之盟,二人相视而笑,认为“此非吾所谓道也”。伯夷、叔齐的道是指神农氏之道:“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他们认为周人的做法说明周德已经衰败,与其与周人为伍而使自身受到污辱,不如逃离他们保持品行的高洁。两人隐迹首阳山,终于不食周粟而饿死。庄子赞扬伯夷、叔齐,“其于富贵也,苟可得已,则必不赖,高节戾行,独乐其志,不事于世。此二士之节也。”[4]987-988庄子赞扬的实际上也是自然之道,利禄不可取,不因外物害命伤性。
《庄子·让王》的记载与《史记·伯夷列传》的记载大致吻合。伯夷、叔齐不慕富贵,独乐其志,不事于世,这一点与道家“道隐”精神相近;但其“志”毕竟尚未脱离儒家仁义之说,与道家主张相背,故又被道家批评为“死名”。道家对伯夷、叔齐的复杂态度反映了道家“道隐”对殷末周初“道隐”以及儒家“道隐”的不同思想:一方面赞同时局混乱时避世而隐、独乐其志;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人道之志,而代之以天道之志。这就解释了为何儒家“道隐”和道家“道隐”结构相似而内容有别。
隐逸文化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隐逸非始自儒道。早在《尚书》中,就已有记载隐逸行为的《微子》篇;代表儒家正统史观的《史记》,其“世家”部分与“列传”部分首篇传主均为隐者(《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可见隐逸在儒家历史叙述中的崇高地位。儒家与道家隐逸本质上都是道隐,且均为殷末周初隐逸文化之流。殷末周初隐者的社会实践,为儒道的“道隐”提供了精神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社会基础。儒家道隐是殷末周初隐逸文化的直接延续,而道家道隐则是用“天道”之“道”代替“人道”之“道”。儒、道两家的隐逸行为是相同的,多为隐居不仕,遁匿山林。儒、道两家隐逸主体的行为方式也基本是相同的,都是对客观世界的被动行为,都是弱者对强者的退让策略。儒家是显性被动,道家是隐性被动。儒、道两家隐逸的出发点也相同,皆源于道之不行。儒道两家道隐的不同主要是二者终极追求不同,儒家隐逸之主体隐逸多为入世,道家隐逸之主体隐逸多为出世。儒道隐逸到魏晋时期开始合流,道家的隐逸成为隐逸文化和隐逸思想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