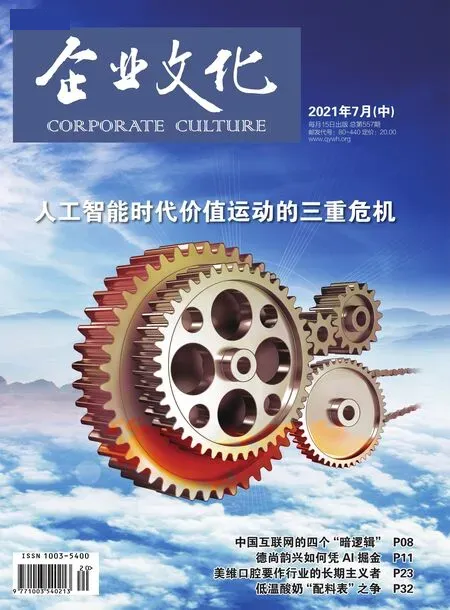人工智能时代价值运动的三重危机
文|黄再胜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通过对劳动的吸纳和规训,不断地用对象化劳动吮吸活劳动,以实现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智能化、商品形态的数据化以及网络协同生产的共有化,正使得当代资本主义价值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窘境。
资本有机构成趋于无限大
自工业资本主义以来,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是资本增值运动的基本逻辑。在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无限扩张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促使“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的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却使得资本增值运动遭遇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即“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把,已经创造了价值作为价值来保持所需要的限度之内”。换言之,资本在追逐自我增殖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引致商品价值实体“空壳化”的致命矛盾。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一旦完全自动化生产成为可能,实现了“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最彻底替代”,商品生产中活劳动因素消失,资本有机构成趋于无限大,商品价值赖以形成的实体基础自然化于无形。退一步讲,即使刻意去维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价值构式,也必将产生一种甚是荒唐的情形,一方面,产品供给极其充裕;另一方面,又因无人问津而导致生产绝对过剩。普遍劳动者连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自由都不复存在,又何以获得收入用以消费。正因如此,最终消费需求日益萎缩,引发资本循环中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断裂,必将使资本主义遭遇“经济奇点”(economic singularity),进一步将商品固有的内在矛盾对立推向极限。一方面,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各种财富得以充分涌流,经济稀缺让步于经济过剩;另一方面,商品生产的价值构式日趋萎缩,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社会实在性不断被侵蚀。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
信息商品零边际成本
美国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在畅销书《零边际成本社会》中预言,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生产力发展终将跃过终点线,即商品生产边际成本趋向于零。实际上,自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认知资本主义新阶段。信息(认知)商品生产成为资本逐利和资本积累的主要场域。相比于传统的有形物质产品,信息(认知)商品具有典型的消费非竞争性,边际复制成本极低甚至可忽略不计。
从商品内在矛盾的现实运动看,信息(认知)商品的零边际成本特征,使其商品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呈现新情况新表征。对此,自治马克思主义强调非物质劳动的特殊性,即工作投入与日常生活的日益融合,武断地认为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进入认知资本主义阶段,信息(认知)商品的价值决定已经陷入“度量危机”(crisis of measurability)。而保罗·迈森则认为,信息(认知)商品生产的零边际成本,只是意味着其价值形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微不足计。供给充裕的信息(认知)商品生产会因遭遇“定价危机”和“利润枯竭”而使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走向瓦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无论是从商品生产过程看,还是从商品流通过程看,一定量的活劳动投入始终是商品价值形成的实体基础。在笔者看来,在探寻信息(认知)商品价值形成的实体因素时,上述论断都混同了产品复制成本和商品再生产成本,只强调其边际劳动投入,而对从构念到商业化应用的整个产品生产周期全部劳动耗费几乎无论及,在此基础上得出信息(认知)商品价值归零的错误结论。
实际上,软件开发等商业实践表明,信息(认知)商品复制成本虽然极低,但开发的初始成本却往往高得令人咋舌,需要大量的复杂劳动投入。从一段时间以来社会热议的IT 界“996”现象,就窥见一斑。从商品的价值总量看,信息(认知)商品价值形成的实体基础应该是从研发、量产、维护到更新的全部劳动投入。信息(认知)商品的个别价值,就是其商品价值总量在社会有效需求量中的均摊。相比于有形的物质商品,信息(认知)商品价值运动面临的挑战,既不是自治马克思主义所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缺场;也不是保罗·迈森所强调“零边际成本”引发的市场定价困境。从商品两重性的对立统一看,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诸如软件、创意等信息(认知)商品生产中,由于其复制成本极低,客观上造就了潜在用户不经市场交换,就占有使用价值的消费可能。如此,信息(认知)商品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流通难以维系,资本主义价值运动的市场基础也就会随之动摇。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平台经济快速崛起引爆了数据革命。借助数据分析挖掘形成的数据商品和服务,成为资本竞相逐利的新宠。相比于图书、唱片等传统信息(认知)商品,数据商品的数字化生产和流通,可以在轻松的鼠标点击瞬间完成,因而具有更加彻底的零边际成本特征。在“自由、免费、共享”等互联网文化冲击下,数据商品生产和数据资本价值运动,自然面临更具挑战性的“价值实现危机”冲击。正如克里斯·安德森所言,“在数字化市场上,免费总是消费者能得到的一种选择……早晚有一天,数字产品王国的生产者会发现,他们一直在和免费作斗争”。
基于共有的网络协同生产
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晶。从本体论上看,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其存在的前提就是人类物质生产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普遍对立。一旦私人劳动无须通过市场交换的社会确证(social validation),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社会分工下的劳动产品直接构成社会财富的元素,价值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就会自行消失。如此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限度不再是资本过度积累和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而恰恰是价值本身的存在性危机了。
自工业资本主义以来,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剥夺性积累,不断制造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不遗余力地拓展人类物质生产商品化的时空域,以维系资本主义资本运动的价值构式。进入认知资本主义阶段,从事信息、知识、符号、情感和关系等生产的非物质劳动,成为财富创造的霸权形态,资本对普遍智能的攫取愈发普遍而显著。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基于通用公共授权(GPL)和Linux 式对等生产,对大众“认知剩余”聚合和利用而形成的“横向规模经济”,显示出巨大的财富创造潜能。维基百科、免费开源软件(FOSS)等成功实践,无不展示出人类物质生产以社会共有逻辑替代资本逻辑的现实可能。并且,在基于共有的网络协同生产模式中,自主的、分布式和全球接入的劳动分配替代了资本控制下的劳动分工,极大地激发了大众创造潜能。3D 打印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推广应用,则进一步为人类有形物质产品生产开启协同共享的“大众生产”模式提供了新空间。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作为“新石油”,成为人类财富创造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数据的要素属性天然地排斥资本逻辑推动的“数字圈地”、数据垄断和数据资本化。毕竟,作为“普遍智能”物化的海量数据,只有作为全社会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才能最大效率地被挖掘分析利用,实现其使用价值的充分释放。正如涂子沛所言,“数据就像基因,掌握一个人的一个基因价值不大,但若掌握一个人的至全部人的全部基因,那价值就巨大了”。仅从大数据意义上讲,人工智能时代生产条件和劳动的社会化进一步发展,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的生产特征得以充分彰显,资本主义交换价值的实践理性也就愈发显得狭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