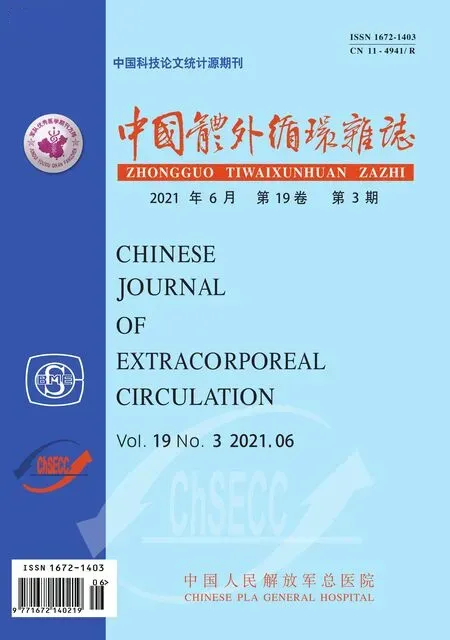心脏手术体外循环转流期间麻醉优化管理
刘 斌
作者单位: 610041 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科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及外科技术的不断发展,心脏手术数量逐年递增。 数据显示,仅2019 年我国近千家医院共开展25 万多例心血管外科手术,而其中经体外循环(extracorporeal circulation, ECC)手术约占70%[1]。 由此表明心血管手术大部分仍需ECC支持。 ECC 期间,麻醉医师和灌注医师共同管理患者,维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和内环境稳定。 但ECC的非生理状态,对患者生命功能会产生巨大影响,麻醉医师应充分了解ECC 期间的病理生理改变对麻醉管理的影响,充分与灌注医师合作,做好转流期间患者的基本生命机能调控,实施更优化麻醉管理。
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流行,体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 技术的应用[2-4]、ECMO 患者的镇静镇痛等问题,又对重症医学、麻醉学、ECC 等多学科医师提出新的挑战,因此掌握ECC 期间麻醉管理的特点更有必要。
1 ECC 的主要病理生理改变
ECC 是在一种非生理状态血液循环及氧合的环境下维持生命机能的,不仅存在血液与生物材料的接触,更受到低温、血液稀释、非搏动性灌注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改变不仅影响到重要组织器官微循环的氧供氧耗,也影响到各种药物药代动力学及药效动力学,包括麻醉药物、血管活性药物等。 麻醉医师与灌注医师共同调控好ECC 期间患者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血液抗凝与拮抗。 麻醉医师应充分发挥在保障患者生命安全和维持内环境稳定中的主导作用,需要做好与外科医师、灌注医师之间的良好沟通。
2 ECC 对麻醉药物的影响
加速术后康复、快通道心脏麻醉等观念普及,心脏手术麻醉用药理念日益趋向利于早期的意识恢复及早期拔管。 麻醉医生应掌握ECC 对麻醉药物血药浓度的影响,做到既保证术中充分镇痛镇静又避免药物蓄积。
ECC 转流初期,血液稀释、低温、肺隔离、ECC管道的吸附作用等致使丙泊酚、芬太尼血药浓度下降40%~60%。 因此,麻醉医师可在ECC 开始时,适量给予镇静、镇痛及肌松药。 ECC 转流后30 min,这种吸附作用逐步接近饱和状态,若保持转流前后药物泵注速度不变,麻醉药物的血药浓度将缓慢上升至转流前或稳定在略低于转流前水平。 后面的变化主要可能与低温下体内药物清除率降低、血浆蛋白结合率下降有关。 ECC 转流引起的血液稀释使得血浆胶体渗透压降低,麻醉药物表观分布容积扩大。 麻醉药物将随着使用时间逐渐蓄积于体内脂肪、肌肉等组织。 ECC 近结束时的复温过程中,其他组织内吸收蓄积的麻醉药物随温度上升而逐渐释放入血,血药浓度逐渐回升达峰[5]。 当体温恢复至36℃时,低温对药物代谢酶抑制解除,体内器官对麻醉药物的代谢率超过其释放入血的速度,血药浓度则较峰值有所下降。 因此,麻醉医师在此期间需根据ECC 手术及ECC 进展,对麻醉药物进行适量增加,做到既规避术中知晓又避免药物蓄积延长患者清醒时间。
3 ECC 期间肺保护策略
大量临床实践及实验表明,ECC 术后肺部感染、肺功能不全是心脏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6],也是患者延长ICU 住院时间的重要因素。 术后的肺损伤可表现为一过性短暂肺损伤,也可表现为中-重度急性呼吸功能衰竭,极大增加术后死亡的风险[7]。 ECC 中的多种原因已被证实为术后肺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如ECC 中血液暴露于人工材料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ECC 期间的肺缺血及缺血再灌注损伤、同种异体输血引起的急慢性肺损伤等。 针对各种风险因素,虽然ECC 技术的不断改进,如提高管路的组织相容性、红细胞洗涤、普遍使用超滤、ECC 期间间断肺动脉灌注等方法,部分避免围术期肺损伤[8],但麻醉医师仍应高度重视,如一定范围使用皮质激素、抑肽酶、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纤溶制剂等药物可减少术后肺损伤的发生。
ECC 转流期间,为了减少左心房的血液回流和干扰手术医师操作,多数麻醉医师选择暂停机械通气。 此时人工氧合器虽可提供全身的氧供,而细小的支气管动脉无法为肺提供足够量的血液灌注,长时间无通气将诱发肺泡上皮的损伤、炎症细胞的浸润、溶酶体的激活,从而引起肺泡萎陷、肺不张、肺顺应性下降,进一步加重ECC 带来的肺缺血及肺缺血再灌注损伤。 但如能保证足够肺通气,即使肺毛细血管缺少灌注,也可维持肺的形态学及能量水平。其原理可能是肺通气借助机械动力作用,减少肺循环中血小板、白细胞及炎性介质的滞留,防止肺内皮细胞功能进一步的损害。 临床研究表明转流期间若以5 ml/kg 的潮气量持续机械通气,可观察到术后肺水肿得以减轻,ICU 带管时间也明显缩短。 因此越来越多学者倾向于ECC 转流期间维持小潮气量的持续肺通气,2019 年《欧洲成人心脏手术心肺转流指南》也将转流中持续气道正压通气列为肺保护的ⅡB 级证据。 因此,转流期间持续小潮气量机械通气,如果再间断辅以小剂量含氧血肺动脉灌注,理论上可从预防肺缺血缺氧的本质上减少术后肺损伤。 但怎样平衡肺通气及间断肺灌注时机,而不影响手术医师操作而延长ECC 时间,尚需多学科商讨研究。 而且此观点也还有所争议。
4 ECC 期间的血液保护
虽然围术期血液保护的实践在我国日益获得发展,但心脏手术却由于病种的特殊性、ECC 对血液成分的破坏以及术中出血量过多等特点,围术期输血率仍然极高。 我国成人心脏手术的同种异体输血率约为70%,部分医院甚至高达100%[9]。 术中血红蛋白过低则难以维持血流动力学的稳定,全身组织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ECC 期间消耗的大量血小板、凝血因子若得不到及时补充,同样会带来术中止血困难、术后引流量增加甚至二次开胸手术的风险。故同种异体输血可短时间纠正患者的病理生理状态,于危急时刻抢救患者生命。 然而日益增多的研究却报道围手术期同种异体输血是术后感染、肾衰竭、呼吸功能不全等并发症的独立可靠相关因素,甚至对患者近期及远期生存率产生不良影响[10]。 心脏手术如何尽量减少围术期同种异体血的输注,依靠于先进的血液管理技术和严格的输血指征。 血液管理技术的改善需要心外科、麻醉科、ICU、输血科等多学科的共同合作。
麻醉方面,ECC 期间在保障终末器官足够血供的情况下可适当施行控制性降压,可明显减少术中失血量。 同时,若无禁忌术中尽可能使用血液回收技术,人工心肺机循环管路中残余机血的回输也应囊括在内。 其次,对于术前血红蛋白偏高、预计术中出血量大且心肺功能尚可耐受一定循环波动的患者,麻醉诱导后可采用急性等容血液稀释方法预存一定血液,转流结束后回输预存的自体血。 急性等容血液稀释不仅改善凝血功能、提高血液携氧能力,并可一定程度上减少围术期同种异体血的输注[11]。再者,ECC 期间麻醉医师应个性化使用止/凝血药物,依据如血栓弹力图等各种检测结果个体化输注血液制品。 最后,针对基于肝素的药代动力学模型对鱼精蛋白使用剂量的研究,有学者建议将鱼精蛋白的剂量减少到初始肝素剂量的1 ∶1 以下,以防止术后凝血障碍,减少术后出血与输血,但结果尚未进入日常临床实践[12-13]。
综上所述,从调整麻醉药物的使用、肺保护及血液保护三方面浅谈了ECC 期间麻醉医师应如何细化麻醉管理,配合灌注医师调控患者术中生命体征。ECC 转流期间灌注医师负责生命体征的主要管理,麻醉医师紧绷的神经也不能松懈,应细节化处理好ECC 转流期间各种问题,尽量减少非生理性ECC 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而保障患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