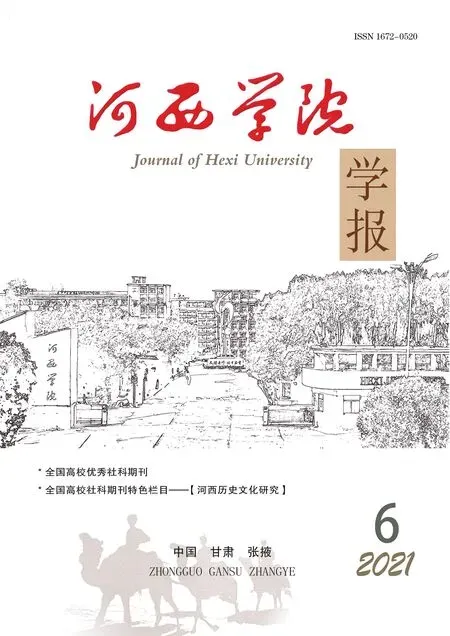孟子性善论的逻辑缺憾与社会价值
李昕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孟子的性善论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过程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作为儒家思想的主流,其影响之深远不可估量,时至今日依旧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价值。随着近代以来中西方思想之间不断地碰撞与交融,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从西方哲学的角度去分析性善论,并得出一些值得反思的结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运用许多形式逻辑的方法去考察孟子对于性善论的论证是否合理,这些带有西方形式逻辑色彩的审视洞察出了性善论中许多逻辑方面的不足。然而这些再思考是否真的能动摇性善论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地位?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看待性善论的不足和价值?在对性善论的逻辑缺憾与社会价值进行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学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方法。
一、从与告子关于人性的三段辩论来分析孟子论证性善论时所存在的逻辑缺憾
孟子是我国古代有名的辩论家,与孟子同时代的人们就评价孟子“好辩”,而我们在阅读《孟子》文本时也会有这种直观的感受。不论是与当时的君王进行政见方面的探讨,还是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对某一哲学论题展开争辩,孟子都“善于针对一些反命题提出自己的正命题给予驳诘,不论这些反命题是怎样提出来的,他都能酣畅地进行辩论,直至把话说完为止。”[1]他能够在辩论时率先用气势压倒对方,抓住对方的语言与论证漏洞步步逼近,让对方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种气势也极易将读者卷入他的语言中,无法自拔地相信他的论证,是典型的“雄辩”。同时,他还非常擅长运用各种典型的事例和生动的比喻来说理,这些辩论方法都对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逻辑思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然而孟子虽然每每通过气势上的压制、步步逼近的驳诘和生动形象的举例最终都能成功地让对方无话可说,但这并不代表孟子对于自己观点的论证过程就是毫无逻辑缺陷的。事实上,孟子的辩论在许多地方都存在着明显的诡辩倾向,逻辑的不严密性经仔细推敲就可以看出。当雄浑的辩论气势从我们的脑海中淡出时,我们就会对他种种的论据和语言产生疑惑,总觉得不能够完全说服自己。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称孟子的论辩逻辑是“甚僻违而无类”。学者们多认为孟子的论证和说理常常是偷换概念、牵强比附,在一些地方存在着隐形的逻辑断点,断点的两端是两个毫无关联的概念、事象。”[2]有时甚至会使得自己的观点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侯外庐先生则将孟子的论辩方法称之为“无类比附”,他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道:“僻即邪僻之谓,无类即附会之谓。荀子逻辑学中的类的概念甚清楚,但孟子有关人性的辩论,其所举之自然物,都是不类的概念。”[3]而这些逻辑问题都在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论的辩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下文就只以《孟子·告子章句上》中孟子与告子三段关于人性论的辩论为例来具体分析孟子在论证性善论的过程中有哪些逻辑缺陷。
《孟子·告子章句上》中载: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4]195
在此段论辩中孟子所犯的逻辑错误主要表现在“过于迁就敌论,而放弃自家主张的立场”。[5]孟子在平日主张“以人性为仁义”,告子则将此作为攻击对象。他将人性比作杞柳,是制作桮棬的原材料,又将仁义比作桮棬,是用杞柳制成的器皿,这就使得人性和仁义有了材料和成品之分。也就是说在告子看来,人性和仁义的关系就与原材料和成品的关系相同,原材料转化为成品必须要经过人力的加工才能完成,那么人性中要想生出仁义的成分,也必须要借助于外力,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这就与孟子“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4]200(《孟子·告子章句上》)的观点相违背。但孟子没有一开始就针对告子所认为的只有借助外力才能使人性中生出仁义的观念进行根本性地反驳,指出他譬喻事物的不正当性,而是默认了他的比喻,顺着告子的思路提醒他:杞柳之所以能够制成桮棬,是因为顺应了杞柳柔软的特性,而没有破坏它。这仅仅只能够表明仁义的生发是顺应了人性而没有违背人性,让人感觉孟子在这里似乎承认了仁义是人性中后天所生成的,这就与他自己的观点前后矛盾。
至于孟子所言“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更是无中生有、无的放矢,告子并没有认为将杞柳制成桮棬是损害了它的特性,孟子在这里把自己的假定强行加于告子的观点之中,最后竟然给告子扣上了“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的大帽子,明显有强词夺理之嫌。孟子在此番论辩中没有抓住争论的根本点,使自己的论述与自己的观点前后不一致,还在对方的观点中强行加入自己想当然的成分,因而在逻辑方面是比较失败的。
孟子和告子的第二段辩论记载道: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4]
在第二段论辩中孟子所犯的主要错误就是牵强比附,且只提出观点而不进行论证。“这种牵强比附,就是从主观需要出发,以‘我’为标准,完全不顾客观实际,不问是否同类,任意牵扯。”[1]在这场辩论中,孟子和告子均采用了水作为论证材料,告子以“水之无分于东西”作比来论证人性无善无不善,而孟子则以“水之就下”作比来证明人性本善。比起水流向的东西,孟子所例举的“水之就下”似乎是水流状态更深刻的本质,所以他的论点好像更能说服人。
这里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人性与水性并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一种机械类比的诡辩手法,就是把两个性质根本不同,或只具有某种表面相似性的对象拿来作类比,由其中一个对象具有某种性质而推出另一对象也具有某种性质,这种机械类比得到的结论是不可靠的。”[2]在这里,孟子和告子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将两个毫无关联的事物进行类比之后,孟子没有对“人性之善”为何“犹水之就下”进行任何的论证,就断言“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若照此不进行论证就随意断言的情况,“那么别人是否可以说‘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呢?’既然不论证,那就有两种可能。”[2]这也是孟子在类比推理中经常犯的错误,只是通过打比方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并没有给出这一事例为何会与这一观点相类比的具体论证,这样的论证不能使人信服。
孟子在此番论辩中一方面举例牵强附会,另一方面则不经过论证就武断地下结论,在逻辑方面体现出了很强的随意性,而这也正是孟子论辩逻辑中最大的弱点,也是他最常犯的错误。
孟子和告子的第三段辩论记载道: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4]
在第三段论辩中孟子所犯的主要错误就是偷换概念,通过将两个不对等的事物进行对比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性”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名词,我们只有在“性”之前冠以一个具体的范围,例如“犬之性”“牛之性”和“人之性”,才能大体地知道这里的“性”是什么样子。但“白”却是一个有着确定内涵和特点的形容词,我们都知道“白”到底是什么样子,并且能够根据它来判断一件特定的东西是不是白色,或者是哪种白色。“换个方式来说,某物之‘性’完全取决于此物本身,而某物是否为‘白’则取决于它是否包含了我们早已独立界定为‘白’的那个特质。也就是说,在短语‘X之性’中,‘性’是‘X’的应变量,而在短语‘白羽之白’中,后面的‘白’并非‘白羽’的应变量,而具有自己独立的意涵。”[6]孟子在没有对“性”与“白”进行充分区分的情况下,就将“生之谓性”和“白之谓白”等同,是对概念的偷换。
接下来孟子更是将人兽之性做对比,以白羽之白非白雪之白、白雪之白非白玉之白,说明犬之性非牛之性、牛之性非人之性。但这只能说明人性与兽性有别,却不能说明人性就是善的。因为禽兽没有分辨是非的意识,无法断定禽兽之性是善是恶,或者说是无所谓善恶,而与无所谓善恶的兽性不同的人性则是有所谓善恶的,但到底是善是恶从孟子的反驳中无法得出。此外最根本的错误还在于“我们用人的思维和人类社会善恶标准,来评判犬牛之性善恶,也是可笑的”。[7]孟子在此番论辩中将“性”和“白”概念互换,通过用人兽对比的方法证明人性善的方法是十分不符合逻辑的,并且最终也并没有得出他想要论证的“人性善”的观点。
二、从孟子提出性善论的目的和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来捍卫性善论的社会价值
从以上对孟子与告子三段辩论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子的辩论在形式逻辑方面具有非常多的纰漏,不同的学者都有对其逻辑进行不同方面的分析和审视。然而问题也随之产生了:既然孟子的这些论述在形式逻辑上不能站稳脚跟,甚至在某些地方因缺乏论证而显得有些强词夺理、咄咄逼人,那么他是如何让人们相信性善论的?性善论又是何以逐渐发展成为儒家思想的主流并深刻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近千年?
想要弄清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眼光就不能只局限在形式逻辑上,也无法再使用西方哲学的那一套思维方式。因为“儒家历来轻于逻辑思维,重于生命直觉”[8]。孟子并不是要通过多么严密的逻辑来证明性善论的正确,而是想通过举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平易近人的例子或常识来启发人们反思自我、体悟本心。虽然这种方法导致他在辩论中多次类比论证不当或者过于以偏概全,但依旧需要承认这些来自于每个人身边的例子的确让他所叙述的道理更加活灵活现、易于理解。毕竟孟子论证人性本善的最终目的还是想要教化民众使民风向善,以及极力说服国君认同他的观点进而推行“仁政”,而民众与国君往往都不是逻辑学家,反而这些越贴近生活的说明越容易使他们信服且无法反驳。当人们透过生活中的例子来反观自己,并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时不自觉触发的恻隐之心,“体察到自己体内那触之能动、动之能觉、呼之欲出、求之必应的良心本心,由此便对性善论坚信不二了”[8]。
当然孟子的观点令人信服的原因也不能排除《孟子》一书的编撰因素,“《孟子》一书编撰者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后人对于孟子的态度和倾向。”[6]在《孟子》中所记录的告子的言论都是极其简约且大多处于守势,我们很难从其中观出告子思想的真实面貌,因此相较于不全面的、简化的告子的言论,大家就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接受孟子清晰的、成体系的观点。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更要关联到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孟子生活在统治者征伐不断、黎民百姓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战国时期,他将诸侯间延绵不休的战争描述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4](《孟子·离娄上》)。孟子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天下之混乱较孔子的时代更甚,统治者们贪图私利、自私卑鄙、巧言令色且不知餍足,将仁义道德抛之脑后,更无法为民众树立正面的效法榜样,自然也会使得民心动荡、不慕正途。此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的孟子便高呼:“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4](《孟子·公孙丑上》)他带着“圣人之徒”的历史使命感捍卫着“先圣之道”,竭尽全力地“正人心,息邪说”[4](《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因此他始终强调性善论,坚决反对告子“性无善无不善”论。“告子的人性论,是以‘生之谓性’为出发点。生之谓性,即是说凡生而即有的欲望,便是性。生而即有的欲望中最显著的莫如食与色,所以他便说‘食色性也’。”[9]但是若只谈食色之性,如何证明人与禽兽之间的区别?若性真是无善无不善,我们该如何把握人生之路、正视道德?基于此,孟子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4]200(《孟子·告子上》)正如孟子与告子的第二段辩论,他的确承认告子所说的“水之无分于东西”,但他更坚持在水无分东西的背后一定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水之就下”。就像尽管我们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好人、坏人等各式各样的人,但这些看似不同的人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共性,那便是“人无有不善”,并以此将人与禽兽区分开来。人们在知道了自己因固有的仁义礼智而与禽兽不同的时候,便能体会到人自身的价值;在认识到作为人良心中本就存有的四端之心后,便能够正视道德的崇高地位。
此外,孟子通过对性与命的论述为人们如何把握人生之路提供极富有力量的方法论:“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4]260(《孟子·尽心下》)在这段话中,孟子明确指出口、目、耳、鼻和四肢所追求的人的肉体自然欲望是“性”,但为什么又接着说这些都“不谓性”?戴震在这里解释为:“‘谓(性)’犹云‘藉口于性’耳;君子不藉口于性以逞其欲。”[10]也就是说,“人的食色等生命欲望的实现先天地就具有着内在的道德规定性,只有在此规定性下,才可称之为人的‘性’;离此规定性,抽象孤立地以食色欲望的满足为人性的内在要求,不顾道德上的可行与否,那也就不可称之为‘性’了。”[11]然后孟子紧接着举出仁、义、礼、智、圣这些人本心所具有的道德规定性则是想要表达,“虽然道德上的尽伦难免有命运的限制,但君子并不以之为借口而不努力去做,因为这正是人性的内在要求。”[11]至此,孟子将选择人生道路的主动权最大程度地交由人们自己,不以自己无法对抗命运为借口而自暴自弃,因为仁义礼智这些上天赋予我们的先验道德,是只要我们不断反求诸己就可以存养与保持的,“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4]200(《孟子·告子上》)。而普通人与圣人之间的差别也只在于圣人善于存养和发扬四端之心罢了,是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4](《孟子·告子下》)。这便鼓励人人向善,即便身处乱世,无法左右周遭环境,但本心中的善性依旧是我们唯一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而把握的,而人们也不能为了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就违背本心的道德准则,这样便与禽兽无异。这些思想都对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稳定民心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杨泽波先生在他的著作《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引用了两段古人精彩的评论来论述性善论在指引人们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所具有的功绩。其一是出自明代吴廷翰的《吉斋漫录》:“圣贤扶世立教,取其可以为天下后世训者,所以为正也。使告子之说行,则人将以性为恶、为伪、为在外、为与物同,而人类化为禽兽矣。犹幸而有孟子之说在,则人皆以性为善、为真实、为在内、为与物异,为仁义之道明,人类不至于禽兽,其为功也,孰大焉!”[8]194其二则出自陈确的《别集》卷四:“孟子兢兢不敢言性有不善,并不敢言气、情、才有不善。非有他意,直欲四路把截,使自暴自弃一辈无可藉口,所谓功不在禹下者。”[8]244而性善论的这些功绩也成为了它能够在今后近千年中一直作为儒家文化的主流思想并影响中华民族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孟子具有高远的理论视域,他并不仅仅把眼光局限于当代,他说得很清楚:‘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公孙丑上》)他要成就的是具有普世性的千秋功业。”[12]由此也可看出告子思想最大的缺陷也在于他“只是就性论性,没有把他的学说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8]276。它虽然符合我们的第一直觉,甚至从近代科学来看也不无道理,但却无法给予当时社会的人们有价值的方法论指引,或者说告子的思想更像是叙述一些客观在发生的事情、一些现象,无法称其为一种人生哲学。
三、结论:对待性善论的正确态度
结合以上对孟子性善论中逻辑缺憾与社会价值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探究孟子辩论中的特色与方法,指出其中的逻辑缺陷,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孟子》的理解,也能促进我们对自身逻辑思维方式的反思和自觉。孟子作为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辩论家,研究他的辩论方法和逻辑缺陷对于丰富我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内容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牢记的是,孟子性善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并不能由其辩论所体现的逻辑性来决定,虽然按照形式逻辑的标准,孟子论证的有效性确实受到质疑,但是并不意味着其揭示的道理没有洞见。我们在看待性善论的合理性和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时,应当适时地抛除西方哲学的思考理路,返回到中国哲学特有的语境中来,把握中国哲学重视生命体验的本质特征,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准确地把握性善论的伟大之处,体会其对于塑造中华民族性格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感受中国古代哲学家心中强烈的担当精神。
正如杨泽波先生在探讨如何研究儒学问题时所强调的:“西哲叔本华说过,一流哲学家从生活中发现问题,二流哲学家从书本上发现问题。这对我们研究儒家哲学也是适用的。学习儒学当然要读书,但更重要的是从生活出发,重视生命体验,而不是从书本到书本,扣着名词概念,做死学问,否则很难读懂性善论,真正踏进儒家的门槛。”[7]这也是在探讨性善论的逻辑缺憾与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我们最终需要领悟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