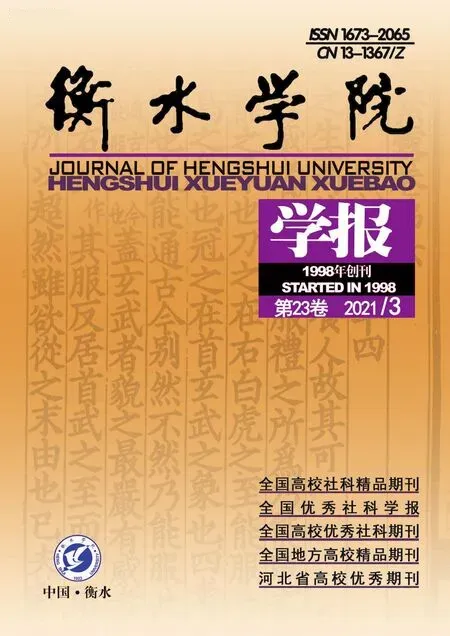董仲舒礼学思想初探
谢遐龄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董子之学为《春秋》学。《春秋》公羊学与其说是史学,不如说是史论——按今日语句,是历史哲学;用古人语句,乃王道学也。司马迁引孔子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所述乃董子之旨。
一、六艺皆尊,独重《春秋》
董子曰:“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明确指出,君子养德,六艺缺一不可。然而董子以治《春秋》公羊学闻名。其文曰: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1]35
六学,六艺之学,也即六艺。《汉书·儒林传》曰:“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①《春秋繁露义证》第35页夹注的引文,六艺作“六学”,“致至治之成法”少一“致”字。这六种典籍全面展现先王之道,故而称为“王教之典籍”。其阐明天道、校正人伦,是国家治理臻于至善的完成了的轨则。
董子语:“《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司马迁《史记·自序》述董子意旨曰,孔子作《春秋》,意在阐明先王之道,而不抽象地谈理论。《春秋》价值巨大,乃“王道之大者”。虽然夸张地称“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实则重点在“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专论国家领导核心(天子、诸侯)和领导干部(大夫)言行得失,确定国家治理(王事)之范则。可见董子所谓“《春秋》长于治人”,所治的人并非庶民甚或一般干部,乃天子、诸侯、大夫等领导干部。其重要在于: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弒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2]3297-3298
引文中“其实皆以为善”是关键。这是说,或许当事人皆出于善意,但由于不通《春秋》之义,则堕入罪恶之渊。担当领导责任者“通于《春秋》之义”,方能明谗贼、通经权、避恶名。“《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深刻阐明了《春秋》与礼学关系。
阐发《春秋》之义,须借孔子之名。而董子面对的现实背景却与孔孟迥异。孔子身当乱世,“王路废而邪道兴”,指示的是拨乱反正途径。董子身当太平盛世,天下统一于汉室,吏治蒸蒸。然而,经秦“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2]3115-3117。汉高祖虽然重视儒学,干戈未定,“未暇遑庠序之事”;惠、吕时期,政局不稳;文帝时虽然征用儒士,然而重视的却是刑名思路;景帝不任儒者;武帝初期,太皇太后窦氏强势,好道家。整个国家机器,任职的主流人才崇尚的是武力和刑罚。黄老之术,要点是无为而治。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生动地传达了道家让弱者任强者欺凌、自生自灭的治国思路。这种思路,在远古小国,或许适用;汉初,战乱之后与民休息,也还可用;社会财富积累之后,权贵渐兴,王室富豪骄横肆虐,在天下一统的郡县制国家,难免导致小民残破局面。上引董子说“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切中时弊,他张大儒家天道为仁的思想,为儒家在中华民族取得永恒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已有的共识是遵奉先王之道。汉朝诸帝注意倾听群众意见,所至会见“缙绅之士”,因而崇奉王道。王道存于六艺;董子倡导六艺养德。六学都重大,各有所长:《诗》长于质,《礼》长于文,《乐》长于风,《书》长于事,《易》长于数,《春秋》长于治人。
司马谈论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理由是“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然而继承他未竟事业的司马迁却推崇董仲舒,归心于《春秋》公羊学。盖因时代的需要。历史选择了儒家:回归王道需要复兴六艺之学;儒家本来是诸子之一,然而自孔子整理六经、以六经教学以来,重振经学时就只有儒者能承担使命。国家要长治久安,不得不托付于儒家。
汉朝诸帝对国家宗教有足够的觉悟,抓得很紧。刘邦起兵时,制造了“赤帝子斩白帝子”的舆论,暗示民众天命将从秦室转移到刘氏。此秦室之故技也。瀛氏始封侯,就僭越私建白帝祠:
秦襄公既侯,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2]1358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2]685
其后,揽已有诸上帝建祠祭祀。既无统绪,又显狂妄自大僭越态度。然而,足以表明他们对宗教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这给我们留下一个历史疑案:秦统一天下,所借并非纯武力,宗教当起极大作用,为什么后世极少提及,仅存司马迁在《封禅书》中留下的资料,且无人问津?尤其是,汉代前期全盘继承秦室的宗教建设思路。为什么思想史家并未关注?
汉高祖起事,先祭社神,再祭蚩尤,后立黑帝祠①《史记·封禅书》记载:“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沿袭秦室制度,也注意分寸,所作所为与自身地位、实力对应。应该承认,他抓住了国家宗教最重要的象征,向天下传达天命归属之信息。然而,豪杰四起共亡秦室,刘邦忙于削平各个山头、完成一统大业,史论“未暇遑庠序之事”。无论宗教制度建设还是思想建设都未及着手,叔孙通立朝仪而已,其后“庠序之事”卓有建树,而宗教制度建设终究未做好,遗恨千年①朱子曰:“礼乐废坏二千余年。”《朱子语类》卷第八十四(《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2876页)。朱元璋论汉朝功业未够伟大,批评文帝:“尝阅《汉书》,濂与克仁侍。太祖曰:‘汉治道不纯者何?’克仁对曰:‘王霸杂故也。’太祖曰:‘谁执其咎?’克仁曰:‘责在高祖。’太祖曰:‘高祖创业,遭秦灭学、民憔悴甫苏,礼乐之事固所未讲。孝文为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使汉业终于如是。帝王之道贵不违时。三代之王,有其时而能为之;汉文有其时,而不为;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者也。’”《明史·孔克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923页)。。
六艺之学,解决的是统治集团(天子、诸侯、士大夫)思想建设问题。《春秋》学要解决的是最为急迫的问题——统治集团成员在治国理政中不犯错误。所谓正确、错误,衡量准则不是得失成败之类的利益,而是王道、天道,这充分体现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子曰:“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1]13注引孔子语“邦无道,危行言孙”,深得董子意。“义不讪上”,孔子所说“畏大人”。远、近,时代义也。即“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所划的时代②《春秋繁露义证》第9-10页,接上引:“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从《春秋》笔法中悟为人之义。《春秋》“世逾近,而言逾谨”,定、哀为君子所见世,故“微其辞”。领会此义,被起用,则发挥作用致天下太平;不被起用,则保身安。此谓“春秋之道”——为臣之道也。
为君之道,则以“君人者,国之元也”提纲挈领。其法:“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休形无见影,揜声无出响,虚心下士,观来察往。谋于众贤,考求众人,得其心遍见其情。”[1]166-167“谨本详始”释“元”义,下文详述。此言“敬小慎微”,讲的是为君者“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豪厘,驷不及追”。成语“失之豪厘,缪以千里”意思就是国家指导思想有些许偏差,贯彻到基层就会产生大毛病。“虚心下士,观来察往。谋于众贤,考求众人”颇见今日群众路线、协商民主义。董子学之时代价值可见一斑。
二、《春秋》大义缘礼而起:天、君、民构架
孔子作《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评定依据是什么?当然是王道。不过这样说似嫌玄虚。实在地说,评判准则是礼法。前引:“《礼》制节,故长于文”,通议也。实则如苏舆论曰:“春秋缘礼而起。”[1]10是董子之意也。
《春秋》之道,浅说“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究其源,则极其正大。董子语“《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也。法古,法先王也:“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圣人观天象领悟天道。贤者只有法圣能力。董子称这为“大数”——重大法则。“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
董子又述师说:“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传其法于后世也。”[1]14宣布的属于基本原理。天下无二道,道,一也。对今天更有警醒意义的是“古今通达”,义即古今情同。此董子“天不变道亦不变”义。今贤动辄称“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谓古今异情,古人所论于今日全然无效。岂知虽有巨变,亦有不变者,且不变者乃根本所在。“失大数而乱”,意在此乎?董子身处之时代与三代对比,亦堪称巨变。针对议者“王者必改制”论调,董子坚定宣称奉天法古为《春秋》之道。天变乎?天永远不变。奉天,谨守天道。三代圣王皆奉天,今王当法先王。法古即奉天。此贤者法圣义也。
董子着重阐述改制非改道。改制,调整礼制也。新“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受命于天,易姓更王,必须改制(调整礼制),顺天意也。紧接着文气一转,写道:“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结论“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1]17-19。
董仲舒所述“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之社会事实,可作为阐述当时国情民性的重要史料看。从春秋到秦汉,中国社会从宗法制转变为郡县制,实乃巨变。人类社会初始结构为氏族。氏族整合为部落,再整合为部落群……原先维系结构依靠血缘关系准则,整合为多个氏族,维系结构须有超出血缘关系的新准则。于是,一个矛盾出现了:血缘关系与超血缘的关系,哪个为重?在西方社会,超血缘准则盖过了血缘准则,或曰,社会高于家族;中国社会,血缘准则仍然占主导地位,家族仍然是最重要的社会存在。中西社会的重大区别,在秦汉时期已然定局。黑格尔《逻辑学》的“主观逻辑”部分有三个基本概念——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主观逻辑还可译为主体逻辑,可以理解为社会哲学。用这三个概念表述,则为:西方社会普遍性强过特殊性,中国社会特殊性强过普遍性。
按董子所述社会事实,秦汉似应普遍性占据主导地位之局面并未出现,仍然是三代时的特殊性优势状况。“天不变”,实则为人情不变;人情不变意为社会事实不变——仍然是家族社会而非黑格尔《法哲学》中描述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解构家族)。
当代中国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相互纠缠、冲突,尚无结果。抽象态度不坚定,普遍性终难占上风。董子提及“人心之动”[1]23,观今日之乐曲,民情抵制抽象态度依旧。
“《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1]6。在《春秋》中,礼地位尊贵,尊贵到何等程度?比自己身体更尊贵。“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所据皆礼。《春秋》记楚庄王杀夏征舒、晋伐鲜虞,是也。不通礼义之旨就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犯天下之大过。“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2]3298。
“缘此以论礼,礼之所重者在其志”,注曰:“缘《春秋》论礼,深得其本。”志,心志,今言意志、意向。《春秋》记事,微言贵志——“《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1]38。礼以正行,志则在心。贵志,直指心志也。
志,意旨、意义。“志为质,物为文。文着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质、文缺一不可。“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1]27,质比文重要。
又,志义为态度。“右志而左物”例,由“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引申为“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由“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引申出“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质,内心态度。态度虔诚最重要。
可见,贬、退、讨,皆在诛心。
董子语“《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确定天、天子、民众三者关系。并宣称“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31-32,这是礼学的基本构架。当前我国学界理解古代社会有个误区——把天人关系与君民关系分割为两个问题域,天人关系涉及的似乎只是道德、思想类的精神境界。实则古人心目中的天人关系,既是思想观念,也是现实结构。由于人们长期浸润在西方思想中,以西方概念理解本土思想,以为天应当有超越性,而超越性不足。乃至认为上天崇拜不够格看作宗教。古代中国思想的天,就是物质自然、精神上帝未分化而笼于一体的。用当代语言叙述,天与人都是“物质的”,也都有“感应性”。天人感应说来神秘,那是因为用西化了的当代汉语理解所致。在古人当属自然之理。天既是物质自然,又是精神上帝。论天道,首先遭遇的是春夏秋冬四时。最大的抽象性的天道,则是乾坤——“法象莫大乎天地”,其来源也。“物质性”何其强也。论及社会,则只看到君民关系。这也是当代思路以政治观社会所致。殊不知古代神人一体、宗教与政治一体。天人、君民在一个结构中——切勿以当代思想解读为分开的两个结构合并成一个,而是本来就只是一个结构。
“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按照当代一些学者的解读,必谓之“君主专制主义”。这是仅仅从政治学角度的解读,是片面的。切不可忘记还有两句话:“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当代学者多半会解读为君主的权谋、利用宗教统治民众。然而这样解读是曲解了古人的思想、古代的社会事实。天、天子、民众是一个结构中的三环。《春秋》大义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重点是“屈君而伸天”——因为《春秋》是给统治集团的成员们及其接班人学习用的,是让统治集团成员敬畏上天,不要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这是礼学中最重要的意图。古礼最重要的是祭礼,祭礼最重要的是祭祀天地。意图就是“屈君”。 为臣民之道,有功则归于君。董子曰:“《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故忠臣不显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1]52
这从属于一条普遍法则。“子云: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又: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诗》云:‘尔卜尔筮,履无咎言。’”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让善。《诗》云:‘考卜惟王,度是镐京。惟龟正之,武王成之。’”
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显哉!’”
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3]1641-1644
这些行为准则,当今中国社会依然通行,被视为美德。证明董子所说“古今通达”至今有效。至于“屈君而伸天”,古语曰:“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归诸天子。卿、大夫有善,荐于诸侯。士、庶人有善,本诸父母,存诸长老。禄爵庆赏,成诸宗庙,所以示顺也。”[3]1567这段文字记于《礼记·祭义》,提示祭天、祭祖之意义。祭天、祭祖越隆重,天子越谦卑,不会出现个人迷信现象。顺字要紧。顺,坤道也。乾健坤顺,天下太平。古今对比,足见董子揭示古代中国“上天、天子、臣民”宗教、政治一体结构之重要。或有论者曰:董子尊君。此论不能说全错,然而仅仅对了一半,且是一“小半”。董子更尊天。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古代中国“上天、天子、臣民”之“宗教-政治-社会”三位一体结构及其内涵的意义。
三、“三统五端”说透显董子礼学的宗教性
虽然现存董子文献缺漏甚多,涉及礼学已是广博。本文只能择要略述一二。
董子的“三统五端”理论是著名的大理论——大一统、正三统。学者们大多从历史哲学角度阐释,本文则从礼学角度看,阐释其礼学意义及内涵的宗教性。
孔子论禘祭十分重要:“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4]又泛论祭礼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3]1681足见古代中国国家是个宗教与政治一体的结构。祭天祭祖之类的宗教活动是最重要的国务活动。礼制既是政治制度,又是宗教制度,体现了宗教与政治的一体性。还说明,关于禘的制度及其解释对于治国理政有重大理论价值。这相当于孔子向后世儒者提出的研究课题。
董子的“三统五端”理论可以理解为对孔子课题的回应。
董子论《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提纲挈领,展示其礼学思想鲜明的宗教性。
史家公认汉代礼制建设欠缺较多,然而,对于祭祀天、帝,还是相当重视的。武帝开始登泰山封禅,其后诸帝重视程度不减,还多次研讨祭天地点。汉之后历朝祭天祭祖都有变动,而重视程度未曾减少。总的原则是:祭祀要追溯到最古的帝王;历代帝王须择杰出的配祀。这是“奉天法古”之落实。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社会的国家宗教是从远古连贯下来的,至少五千年;历代皇室都认为,既然君权天授,作为受命的天子,自己就是这个国家宗教的教主继任者。怎样祭天,祭祀时配多少先祖、前朝帝王,就成了重大实践问题。
董子面临的使命,还有其特殊的维度——促使国家治理贯彻儒家的仁政主张。他在答武帝问的对策中写道: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5]
依《春秋》文“春王正月”,寻绎王道之端,在这个“正”字。而“正”字在“王”字后面,“王”字在“春”字后面。春是天道运行;正是王应该做的事。所以“春王正月”的意思是:上,承接天之所为;下,正己所为——正王道之端。可见,王者无论打算做什么,都应根据天道确定准则。
解释“春王正月”之后,董子宣称天道之大者在阴阳,再设定阳为德、阴为刑——颇似现代方法,构建理论时,建立公理、公设,而后再演绎出全套定理。如此确定了仁政的理论根据。又: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此释大一统。董子明确要求君王正心。董子贵元,意在此乎?)
《春秋》为什么不称“一年”而称“元年”?一,够伟大;而元,内涵丰富,意旨为大。把一改称元,表示(视,示也)提升开始,意图是正本。
在“元”字上做文章是公羊家的大理论。董子有所创意,“谓一元者,大始也”[1]67,把一改称为元,强调开始。读史,常见朝廷改年号,或称改元。其义深远——与天下重新开始。意思是之前不少错误,天下不满意;现在总结经验教训,另定路线。
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①《春秋繁露义证》第147页。苏舆把这段移至第68-70页。笔者引用时稍改钟哲所断标点。
这段话涉及重要哲学问题——元是否在天地之前?由苏舆加在“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句的按语看,似乎把元提升为最高概念:
俞云:“乃在乎”三字衍。安在乎天地之前,言不必在天地之前也。《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圣人之言,未有言及天地之前者。
舆案:何注言“天地之始”,即本此文。三字非衍,所谓以元统天也。宋周子无极而太极之说,亦本于此。《易》“太极生两仪”,圣人之道,运本于元,以统天地,为万物根。人之性命由天道变化而来,其神气则根极于元。溯厥胚胎,固在天地先矣。《说文》列元字于天字前,亦即斯旨。《鹖冠子》“有一而有气”,宋佃注云:“一者,元气之始。”由是言之,人本于天,天本于元,元生于一,是故数始于一,万物之本也。[1]69
苏舆的引申有调和儒、老意;且“元生于一”未必是董子旨。董子所谓元,相当于一,语义加深,哲学位置却相当。依董子“天地人万物之本也”②《春秋繁露义证》第168页:“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此语境中“人”略相当于“社会”。之说,天、地、人皆本于元,“人本于天”亦须商量也。本文不深究哲学,苏舆之说是否妥当亦搁置不论,而董子把“元”置于崇高哲学位置则是极为明显的。
明白“元”之深意,就明白“改正之义,奉元而起”之意。注谓“奉元,疑作奉天。”非也。“奉元”义长。董子曰:“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祢,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一其司。”①《春秋繁露义证》第195页。“远追祖祢”钟肇鹏校补本改作“远近祖祢”,见《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444页注六)。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1]100-101。王政感动天象。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1]70此公羊义。“以元之气正天之端”,天本于元;政莫大于正始,即位,一国之始。王政之正,于即位正端。
上述各端都有相应的仪礼,如开春祭青帝,即位祭祖……“五端”说,揭示这些祭礼意义。这些祭礼应当怎样安排,要根据贵元正本原则设计。
“三统”说则阐明祭天、祭祖、祭祀各代先王的制度安排。
王者受命祭天祭祖,诸侯庙受祭祀,属祭礼,礼制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义:贵元正本。何以表明继统受命?董子认为“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化四方之本”,是“三统五端”②《春秋繁露义证》第196页。注谓“五端,即五始”。第71页苏舆“案:五始,元年一,春二,王三,正月四,公即位五。”《春秋》大义所在。,三、五就成为制定礼仪的依据。兹以正黑统为范例:
《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
《春秋》曰:“杞伯来朝。”(《春秋》文)王者之后称公(杞为夏之后人,应称公爵),杞何以称伯(伯爵)?《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把《春秋》看作新的朝代,以鲁为新王,因而要降低夏的政治待遇)。《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显示自身是新王),绌王谓之帝(原先以“王”的称号标志的待遇,降低为以“帝”的称号标志的待遇),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封地缩小担任祭祀)。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前两朝代的后人封地相当于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保留服色、礼乐体系),称客而朝(宾客待遇,来朝见)。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本代、上代、上上代,共三代,称王。此例,《春秋》、周、殷同时称王。两代以前,五代称帝。三王五帝,显示三统五端。所谓通三统,不把正赤统前代、正白统上上代看作臣子;三代之祖并称王)。
是故周人之王(重提周,与《春秋》作对比,加深读者理解),尚推神农为九皇(神农原称帝,周受命,待遇降级为皇,列为九皇之一),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帝轩辕改谥号,称作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原先就已称帝,周受命仍然保留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舜本称王,现降低待遇称帝),录五帝以小国(名号由王提升为帝,待遇从大国降低为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前两代之后人给予公的爵号、待遇大国,称作先王之后、宾客待之,接受其朝见)。
《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周时禹称王,《春秋》新王,夏越出上两代,因而要降低待遇,称号相应改为帝),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后也。称子又称伯何?见殊之小国也(回答前面提问“杞为什么不称公、而称伯”)。
黄帝之先谥,四帝之后谥何也?(五帝中为什么黄帝的谥号在帝号之前,其他四帝谥号在帝号之后)曰:帝号必存五,帝代首天之色③此句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454页)校点为“帝号必存五代,黄首天之色”,帝字依苏舆注“帝疑作黄”径改为黄。,号至五而反。周人之王(周受命为王),轩辕直首天黄号,故曰黄帝云(此处文字或有错、漏。苏舆注曰“黄帝同天,天不可屈,故首黄号”。大意是:轩辕功高齐天,但不可屈天为谥号,天依五行黄色最尊,因以为谥,置于帝号前)。帝号尊而谥卑,故四帝后谥也。帝,尊号也,录以小何?曰:远者号尊而地小,近者号卑而地大,亲疏之义也(这是条重要原则。年代越早的,称号越尊贵;年代越近的,封地越大。年代远近表现关系的亲疏。当代与前代、上上代称王;再前面五代称帝。帝比王尊贵。然而封地减小。王封以大国;帝则小国)。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复者、有三而复者、有四而复者、有五而复者、有九而复者,明此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在世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死亡及天命转移,则称王),绌灭则为五帝(越过前两代则称帝),下至附庸(封地降为附庸),绌为九皇(待遇降、称号再尊贵,称皇),下极其为民(无地称民,民为上古无名号之君;或逸其名号)。有一谓之三代,故虽绝地(无封地,民是也),庙位祝牲犹列于郊号(郊祭时有其位),宗于代宗(岱宗封禅时有其位)。故曰:声名魂魄施于虚,极寿无疆[1]187-189,197-203(德盛则声名永久永享祭祀,魂魄不至于消散)。
董子提出的“三统五端”体系,贵元正本,理论基础深刻正大,治国体制宽宏博大(与前两代并列称王,土地人民及宗教体制全部保留——区別在于,只有受命之君称天子,行祭天大典),对于所有先王都给予应有尊崇和待遇,充分体现国家宗教的继承性、一贯性。仁政之大者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董子“三统五端”学说,回答的不正是“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吗?(其他服装、祭器、时节等,董子皆有论列,文多不录)如此解答孔子课题,大哉!从中还可引申出殷周至春秋时期各国地位之说、新朝对待前朝态度(待以宾客,而非臣下,更非阶下囚)。中华文明传统,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