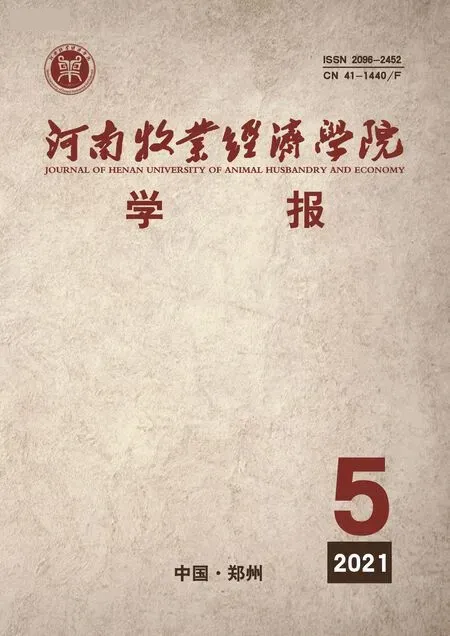昂扬疏狂的青年杜甫形象探析
谢其泉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教务处,河南 郑州 450002〕
诗人的文化形象是诗人在文化史及当代文化生活中赋予读者的总体印象,这一总体印象建立在诗人的传世作品、人生经历、个人品德的基础上,在社会传播与接受中,又受到诸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进而呈现丰富多元的面貌。从先秦时期的《诗经》开始,我国诗歌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诗歌发展历程中,涌现了大量的优秀诗人,但其中能被称为“伟大诗人”的,却屈指可数,能晋称“圣”的诗人则仅有杜甫一人而已。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志,却以深沉细腻的笔调,记录了国家、社会、人民的苦痛与磨难,被后人冠以“诗圣”这独一无二的殊荣。杜甫因“诗圣”名垂青史,但“诗圣”的光环也掩盖了杜甫形象的丰富性,局限了大众对杜甫的理解与认知,不利于杜甫诗歌与思想的传播与研究。我们拟从新的角度,剖开杜甫的“诗圣”光环,深入分析青年杜甫的形象特征,挖掘杜甫文化形象的丰富内涵。
一、杜甫“诗圣”形象辨析
“圣”这一词语,在长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一个十分神圣的字眼,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儒家对一个人人格的最高评价。“圣”字在甲骨文中已见记载。《说文解字》云:“圣,通也。从耳,呈声。”本意指天生的“听觉官能之敏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传》云:‘人有通圣者,有不能者。’《周礼》:‘六德教万民,智、仁、圣、义、忠、和。’注云:‘圣通而先识。’《洪范》曰:‘睿作圣。’凡一事精通,亦得谓之圣。从耳。圣从耳者,谓其耳顺。《风俗通》曰:‘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1]
由此可知,“圣”首先有“精通某一件事”的意思,就这一点来说杜甫是当之无愧的。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期,五古、七古、五律、七律等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杜甫以其天纵之资,在这些诗歌体裁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而且他在诸多领域的实践与探索皆具有开创性意义,是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元稹评价他:“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2]就诗歌创作而言,杜甫取得了承上启下、彪炳时代的成就,成为我国诗歌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是杜甫得以称“圣”的基本条件。
孔子在“一事精通”这一基础上,对“圣”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论语·雍也》篇: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3]孔子认为“圣人”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特质:一是在个人修养上,拥有崇高的品德,能够“仁而爱人”。二是在社会贡献上,能够关心底层民众,给民众带来好处,造福于民。孔子的圣人观是儒家圣人标准的基础,后世对“圣人”的评判标准皆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4]从杜甫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来看,以“圣”字来评价他是恰如其分的。杜甫一生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准则,对国家和人民饱含深情。他关爱妻儿、兄弟,孝顺抚养自己长大的姑母,同时一生贯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5](《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下文仅注篇目)的精神追求,每时每刻都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思索。对底层人民的困难,他报以极大的同情和关怀,用细腻深邃的笔调抒发饱含悲悯的愁思和哀叹。这些正是“诗圣”这一光环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杜甫之才本已凤毛麟角,其心灵之深广、其心胸之博大、其情感之深沉、其品德之崇高亦殊世难遇,而杜甫更能够以诗承其胸臆,以诗言其心声,以诗融汇时代,以诗为天下苍生造像,以诗为黎民百姓歌哭,可谓当之无愧的“诗圣”。
但杜甫的“诗圣”形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杜甫的一生以天宝五年入长安求官为分水岭,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早年的昂扬向上和中年以后的落魄辛酸。天宝五年之后,杜甫开始了颠沛流离、贫苦交加的生活,这也是杜甫慢慢走向“诗圣”形象的起点。但在此之前,即杜甫的青年时期,以“诗圣”形象来概括杜甫是不恰当的。在杜甫的诗作当中可以看出,其早年是一位昂扬疏狂的青年才俊,与老年沉郁清癯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探索、思考杜甫的青年生活,还原一个真实、独特的青年杜甫形象。
二、青年杜甫形象分析
学术界对杜甫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后期沉郁顿挫的诗歌创作,但对杜甫早年的诗作、经历往往鲜有关注。不同于杜甫中年的落拓困苦、晚年的四处飘零,杜甫的青年时代是极其精彩生动的。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且自幼聪慧,因此早年就有了一定的名气,是远近闻名的青年才俊。杜甫家境殷实,且唐代历来就有游历天下的传统,因此杜甫在青年时代游览了壮丽的山河,并结交了一批知名士人如李白、高适等。盛唐是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国家的强大使生活于这一时代的文人士子都有一种志气高昂、放荡狂妄的心态。这一心态是盛唐诗人所独有的,中晚唐诗人苦吟、低沉的特质在他们身上丝毫未有显现。杜甫的青年时代正是唐朝的“开元盛世”,因此杜甫与这一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都有一种自信、疏狂的情态,这在杜甫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诗作中皆可找到痕迹。
1.才华横溢的士人形象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簪缨的官宦家族,其远祖可追溯到东晋时期著名的学者、将领杜预。杜预注解的《春秋左氏传》在后世影响深远,杜甫对此也十分骄傲。杜氏家族在隋唐时期更加显赫,人称“京兆杜氏”,属于关中六大名门望族之一,时人赞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足见杜家之声望。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高宗、武后时期著名的文人,与苏味道等人并称“文章四友”。《旧唐书·杜审言传》记载,杜审言是唐高宗咸亨元年进士,授九品隰城尉,后被武后赏识,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晚年回到京城,授国子监主簿及修文馆直学士,直至去世。[6]4315杜审言在初唐诗坛名望甚高,五律即是在他的推动下走向成熟。高棅曾说:“长篇排律唐初作者绝少,开元后杜少陵独步当世,浑涵汪洋,千汇万状,至百韵千言,力不少衰。及观杜审言《和李大夫嗣真》之作,乃知少陵出自其祖,益以信‘诗是吾家事’矣。”[7]杜甫的诗歌创作受到祖父很深的影响,他对祖父的诗风及技巧有充分的研究和继承,因此杜甫在诗歌里自豪地宣称“诗是吾家事”。
杜家在当时十分显赫,这在杜甫的母亲身上也有所体现。杜甫的母亲出自清河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皆是当时的高门望族。唐朝时期虽然已经有了科举制度,但世家大族在当时仍然极具影响力。因此郡望和姓氏是当时士人择偶的重要标准。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8]皇室子弟有时亦不能娶到如崔氏、卢氏这等世家大族的女子,杜家能够迎娶关东望族的女子,足见杜家的兴盛和地位。杜甫成长于这样的家庭,自然是受到良好的教育。
杜甫出生高门,且天资聪慧,可谓自小就意气风发。杜甫晚年的诗歌中,经常自豪地提起自己早年的事迹,如“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有人认为,如骆宾王者,以神童传世,然而在童稚时期,只是对着白鹅这种家禽歌咏一番,而杜甫在七岁时就能够以凤凰自比,这种格局与气概是十分惊人的。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中提到:“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淋漓顿挫。”杜甫作此诗时,已是人到中年,但几十年前观看的剑舞仍然历历在目,这种超人的天赋,着实不是常人能及。
杜甫自幼秉承家学,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在儒家经典上,用功颇深。杜甫《进雕赋表》云:“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杜甫对儒家经典十分熟稔,在诗歌创作中他可以将儒家典故信手拈来。金启华先生在《杜诗证经》一文中,详细考证了杜诗出自儒家经典的典故数目,其中出自《诗经》的有106处,出自《尚书》的有12处,化用自《礼记》的有14处,引自《周易》者20处,来源于《左传》者27处,来源于《论语》者4处。[9]这些数字并不能代表杜诗的全貌,但已体现出杜甫深厚的儒学修养。杜甫在思想与品行上一直以儒家标准要求自己,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也经常援引儒家经典。如《又示宗武》诗:“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杜甫在教育儿子宗武时,将“饱经术”作为作诗和做人的根本,足见杜甫对儒学的推崇及其儒学功底的深厚。
杜甫晚年在回忆自己的早年经历时,曾自豪地说:“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人早年间曾与当时的显贵名流如李邕、王翰等互有来往,受到当时名士的推崇与看重。早年间与李邕的会面,就让杜甫印象深刻。李邕出自名门,其父李善注释《文选》,乃是举世闻名的学者名流,李邕自己也是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天宝四年,杜甫在第一次科举不中、游历山东之时,时年68岁的北海太守李邕竟屈尊前往齐州与杜甫会面。《新唐书·杜甫传》记载:“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10]2212李邕此时已名满天下,杜甫却只是个30出头的青年,两人在齐州历下亭把酒高会,相谈甚欢,席上两人谈古论今,也谈及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这让杜甫十分感动,留下了“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的名句。对杜甫这样一位白身的青年文士,李邕能够如此礼遇,足见青年杜甫的才华与名气。
2.交游广泛的诗人形象
盛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的一个时代,国家蒸蒸日上,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正如杜甫诗中所写:“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其二)随着国家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民众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大,商旅往来也日益频繁。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向东直到东南沿海,甚至远达高句丽、日本,西南可达南诏诸国。水路交通更是发达。《旧唐书·崔融传》记载:“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6]4412良好的经济基础,稳定的社会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为盛唐诗人的广泛交游提供了重要基础,杜甫青年时期就有过多次漫游的经历。
杜甫在开元十八年开始了自己的漫游生活,直到天宝四载结束。《新唐书·杜甫传》载:“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10]2212杜甫在这期间创作了一批流传甚广的诗歌,这些诗歌是杜甫早期的作品,诗歌的意境、价值自然不如其晚年的成熟之作。且这一时期杜甫在诗歌技巧上仍然十分稚嫩,在创作手法上有较多的学习祖父杜审言诗歌的痕迹。但这些作品是杜甫正值意气风发之时所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时候的杜甫还没有历经沧桑,对生活与未来充满希望。或许诗歌技巧不如晚年那么流畅自然,思想价值也不如晚年那么崇高,但却能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杜甫。此时的杜甫尚未经历“朝叩富儿门,暮随车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艰辛,没有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发出“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赠卫八处士》)、“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的慨叹,而是在名山大川、繁华都邑中留连驻足,痛饮狂歌,结交天下名士,是一位交游广泛、潇洒不羁的青年诗人。
杜甫的早期作品存世不多,仅二十余篇,但却充分地叙写了其早年的生活、交游经历。在齐鲁之地漫游时远眺东岳泰山,他写下脍炙人口的《望岳》。此诗描写了壮丽宏阔的巍巍泰山,并在诗中抒发了自己攀登顶峰、胸怀天下的豪情壮志。在游览繁华的东都洛阳时,杜甫被帝国的强大与兴盛深深震撼。观赏龙门寺夜景时,诗人以细腻微妙的笔触,写下了“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游龙门奉先寺》)的诗句。在齐赵之地漫游时,杜甫也和很多名士贤才诗酒唱和,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如在兖州所作《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在梁宋之地漫游时,杜甫偶遇李白、高适,三人结伴同行,长达数月之久。在这一时期,唐朝三位顶级的诗人相互学习切磋,诗酒唱和,“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在杜甫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杜甫在青年时代的广泛漫游,使其有机会结识众多名士。较为知名的有崔尚、魏启心、韦之晋、寇侍御、许登、李白、高适、李邕、郑虔等。杜甫早年与崔尚、魏启心往来甚密。两人当时都是官身,杜甫是一介布衣,但两人都对杜甫评价甚高。杜甫晚年追忆道:“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十四五岁的年纪,杜甫已经开始声名鹊起。杜甫曾在诗中自信地写到:“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大约在开元十八年,杜甫游历来到郇瑕,与韦之晋、寇侍御结识。杜甫在这里与韦之晋结下深厚友谊,韦之晋去世以后,杜甫还曾写诗追忆“凄怆郇瑕色,差池弱冠年。丈人叨礼数,文律早周旋”(《哭韦大夫之晋》)。
开元二十四年,杜甫在游历过吴越之后,回到老家巩县,并在这一年到京兆参加贡举,可惜再次名落孙山。“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杜甫十分失望,收拾行囊,继续开始新一轮的“梁宋之游”。在这次游历中,青年杜甫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李白。这一次会面是诗歌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事件,大唐诗坛最璀璨的两颗双子星终于会面,从此开始了一段传唱千古的佳话。李白与杜甫共同漫游,寻仙访道。后又遇到高适,这三位大唐杰出的诗人相约同行,每日饮酒纵马,游历唱和,留下了很多传世的佳作。晚年杜甫在《遣怀》一诗中回忆起当年与李、高二人在梁宋之间的交游时,仍然激动地写道:“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这期间,李白对杜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写下多篇记录与李白交游的诗歌——《赠李白》《梦李白》《天末怀李白》《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等,其中都洋溢着两位伟大诗人的深厚情谊。
杜甫在长达十五年的漫游过程中,结交了诸多文人墨客、时贤名士,并用诗歌描写祖国壮丽山河,抒发豪情逸思,在我国诗歌史上留下了别具光彩的印记。杜甫的青年漫游是我们理解杜甫形象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盛唐气象的一个直接表现,值得给予更多关注。
3.昂扬疏狂的青年形象
盛唐是一个极其浪漫、极其昂扬的时代,国家的强盛使青年人朝气蓬勃,热血沸腾,渴望出将入相,建功立业。在这种心理影响下,盛唐诗歌呈现出“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的时代特点。盛唐诗人大多怀揣政治理想,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满自信。王之涣登楼远眺,发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的兴叹。李白在拜谒李邕时,以鲲鹏自比,发出“大鹏一日从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的豪言壮语,奉召入京时高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即使被赐金放还后,也没有意志消沉,仍是高呼“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青年人成长于国家强盛时期,宏大壮阔的气象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认识,在诗歌创作上就表现为昂扬向上的精神、自信疏狂的语言。杜甫的青年时代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度过的,因此很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这在杜甫早期诗歌创作中就有所体现。
大众历来认为李白潇洒狂傲,杜甫苦大仇深,郁郁不得志。殊不知,杜甫在青年时代也是十分狂放不拘的,这在他的诗作中多有体现。杜甫出身名门,远祖杜预名垂青史,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因此杜甫从小就有“诗是吾家事”的信念。尤其祖父杜审言久负才名,在高宗、武后时期有很大影响力。杜审言对自己的文章和书法都十分自信,史书对他的记载不多,笔墨却主要集中于他的狂傲。《旧唐书·杜审言传》载:(杜审言)“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6]4315称自己的文章比屈原、宋玉还好,王羲之看到自己的书法也要敬佩不已,足见其自负和张狂。他的这种性格对青年杜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杜甫晚年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追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这样说道:“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杜甫宣称自己的辞赋可以和扬雄相比,诗歌可以和曹植等同,可谓与祖父的自诩有异曲同工之妙。晚年的杜甫依然如此自信,未经磨难的青年杜甫想来定是更加疏狂。
在杜甫的早期诗作中,可以看到很多描写他雄心壮志的句子。杜甫在漫游齐鲁时,曾远眺泰山,留下了传世名篇《望岳》。此时的杜甫意气风发,人生一片光明,抒发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豪情壮志。在见到房兵曹的胡马时,杜甫作诗称赞,诗中以骏马自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诗》),此时的杜甫亦如骏马一般,想要纵横天下,一往无前。在看到友人画中的苍鹰时,杜甫描写这只苍鹰“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锋芒毕露、翱翔天下的苍鹰正是杜甫自己的写照。青年时期的杜甫,还没有经历国家的动乱,遭受生活的打击,他与盛唐时期的青年一样,身上洋溢着高度的自信与昂扬的精神,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三、探析杜甫青年形象的意义
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其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卓越的诗歌艺术成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并在世界诗歌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杜甫作品,传播杜甫文化形象,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社会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具有积极意义。当下读者对杜甫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很多人认为杜甫的内心苦大仇深,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杜甫的人生黯淡漂泊,而忽略了杜甫青年时期昂扬疏狂的一面。这主要源于长期以来,对杜甫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杜甫中晚期忧国忧民、感怀伤时的作品。虽然杜甫被一步一步地捧上神坛,戴上“诗圣”的桂冠,但却造成读者对杜甫的认知和理解产生了很大的隔膜,尤其在当代难以使杜甫的诗歌和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识。探析青年时期的杜甫形象,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青年时期的杜甫与晚年截然不同,这时的他还没有那么成熟,也没有经历后来的人生大变,对未来充满期望。他有张狂自信的一面,也有纵马狂歌的生活,这样的杜甫更加“可爱”,更接近一个真实的“人”,更能引起当下年轻人的共鸣。尤其在网络时代,青年杜甫的形象,具有类似雍正“朕就是这样的男子”般的传播力。而这种正向传播,远比“杜甫很忙”之类的恶搞传播更有意义。青年杜甫形象,能与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气象产生一定的呼应。杜甫作为“诗圣”,是中华文化的最佳“代言人”,而他所“代言”的,不仅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厚重沉稳的一面,还有中华文化昂扬奋进、刚健有为的一面。
作为跨越盛唐与中唐两个时期的伟大诗人,杜甫青年时期的形象与其晚年是大不相同的。青年时期的杜甫,才华横溢,远近闻名。在游历名山大川时,杜甫结交了很多名士、朋友,这成为他一生的精神财富。青年时期的杜甫,痛饮狂歌,壮志凌云,这样的青年杜甫值得我们去喜欢,去研究,去推崇。将杜甫的青年形象与其晚年形象结合起来,有利于我们研究杜甫的心理发展及其思想发展历程,对构建一个完整的杜甫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