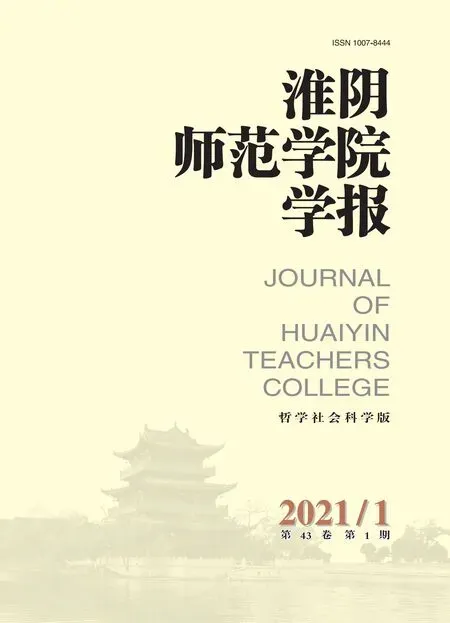论刘知几双重人格的形成及表现
杨绪敏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唐代著名史学批评家刘知几的《史通》以“多讥往哲,喜述前非”[1]292而受到后人的批评,比如明代学者陆深称其“是非任情,往往捃摭贤圣”[2]552。郭孔延则称其:“薄尧、禹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诃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谬,高自标榜,前无贤哲。”[3]清代学者钱大昕更是指斥其:“于迁、固已降,肆意觝排,无所顾忌。甚至疑古、惑经,诽议上圣。阳为狂易悔圣之词,以掩诋毁先朝之迹。”[4]303在此且不去论此批评是否得当,但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刘知几在史学批评领域无疑是一个勇士。他不仅详论史家之得失,倡导“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1]193的“直书”精神,更是敢于怀疑儒家经典《尚书》《春秋》记载的虚妄。在《史通·疑古》篇中,他直接指斥《春秋》等“六经”,“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则隐讳”[1]380-381,并把这种曲笔讳饰的起因归结为孔子的说教。他指出:“《论语》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1]380由此提出《尚书》记载可疑者10条,其中有论及对尧的增美和对桀纣的憎恶,并质疑二帝三王禅让征伐之事。在《史通·惑经》篇中,他以十二“未谕”、五“虚美”质疑《春秋》记事之虚妄。他指出:“《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1]409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子和儒经,因此被后人视为“非圣无法”[1]394,“名教罪人”[4]303。这显然与他“性资耿介”[2]552有相当的关系。然而他在生活中的为人处世思想与在史学批评领域中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示了他在生活中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为学则勇于直言、敢于指斥圣贤的双重人格。
刘知几的双重人格的形成,与他本人的境遇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在仕途上并非一帆风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考中进士,被授予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主簿(正九品下),在此任上近20年一直不得升迁。为了能够引起朝廷的关注,他在武后天授元年(690)和证圣元年(695)先后4次上疏武后,针砭时政并提出革除弊政的主张。4次上疏的内容集中在“吏治”和“法治”等问题上。比如针对当时封官的冗滥、官员的不学无术以及武后的纵容态度,他尖锐地指出:“至如六品以下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其有行无闻于十室,即厕朝流,识不反于三隅,俄登仕伍。斯固比肩咸是,举目皆然。”[5]1181因此他建议沙汰邪滥官员,清除尸禄谬官。在上疏中,他还批评朝廷频繁调动地方官吏的做法,指出:
历观两汉已降,迄乎魏晋之年,方伯岳牧,临州按郡,或十年不易,或一纪仍留。莫不尽其化民之方,责以治人之术,既而日就月将,风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渐百城。今之牧伯,有异于是,倏来忽往,蓬转萍流,近则累月仍迁,远则逾年必徙,将厅事为逆旅,以下车为传舍。[5]1198
由此主张:“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5]1198
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朝廷滥赐阶勋的做法,指出:“每岁逢赦,必赐阶勋,无功获赏,徼幸实深,其釐务当官,尸素尤众。”因此主张:“赐阶勋应以德举才升。”[5]1495再如针对唐王朝频繁地赦宥罪犯,他上疏批评道:
自皇帝受命,赦宥之泽可谓多矣。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若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敓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无疑惮。设使身婴桎梏,迹窘狴牢,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此忖度,咸果释免。[5]728
并呼吁朝廷:“而今而后,颇节于赦。”[5]728
刘知几的4次上疏,词语直率而尖锐,表现了他耿介正直的性格。遗憾的是,武后看了他的上疏后,只是“嘉其直”而“不能用”[6]4519。无疑给刘知几泼了一盆冷水。这也直接导致了他处世思想的变化。
刘知几给武后上疏的动机,无非两点,一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看到朝政的日益腐败,作为一个士大夫,他觉得应该挺身而出,针砭时政,为国担当;二是长期被埋没在基层,希冀通过上疏,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有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应该说,这两种动机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当时正值武后大开告密之门,酷吏竞为罗织之时。史官描述当时的情景是:“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造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时法官竞为深酷。”[7]6465甚至“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7]6485。面对严酷的现实,刘知几事后对自己的不计后果、直言劝谏感到后悔。就在他上疏不久,证圣元年(695)他写了《思慎赋》。《新唐书·刘子玄传》称:“时吏横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诛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无良而甘于祸,作《思慎赋》以刺时。”[6]4520这里只说对了一半,“刺时”固然不假,但刘知几作该赋的主要目的还在于自警和警诫他人。
《思慎赋并序》开头便揭露了历代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严酷性:
然历观自古以迄于今,其有才位见称,功名取贵,非命者众,克全者寡。大则覆宗绝祀,埋没无遗;小则系狱下室,仅而获免。速者败不旋踵,宽者优在子孙。至若保令名以没齿,传贻厥于后胤,求之历代得十一于千百。[8]1653
从而揭示了“位高权重者危”这个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何避免陷入这种悲惨的境地?刘知几进行了反思。“吾尝终日不食,三省吾身,觉昨非而今是。”[8]1653在其《慎所好赋》中称:“虑今是而昨非。”[9]1654他所追悔的“昨非”,明显包括自己往日的直言敢谏。于是他决心“舍旧而谋新”[8]1653。所谓“舍旧而谋新”,就是要改变以往的做法,采取新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
他的“谋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慎言语。刘知几认为:“祸福无门,唯人自招。”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出“多言之必败”的结论。由此提出了“慎言语”“守愚养拙”[8]1653-1654等主张。他说:“揆荣辱之在身,犹枢机之发口,倘一言其靡慎,奚四大之能守?”[8]1654面对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他选择了慎言以避祸。他从天授、证圣年间四次上疏武后之后便沉默了。后来武后虽然多次下诏命九品以上官员,极言时政得失,但再也没有他上疏批评时政的记载。他虽曾有过几篇奏议,如《衣冠乘马议》《孝经老子注易传议》《重论孝经老子注议》等,但都是有关朝廷礼仪和学术方面的议论,根本不敢触及敏感的时政问题。
二、慎交友。他认为:“夫化赤渐于邻丹,为黔资于迩墨。生于麻者既革其操,染于蓝者亦变其色。”[8]1654因此他主张不可乱交友,更不可攀附权贵。他认为交友倘若不慎,往往会招致祸患。历史和现实中那种“始刎颈以交约,终反噬而相屠”是不乏其例的。而那些攀附权贵者“自谓方江湖而共永,比嵩岱而齐坚”,其结果是“一朝失据,万古凄然”[8]1654。有的甚至落得个灭身夷族的下场。终其一生,他结交的朋友多是志同道合、趣味相投者。他称:“惟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1]289其中提到的徐坚,是一个“遍览经史”“多识典故”[10]3175-3176、直言敢谏的博学史官。《史通》问世后,屡遭时人批评,唯有徐坚认为:“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6]4521朱敬则,为人倜傥重节义,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时人称之为“忠正义烈,天下所推”[6]4221。刘允济,工于文辞,早年与著名诗人王勃齐名,长期担任史官,主张秉笔直书,反对曲笔讳饰。薛谦光,贯通文史,曾任御史大夫,为人耿直,不避强御。元行冲,博学多才,为人“性不阿顺,多进规诫”[10]3177。吴兢,博通经史,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劝谏,倡导秉笔直书,是一位多产的史学家。裴怀古,曾任监察御史,能秉公执法,为人宽厚正直,有胆略。曾两次出使西南,平定蛮夷叛乱。以上7人,除裴怀古一人为武周时名将外,其余6人大都担任过史职,并有著述。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为人刚正耿直,政治眼光敏锐,敢于直言劝谏;在史学领域,提倡秉笔直书,反对曲笔讳饰。刘知几和他们之间确实做到了“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
三、知止足。刘知几认为,人生招祸,往往是由于人们日益膨胀的贪欲造成的,因此主张“欲不可纵,俭以足用”[11],“节其饮食,谨其容止”[8]1654。他认为,一个人无论在政治要求上还是在物质要求上都不可贪得无厌,而要“知满损而谦益”,因为“彼满盈之难守,伊荣茂之易落”[8]1653-1654。在政治上他主张要“怯进勇退”,自称:
每思才轻任重之戒,智小谋大之忧,观止足于居常,绝觊觎于不次。是以度身量衣,量腹而食,进受代耕之禄,退居负郭之田。庶几全父母之发肤,保先人之丘墓。一生之愿,于是足矣。[8]1653
他非常赞赏西汉张良功成身退的做法,“智哉张子房,处世独为工,功成薄受赏,高举追赤松,知止信无辱,身安道亦隆”[12]。在物质要求上,他主张君子要“严其墙仞,戒以心胸。知躭味之易入,俾回邪而不容”。做到“自然契己坦荡,清心肃雍”[13]1654-1655,勿玩物丧志。在行动上要做到“衣服有常,非敢玩于千袭;饮食不溽,宁专美于八珍?”[13]1654-1655刘知几这种“知止足”的主张显然受到老子所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4]33以及“知足不辱,知止不殆”[14]33等思想的影响。
然而真正做到“知止足”“清心肃雍”又谈何容易。在现实中,刘知几对自己久居卑位而不得升迁是牢骚满腹的。他自称:“孝和皇帝(指唐中宗)时,韦、武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朱紫,予以无所傅会,取摈当时。(原注:一为中允,四载不迁)”[1]589又称自己“以守兹介直,不附奸回,遂使官若土牛,弃同刍狗”[1]592-593。他在给萧至忠信中称朝廷对待自己是“求史才则千里降追,语宦途则十年不进”,“相期高于班、马,见待下于兵卒”[1]593。并称“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倘使士有澹雅若严君平,清廉如段干木,与仆易地而处,亦将弹铗告劳,积薪为恨。况仆未能免俗,能不蒂芥于心者乎!”[1]593-594可见,刘知几的处世思想与现实是矛盾的,一个人想的和做的真正统一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四、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在《史通·直书》篇中他指出:“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也?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1]192就是说,君子是崇尚为人正直的,但现实中许多人“趋邪而弃正”,这是因为面对严酷的现实,只有顺从才能自保。这种思想在刘知几的《咏史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泛泛水中萍,离离岸边草。
逐浪高复下,从风起还倒。
人生不若此,处世安可保?
蘧瑗仕卫国,屈伸随世道。
方朔隐汉朝,易农以为宝。
饮啄得其性,从容成寿考。
南国有狂生,形容独枯槁。
作赋刺椒兰,投江溺流潦。
达人无不可,委运推苍昊。
何为明自销,取讥于楚老。[15]
在刘知几看来,人生就如同水中浮萍、岸边弱草,如不随风逐浪,就很难自保其身。他非常赞赏蘧瑗“屈伸随世道”和东方朔弃官归农的做法,而不赞成屈原那种对世俗毫不妥协的态度和“伏清白以死直”[16]510的行为,故而诗的结尾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何屈原要那样毁灭自己,而让楚国的渔父讥笑呢?对于渔父讥刺屈原的那番话,刘知几似乎从中受到很大的启迪。据《史记》载,屈原被顷襄王放逐后,在泽畔遇一渔父。渔父问他何故至此?屈原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17]刘知几之所以对渔父这番话感兴趣,是因为他在官场上与屈原有着类似的遭遇。屈原曾自称“不周于今之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16]510。刘知几也称:“于时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间,忽忽不乐。”[1]589又称:“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1]290他因此感叹道:“彼独洁之为难,因群醉之所丑。”[8]1654但他不赞成屈原所采取的那种“宁溘死以流亡兮”,而不愿“背绳墨以追曲兮”[16]510的不妥协态度。他认为最好的解脱办法是像渔父所说的与世推移、随波逐流以明哲保身。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做到“爱发肤而不伤,保家室以不耻”[8]1654。这一点,他在《思慎赋并序》中说得十分明白:“庶几全父母之发肤,保先人之丘墓,一生之愿,于斯足矣。”[8]1653
总之,刘知几从为人耿直、勇于直言转变为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完全是因为封建专制统治者的高压政策造成了他性格的扭曲。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不敢也不愿抗争,采取了随波逐流、与世沉浮、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而在学术领域,由于他主要是评古而不是论今(当然对唐代设馆修史他是持批评态度的,对唐修诸史也多有指斥),因此他感觉不会立即招致祸患。尽管《史通》问世后,“见者亦互言其短”,但他“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1]292。因此在学术批评领域他不改耿直刚正的本性,勇敢地拿起批判的武器,矛头直指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神圣不可动摇的儒家经典,并实事求是地评说历代史籍的长短得失,被誉为“史家之申、韩”,表现了一个史学家实事求是、敢于直书的优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