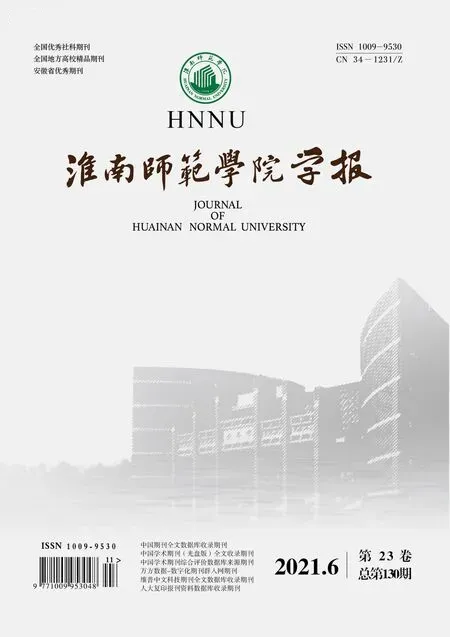晚清至民国商事活动中掮客行为研究
孙佳雨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国学辞典》对“掮客”一词的解释是经纪人,是指以独立第三者的立场,媒介他人间商业上的交易而收取佣金的中间商人。从这寥寥数语的解释当中,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中,“掮客”有着和“牙人”或者“经纪”相同或者相似的含义。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文化的变迁,掮客的含义发生了一定转变,经济上的意义已被淡化,出现了包括政治掮客、文化掮客等在内的其他含义。今人学者对于“掮客”的研究也多从政治及文化方面入手,反而忽视了其原本的内在含义。明清以来,在长途贩运及商品经济发展之下,“掮客”——这一有着和“牙人”及“经纪”相类似职业的群体,往往就是商品交易这一闭环之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拟从此方面入手,探究掮客从晚清至民国时期在商事活动中的种种经营行为,并分析其在不正当经营行为之后所遭受到的包括经济、人身及道德上的处罚。
一、从牙人到掮客:一脉相传中的变动
从经济史方向来研究掮客的文章近年来少有,且往往是从“驵侩”“牙人”及“牙行”等角度进行分析与探讨,虽然冠以“掮客”之名,实际上其研究重点仍着眼于宋、明、清时期的牙人群体身上。早在1990年,龙登高先生在《论宋代的掮客》中论及“掮客在先秦两汉谓之驵侩,唐五代史称牙人”“掮客阶层的主体则是茶肆、邸店、居停等主人”,并且指出“主持市场交易是宋代掮客的重要任务”[1]。同时,以掮客之名分析宋代牙人的种类,指出牙人的发展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认为正是因为牙人经济的发展才维护了市场的有序化,使其得以加强[1]。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梁章钜《称谓录》中的“牙人”目中,“掮客”这一词条并未收录进去。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梁章钜生活的时代,即清道光年以前,“掮客”一词尚不能指代“牙人”。
由于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原因,“掮客”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存在价值。部分学者梳理了掮客在经济领域里的种种形态,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掮客”这一称谓的意义是逐渐扩大的,从唐时形成的“专替人介绍生意撮合买卖以赚取佣金”的牙人[2],到近代中国受雇于外商、“主要替洋商办事”的买办[2]。作者显然也是用现代意义上“掮客”一词的普遍含义,来涵盖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贸易居间人。
必须指出的是,掮客是一个有着地域性特殊含义的群体,晚清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3](P452):
说话间,有人来访金子安,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子安回说:“价钱不对,前路肯让点儿价再做商量。”那人道:“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子安道:“我也明知道,不过我们买来又不是自己用,依然是要卖出去的,是个生意经,自然想多赚几文钱。”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自去了。我问:“是什么白铜,有多少货?”自安道:“听说是云南藩台的少爷,从云南带来的。”我道:“方才来的是谁?”子安道:“是个掮客。(经手买卖者之称,沪语。作者吴趼人自注。)”我道:“用不着他,我明天当面去订了来。”
清代文学家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虽是一部长篇小说,但却带有自传性质,描述了主人公经商到失败的全过程。小说中带有当时的市井色彩,能够更加全面完整地展现出在当时不易被正史所详细记载的小商人阶层的日常经营活动,因此选取清人所做的小说内容对当时的历史事件进行佐证,其可信度较高。
吴趼人在小说中特别标注“掮客”为“经手买卖者之称,沪语”。本文对这一标注进行分析,其至少可以传达两处信息:其一是“掮客”在清代为上海地区的方言;其二,作为通俗读物的小说,作者的读者阶层所面向的是普通人民群众,而作者在小说当中特意将“掮客”一词标注出来并且作以解释,这足以证明,此称呼至少在晚清时期尚没有普遍使用于全国范围,仅在上海地区所行用。
陈伯熙编著的《上海轶事大观》中也同样指出,“掮客”的叫法,“独沪上有之”[4](P94)。据此,我们再看今人对“掮客”的研究,以“掮客”作为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概念,来指代中国历史上顺应商品经济的潮流而出现的驵侩、牙人、牙行等职业,这一观点显然是有待商榷的。既然并不能够完全指代中国历史上因为商品交换而产生的所有中间商群体,那么作为同样从事第三方交易的中介人,“掮客”又与明清时期的“牙人”“牙侩”有何区别呢?
明清时期,牙人的主要职能有以下几点:1.代客收货卖货。明朝政府规定,商人在市场上交易必须经过牙行。由于长时期从事某一种商品的居间贸易,牙人对市场行情较为熟悉,而一些从外地远道而来的客商对异地商情不太了解,为了能在第一时间以合理的价格收购质量上乘的货物,他们往往要与掌握着商情信息的牙人沟通。2.充当歇家提供服务。为了顺应长途贸易的发展,也为了能够更好地招徕客商和引入货源,牙行逐渐兼具了歇家的功能,为一些远道而来的外地客商提供良好的服务,包括提供住宿、茶饮、饭食等,甚至帮客商卸货上货,代其雇佣车船人丁。当然,其所做这一切的根本目的,仍是为了“日获进益甚多”。晚清的掮客也是将和客栈有相似餐饮功能的茶馆当作进行居间贸易的主要场所。包树芳在《茶馆中的商人与生意:近代上海茶会考察》一文中指出:“茶馆并非掮客的唯一活动场所,却是最重要的场所……各业茶会掮客人数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业的兴衰。”[5]但与明清牙人不同的是,掮客只是将茶馆茶会作为一个交易的场所,正如《上海轶事大观》中所记“凡操掮客之业者,盖以茶楼为营业之机关”[4](P94)。他们并未像明清时期的牙人一样,将行业与客栈的功能联系统一起来。3.稳定市场秩序。明人李晋德所作《客商一览醒迷》一书中对牙人的权责作了明确的记录:“所谓牙者,权贵贱、别精粗、衡重轻、革妄伪也。”[6](P276)从该文本中可以看出牙人在市场上的主要职责是权衡评定商品的价格,甄别货物的质量高低,监督并且革除市场上一些虚假且不正常的商业行为,实际上其承担了一部分官府的职责。然而相对于牙人的这些职能,掮客却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与之相应的责任,非但不能维持市场的正常秩序,反而在经营过程中有时会存有诈骗行为。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所记载的一则故事[7](P400-401)很能说明问题:
“权贵人家”唐二乱子家大业大、财大气粗,想要买一个翡翠领管,他表兄何孝先便说:“你不是要买翡翠领管么,我替你找了好两天,如今好容易纔找到一个正真是满绿,你不信拿一大碗水来,把领管放进里头,连一大碗水都绿的碧绿的。”唐二乱子道:“要多少价钱?”何孝先晓得他是大老官脾气,早同那卖领管的掮客串通好的,叫他把价钱多报些,当时听见唐二乱子问价,便回称:“三千块。”谁知唐二乱子听了,鼻子里“嗤”的一笑道:“三千块买得出什么好东西?快快拿回去,看了亦不要。”那个卖领管的掮客听他说了这两句,气得头也不回,提了东西一掀帘子竟去了。
何孝先摸清楚了唐二乱子的脾气,知道他非“贵”不买,于是事先就已经和那卖领管的掮客串通一气,抬高了价钱。虽说因为唐二乱子仍是嫌低对价格不满意,导致最后的交易并未成功,但实际上这种行为已构成诈骗犯罪。在这场并未成功的交易中,何孝先和掮客为了让唐二乱子购买产品,故意变动产品价格,存在诱导消费的嫌疑,完全违背了牙人“权贵贱”“革妄伪”的职责。而在这场交易中,卖领管的掮客听得唐二乱子对产品不满意,非但没有发挥自己身为贸易居间人的作用和能力,重新为买家寻找称心如意的产品,反而“一掀帘子去了”,可见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赚取贸易居间所得的佣金,而是为了赚取销售产品之后的利润。小说当中没有明确说明这个掮客到底有无领贴经营,亦没有指出领管到底是掮客自有经营还是代他人售卖,但该掮客应当是身兼贸易居间和卖货于一身无疑。再者抛开身份不谈,唐二乱子是要购买领管的“买家”,那掮客是贩卖领管的“卖家”,何孝先作为在其中联系“买家”和“卖家”的“中间商”,他显然在这场交易当中的身份反倒更像个“掮客”,可见在晚清时期,掮客和买卖双方的身份界限早已模糊。
二、艰苦求利:掮客的日常商事活动
为了确保交易的正常有序进行,明朝政府对牙人有着极高的要求,家道殷实、有抵业人户方可充任。然而到了晚清时期,上海地区的掮客似乎并无此项规定,一些没有家业的寻常百姓为了谋生亦充当起掮客,从事居间贸易活动。
通过对比柑橘与根系土各元素含量,可得出各元素富集系数,柑橘硒与锌元素富集系数分别为0.036与0.01,四种重金属富集系数分别为汞0.052、镉0.006、砷0.001以及铅0.002。
在明清两代,由于时代水平的限制,人们在提起牙人、掮客等居间贸易者的时候,总是带有几分鄙夷的色彩,认为他们不用付出辛苦的劳动,两张嘴皮子上下一碰,就能够玩转卖家与买家于股掌之间,从而得到不菲的酬劳。上海地区的方言里甚至将“掮客”称之为“吃白相饭的”,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中将之解释为“不务正业,游荡为生”[8](P20)。可见在晚清至民国时期人们对于掮客的看法向来带有贬义色彩。
陈伯熙在其编著的《上海轶事大观》一书中概括掮客从事商事活动的特点为:在上海“业此者甚众,盖对于买主卖主之间居间人也。凡欲一宗贸易,由掮客介绍而成者,例得酬金,俗谓之佣钱。收入之多寡,以操业之种类及贸易之额数而定。”[4](P94)掮客在经营行为中,其作为买主和卖主之间的中介人,发挥其对市场商情了解的作用,为卖家售出一个良好价格,为买家寻求称心如意的货物,若交易达成,则掮客可在两方之间获得酬金。有人说掮客“是一种不需本钱,是既杀卖主,又宰买主,专靠玩‘空手道’牟利的角色”[9]。
但实际上,头脑灵活、心思狡黠的掮客往往是极少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从事居间贸易这样商业行为的往往并不能给一些个体掮客带来相对稳定且丰厚的收益。掮客要促成一桩买卖往往并不轻松,甚至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以连接买家和卖家,在其中反复沟通和交流,要达成让主客双方都能够满意的价格,最后生意才能做成。如上文介绍的唐二乱子购买领管一例,便正因其对价格不满意,才导致交易未达成。往往买主提出相关要求,掮客若不能为其寻找到称心如意的产品,交易时间则相对会被拉长,若是到后期买主在别处遇到心仪的货物则很可能会单方面毁约,而掮客之前的一番辛苦全都白费,其所付出的成本自然比较大。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的主人公要替同学兼挚友吴继之买一个如意,但是“那如意他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又不指定一个名色,怎么办法呢?明日待我去找两个珠宝掮客来问问罢。”[3](P131)因为吴继之挑剔且又没有指明要求,所以主人公“我”便决定找专门从事珠宝居间的掮客来买如意。之后“早有伙计们代招呼了一个珠宝掮客来,叫做辛若江。说起要买如意,要别致的,所有翡翠、白玉、水晶、珊瑚、玛瑙一概不要。若江道:‘打算出多少钱呢?’我道:‘见了东西再讲罢。’说着他辞去了”[3](P131)。文中“我”要买的如意既对材质很挑剔,又没有说明究竟想要什么样子,甚至连价格区间都没有给出,实在是等于给这珠宝掮客出了一个难题,让其在寻找货物的时候范围过于广阔。过了一两日“再坐一会儿已是十点钟时候,遂惠了茶账,早有那辛若江在那里等着,拿了一支如意来看,原是水晶的,里面藏着一个虫儿,可巧做在如意头上,我看了不对,便还他去了。”[3](P131)又一日午后,“下午的时候,那辛若江又带了两个人来,手里都捧着如意匣子,却又都是些不堪的东西,鬼混了半天才去”[3](P133)。因为没有向掮客说明具体要求和条件,导致其在市场上漫无目的地寻找,而寻到的产品都无法让买家满意。这一场买如意的交易来回反复三次,但最终不了了之,“我”最后并没有在珠宝掮客辛若江手中买到如意,而是买了友人从贵州带回来的。交易没有完成,辛若江自然无法拿到所得之酬金,掮客的一番辛苦算是白忙活一趟,尽数付之东流。
晚清至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掮客种类繁多,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市场和商情,掮客往往都只从事单个商品的经营活动。当时在市场上进行活动的包括古董掮客、书画掮客、珠宝掮客、棉布掮客、药品掮客、诉讼掮客等,《上海地产大全》当中形容辛苦钻营的小掮客“人数最多,处境亦最困”。人数庞大的掮客为了能尽早把握住商机,往往四处奔波寻求生意,若是买卖双方达成一致,生意做成,则此前付出的努力有所回报,然而商事活动变故颇多,其中辛苦自然不言而喻。正如1947年《生活文摘》所记录的时人对于掮客工作所发出的感叹:“这是个相当艰苦的职业,看似容易,做起来也辛苦不堪,赚取佣金委实不易。”[5]
三、严惩欺诈者:掮客不正当经营行为的后果
掮客从事居间贸易,仍属于商人阶层,具有商人追求利润的本性。《上海地产大全》中指出掮客“其有深具经验手腕高尚之流,尚能于艰苦奋进之中,独占一席。若夫初出茅庐,阅世未深之辈,除每日在茶楼品茗之外,绝难成就。抑且地产交易,动以万计,耳濡目染,渐长奢风,举止动作,相习成俗。谋职业,则机缘难遇。觅工作,则一无所长终至进退失据,悔恨无从。天下至愚之事,熟有过于此者。凡素乏经验而与滥竽其间者,可不猛省乎?”[10](P378)掮客资本有大小之分,势力亦有高下之别。有头脑灵活的掮客肯下苦功夫,能够在该行业中独占一席,但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初出茅庐且阅世未深之辈,非但难以达到此等成就,反而受到日渐兴起的奢侈之风影响,耳濡目染,相习成俗。由于上海地区从事居间贸易的人数众多,一些势力较小且没有资本傍身的掮客压力就加大。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便开始不务正业,投机取巧,钻营度日,甚至以欺诈为生。
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计》中就记载了一个叫做陶子尧的官员被上海一帮“露天掮客”骗得十分凄惨,最后白白丢了几万两银子的故事,且看一下他被骗丢银的经过:山东候选通判陶子尧受到抚台赏识,被派上海采办机器。陶子尧对机器一概不通,又不懂和外国人签订合同购买机器的业务,机缘之下,认识了一个叫做魏翩仞的上海掮客。其在和魏翩仞交往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叫做新嫂嫂的妓女,新嫂嫂人聪明会说话,很能讨得陶子尧喜欢,两个人情投意合,如胶似漆,便整日厮混在一起,一连多日买珠宝、打首饰、添置新衣服等。新嫂嫂生日之时,还叫了一个戏班子,宴请众人。他采买机器的钱只有两万资本,眼下钱花似流水,陶子尧算了一笔,心想往后注帐多时报销一笔就行,也不在意。
魏翩仞看见他的钱花得淌水一般,不加爱惜,心上便想:“他的钱。也就用的不少了,若不从此时下手,更待何时?”然后找同是掮客、惯常联手的仇五科商量,仇五科便说:“你去同他说,后天开公司船,他要办机器,同他到我这里来。大家都是自己人,同他便宜就是了。”魏翩仞将这话同陶子尧一讲,陶果然上钩,同洋东签了合同,付了一半的银子。从这里开始,陶子尧就开始一步一步落入了魏翩仞和仇五科的圈套。之后又和新嫂嫂厮混,拨下来的二万两银子所剩无几,于是便打电报向抚台再讨,等了一个半月却一直没有消息。不想又过了些日子,陶子尧从其姐夫那里得到消息,说机器已经另托外国人办好,价钱便宜,而且包用,叫他不要办了。陶好象被当头浇上一瓢冷水,同魏商量,说机器不要了,叫他退钱。魏自然不肯,道:“同外国人打的合同,怎么翻毁得来?”到了这一步,陶子尧开始泥足深陷,被这两个掮客糊弄着定办了机器,又不能退,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陶和自家姐夫商量洋人不肯退机器的事情,姐夫回电报,上面写的是:“上峰不允购办机器,婉商务退款二万,悉数交王观察收。”二万银子陶已经花了个七七八八,自然是掏不出来,又同魏商量。魏出了一个损招,买机器二万二的银子,让他同王观察说花了四万,之前的二万不够,又托朋友在庄上借了二万。又让他请外国律师,魏狮子大张口,要五百银子帮他请律师,陶不肯,只给了魏二百,魏却拿着二百银子,只划了五十两出来请了个讼师。陶子尧既撒了另借二万两银子的谎,自然是要想办法圆谎,王观察问他要收条,魏翩仞便又给他出主意,让其在仇五科跟前另外订了一张定办四万两银子机器的假合同。仇五科也叫陶子尧另外写了一张借银二万,即以定办机器合同做抵的字据。这两份合同,握在了魏翩仞和仇五科这两个居心不良的掮客手里,就等是陶的把柄让他们两人给攥住了。陶只定了一万出头银子的货,却向上面报了四万,再加上他自己亏空的近万把银子,剩下的钱魏翩仞果然就不想分给他了,而且不怕他闹:“怕他怎的!他一共有两分合同在咱手里:一份是前头打的,是二万二千银子;一份是第二次打的,上头却写的明明白白是四万,原是预备同山东抚台打官司的。虽说是假的,等到出起场来,不怕他不认。他能够放明白些,不同我们争论,算他的运气;若有半个不字,我拿了这两分合同,一定还要他找二万二出来。”仇五科道:“有两分合同,要两分钱,就得有两分机器。”魏翩仞道:“原要有两分机器才好。他多办一分,我们多得一分佣钱。”这边魏、仇两个掮客已经将陶子尧算计的明明白白,那边他还在想“下余的一万八,是魏翩仞、仇五科两个人出力弄来的,少不得要谢他俩一二千银子,我总有一万好赚。 ”此事后来又断断续续纠缠了许久,陶子尧不想平白被讹,又花钱找了许多人帮忙,后来每个人送了两千,又给新嫂嫂两千,还被魏翩仞拿走了一千五,陶损失银两好几万。这桩案子到此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该故事虽为小说中所记载,可能含有夸张的修辞手法,但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当时这种掮客进行欺诈勒索的事情已较为普遍,因此作者才会将其当作一种常态展现于故事当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杨兰泉等讹诈俞锦泉未成讯明请示案”当中就记载了一起苏州商人梁幼亭为掮客所欺诈,从而导致名利两失的案例。光绪二十七年(1901),掮客王有福介绍德清县官豪奴之子俞锦泉等三人,假托贸易之名与梁幼亭约在茶房见面。七月初,俞锦泉等三人在码头开设赌局,王有福借故邀请梁幼亭去游船,邀其同赌。梁幼亭推辞不肯,千克王有福遂向其借去四百七十元,俞锦泉三人更是蛮横得将其身上票洋一千七百元拿去。经此一遭,梁幼亭惨遭赌骗,名利两失,事后再找王有福评理,王却避而不见。
掮客的工作比较辛苦,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唯利是图的投机活动,部分掮客钻了市场的空子,又有些掮客巧舌如簧欺诈别人,也无怪时人评价他们“既杀卖主,又宰买主”了。
《官场现形记》中魏翩仞和仇五科虽然存在欺诈行为,但在小说当中并没有点明其因为欺诈行为暴露之后所承受的后果。实际上,掮客在从事这种居间贸易的活动当中,欺诈行为一旦暴露,就会受到官府、行业经济和道德上的处罚。
1893年5月18日《申报》当中就记载了一条书画掮客因诳骗他人而被控告,最后受到官府责罚的案例[11],摘录于下:
苏人周锦山诳骗许锡甫等玉器物件由捕房包探张九意拘获……周锦山即周经山,向为书画掮客,现被许锡甫等控告诳骗,已将典押各赃吊案请训。许锡甫、严申甫、居锦春、谢阿三、张永清、陈云全等同称周经山诡言有主顾,骗去仇十洲手卷及香炉古玩等物先后典押现已吊齐原赃,请求给领。周供系苏州人,向籍骨董糊口,此次掮销各货,不敢诳骗,只因生涯拮据,暂付质库以应急需耳。质铺伙呈票请追质本,蔡太守判周管押一年,期满笞一百板,谕各施主给偿质铺半本,始准领赃。
掮客周锦山谎称有主顾,却把卖家的香炉古玩等送到质铺典当,既坑卖家,又坑买家。这种行为在当时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掮客欺诈行为,一旦被人告到官府,构成商业诉讼,就会受到限制人身自由及肉体惩处等责罚。周锦山后被几个卖家一起告到官府,被判处“管押一年,期满笞一百板”,而各位失主还要“给偿质铺半本”,才准将货物领回,这实际上造成了卖家和质铺双方共同的经济损失,可见掮客的欺诈行为一旦构成,就会牵连甚广。
除却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以外,掮客私充作假的行为同样会被行会所排斥。晚清至民国时期苏松地区为了防治顶冒他店牌号而立下的牌禁,就很能说明这一点。1916年上海土布业公所公议不许顶冒他人字号,“新号勿许同名”,沿用历次牌禁所修整的“丙辰牌律”[12](P367-368)当中就对掮客经受冒牌有所规定:
冒牌罚则:
甲 同业如有顶冒他号已经注册之同路同货牌号,经本所查明,或被本牌呈报,查有实据者,将冒牌之货尽数充公。如有掮客经手并须追查姓名,由公所通告各号,以后永不准该掮客再掮布。如号家徇情私相授受,亦须处罚。
掮客欺诈行为被写进牌律当中,证明这一情况其时已普遍发生。由此可见,在明清至民国时期,掮客的欺诈行为除了在经济上欺骗卖家买家,还会从事经营冒牌商品活动,而一旦被发现,就会由公所通知各号,永远不许其再掮布。结果其不但会在整个行业中受到相应惩罚,且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除此以外,自清光绪中期以后,上海棉花业因为有掮客的加入屡屡发生冒牌交易,而为了整顿花业行规,“须知该商刑永顺等公同选用掮客”“诚谨晓事者”十八人,“凡未经选用之人,不得挟嫌嫉妒,勾串作弊。倘敢玩违,许该商等指名禀究,决不宽贷”[13](P838-839),即对行业在选用从事者的时候,重视对其德行的选用。而一但掮客德行有失,做出对于行业不利的行为时,则一定要追求其责任,行业之中对有不端行为的掮客也不再使用。
四、结 语
“掮客”作为晚清至民国上海地区商品交换当中的重要环节,承担着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连接买家与卖家的作用,对从事商品经济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学者在梳理掮客于不同时代的称谓及含义时,认为其在秦汉时被称为“驵侩”,唐宋以后被称为“牙人”“牙商”“牙侩”等,但实际上掮客这一职业虽与上述行业有着相似的地方,但亦有其本身的独特之处。正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作者吴趼人所著内容,掮客为“经手买卖者之称,沪语”。作为从事第三方居间贸易的中介人,“掮客”这一词语有着其地域性的特殊含义。根据梁章钜《称谓录》当中所记载的内容推断,“掮客”一词至少在清道光之前,并未同“牙人”有所联系,而这一称呼在晚清时期尚只大规模行用于上海地区,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现代学者往往用“掮客”来指代中国古代历史上包括驵侩、牙人等在内的所有居间商人,这一观点应当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同牙行歇家相比,掮客亦将和客栈有着相似功能的茶馆当作活动的主要场所,但只是“以茶楼为营业之机关”,并未将其经营和茶馆发展成包括住宿、饭饮、买货卖货于一身的场所。而且掮客亦并没有履行牙人“权贵贱、别粗精、衡重轻、革妄伪”等一些承担了官府维护市场正常健康运行的责任,这是因为在晚清时期的上海地区,一些掮客早已经和买卖双方的身份界限变得模糊,他们不以赚取贸易居间所得的佣金为目的,反而是为了赚取销售产品之后的利润。
正因为掮客的身份仍属于商人阶层,其仍然附有商人追求利润的本性。再加上掮客“是个相当艰苦的职业,赚取佣金委实不易”,这便导致其一部分人开始钻营取巧,以欺诈为生。然而掮客的欺诈行为一旦构成,就会“既宰卖主,又杀买主”,造成买卖双方的损失,亦会使行业动荡,牵连甚广。因此,晚清至民国时期为了抑制这种情况的发生,官府和行业都会对其欺诈行为进行处罚,而掮客亦会受到包括官府、行业甚或是经济和道德上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