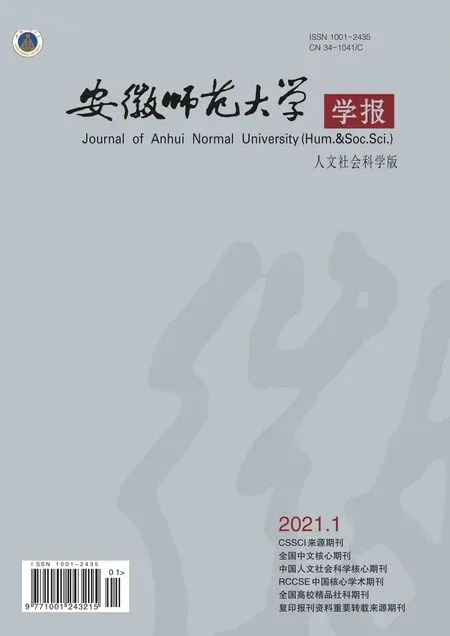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缘起、运行、调整与改革*
刘 涛
(浙江大学1.公共管理学院;2.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杭州310058)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几个主要运用社会保险制度来应对及协调长期护理风险的国家之一。[1]德国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进程中所积累的丰富理论知识、制度架构及技术经验,对于当前正在筹备第二轮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我国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本文将全面介绍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体制架构设计及运作模式,充分探索德国是如何在其社会经济及制度文化环境中实现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机制上与组织架构上的整合,同时介绍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如何运用社会资源来为该项制度融资的。此外,本文还将进一步展现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财务状况及可持续性等。本文的重点将聚焦于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近几年所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不仅介绍德国长期护理保险技术层面的重要创新与政策改变,同时也会深刻剖析制度革故鼎新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价值理念嬗变。由于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近年通过系列改革后产生了较大程度的转型,而我国学术界和实业界对此系列新改革还鲜有涉猎,本文通过对于这些新型改革的介绍与深度分析,试图为正在进行政策试点与实验的我国提供重要的技术资源层面和思想资源层面的支持。
一、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源起
1994 年,德国联邦议会经历了漫长的讨论与辩诘,最终通过了长期护理保险的议案。关于德国是否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的争论与疑惑最终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德国确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样,继历史上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制度后,德国又再次首创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保险制度。[2]
关于德国为什么在1990 年代建立了这项新型制度,当时德国为什么选择的是社会保险制度而不是其他制度选项,有关此方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依然鲜见,学术界还不足以凝结成强大的共识以解释为何德国在那个时间节点选择了这样的制度选项。本文通过大量校阅、整理早期的德文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初创时期的文献,倾向于运用美国著名社会政策及福利国家研究学者保罗·皮尔逊所提出的“福利国家路径依赖”的观点来解释德国创立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3]“路径依赖”学派的观点认为,一国基于其本身历史文化传承而来的“制度基因”及过去所采取实施的制度具有沿着相同发展路径“惯性前行”的趋势。皮尔逊因此深刻地提出了福利国家社会保障项目具有“制度粘性”(institutional stickiness)的观点。德国由于历史上属于俾斯麦式的社会保险制度首创国,其社会保障制度的“主干”始终为社会保险制度,因此德国在国际上拥有了“社会保险国”及“俾斯麦模式”的美誉。[4]因此德国在面临长期护理新型风险时刻同样因袭了历史传统,而倾向于运用社会保险制度来解决长期护理保险之谜题。
一般观点认为德国经济强大,因此具备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坚固的经济和财务基础。这样的观点其实并不全面。图1 显示,在两德统一后的整个1990年代,德国的经济处于“滞胀”时期,不仅经济成长大幅下滑,而失业率也居高不下,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1994及1995年其失业率一度超过了10%。在制度创立之前,德国事实上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基于两德统一而来的巨额财政负担,而德国并没有因为经济放缓而放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之步伐。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今天正在努力创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我国是非常重要的。

图1 德国1990年代失业总人数及失业率状况
二、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基本概况
从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一名称,我们就可以看出其是一项社会保险制度。[5]之所以称其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而不是长期护理救助制度或是长期护理普遍服务制度,乃是因为该项制度完全采取了社会保险其他几项制度的基本运行方式、方法。言及长期护理的社会保险制度,其基本特征还是基于筹资模式。德国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来自于雇主与雇员共同承担的长期护理保险保费,而不是依赖于国家的财政税收。如同其他社会保险项目,长期护理保险费用以企业为单位来征收,每位有强制义务参加社会保险的德国雇员之税前工资都将被自动扣除一笔长期护理保险费用,而长期护理待遇则由企业单位之上的社会自治的公法团体来管理、给付。这些构成了一项德式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特征。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经办与运营借助了原有的制度机构体系。德国在其医疗保险制度的经办机构——疾病基金(Krankenkasse)之内建立了一个单独的护理基金(Pflegekasse),而所有具有法定义务参加德国长期护理保险的雇员与居民也同样具有强制义务同时参加德国长期护理保险。这样,借助医疗保险制度的数据优势与现成组织架构优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制度“界域”。然而德国医疗保险与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机构关系的独特性在于“借力不借道”。虽然在疾病基金内部内植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的经办机构——也就是护理基金,但是两个基金之间的账户通道及管理通道是相互隔绝的,一个基金无法向另外一个基金借用盈余的金额使用,两个基金之间完全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管理,因此两个经办机构之间的账户资本挪用的状况是完全不存在的。这充分保障了长期护理保险这一新生制度的独立性。
从覆盖群体角度来看,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与德国早期传统的理想型态下的雇员社会保险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区别。其制度类型更加类似二战结束以后所凝结而成的新社会保险制度,笔者称其为带有一种“准全民性质”的社会保险制度。其制度特征为:不再仅仅是雇员为唯一参保群体,越来越多的居民也通过不同制度安排而纳入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来。

表1 德国法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覆盖机制
表1显示,如同德国其他社会保险制度特别是医疗保险制度一样,德国建立了一张综合宽阔的长期护理保险网络,覆盖了大多数德国居民,而使得该项制度早就超越了传统的雇员社会保险制度。除了雇员按照工资的比例每月由雇主、雇员缴纳3.05%的长期护理保险费用之外,①没有子女的德国雇员还需额外缴纳0.25%的长护险保费,这样总计缴纳保费达到收入的3.30%,这是因为长护险与老龄化及人口抚养率密切相连,对于人口走势尤其敏感。德国对家庭在社会保险领域特别是长护险领域有相当明确的优惠政策。例如家庭中无收入或是无固定收入一方,可以随着家庭主要收入者免费参加长护保险,而儿童也随父母免费参保。大学生甚至外国留学生都有强制义务参加法定长期护理险,需缴纳一个固定金额的长期护理保费。当前大学生每月需缴纳的长护保险费为24.82欧元,有养育孩童的大学生则每月缴纳22.94欧元。而针对低收入者,如同医疗保险制度一样,在450—850欧元的收入档之内,征收的长护险保费随着收入降低而降低,而雇主缴纳的部分则不断上升;收入低于450欧元之下的,雇员则完全豁免缴纳长护险费用份额,而由雇主单独承担缴费。针对领取失业救助及社会救助的群体,长护保险费用由失业保险机构及社会福利机构来承担,而退休人员作为长期护理保险的主要受益者须单独缴纳长护保险费用。而人数不多的德国农民也有法定义务参加特殊的由保费筹资的农业长期护理保险。即使联邦德国国防军也必须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军人也需缴纳雇员部分之保费。德国少数可以灵活选择参加(或不参加)德国长护险的群体为自由职业者,例如艺术家、夜校老师等。另外收入在一定界限之上的高收入群体也可以豁免强制参加法定护理保险的义务。然而即使对于这部分人群,如果其没有选择参加法定长期护理保险,也必须参加私人长期护理保险,两种保险制度必须参加其中之一。
通过以上常规制度的安排以及通过社会不同群体的安排,德国实现了长护险领域较高的覆盖率。截至2018年,德国7 275万居民参保法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另有928万德国居民参保私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参加法定长期护理保险的居民占德国总人口的87.8%,而参加法定长期护理保险及私人护理保险的德国居民占总人口的99.1%。这样,整体而言,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了超高的覆盖比率,远远超过传统俾斯麦雇员社会保险的范围,呈现出全民保险的特征。
根据德国健康部提供的统计,到2018年底,总计368.5万德国居民在法定长期护理保险的范围之内获得了长护险待遇。德国的长护险内护理方式主要分为居家护理与入院式护理两大类别,其中居家护理又包含了家属护理及护理服务公司、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的流动上门护理服务,入院式护理包括在养老院与护理院等机构之内接受的护理。截至到2018年年底,290.5万获得护理待遇的德国居民选择了广义上的居家护理,而78万居民选择了入院护理,也就是我国语境中的机构式护理。选择居家护理的人数为入院(机构式)护理人数的3.7倍。
图2 显示了自1995—2018 年德国长期护理人数的变动。1995 年德国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的受护人数为106.1 万,而2018 年则达368.5 万,上升幅度为247%。选择居家护理的人数则从1995年年的106.1 万上升到2018 年的290.5 万,上升幅度为174%。选择入院机构式护理的人数则从1996年的38.4 万上升到2018 年的78 万,上升幅度为103%。无论是从上升幅度来看,还是从居家及机构护理占总受护人数的比率来看,在长护险建立23 年的时间内,选择机构护理的比重并没有显著上升,反而在这一时间段内有所下降。(入院式)机构护理从1996 年的24.9% 下降到2018 年的21.2%,而居家护理则在同一时间段从1996 年的75.1%上升到2018年的78.8%(图3)。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长护险制度1995 年建立以来,选择居家护理的人数至2007 年一直呈现平缓下降趋势,而2008 年以后则呈现平缓上升趋势,而2016年后实施长护分级重大改革以来,近两年居家护理上升趋势更加显著。而同一时间段,选择(入院式)机构护理的人数自长护险建立以来至2007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而2007 年之后则呈现平缓下滑之势,尤其是在新近的改革之后其下降趋势较为显著。
德国的法定长期护理保险根据护理需求和身体失能程度对接受护理居民进行分级,由疾病基金的医疗服务中心(MDK,Medizinischer Dienst der Krankenversicherung 的缩写)对身体是否失能及身体失能程度提供医疗及护理领域的专业鉴定。德国自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来,一直将护理等级划分为三级,但通过2017—2018 年的主要改革其分级制度改为五级。图4 显示了2017—2018年长期护理保险主要改革以后,五个护理级别的人数分布。其中护理二级人数最高,2017 年、2018年分别有127.3万、138.42万居民被划定为护理二级,而2017 年、2018 年共计69.9 万、77.3 万居民被划归至护理三级,为五个等级中人数第二高的受护群体;而护理最高等级——也就是身体失能最严重等级的第五级人数也最少,2017 年与2018 年护理第五级的人数基本持平,保持在10.9万人左右。按百分比计算,2018 年护理二级占受护总人数的47.6%,护理三级占26.6%,护理一级、四级、五级分别占受护总人数的11.8%、10.1%、3.8%(图5)。

图2 1995—2018年德国接受长期护理绝对人数变动(按居家护理、入院护理及总人数)

图3 德国1996年至2018年居家护理及入院护理占总受护理人数比重变动

图4 德国2017年、2018年法定长期护理保险五个护理等级的人数分布

图5 德国2017、2018年法定长期护理保险五个护理等级的百分比
三、德国长期护理保险的整合机制与财务状况
我国在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及实施过程中常常面临着制度整合、经办机构整合、筹资机制整合等诸多难题。这使得我们更加关注德国在其长护保险制度建立以来的整合问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德国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特别是在建立长护险过程中所经历的发展路径与我国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别。首先,德国没有在制度建立过程中实施地方试点政策,没有了各地的试点,也就没有了地方的“百花齐放”及各种不同的地方制度的多样性安排。德国的特点在于其多党竞争及议会民主制度,因此在新制度建立过程中,需要凝聚跨党派共识以及弱化在野党的反对浪潮和抵制力量。所以在长护险建立之前十至二十年,议会的讨论、辩论、争执是常态。而制度一旦建立之后就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其整合程度自诞生之日就处于相对较高的状态。笔者称德国建立长护保险的过程是“乏试验”的一步到位的立法过程。这一点相较于我国不断试点实验的立法过程,的确提供了另外一种制度建立及政策立法过程的思路。其次,德国长护险的建立之初,其组织架构及经办机构就处于相对清晰的状态之中,并没有出现我国社会保障领域里常出现的“九龙治水”的局面。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提到的,长护保险制度虽然和医疗保险制度具有一定的“制度交界面”,德国长护保险制度也部分借助了医疗保险现存的制度及组织架构。例如德国在疾病基金内部内植了一个护理基金作为长期护理保险的经办机构,但护理基金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公法团体,具有完全独立于医疗保险之外的独立地位,实施自我管理、自负盈亏、独立运行。这样的制度安排防止了其他制度或是其他域外经办机构干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运行,促进了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德国第五大社会保险险种的制度独立性。在德国联邦政府层面,德国联邦劳动及社会事务部(BMAS,Bundesministerium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的缩写)负责全德涉及到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的所有政策领域,而在联邦劳动及社会事务部之下又设有联邦社会保障局(BAS)①联邦社会保障局的前身机构为联邦保险局(Bundesversicherungsamt)。自2020年始,联邦保险局更名为当前的社会保障局。,为联邦层面专门负责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保险的国家机构。由上述两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较高整合程度的制度。这也是在德国长护制度领域,制度及经办机构整合没有成为一个焦点议题的重要原因。这里,德国不同的制度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参考与深思。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一项典型的社会保险制度,实施的是由社会保险费用来筹资的方式,而国家财政不介入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给付。长护险费率发展状况在一定层面上可以直接折射出长期护理领域里不断上升的需求。在长护险制度建立的1995年,其费率为税前工资的1.0%,其后至2007年保持在税前收入的1.7%,2008年其调升为1.95%,2013年其又再次调升为2.05%,而2015年又调升至2.35%,仅仅两年后又在2017 年升至2.55%,而2019年至今则保持在3.05%(图6)。德国长期护理保险费率在近十年连续不断的调升反映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结构性改革以及长期护理需求不断上升的基本事实。
如果从长时段及全局性的角度来审视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各险种保费的发展,可以看到德国自两德统一以来一直试图控制社会保险总费率,德国一般的社会共识是将社会保险几大险种总计费率控制在税前收入的40%以下。自长护保险制度建立以来,新建立的长期护理保险在整体格局上并未使得社会保险的总计费率状况失控。由于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特别是失业保险领域,德国成功地控制了费率,因此,近年来德国社会保险的整体费率稳中有降,2019 年社会保险总费率维持在税前收入的38.85%。
图7 显示了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03—2018 年以来的财务发展状况。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从2003至2007年,德国长期护理保险每年的财务处于净负的状态,而2008年至2016年则处于较长时段的盈余状态。联系到图6德国长护保险费率的发展,笔者发现这一时段的收支盈余与德国在同一时段不断提升长护险费率直接相关。而在2016 年之后进行长护险分级制度改革之后,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年度财务又出现了净负的状况。2018年德国长期护理保险收入为377.2亿欧元,支出为412.7 亿欧元,当年净负为35.5 亿欧元,当年长护险的累计结余从2017年的69亿欧元大幅下降到2018年的34亿欧元。

图6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费率发展趋势(1995—2019年,占税前收入百分比)

图7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财务状况(2003—2018年,单位:亿欧元)
如果区分居家护理与入院式机构护理,前者的支出从2003年的82亿欧元上升至2018年的235亿欧元,上升幅度为187%;而后者的支出则从2003年的84亿欧元上升至2018年的148亿欧元,上升幅度为76.2%;而在同一时间段,长期护理的总支出费用从166亿欧元上升至383亿欧元,上升幅度为131%。
四、近年德国长期护理保险的主要改革措施
自2017年以来,德国长护保险制度实施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改革措施,而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与德国分级制度发生的重要变化紧密相连。[6]本文选择分级制度改革作为理解德国长护保险制度改革的一项枢纽核心措施。围绕着分级制度的改革,德国长护保险在理念上、技术上、范式上乃至涉及到长护保险的核心信念上(core belief)都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抓住分级改革这条总纲,有助于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理解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变化。
在2017 年改革之前,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为三个主要级别。根据上文所介绍的,医疗保险中医疗服务中心负责身体失能的鉴别与分级鉴定,等级越高,就标志着身体失能程度越高,相应的护理需求也就越高。自2008 年开始,德国将失智人员①也就是我国在医疗及护理领域的日常口语中常常指涉的“老年痴呆症”。定义为一个单独的护理级别,为这个群体建立了一个单独的护理0级。事实上,德国护理级别的重要改革之前已经呈现出护理级别“三加一”的局面。将失智人员单独定义为一个护理级别,这是德国长护历史上的一次重要转变。
2017 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在核心思想理念上更加重视接受护理人员的自主生活能力以及甄别出那些影响受护人独立生活能力的因素,同时德国的新改革更加注重细致精确地校准具有长期护理需求的人群,让更多事实上具有长期护理需求的群体可以更加容易获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新改革大幅降低了领取长期护理保险的难度和障碍度。这其中比较核心的改革是显著突出精神和心理层面在长期护理中的因素,在更大范围内将认知和心理障碍等因素纳入到长期护理保险之中来。因此长护险从三级到五级的改革并非单纯涉及到技术标准的精确化重置,更涉及到核心理念领域的一些认识论转变以及理论基础的创新。在这一过程中,认知障碍、失智人员包括具有一些心理问题、精神气质性疾病人员是这一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受益者。
与过去“三加一”时代的分级制度不同,德国的长期护理及医疗护理实业界通过大量实践知识的积累认识到了将认知领域之失智作为一个单独的、最轻微的级别与其他三个级别相区分开来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认知障碍可能贯穿从身体失能较轻至较重的每个级别,乃至存在于护理需求的每个等级内,因此新改革将认知障碍症融入了长期护理的五个新分级中去。换句话说,认知障碍、失智及精神心理问题等与老龄化、护理需求等完全可能交织在一起,而不是截然分开的不同问题或是不同护理阶段。而且随着高龄化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具有护理需求的高龄、超高龄人员可能也同时具有认知障碍、心理问题及身体失能。在新分级改革中,德国采取的做法是原有级别自动向上浮动一级,而原有级别中有因认知障碍症制约了日常生活及行动能力的人群则向上浮动两级,例如原有的1、2、3 级分别调高至2、3、4 级,原有的1 级加认知障碍症则提升到3 级,2 级加认知障碍症则提升到4 级,3 级加认知障碍症则调高到5级,而原先未被纳入长期护理等级的较轻微失能群体在新分级中则被纳入长护一级(表2)。由这项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在新长期护理等级中认知障碍及心理因素的权重大大增加了,同时新改革使得更多轻微身体失能群体可以较为容易地申请到长护待遇。

表2 德国新旧长期护理等级改革的转变方法

图8 德国新分级制度鉴定标准及其权重分布
在实施分级改革之前,德国对于长期护理保险三个等级的划分借助于四方面的鉴定标准,包括(1)与身体相接触的护理,(2)膳食餐饮,(3)活动能力,(4)家政家务自理。与身体相接触的护理包含了洗漱梳头、淋浴洗浴、擦洗身体、卫浴如厕、置换尿布及排尿袋等。膳食餐饮包括自我准备三餐的生活能力以及自主进餐、用餐的能力等。活动能力则包括了能否独立起床、就寝、穿衣解衣以及能否独立户外活动、散步、上下楼梯及搬迁等。家务家政则包含了购物、买菜、做菜、打扫房间以及日常家庭卫生包括洗衣等。根据上面这四大项目的各类小项目,鉴定机构会根据生活自主能力及不能自主能力做出相应的评分,根据每项分数的累积最终确定失能等级。而护理等级改革之后,对于新(五个)等级评估的鉴定标准也进行了重要的改革。笔者称这样的改革为增量调整。“增量”改革是指过去的鉴定标准依然保留,然后在过去标准的基础之上叠层添加新鉴定标准,并对新增标准进行类别和结构调整。改革后新的鉴定标准如下:过去的标准3“活动能力”保持不变,转化为现在的标准1,活动能力特别是空间的移动能力占新鉴定标准权重的10%;而过去的其他三项标准包含与身体相接触的护理、膳食餐饮、家政家务自理现在则转化为鉴定标准4“自我调养能力”,这三项合并而成的标准4占新鉴定标准权重之40%。在其余新增加的鉴定标准之中,主要涉及到认知、心理及精神气质等方面的因素,新增标准所占权重达到50%(图8)。
新增的鉴定标准包含标准2“认知和交往能力”(权重为7.5%)、标准3“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权重为7.5%)、标准5“克服及应对医疗及疾病治疗之要求”(权重为20%)和标准6“日常生活塑造与交往”(权重为15%)。具体而言,标准2“认知和交往能力”包含了对生活周围的人、事、物的回忆及记忆能力,包括能否在认知层面清楚地辨识家人、熟人、邻居及专业照护人员,能否清楚地辨别周围的生活环境及居住环境,是否保持有基础的方向感,能否在时间向度上对日期(年月日及每周)等有正确的记忆,能否对生活中的过往事件保持有记忆,能否保持着长期记忆,能否驾驭生活中多步骤的行为活动(例如铺好餐桌用餐等),能否在生活中做出独立的行动及选择,能否在生活中具有接受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例如读书与看报),能否识别生活中的危险与风险,能否自主表达出生活中的需求(例如饥渴、冷热、疼痛)等,能否理解他人提出的针对本人需要的问题(例如是否理解关于是否要用餐和洗浴的提问),能否参与和他人的谈话与对话等。标准3“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包含了受护人的异常行为例如离家出走的倾向或是在无人注意及看管的情况下离开住所,夜间喧闹与在房屋来回不停走动,时常出现的躁动不安的状态,也包括自残及伤害自己的行为,以及(攻击性)损害物品的行为,针对他人的攻击性行为(包含了言语攻击及行动上的攻击),针对他人的谩骂及威胁,音量大幅提高包括尖叫等,除此之外还包括对于护理的防御、排斥和拒绝,反对护理人员对其进行身体护理与医疗护理,有带有精神气质的迫害想象以及恐惧感,或是在极度抑郁状态下而精神萎靡不振、无所作为,还包含其他一些不正常的偏离社会常规的行为。标准5“克服及应对医疗及疾病治疗之要求”(权重为20%)包含了用药协助,包括协助口服药物、使用眼药水及滴耳剂,协助使用栓剂和药物贴剂等,协助使用注射剂(例如胰岛素注射剂或药物泵),静脉通路及置管,协助使用呼吸充氧设备,涂抹医生规定使用的软膏及药剂等,测量血压、血糖及体重等,协助使用有助于身体活动的辅助工具例如假肢、眼睛和压力袜等),换药及伤口护理等,照口护理,协助导管插入及协助通便等,在家庭环境中的辅助治疗措施例如呼吸调节、自我锻炼与语言治疗等,协助看医生、看病等,协助在其他医疗机构接受一些短时或长时的特殊训练及治疗等例如职业治疗、言语治疗,遵守饮食或其他一些与疾病及治疗有关的行为规定。标准6“日常生活塑造与社会交往”包含了日常生活的计划安排以及实施这些计划安排以及根据具体变化改变原有计划安排的能力,还包含能否自行合理休息及睡眠,能否保有正常的日夜生活的节奏,能否在时间向度上对未来的生活进行合理安排,与其他护理人员和家属的互动与交流能力(例如能否交谈以及与他人接触及互动),能否在自己的居住环境之外与其他朋友、同事、熟人进行互动,受护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保留原有的社会交往网络等。
根据上述鉴定标准1—6 及其下含的各个子标准及属项,德国经历长护保险制度改革后将长期护理需求群体根据积分分成了当前的五个级别。长期护理第1 个级别获得的鉴定评分是12.5—27分,被定义为“生活自理能力的轻微受损”,第2个级别获得的鉴定评分是27—47.5 分,被定义为“生活自理能力显著受损”,第3个级别获得的鉴定评分是47.5—70 分,被定义为“生活自理能力严重受损”,第4 个级别获得的鉴定评分是70—90分,被定义为“生活自理能力最严重受损”,第5个级别获得的鉴定评分是90—100 分,被定义为“有特殊护理需求的生活自理能力最严重受损”(表3)。

表3 德国长期护理新级别的评定
经历长护险从三级到五级的改革之后,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当前的待遇如下:如果选择了家庭成员的居家护理,那么受护人可以得到一笔护理现金的补贴分配给家人,其金额从护理一级的无特别待遇上升至护理五级的每月901欧元,另外选择家属护理的家庭从一级至五级每月可以获得额外的125 欧元的“减压金”;如果选择的是居家护理中的(由专业服务机构提供的)流动上门护理服务,那么服务待遇则要高于家属护理,受护人可以获得的服务待遇超过家属护理两倍多,从护理二级的689 欧元直至护理五级的1 995 欧元。受护人员也可以选择部分入院式的护理,也就是白天或是夜间在护理院或养老院接受护理,而另外的时段则居家护理。选择半入院式护理的待遇从护理一级的无待遇一直上升到护理五级的1 995欧元。而如果选择全入院及全机构式护理,那么每月所获的服务待遇从护理一级的125欧元上升到护理五级的2 005欧元。除了以上的几种主要护理待遇以外,德国还有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如果选择的是居家护理中的家属护理,若家属因为生病、短期休息、度假等原因而一年在某些时段无法完成护理任务,那么可以在这段时间寻找其他家庭成员、近亲或是依靠专业的上门护理服务机构来在这段护理空窗期代理护理,代理护理最长给付时间为六周;如选择的是其他家人或近亲来代理护理,那么从护理二级至护理五级每年可以获得474 到1 351.50 欧元的额外补贴待遇;如果选择的是服务公司的专业代理护理,那么每年从护理二级到护理五级每年可以额外获得1 612 欧元的待遇。而短时护理则是另外一种特殊状况:选择居家护理的受护人,每年如果有一定的时段需要入院机构护理,例如出于疾病治疗和康复训练的需要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申请短时(入院)护理,这里的短时是指主要在居家由家属护理的前提下一年有部分时间短时接受入院式护理,短时护理给付时间为每年八周,受护理人(二级至五级)可以每年申请额外1 612欧元的补贴待遇。除此之外,当前德国还有护理形式多元化的趋势,一些老年人结伴成为一个互助的护理群体,住在一个公寓为单位的各个套间之内,每一个护理群体构成的居住团体可以每月获得214欧元的补贴(表4)。
除了针对护理服务所提供的现金待遇及服务待遇之外,在其他一些领域,例如技术设备及长期护理基础设施等领域,长护保险也提供一些补贴待遇。例如在入院式机构护理中,住院费用及餐饮费用需要个人自理,但是在针对残疾人的护理群体,护理基金可以提供10%的住院费用补贴,最高补助额可达每月266欧元;而个人使用的护理设备及辅助器械等,每月可以获得额外40 欧元的补贴。而技术护理设备及硬件包括用于护理的辅助硬件设备例如护理床及配套设备、与护理床配套的桌板、护理轮椅、浴缸升降器,同时还包括针对护理人员的特殊淋浴及洗浴设备包括淋浴车等,也包括提高受护人自主生活能力的呼叫系统等,这些护理设备设施的增添及改善等完全由护理基金来给付。另外,养老院及护理院改善居住环境的设施,对居住房间及楼层等进行适宜护理的改造等,对于这些改造措施每项可以从护理基金获得4 000欧元的补贴(表5)。

表4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主要待遇(欧元)

表5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辅助设备、器械及其他补贴
德国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制定统一的长护服务目录或是长护服务项目表,但一些服务公司和护理机构根据德国社会法典第十一部“法定长期护理法案”[7]制定了一些长期护理服务项目目录。各服务公司及机构的项目目录虽非完全一致,但皆参照德国社会法典而来,一般分为多个大项,而每一大项下还包含子属项,例如基本生活护理包含了全身清洗如洗澡淋浴等,也包含了洗漱护理服务例如口腔清洁护理、刮胡子、梳理服务、皮肤护理、指甲护理,也包含了协助更衣等;排泄护理则包含了协助如厕、协助安置大小便装置、清洗便器、清洗被罩床单,也包含了大小便节制训练及失禁护理,也包含了导管护理、尿袋安置及更换,还包含了医疗意义上的人工肛门照护(在腹部设置大肠与小肠造口);而协助进食护理则包含了准备食品及饮料、呈递及帮助用餐及饮水、注意食品的洁净与卫生、介绍与饮食相关的知识(例如针对糖尿病人);而协助起身运动训练等则包含了扶起、抬起床上的受护人员、协助起床就寝、协助进行起身练习,协助展开站、卧、行走、坐等练习,也包括协助受护人离开居住房间外出散步及上下楼梯等;住所卫生护理则包含了清洗打扫所有与生活相关领域包括住所、洗浴间、洗浴设备等,也包含清理垃圾等;而购物买菜服务则包含了购买食品、将食品放置到合适存储之处,也包含了买药、取药服务,还包含了将衣物送去洗涤及取回洗净衣物等;陪伴服务包括陪伴客人来访、陪伴外出散步、陪伴参观文化设施(例如博物馆、展览与音乐会等)、陪伴至公共机关办理手续等;支援服务包括协助游戏及个人爱好的维护,协助照顾家庭宠物,协助处理情感问题及维护受护人的朋友联系,协助对未来实施规划等;监管服务包括识别及防范生活中的隐患和安全风险,训练方向感等;帮扶服务,包括帮助训练对过去事务的记忆及促进记忆能力的恢复,帮助受护人与他人的交谈,帮助生活中的安排与计划,帮助训练理解与认知能力,帮助维持日夜的正常生活节奏。
五、总结与面向未来的发展
本文分析了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历史性缘起及主要运行方式及制度特征,同时也着重介绍了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当前所实施的主要改革。本文提炼出以下几个核心观点供我国决策者参考。(1)德国长期护理保险是在德国经济黯淡、失业率高涨、两德统一的巨大财政负担下建立的。[8]与一般的认知不同,德国不是在经济优越与宽裕的条件下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因此建立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关键性因素不是经济与财政,而是国家的总体政治意志。(2)正因为德国在经济下滑时期建立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考虑到经济因素与工商业界的受压及反弹区间,所以初始就规定单纯依靠社会保险费用来筹资,而国家财政不再额外介入。由于制度的粘性,这样的制度安排一直保留到今天。但随着长护保险的刚性需求不断上升,这样的税收不介入的做法越来越受到挑战与质疑。(3)德国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的是广覆盖、宽准入、中低水准的待遇给付,通过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将非雇员的居民及社会弱势群体也纳入到长期护理保险中来,同时通过新分级改革进一步降低了获取长护保险待遇的障碍度,在待遇上提供中等偏低水平的保障待遇,国家法定的社会护理制度承担了首要责任,长期护理救助依然扮演着拾遗补漏的辅助作用,[9]而个人及家庭也要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这样的责任主体多元化充分考虑到了长期护理保险的刚性需求及责任多方共担的因素,值得我们借鉴。(4)德国在2017 年以来的改革中在长期护理鉴定、分类及分级中大幅增加了对于认知障碍、失智及精神、心理和社会因素的考虑,应该说,在这一点,德国继续走在了全球长护事业的前列。德国的新改革经验值得我们探讨与学习。(5)德国不采取地方试点而直接在联邦层面立法建立制度及推进改革的做法同样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事实上社会保障新制度建立过程中是否需要反复试点,是否试点越多越好、试点时间越长越好,的确值得我们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