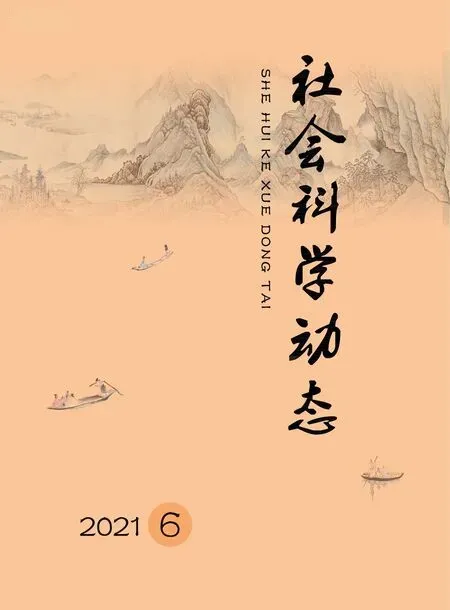德国历史学派是建构中国经济学的理想范式吗?
潘 凤 闫振坤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近代中国自林则徐、魏源起,就从未停止过通过借鉴他国先进经济思想谋求本国繁荣富强的探索。作为引导后起国家加速崛起的经济流派,德国历史学派的学术思想和实践表现无疑成为众多后起国家学习借鉴的榜样。近代中国以来,德国历史学派至少两次对中国经济的实践探索和中国经济学的建构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一次在民国时期,以刘秉麟、张敏珊、唐庆增等为代表的经济学者盛赞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之严密精到,研究方法之一丝不苟,为泰西经济思想界生色实多”①,并将其作为建构中国经济学的榜样。另一次则在建国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构中国经济学、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研究重回国内学术界视野,在此背景下,作为以国家为分析对象的德国历史学派由于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深度契合又重新得到重视。贾根良、黄阳华②、高德步③等学者积极倡导以德国历史学派为参考建构中国经济学,周文、孙懿④、袁辉⑤等诸多经济学者积极倡导历史分析方法的回归。
作为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典型学派⑥,德国历史学派在重新赢得理论价值认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演化过程和时代价值做更为全面的评估。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特质能否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历程?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理论价值又有多少?换言之,德国历史学派是否适合作为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理想范式?回答这些问题离不开对德国历史学派理论体系的深刻透析,同时也必须对其理论特质能否与中国现时代的阶段特点相契合做出评判。以下尝试从德国历史学派发端的哲学属性切入,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相较以往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文献研究,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沿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思路,将一个时代形成的经济学思想与哲学进行结合分析,从经济哲学的视角分析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属性;二是剖析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点,从理论与时代特征能否契合的角度,分析新时代下德国历史学派对建构中国经济学的适用性。
一、黑格尔主义下的德国历史学派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自1776年现代经济学开辟以来,尽管经济学从理论体系、分析范式等诸多方面完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几百年来,经济学的发展演化从来没有和其所处的时代及哲学思想相割裂。从这个角度上讲,德国历史学派的萌生也概莫能外。从时代背景上看,德国历史学派的萌生是与德国历史哲学的兴起相伴而行的。作为德国历史主义的巅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经济学领域的德国历史学派。黑格尔将历史分析上升到一种理性和自由的高度进行分析,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理论体系入手,德国历史学派的诸多思想脉络便跃然纸上。
第一,德国历史学派与德国历史哲学在民族特质分析上的相通性。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考察了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文化特质等要素对形成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黑格尔认为,各个民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承载者。怀着对德意志民族的强烈热爱,黑格尔将古日耳曼人的自由精神视为历史演进的高峰。这种基于本民族的特质、为本民族发展辩护的哲学理论无疑对经济学领域的德国历史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无处不饱含着对德意志民族崛起的挚爱与思考。正是基于对本民族繁荣理想的无限崇尚,李斯特坚决反对不基于自身国情出发的一切“世界主义经济学”理论。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雪尔、施穆勒继承了早期德国历史学派的民族特色研究传统。如施穆勒坚定地认为,经济学理论“不能脱离地点、时间和民族,而其基础应当首要地从历史中去探求”。这些见解无疑显示出德国历史哲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研究的一脉相承。
第二,德国历史学派与德国历史哲学在思想主旨上的相通性。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家主义与正义自由理解的相通性。黑格尔认为,“在世界历史的所有现象中,我们真正的对象是国家。因为国家是个体从出生开始就要对其有所信赖、有所习惯的普遍理念和普遍的精神生活,在国家之中,个体才能获得自己的存在和实在,才能获得他们的知识和意志。”⑦黑格尔是国家主义的崇尚者。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尽管从自由和正义展开,但它们均内生于国家的强权之中。对国家强权的迷信与崇拜塑造出德国历史哲学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黑格尔甚至将绝对君主专制下的普鲁士看作地球上正义的化身。⑧毫无疑问,黑格尔主义的这种态度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主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李斯特以外,德国历史学派的另一位先驱亚当·缪勒认为,现代自由主义诱发的自由企业和竞争产生无秩序,会使传统的个人联系变得松弛,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充斥着恢复国家力量和中世纪制度的强烈呼吁。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更加强调国家力量下的正义与自由。李斯特认为,只有在政府参与下的关税保护政策,才能促使世界联盟及持久和平局势出现,最终实现真正意义的自由贸易。从强权背后的正义与自由起点出发,德国历史学派倡导的关税保护等基本主张无疑是这种逻辑起点下的自然延伸。二是对精神生产力理解的相通性。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体系中,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的精神,在于该民族体现了世界精神的哪个阶段。显然这种强调民族精神特质的思想影响了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高度颂扬了精神力量的重要性。李斯特认为,相较“物质资本”,“精神资本”更加重要。在决定社会进步的六大生产力之中,精神生产力是生产力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⑨后续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雪尔、施穆勒等也有强调精神作用的重要论述。
第三,德国历史学派与德国历史哲学在方法范式上的相通性。反对抽象演绎、主张历史演化是德国历史学派众所周知的鲜明特质,然而,隐匿在德国历史哲学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方法范式的衔接却较少为人所知。如前所述,黑格尔历史哲学将世界历史看作一种合理且必然的过程,而这种世界历史向理性和自由演进的过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经历了从东方向西方、由历史儿童期向历史成熟期的过渡,这种过渡和演进的过程构成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演化分析范式,而对自由与理性的追求则成为这种演化分析的终极目标。与历史哲学类似,德国历史学派表现出对这种分析范式的继承。如德国历史学派早期的李斯特摒弃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方法,转而采用历史演化的方法论述了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旧历史学派罗雪尔采用生物类比的方法,将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为幼年、青年、成年和老年四个阶段,这无疑表现出与德国历史哲学更高程度的相通性。新历史学派的领袖人物施穆勒则更加系统地论证了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将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归纳为“历史归纳法”、“历史生理法”和“历史统计法”三类。⑩相较旧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完成了由“历史归纳法”“历史生理法”向“历史统计法”主导分析范式的转化,并未脱离历史演化分析的基本范式。由于德国历史学派和历史哲学塑造的历史演化的鲜明特征,以至于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直接将所有注重历史的、归纳的、伦理的经济学派统称为德国学派。⑪
二、马克思、熊彼特等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批判与继承
带有鲜明黑格尔历史哲学意蕴的德国历史学派自萌生之日起,就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进行批判和思辨,由此也就注定了其会受到多领域的评论和批判。
首先,从德国历史学派萌生的哲学渊源出发,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蕴含的有缺陷的辩证主义与唯心主义给予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曾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蕴含的辩证法有针对性地批评,“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缺失,是因为它建立在精神首要、物质次要的基础之上的”⑫,马克思也对李斯特的历史学派观点评述,“李斯特先生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现实的社会组织是无精神的唯物主义……他永远也想不到,国民经济学家只是给这一社会制度提供相应的理论表现。”⑬在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和李斯特历史学派的国家主义观点时,马克思也对历史主义的国家主义观点给予了深刻的反思。如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将国家的出现看作市民社会产生的原因。马克思对此深刻批判,认为黑格尔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形成的逻辑,并没有正确认识市民社会的起源。与之类似,在对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的国家主义观念批判中,马克思认为,李斯特笔下的国家洋溢着一种神圣色彩,缺乏对工业生产过程中社会关系的深刻考察。从马克思的著述时代来看,尽管晚年的马克思曾对李斯特的历史主义观点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毫无疑问的是,德国历史学派萌生的哲学渊源与马克思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众多领域完全排斥。
其次,在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体系上,以熊彼特为代表的经济学大师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从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希尔德布兰德、罗雪尔、克尼斯到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穆勒和新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斯皮索夫、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熊彼特都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评价,其中尤以对新历史学派代表施穆勒的评价为重点。在熊彼特的经典巨著《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首先肯定了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将历史工作作为研究的主题可以“大大促进对于社会过程的精确了解”,但在对施穆勒的批判中,熊彼特毫不掩饰地扩展到了对德国历史学派总体的评价。以施穆勒的著述为批判对象,熊彼特认为其所有一切思想的根源并未摆脱德国的过去传统——“史料学的高水平,对历史事实的普遍尊重,理论经济学的低水平,对理论经济学的价值缺乏尊重,把国家置于最崇高的地位,而此外的事物则重要性较小。”⑭在对历史学派研究成果的评价上,熊彼特基本持一种轻视甚至蔑视的态度。熊彼特认为,“希望只消整理一下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无须借助人们在专题研究以外还须花费的思维活动,就可以把历史专题研究成果与‘普通经济学’熔焊在一起,这当然只是一种妄想。”言下之意在于,历史学派尽管可以在史料收集整理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如果没有更具逻辑性的思维探索,这种理论体系也很难有所建树,这无疑是在深化德国历史学派“理论经济学低水平”的认识。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定义极为严格。若按照熊彼特经济学定义,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雪尔、斯皮索夫、马克斯·韦伯等更应从属于经济哲学家、历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的范畴,这显然是对德国历史学派理论贡献的进一步贬低。
再次,在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范式上,尽管其开辟了历史演化分析的基本范式,衍生出“历史归纳法”“历史生理法”“历史统计法”等历史分析方法,但总体来看,这种分析方法在揭示经济规律和解决具体经济问题上面临诸多挑战,提出对历史学派尖锐批评的典型代表是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门格尔、杰文斯等人。19世纪80年代,门格尔与施穆勒有关经济学方法的论战爆发。在这场论证中,门格尔试图通过厘清历史与理论的边界甄别出德国历史学派的根本错误。门格尔认为,“具体社会现象的历史理解绝不是我们以科学研究方式所要做到的唯一事情,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在于将历史科学、实践科学与理论科学混为一谈。”⑮
最后,在德国历史学派的衍生传承上,作为与历史学派关联最为紧密的美国制度学派尽管继承多于批判,但其拓展的历程也恰恰反映出德国历史学派的诸多缺陷。在美国制度学派的领袖人物凡勃仑的著作《古斯塔夫·施穆勒的经济学》中,凡勃仑对德国历史学派有一个总结性的评语,认为“德国经济学的这一更古老传统缺乏建设性的科学成就,也就是说,缺乏理论……这种保守的历史经济学在理论方面似乎是一块贫瘠之地”⑯。在对旧历史学派的批判中,凡勃仑毫不掩饰地将其作为历史经济学的“初级阶段”加以贬低。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们列举了诸多经济学大师对德国历史学派观点、思想、方法论等众多领域的批判,但毫无疑问的是,历史学派仍在他们构建自身理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马克思、熊彼特、门格尔等都肯定了德国历史学派在弥合古典经济学一般缺陷中的重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已经远播美国、日本等众多国家,但这难掩其在德国日趋衰落的现实,深入剖析德国历史学派嬗变和隐没的缘由无疑对中国当代的经济学体系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德国历史学派的嬗变与隐没缘由
归结德国历史学派隐没的缘由,大概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理论的缺陷。德国历史学派尽管在德国的统一与崛起过程中划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不能否认的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贡献却极为有限。恰如熊彼特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贡献的低水平”嗤之以鼻一样,德国历史学派在李斯特以后,再无学者能在经济理论上做出与李斯特比肩的学术贡献。
第二,方法的局限。深受德国历史哲学影响的德国历史学派尽管从黑格尔主义那里继承了历史主义和辩证方法,却不仅没有使这一认知方法向“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正确方向推进,反而随着学派的演进,原本历史学派恪守的历史主义方法逐步由“哲学的历史”向“原始的历史”“反思的历史”退化,以至于在罗雪尔之后,德国新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坚定地认为,无需寻找规律,只需罗列历史事实就可说明一切。⑱
第三,时代的影响。一种经济学说能否在本国的经济实践中大放异彩取决于这种学说与经济实践特征的契合性。萌生于德国统一和德意志民族意识崛起时期的德国历史学派无疑是该时期理论诉求的体现。在德国走向统一和德国民族意识崛起的历史时期,德国历史学派作为德国官方学派,其思想体系和理论特点与德国的时代特征无疑是契合的,但到了德国发展的成熟期,随着德国已经从初级的农业国走向富强的工业国,李斯特开创的这套理论体系便由于目标已经实现而失去了理论实践的时代根基。
第四,外在的冲击。当经济理论在历史学派的领域几乎沉默的时候,以“边际革命”为代表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正在占据经济学研究的主流。除了“边际革命”诱发的经济学范式冲击以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国历史主义的哲学根基和方法体系,由此德国历史学派加速了在德国学术领域隐没的进程。
四、对建构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启示
一部德国历史学派的演进史,恰恰也是一种经济学说与时代特征交互碰撞、生发演进乃至衰退隐没的历史。德国历史学派的演进为我们建构中国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观察视角。透过德国历史学派的演进历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个有意义的理论启示:
第一,一个理想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必须对时代诉求积极回应、在理论演进上与时俱进。德国历史学派兴起于德国民族统一和国家崛起的时代背景,李斯特等先驱开创的历史主义分析范式回应了时代需求、切中了德国振兴发展的时代脉搏,这是其能在德国乃至世界范围赢得认同并取得积极效果的原因。但如果一种理论仅仅满足于国家成长某一阶段性的需求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第二,立足于本国实际、而又不拘泥于本国实际,秉承世界眼光是构建经济学的基本态度。经济学理论固然有国情之别和派别之分,但在某些具体经济问题或某些大的经济发展趋势判断上,仍是可以找到一些共性规律和共同的解决办法的。秉承“隔离主义”或高度的民族主义态度,固然可以厘清本民族的部分发展思路或发展特点,但脱离世界眼光的审视,必然会造成前进道路的迷失。由此认为,建构理想的经济学,应该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第三,建构一种理想的经济学范式应该有一种正确的哲学根基作为指导。建基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历史学派尽管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汲取了充足的营养,但辩证唯心的哲学缺陷最终限制了德国历史哲学的持续演进。在德国历史学派的后续演进过程中,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没有给予德国历史学派立足现实、回应时代关切的理论张力,最终使德国历史学派陷于一种保守僵化的理论困境之中,甚至在此后没落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范式,一切回归至原始历史的记述之中。
时下,中国正在完成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转变。站在理论演进的视角来看,德国历史学派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解释能力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德国历史学派理论的缺陷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尤其在中国由边缘走向世界中心、经济发展的格局由本国转向世界格局的大背景下,中国更应该秉承一种开放发展的态度,保持一种世界眼光。在经济学范式的哲学根基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予我们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这无疑是较黑格尔历史哲学更加科学、更高层次的历史观,这一哲学理论同时也给予我们建构中国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更有张力的思想武器。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观点仅仅是一种参考,新时代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更应该着眼未来,采用更加科学的范式来建构。
注释:
①严鹏:《德国历史学派与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德国研究》2011年第2期。
②贾根良、黄阳华:《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南开学报》2006年第4期。
③高德步:《历史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的当代构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1期。
④周文、孙懿:《经济学发展趋势与中国经济学的新构建》,《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⑤袁辉:《经济学的“历史”批判——兼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经济学家》2011年第3期。
⑥朱成全、刘帅帅:《德国历史学派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批判及启发》,《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⑦ [德]黑格尔:《黑格尔历史哲学》,潘高峰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
⑧ [美]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晏智杰、刘宇飞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359页。
⑨刘帅帅:《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研究》,东北财经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
⑩何蓉:《德国历史学派与19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的启示》,《社会》2005年第3期。
⑪[英]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惠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⑫刘玲:《马克思唯物史观对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辩证分析》,《课程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2页。
⑭[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94—95页。
⑮C.Menger,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3,p.23.
⑯[美]凡勃仑:《古斯塔夫·施穆勒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22—223页。
⑰[美]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邸小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页。
⑱魏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经济科学》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