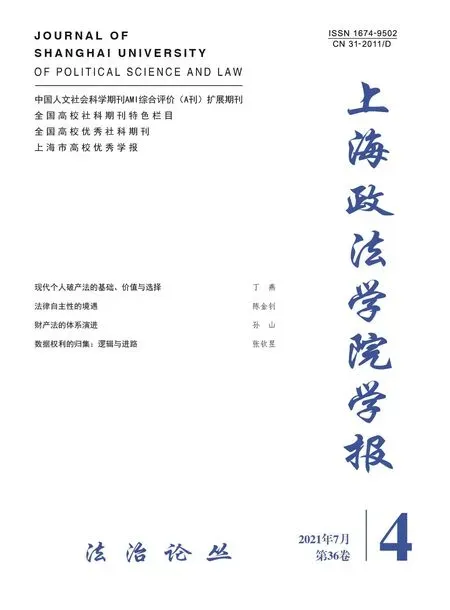肖像权的特质与规则表达
温世扬 刘 昶
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专设人格权编,确立了人格权保护的一般规则和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基本规则。该编将肖像权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于第四章(第1018 条至第1023 条)作了专门规定,加上第一章“一般规定”中有关肖像权的规定,构建了肖像权的独特规则体系。本文拟对肖像权的特殊性质与权能构造略作阐析,并对《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相关规定予以解析,以期能裨益肖像权制度的适用。
一、肖像权:从财产权到人格权
肖像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以其“肖像”相关利益为内容的民事权利。在中国现行民事立法和当代民法理论中,肖像权属于人格权范畴已属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于第五章“人身权”一节(第四节)专设规定(第100 条):“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民法通则》实施后,相关司法解释(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9 条、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 条)和民事单行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 条)均规定了对肖像权的保护。在2015年启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于肖像权的人格权属性也不存在争议,2017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将肖像权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规定于“民事权利”一章(第五章第110 条),其后完成的《民法典》人格权编更是专设一章(第四章)对肖像权予以规定。然而,这种对肖像权的定性与立法安排,在比较法上并非一种普遍立场。
在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肖像权并非通过民法典得到肯认和保护(与其他具体人格权一样),其法律性质也经历了由财产权向人格权的嬗变过程。法国乃近代民法典编纂的先行者,但《法国民法典》对肖像权未设规定,肖像权系由实务所创设(1858年的Rachel 案确认了家属对死者容像绘制与公开的权利,其后对肖像的保护扩及于生存之人,包括绘画、拍摄,尤其是利用他人肖像作广告),法国法院对肖像的保护系以被害人对其肖像享有所有权为依据。1970年法国制定《公民个人权利强化保护法》,并在《法国民法典》中增订第9 条第1 项规定,“任何人均享有其私生活应受尊重的权利。”这一规定对推动法国人格权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晚近的法国司法实务认为,肖像权属于私生活权利范畴,学说则认为,肖像权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权利。《德国民法典》也未对肖像权作出规定,该国对肖像权的保护同样缘起于一宗擅自拍摄死者(德国首相俾斯麦)仪容案件,帝国法院以侵入他人住宅构成侵权行为为由判令拍摄者交出底片;其后,德国于1907年制定的《艺术及摄影作品著作权法》将肖像纳入著作权保护范畴,规制了肖像作品的传播与公开展示行为。20世纪50年代,有鉴于《德国民法典》对人格权益保护的不足,德国联邦法院创设了“一般人格权”这样一种“框架性权利”,将名誉、生活安宁等精神性人格利益纳入其保护范围,《艺术及摄影作品著作权法》无法保护的肖像制作权也被纳入一般人格权范畴,而《艺术及摄影作品著作权法》所确立的肖像权则被学者称为特别人格权。①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136 页。
在美国,对肖像权益的保护也经历了由一元保护到二元保护的实践历程。1903年纽约州颁布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隐私权法。该法规定,为了广告和商业的目的,未经许可而使用他人的姓名和肖像,属于侵权(侵害隐私权,即“个人独处的权利”)和轻罪。但隐私权仅具有防御功能,即排除他人对姓名、肖像的擅自使用,而不包含积极利用的内容。因此,在1953年的“海兰案”中,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弗兰克法官明确提出“公开权”(The Right of Publicy)的概念,即允许他人独占性地使用自己肖像的权利;次年,知识产权学家尼莫(Nimmer)教授发表题为《公开权》的论文,论证了其作为一项财产权利的独立性;其后,通过1977年最高法院对“萨奇尼案”(有关表演者形象)的判决,“公开权”在全美范围内获得了认可,并被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重述(第3 版)》中。②参见李明德:《美国形象权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冬季号。至此,肖像使用(许可)权在美国法上被纳入“公开权”范畴,从而使自然人的肖像利益受到隐私权和“公开权”双重保护(“公开权”仅保护肖像的财产性价值,肖像上的精神利益仍属于隐私权保护范围)。
我国《民法通则》第100 条明确了肖像权的人格权性质,但并未全面、准确地揭示肖像权的人格权内涵。该条规定:“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依其文义,肖像权的权能仅限于“禁止他人以营利为目的使用自己肖像”,侧重保护的是肖像上的财产利益,至于肖像所承载的精神利益则语焉不详。依此规定,对他人肖像的非营利性擅自使用、擅自制作他人肖像、丑化他人肖像等行为均无法纳入侵害肖像权行为范畴,肖像权名为一项人格权,实为一项内容偏狭的财产权。①有人认为,肖像权是公民对自己肖像所享有的一种所有权。参见张华:《关于肖像权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河北法学》1994年第5 期。这与我国学者对肖像权内容的通说不一致(如认为肖像权的权能包括肖像制作权或肖像再现权、肖像利益维护权)②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 页;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37 页;李开国:《民法原理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 页。,“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更是受到广泛批评③参见吕彦:《公民肖像权若干问题研究》,《现代法学》1990年第4 期;王兰萍:《对侵犯肖像权认定的思考——兼谈〈秋菊打官司〉的官司》,《法律科学》1995年第6 期;杨立新:《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 页;王成:《侵犯肖像权之加害行为的认定及肖像权的保护原则》,《清华法学》2008年第2 期。,且没有得到审判实践的严格遵从。④参见张红:《人格权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180 页。及至《民法典》编纂,人格权编在广泛吸收相关理论成果和比较法经验的基础上,对肖像权的权能作出了全面宣示,充分揭示了其人格权属性。
以上考察表明,肖像权作为一项实证法上的权利,并非“天然”地属于人格权范畴,而是随着各国法治实践对肖像利益保护范围的逐渐扩张(由财产利益到精神利益),才被纳入人格权保护体系。正因如此,肖像权具有某些不同于其他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权的特质,并呈现出特殊的规则构造。
二、肖像权客体的复合性
权利客体是对权利设立在何种基础上的说明,是立法者通过授予主体法律上的权利予以保护的利益的具体化。⑤参见方新军:《权利客体论——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165 页。关于人格权的客体,我国学界存在“人格说”⑥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7 页;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 页。“人格利益说”⑦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 页;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4 页;方新军:《权利客体论——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 页。“人格要素说”⑧参见李永军:《民事权利体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 页;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 页。等不同见解。基于“权利设立在何种基础上”的权利客体意蕴之理解,笔者赞同“人格要素说”,同时认为,“人格要素说”与“人格利益说”并无实质差异,“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这些利益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的必备要素,因此,也是与人不可分离的(人格)要素”,“在抽象的意义上,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人格要素则是人格利益的具体化。”⑨同注⑤,第191 页。
基于对人格权客体的上述认识,肖像权的客体应当是与自然人外部形象相关的人格利益(或称肖像利益),而不是我国部分学者所称的“肖像”。①参见吕彦:《公民肖像权若干问题研究》,《现代法学》1990年第4 期;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 页;隋彭生:《论肖像权的客体》,《中国法学》2005年第1 期。因为肖像只是自然人外部形象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再现,本质上属于“无体物”或“作品”的范畴(故肖像在德国最初仅受《艺术及摄影作品著作权法》保护),对肖像“作品”的保护,并不足以全面保护自然人对其外部形象所享有的人格利益,尤其是作为人格权核心的精神利益。换言之,肖像权的客体,是包含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自然人外部形象所体现的利益。②参见龙显铭:《私法上人格权之保护》,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101 页;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 页;张红:《人格权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63-165 页。也有学者认为肖像权的内容包含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参见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 页;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1 页。这种权利客体(肖像利益)的复合构造,是肖像权及其他标表型人格权的重要特点。
自然人外部形象所蕴含的精神利益,是肖像权客体的本体和肖像权作为人格权的存在基础。与其他人格权一样,这种精神利益的实质,就是权利主体的人格尊严。正如拉伦茨所言,人格权实质上是一种受尊重的权利,一种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③参见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9 页。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将人格权设置为一种“受尊重权”。参见龙卫球:《人格权的立法思考:困惑与对策》,《法商研究》2012年第1 期。,人格利益的核心内容是人格尊严(《民法典》第990 条第2 款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抽象化表述人格利益),体现的是人的精神性需求。自然人的外部形象,也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在德国早期司法实践中,对肖像的保护就体现了对人格尊严这种精神利益的保护。如在“齐柏林案”(Graf Zeppelin 案,1910年)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以原告的姓名及半身像申请商标登记,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并在判决理由中指出,与意定商品产生链接,系触犯一个情绪敏感之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将自己的肖像置于商品上惹人注目的行为并不符合每个人的品味。④参见张红:《人格权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 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院创设“一般人格权”对肖像上的精神利益加以保护,使肖像权具有完整的人格权意义。自然人外部形象所体现的精神利益,体现在肖像的制作(再现)、公开、不受玷污丑化等方面。以此作为肖像权保护的重点,既是人格权的本质要求,也是各国、各地区肖像权保护立法的共同立场。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0 条规定:“如果自然人本人或其父母、子女的肖像未被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陈列或发表,或者肖像的陈列或发表对该人或其亲属的名誉构成了损害,则司法机关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作出停止侵害的决定。当事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受影响。”⑤《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丁玫、张宓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 页。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法典》第80 条第3 项规定:“肖像之复制、展示或做交易之用,按照第73 条之规定可能侵犯肖像权人之名誉权时,即不得为之。”美国通过1905年的“帕维斯基诉新英格兰生命保险公司案”确立了对肖像的隐私权保护模式,后来创设的“公开权”只是隐私权的扩张。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典》第36 条规定:“盗用或者使用他人肖像或者声音,除大众合理的公开信息外,都属于侵犯他人隐私。”⑥《魁北克民法典》,孙建江、郭站红、朱亚芬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 页。我国《民法通则》第100 条虽然未充分揭示肖像权的精神利益内容,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法院明确主张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不影响肖像权侵权责任认定的案例①参见张红:《人格权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 页。,法院通过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实现对肖像权的保护,有的法院甚至支持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②参见“陈立中诉江西法制报社侵犯肖像权、名誉权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996)海民初字第2498 号民事判决书。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2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61 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适用于侵害肖像权案件,体现了对自然人外部形象所蕴含精神利益的保护。
对自然人外部形象所蕴含的物质利益的保护,是肖像权保护范围的“扩张”。这种扩张,源自自然人外部形象经过“物化”(即形成“肖像”)后所蕴含的经济价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自然人(如演艺明星)的肖像对特定市场主体的产品或服务具有广告功能或品质“加持”功能,因而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以肖像使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明星代言”现象在当今全媒体时代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每一个自然人的肖像都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蕴含着一定的物质利益。对肖像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在比较法上存在不同模式:一种是“人格权”模式,即将肖像财产利益纳入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例如,德国除将《艺术及摄影作品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肖像权益视为一种“特别人格权”外,还通过对“一般人格权”的“赋能”,对自然人肖像上的财产利益加以保护。在“Paul Dahlke 案(1956年)”中,德国联邦法院判决认为,肖像权得经本人授权与他人作商业上的使用,系具有财产价值的排他性权利。③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136 页;第281 页。另一种是“知识产权”模式,即将此类财产利益纳入知识产权范畴。如荷兰、意大利均在著作权法中规定了肖像权人对其肖像的利用、公开的权利,美国则通过创设“公开权”这样一种财产权(知识产权),对包括肖像在内的个人肖像特征的财产价值加以保护。对此问题,我国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借鉴美国法上的“公开权”制度保护肖像等人格标识上的财产利益(有的学者将其译为“形象权”④参见李明德:《美国形象权法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冬季号;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法学》2004年第10 期;杨立新、林旭霞:《论形象权的独立地位及其基本内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 期。但也有学者以“形象权”指称基于自然人生前个人形象产生的权利。参见董炳和:《论形象权》,《法律科学》1998年第4 期;,也有学者将此项权利称为“商品化权”“人格标识商品化权”“人格商品化权”⑤参见谢晓尧:《商品化权:人格符号的利益扩张与衡平》,《法商研究》2005年第3 期;杨立新、林旭霞:《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及其法律保护》,《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 期;张丹丹、张帆:《商品化权的理论争论与反思》,《时代法学》2007年第5 期;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07 页。,或称“商事人格权”⑥参见程合红:《商事人格权刍议》,《中国法学》2000年第5 期;熊进光:《商事人格权及其法律保护》,《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5 期。),主张将肖像等人格要素既作为人格权的客体而对其精神利益予以保护,又作为财产权的客体对其财产利益予以保护,将人格权客体商业化利用所生财产利益从人格权制度中抽离而赋予其财产权的外衣。⑦参见蓝蓝:《人格与财产二元权利体系面临的困境与突破——以“人格商品化”为视角展开》,《法律科学》2006年第3 期。但上述观点并未得到我国立法的回应。相反,《民法通则》第100 条“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之规定,已表明我国立法对肖像财产利益的保护。《民法典》秉持了这一立场,将自然人外部形象所蕴含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一并纳入肖像权的范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肖像权益“一元化”人格权保护模式。
三、肖像权的双重权能及其规则表达
人格权是“一种受尊重的权利,一种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故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格权仅为一种“防御权”,而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言具有“支配性”。①参见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 页;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 页;姚辉:《人格权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 页。我国一些学者之所以主张人格权具有支配权属性,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传统民事权利尤其是所有权构造的路径依赖(将人格权客体视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二是具体人格权的模式效应(某些人格要素已经与人的本体“渐行渐远”);三是人格标识商品化现象的启示。②参见温世扬:《人格权“支配”属性辨析》,《法学》2013年第5 期。笔者认为,人格标识商品化现象并不能证成人格权整体上具有“支配权”属性,但彰显了肖像等人格标识的财产价值,也体现了肖像权由消极权能向积极权能的扩张,即肖像权权能的二重性。
(一)肖像权的消极权能:防御权能
肖像权属于绝对权,意味着权利人得向任何第三人主张其权利,当他人未经肖像权人许可擅自制作、使用权利人的肖像,或实施丑化、污损、伪造他人肖像的行为,或有即将实施上述行为的情形时,肖像权人既可以主张人格权请求权,也可以在精神损害或财产损害发生后,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
1.人格权请求权
不同于大陆法系传统上将侵权行为纳入到债法体系下、以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采用“大侵权模式”,该法第15 条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绝对权请求权也纳入侵权责任中,从而形成侵权责任的统合。③参见王利明:《论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离》,《中国法学》2019年第1 期。虽然《民法典》第1165 条第1 款相比《侵权责任法》第6条增加了“造成损害”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且单设第二章规定损害赔偿,似有意实现向大陆法系传统侵权责任内涵(侵权之债)的回归,但是,《民法典》第1167 条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可见《民法典》并未完全实现绝对权请求权与侵权责任的分离。人格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同系绝对权请求权的下位概念,《民法典》第995 条所规定的人格权请求权条款,也是《民法典》第1167条的特别规范,应当优先于一般规范得到适用。④参见周友军:《〈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守成与创新》,《当代法学》2021年第1 期。当第三人违反《民法典》第1019 条的规定,在不满足合理使用的情形下,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实施了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肖像的行为,抑或以丑化、污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肖像权时,肖像权人可主张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人格权请求权,以使肖像权益恢复至受侵害前的状态。人格权请求权的成立并不需要义务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也不以权利人遭受财产或精神损害为条件,因其目的在于使人格权恢复至受侵害前的状态,而非损害赔偿。
为强化人格权的保护,《民法典》第995 条特设人格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其中关于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的规定与《民法典》第196 条关于诉讼时效排除适用的一般规定相同,关于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的规定则属于《民法典》第196 条所称的“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其中,消除影响请求权、赔礼道歉请求权可适用于肖像权。
2.损害赔偿请求权
(1)精神损害赔偿。肖像权作为人格权,首先蕴含着精神利益。修正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 条规定,自然人因肖像权遭受非法侵害,得向人民法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随后的《侵权责任法》第22 条规定,行为人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第1183 条承袭了这一规定。所以,在权利人的肖像权受到侵害,并对权利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情形下,权利人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此项规定与德国司法实务标准并不相同,虽然《德国民法典》第253 条第2 款并未规定除侵犯身体、健康、自由或者性自主权以外的一般人格权所产生的民事责任,但司法实践中却通过目的性扩张的手段,将一般人格权纳入其中,只有当行为人存在严重侵害一般人格权或基于重大过错侵犯一般人格权时,权利人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①参见[德]埃尓温·多伊奇、汉斯-于尔根·阿伦斯:《德国侵权法——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及痛苦抚慰金》,叶名怡、温大军译,刘志阳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 页。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仅影响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酌量,并不影响请求权的成立。
精神损害赔偿兼具补偿功能与安抚功能,前者填补的系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赔偿的痛苦情绪,后者则更强调发挥法律的惩罚功能,所以,加害者越具有主观可课责性、造成受害人的精神痛苦越剧烈,实施侵权行为的目的越恶劣,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义务即越正当,赔偿数额也越多。②同注①,第234-235 页。对此,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 条有明确的规定。故当肖像权人的权利被他人非法侵害时,权利人可依据该条请求法官确定可得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 条将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酌定标准,这也是精神损害赔偿安抚(惩罚)功能的体现。但是,因为《民法典》第1182 条的得利剥夺规则也体现了赔偿、预防及惩罚的多重功能,若于精神损害赔偿计算时基于得利因素提高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又于财产损害赔偿时采用得利剥夺规则,实质上将会产生“双重惩罚”效力,同一侵犯人格权益之行为于此处被惩罚2 次,对受害人保护明显过重。所以,若以得利为基准计算财产损害赔偿,则不应再将得利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酌定因素。
(2)财产损害赔偿。肖像权作为标表型人格权,除精神利益外,也蕴含经济利益,具有独立使用的经济价值,对于名人肖像而言尤其如此,因此,第三人具有擅自利用肖像权人肖像为自己谋求经济利益的可能。《侵权责任法》第20 条为肖像权被侵害时所产生的财产损失创设了特殊的损害赔偿规则:侵权人应首先以被侵权人产生的损失为限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当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时,以侵权人的实际获利为限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仍然无法确定得利数额的情形下,则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民法典》第1182 条一改《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赋予权利人选择权,即其可选择主张权利人所产生的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删除了得利赔偿规则适用的前置要件。此项修改,有利于受害人得到救济,并且达到遏制与震慑侵权行为的目的。①参见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75 页。
值得注意的是,除《民法典》第1182 条的规定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54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71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63 条也规定了以得利作为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与《侵权责任法》《民法典》规定的不同之处在于,知识产权领域增设许可使用费作为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实际损失”“许可使用费”“所得利润”三选一的多元化损害赔偿方式首先于德国知识产权领域得到创设,之后被引入到人格权益的保护之中。因此类规则的创设不同于损害赔偿传统之计算规则(差额说),也与“禁止得利”原则不符,违反了损害赔偿固有的损失填补功能,故受到传统教义学的质疑。②参见岳业鹏:《论人格权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以〈侵权责任法〉第20 条为中心》,《法学家》2018年第3 期。事实上,在人身权益以及无形财产权侵权领域增设利润剥夺规则,便已彰显了现代的损害赔偿制度不单单具有损害填补功能,也具有预防功能与惩罚功能。③参见张家勇:《基于得利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规范再造》,《法学》2019年第2 期。侵权法的预防功能体现在,当侵权人之得利小于被侵权人的损失时,通过完全赔偿规则即可完全填补权利人之损失,从而起到震慑侵权人的效果。而当侵权人之得利大于对被侵权人造成的损失时,作为经济理性人的侵权人仍然具有侵权动机,因其从侵权行为中所获得的利润可完全填补其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且仍存有经济上之剩余,此时侵权法无法较好地发挥预防功能。另外,不当得利中的得利也不包括利润,其客体仅指向客观财产价额及原物用益价额,不包含任何预防功能④参见缪宇:《获利返还论——以〈侵权责任法〉第20 条为中心》,《法商研究》2017年第4 期。,仅具有利益矫正功能,故即使在知识产权法领域,将不当得利改造为损害赔偿方式,也无法抑制侵权人的侵权动机。如果引入利润剥夺规则,将其作为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因侵权人最终会一无所获,法律能够为抑制可能的侵权行为提供充分的制度激励,其预防功能即可得到充分发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的个别规范也凸显出惩罚功能,例如,知识产权领域(《民法典》第1185 条)、产品侵权领域(《民法典》第1207 条)、环境侵权领域(《民法典》第1232条),均规定在故意侵权的情形下可适用惩罚性赔偿。因恶意的主观状态具有更高的可课责性,故有必要通过惩罚手段达到教化侵权人的目的。对于得利剥夺而言,因其与受损人的损失全然无关,其目的并非损失填补,仅着眼于得利人的利润,在得利数额大于侵权人的损失时,其便具有惩罚功能。若侵权人的主观状态仅为过失,基于惩罚目的剥夺全部利润,既与以故意为基点构建的惩罚性赔偿的制度体系相悖,难以起到惩罚教化的目的,也过度干涉侵权人的行为自由,完全否定过失情形下因侵权人自身的劳力与智慧对利润创造的贡献,从而导致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天平的失衡。因此,为避免矫枉过正,应将利润剥夺规则的适用限定于侵权人故意的情形。⑤学界多持此类观点,具体可参见温世扬:《论“标表型人格权”》,《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 期;岳业鹏:《论人格权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以〈侵权责任法〉第20 条为中心》,《法学家》2018年第3 期;孙良国:《论人身权侵权获益赔偿的性质、功能与适用》,《法律科学》2011年第4 期。
综上所述,对《民法典》第1182 条应当作限缩解释,肖像权人仅对于“故意”侵犯肖像权并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人才可主张以利润剥夺为基础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当然,肖像权人也可基于《民法典》第985条的规定,基于自身人格权益被侵害的事实,向侵害者主张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即肖像使用费。
3.肖像的合理使用
如果任何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都要征得肖像权人同意,将会对社会运行效率带来负面影响。有鉴于此,《民法典》第1020 条创设了肖像合理使用规则,以期达到恰当协调肖像权与公共利益关系的目的。有观点从他为性角度解读肖像合理使用规则。根据此种观点,他人本就有使用肖像权人肖像的权利,只有在存在合理隐私期待时,肖像权才不能为他人自由使用。①参见陈甦、谢鸿飞:《民法典评注(人格权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38 页。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与肖像权作为绝对权“不容他人侵犯”的固有属性难以契合。肖像权作为一项人格权,法律赋予肖像权人制作、公开、使用肖像的权利,除非基于维护、增进公共利益的需要,否则他人不得擅自使用肖像权人的肖像,不能认为肖像属于“公用物”。况且,除了首次公开(包含公开使用)肖像涉及隐私以外,秘密使用肖像以及制作、公开使用权利人已经公开的肖像均与隐私无关。
⑴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之所以创设此项合理使用规则,是因为此类行为有益于公共福祉: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而使用他人肖像,有利于提高民众的文化修养;为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而使用他人肖像,对促进社会进步以及文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②参见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36-137 页。根据《民法典》第1020 条的规定,此处可以使用的肖像必须是他人已经公开的肖像。因肖像的公开系肖像权人对隐私的自决,在非公开情形下,肖像蕴含着肖像权人的隐私利益,擅自使用他人未公开的肖像,不仅侵犯权利人的肖像权,也侵犯其隐私权。
应当如何理解此条所规定的“必要范围”?因肖像权合理使用规则本就对著作权的合理规则作较多借鉴③参见张红:《肖像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中国法学》2014年第1 期。,故对此问题可以借鉴知识产权领域学者的解释。有学者通过运用“三步检验法”指出,在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以及无理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下,即便于文义上符合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事由,也应当构成“不合理使用”,从而对著作权人承担侵权责任。④参见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0 页。修正后的《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11月11日通过,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第24 条也对此作出了一般规定,使用他人作品,不得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即便对作品的使用是出于个人学习、研究等目的,但当使用行为与权利人的著作权可能构成市场竞争关系,并有为权利人带来重大损失的较高概率时,即构成“不正常利用”。⑤对于三步检验法的具体解释与适用,可参见熊琦:《著作权合理使用司法认定标准释疑》,《法学》2018年第1 期。简要来说,三步检验法系由《伯尔尼公约》所确立的、检验著作权合理使用行为是否能够阻却违法性的方法。其检验步骤有三:“在特定情形下”“与作品的正常使用不冲突”“没有无理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三个要件。所谓“特定情形”,即为法律明文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正常使用”则指代未与著作权人事实上构成市场竞争关系,并为权利人带来重大损失的行为。“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合法利益”应当解释为一种辅助性的程度判断方法,通过在个案中比较著作权人的预期收益和使用者的预期收益,辅助判断“在特定情形下”和“与作品的正常使用不冲突”的认定是否过于严格,并以此对个案中的合理使用适用范围进行微调,而不能将其作为完全独立的和封闭的判定要件进行适用,否则,将出现“三步检验法”第二步和第三步的重复适用问题。例如,通过P2P 软件大量下载歌曲的行为,即使使用者抗辩其行为系基于个人欣赏为目的的合理使用行为,也应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得出以下推论:使用人的大量复制行为具有以营利为目的,挤占权利人市场份额的高度盖然性。故在此情形下,使用人的行为并不构成合理使用。肖像的合理行为也应作相同处理,他人不具有利用肖像所蕴含经济利益的正当性,超出必要范围内的肖像使用行为应认定为具有利用肖像权所蕴含经济利益的高度可能性,所以,在此情形下使用人的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
⑵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这是为保障新闻自由及公众获取信息利益权利而确立的合理使用规则。其要义包括:首先,实施新闻报道必须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而不能以营利、人身攻击为目的。①参见张民安:《无形人格侵权责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0-711 页。新闻报道的内容不仅包括具有历史与政治意义的事件,即便是仅具有一般社会意义的娱乐性报道,只要其有利于促进社会公众意见的形成,也可构成合理使用。其次,在新闻报道中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必须以“不可避免”为前提。如对重大节日庆典等活动进行报道,即便肖像权人是被动入镜,也应认定此构成对肖像的合理使用,因为于画面报道中,利用他人肖像属于不可避免的情形,肖像仅系新闻报道的一部分。应当认为,只有在不使用肖像权人的肖像,即会影响新闻报道的完整性及真实性的情形下,才符合此条所规定的“不可避免”要件。②参见王利明、程啸、朱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65 页。例如,肖像权人实施了不文明行为,行为人本可通过批评教育的手段纠正此类行为,或以文字形式对此类行为进行批评,若选择公布肖像的手段对此予以报道,则有违比例原则,此时,应当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因不满足“不可避免”要件而构成侵权。
⑶国家机关为依法履行职责,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肖像。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使用他人肖像的正当性。如公安机关在通缉令中使用被通缉者的肖像,或司法机关在诉讼中使用他人肖像作为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机关执行公务时使用他人肖像不能超出合理使用的必要限度,一般仅涉及公民本人,否则需要对此作相应说明或施加技术手段保护其他人。例如,在“李海峰案”中,原告等人并非案件当事人,仅是履行公民的协助配合义务参与指认,但是,电视台在播出相关片段时未对原告等人加以技术处理,仅对真正的案件嫌疑人进行技术处理,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权,此应可认为已经超出了必要限度。③参见张红:《民法典之肖像权立法论》,《学术研究》2019年第9 期。
⑷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一般而言,自然人既然出现在公共环境中,即表明其已具有被他人“看见”的合理预期。若他人在对公共场所进行拍摄,其目的就是为了拍摄事件及景色,而非特定人物,此时因该人物仅为事件及景色的点缀,并没有起到突出强调作用,故出于保护他人创作自由的考量,应于必要范围内,认为他人可合理使用权利人的肖像。比较法上也存在相似规定。如德国《艺术及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3 条第1 款规定,若图像上的人物仅是作为自然风景或者其他地形图像的附属品出现,则可以构成对肖像权的合理使用。④参见[德]图比亚斯·莱特:《德国著作权法》,张怀岭、吴逸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0 页。再如,在法国,符合以下两项条件时,行为人拍摄他人在公开场所的相片无须他人事先同意:一方面,行为人拍摄的照片没有聚焦主张肖像侵权责任的原告的肖像;另一方面,行为人拍摄的照片应当显示被拍摄相片的人是在公开活动而非私人活动。⑤参见张民安:《无形人格侵权责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8 页。
有学者认为,即使拍摄的客体为特定公共环境,肖像权人仅系摄制作品的点缀,摄制者也没有主观恶意,但只要使用人的目的满足营利要件,使用他人肖像之行为即不构成合理使用。①参见张红:《人格权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 页。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根据使用人的主观目的即否定肖像权利用构成合理使用的可能,关键在于他人是否实质上构成对肖像权所蕴含经济利益的利用。基于艺术创作的需要,于拍摄特定公共环境时将他人摄入往往在所难免,即便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了该照片抑或影像,只要实质上并没有通过利用他人肖像提高自身创作的经济价值的可能性,因肖像部分并不具有不可替代性,人物形象本身也没有为作品带来审美上的特殊性,在其仅被作为画面一部分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此时仍可成立合理使用。否则,必将极大地限制创作者的行为自由,并引发诉讼泛滥。
⑸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民法典》第1020 条第5 项将“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作为肖像合理使用的一般事由(兜底条款)。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使用肖像的情形,譬如,纪念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可复制本馆收藏的肖像作品,展示、复制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肖像作品。②参见陈甦、谢鸿飞:《民法典评注(人格权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39 页;张红:《民法典之肖像权立法论》,《学术研究》2019年第9 期。再如,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也可善意使用他人肖像。为了肖像权人本人的利益,包括对先进人物的照片进行展览、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人而张贴寻人启示等情形。此处虽未采用“不可避免”“必要范围”等表述,但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也应当将上述因素作为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③参见王利明、程啸、朱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67 页。
合理使用权利人的肖像,是否需要支付相应报酬?即《民法典》第1020 条所规定的肖像权合理使用规则,是否包含了肖像权使用的法定许可,亦即仅免除行为人的侵权责任,但并不免除肖像使用者的报酬支付义务?笔者认为,对此仍可借鉴著作权领域的相关理论加以论证。
著作权制度中创设合理使用规则,是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一般而言,合理使用应该服务于版权法所意欲实现的四项目标:表达自由、新闻自由、技术进步和作品创作。除此之外,合理使用应考虑该使用行为是否影响作品的正常使用,即应该考虑其对作品的使用行为是否与版权市场或其重要的潜在市场中的利用方式相竞争。替代性作品的出现会产生竞争损害,但著作权法仅禁止不正当的竞争损害。④参见梁志文:《著作权合理使用的类型化》,《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 期。由此可知,公共利益(包括但不限于科研学习、公共安全、艺术表达与创作自由等)是合理使用规则创设的重要原因。⑤美国版权法最先引入了合理使用的判断规则,且通过一般条款的方式赋予法官以充分的自由裁量。该法第107 条规定:“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确定对一部作品的使用是否为合理使用,要考虑的因素应当包括:(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包括这种使用是否有商业性质或者是否为了非营利的教育目的;(2)有版权作品的性质;(3)同整个有版权作品相比所使用的部分的数量和内容的实质性;(4)这种使用对有版权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法定许可规则而言,其制度创设目的系为了解决交易成本问题,大量利用行为都需要获得权利人的许可,使新技术带来的传播效益被许可增加的交易成本所抵消,限制作品有效利用的障碍逐渐由“技术不能”转变为“制度瓶颈”。因此,有学者主张,应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通过限制著作财产权的排他性来发挥数字传播的效率。一般认为,排他性的著作财产权适用于交易成本较低的条件下,而法定许可则适用于交易成本较高的环境中。①参见熊琦:《著作权法定许可的正当性解构与制度替代》,《知识产权》2011年第6 期。笔者认为,法定许可的创设理由在个别情形下也可能与公共利益相关(如《著作权法》第25 条所规定的教材编写之法定许可),然而其实质在于,不论法定许可事项是否与公共利益有关,皆极大可能构成对著作权人的交易替代,对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但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及提高传播效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考量,可通过创设法定许可规则达到提高传播效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目的。
若将以上理论适用于肖像权,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无论是学习研究、信息利益、安全利益抑或摄制创作),或者维护肖像权人自己利益的需要,在对肖像权人的合法权益并未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以及并未实际利用肖像权所蕴含之经济利益的情形下,只要使用者实施的使用行为仍在必要范围内即可构成合理使用,无须向肖像权人支付报酬。换句话说,合理使用规则要求使用者出于促进公共利益及维护肖像权人利益的目的利用肖像,其利用的并非肖像权所蕴含的经济价值(或者至少不会影响),故自不需支付报酬。若将法定许可规则运用于肖像权利用规则中,其需要回答的问题为:肖像使用者分享肖像所蕴含经济利益的正当性何在?提高作品传播效率具有高度艺术欣赏价值,有利于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但肖像的传播往往仅能为肖像使用者自身带来经济利益,其也会与肖像权人构成实质上的替代市场竞争,所以单纯出于提高传播效率的目的利用肖像,设定法定许可规则并不具有规范上的正当性。
(二)肖像权的积极权能:使用许可权
肖像权的积极权能即权利人对其肖像的“支配权”权能,包括肖像制作权、肖像使用权、肖像公开权和肖像使用许可权(《民法典》第1018 条第2 款)。其中,肖像使用许可权因涉及相对人利益而成为法律规制的重点,《民法典》第1021 条、第1022 条设立了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特别规则。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规则不仅适用于作为面部形象之狭义肖像的许可使用,因我国肖像权采“外部形象”之广义概念,故只要是可被他人识别、与特定自然人建立同一性联系的外在形象(如角色形象),都可适用《民法典》第1021 条、第1022 条所创设的肖像许可使用规则。另外,《民法典》第1023条第1 款也通过扩张的手段,统一了姓名等标表型人格权的许可使用规则。
1.肖像许可使用的方式
对于肖像等人格标识许可使用的具体方式,《民法典》未作规定。有学者将人格标识许可利用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负担行为设立相对权性质的许可;另一种是通过处分行为设立绝对权性质的许可。后者又分为排他商业许可和独占商业许可。②参见于晓:《自然人人格标识商业利用的制度构建》,《理论学刊》2018年第1 期。笔者认为,肖像的许可使用主要是为了商业宣传,其作用与商标相似,因此,其许可使用方式可参照商标许可使用分为以下三种:⑴独占许可。即被许可方在约定期限和地域内对许可的肖像享有独占使用权,许可人不得自行使用该肖像,也不得将该肖像授予他人使用。通过此类许可取得的肖像使用权具有强烈的“用益物权”属性。⑵排他许可。即被许可方在约定期限和地域内,就许可的肖像可排除第三人的使用行为,许可人不得将该肖像授予第三人使用,但自身可继续使用。⑶普通许可。即权利人许可他人在约定期限和地域内使用其肖像后,既可以自行使用该肖像,也可以为第三人另行设定新的许可。
2.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的解释
《民法典》第1021 条规定,当合同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理解存在争议时,应当作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从文义上看,此条规定的是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规则,以凸显对人格尊严的优先保护,将人格权保护置于财产权之上。①参见王利明、程啸、朱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72 页。这与《民法典》第142 条第1 款、第466 条所规定的,当对合同文义存在理解争议时所采纳的客观解释规则并不相符。有利解释规则作为客观解释规则的例外,通常仅适用于合同双方存在实质上不平等、对合同文本存在两种以上解释可能之情形。如《民法典》第498 条规定,当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应当按照通常理解进行解释。但当对格式条款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民法典》第1021 条的规定直接跳过对合同文本的客观解释,不论肖像权人与使用人是否存在经济地位等实质上不平等的情况,径直适用有利解释规则,实属立法创举。
笔者认为,应当对该条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即该条应仅适用于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情形。②参见温世扬:《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评议》,《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3 期;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民事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民法典人格权编条文理解与司法适用》,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11 页。当合同文本存在约定不明的情形时,首先应当通过体系、历史、目的解释等手段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不应直接越过此阶段,不对含糊的文本作必要解释与澄清,径行作对肖像权人的有利解释,否则即有可能违背诚信原则。因为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皆会对合同文本的可能涵义有合理信赖,此种信赖不仅体现在主动签订条款一方对使用文字内涵的期待,也体现在条款接受者作为理性行为人对合同文本可能内涵的期待。当通过对法律行为进行解释能够得出单一结论时,不能基于保护人格权益这一单一目的片面保护肖像权人,而置另一方对合同内涵的信赖于不顾,否则有悖于诚信原则。毕竟,对人格权益的保护并非全然放弃信赖保护的正当理由。但是,当对合同文本存在两种以上解释可能时,若肖像使用者对此多义解释具有过错,则基于过错归责原理,采纳对肖像权人有利解释规则固属正当;即便肖像使用者对此多义解释并无过错,但基于风险归责原理,出于保护人格权益的目的,采纳对肖像权人的有利解释规则,将风险分配于肖像使用者也属必要。③信赖保护中的过错归责与风险归责,可参见叶金强:《信赖原理的私法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170 页。
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的解释规则与格式合同的解释规则可能会发生冲突。当格式合同的制定者是肖像使用者时,无论是基于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解释规则,还是格式合同的解释规则,当存在两种以上解释可能时,都应当作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但当格式合同制定者是肖像权人时,解释冲突即会出现。笔者认为,此时应当适用格式合同的解释规则,作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者(肖像权人)的解释。这是因为,格式条款解释规则本意即为矫正因形式正义所引发的不公平问题,其目标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主体平等,对人格权益的保护不能以牺牲实质平等为代价。
3.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的解除
《民法典》第1022 条根据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期限是否存有约定,规定了不同的合同解除规则。该条第1 款规定,当事人在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均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应在合理期限前通知对方。此条规则实系注意规定,为《民法典》第563 条第2 款“不定期继续性合同得任意解除”规范内涵的重申。无固定期限的继续性合同之所以得被任意解除,是因为既然合同没有约定期限,双方当事人自然也不会对合同存续拥有长远的预期,解除合同并不会损害双方当事人的信赖,且此类合同的长期存续将有可能损害当事人的自由,增加履约风险。①参见王文军:《论继续性合同的解除》,《法商研究》2019年第2 期。此外,该条规定在合同约定不明确的情形下,双方当事人均可任意解除合同,实际上跳过了意思表示解释程序。对此应当首先进行意思表示解释,若通过意思表示解释可得出明确的许可期限,则适用该条第2 款规定的正当事由解除规则;否则才应当视为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没有约定期限,双方当事人可主张任意解除。关于解除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对方的法律后果如何,学界对此存在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在没有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当事人的,不能发生解除的效果。②参见王利明、程啸、朱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80 页。也有观点认为,此时解除通知并非无效,仅须认为解除通知延续至合理期限之后发生效力。③参见朱虎:《分合之间——民法典中的合同任意解除权》,《中外法学》2020年第4 期。笔者认为,对此应采第二种观点,直接否认解除权的效力未免因噎废食,延展解除通知行使后的合理期间即可达到平衡双方利益的目的。若解除权人在发出解除合同后,在本应交由相对人采取处置措施的合理期间采取不当行动,并对相对人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在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使用期限的情形下,《民法典》第563 条第2 款规定肖像权人可以基于正当理由解除许可使用合同。对于何为此处规定的正当理由,学者间存在不同的见解。有观点认为,随着生活阅历及价值观的转变,肖像权人价值观有可能会发生改变,此时权利主体有绝对的权利自我决定如何展现自己新的人格特性,所以可解除合同。此外,利用行为若侵犯权利人的一般人格权时,权利人也可解除合同。④参见刘召成:《人格商业化利用权的教义学构造》,《清华法学》2014年第3 期。有观点将人格利益置于绝对优先地位,认为任何影响人格尊严的因素都可作为此条规定的正当理由,从而赋予肖像权人以宽泛的解除权。⑤参见廖焕国:《论人格权许可使用合同的法定解除——兼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第八百零二、八百零三条》,《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8 期。笔者认为,一旦权利人对肖像利用作出许可,即表明其对肖像权中所蕴含的经济利益作出了让渡,其即不应再以任何经济上的理由充当正当事由,通过解除合同的手段剥夺使用者本可获得的经济利益。当然,若使用者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肖像权人可行使合同解除权,只不过此时的请求权基础系《民法典》第563 条。此外,因肖像权具有人格性与财产性双重属性,肖像权人对自身肖像所具有的精神利益不能作出任何让渡,肖像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其背后彰显了法律对人格尊严与人格自由的保护。因此,当肖像使用权人的行为存在侮辱肖像权人之人格、侵犯权利人的人格尊严的情形时,权利人可主张解除合同。至于单纯的肖像权人自身观念的变化是否足以充任此处的正当事由,因此种解释方案无疑使“正当事由解除权”向“任意解除权”靠拢,故在对此类解除作出扩大解释时需更加慎重。
对此,可首先考究任意解除权设定的立法目的。任意解除权广泛存在于服务合同(委托合同、承揽合同、运输合同)领域,之所以在此类合同中赋予委托人以任意解除权,是因为以委托合同为代表的为之债务中,合同的信赖被大大地主观化了,此类合同既以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处理事务为中心,合同的维系就极其依赖双方的互相信赖。和与之债务中人对物的信赖可以客观化不同,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是极为主观的,法律强令委托人继续维系合同的效力,有违此类合同的宗旨。肖像权许可使用合同系与人格利益相关联的合同,人的因素在此类合同中占有较高比重,故赋予肖像权人以宽泛的合同解除权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况且,《民法典》第1022 条第2 款规定了在可归责于肖像权人的事由时使用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若将该条的正当理由严格限定在侵犯肖像权人人格尊严的事由之内,因肖像权人此时不具备可归责性,故不具有产生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以承担履行利益意义上的违约责任为代价赋予肖像权人宽泛解除合同的权利,能够实现肖像权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对肖像权人行使解除权形成一定制约,将因正当事由的宽泛解释而对合同稳定性的破坏降至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