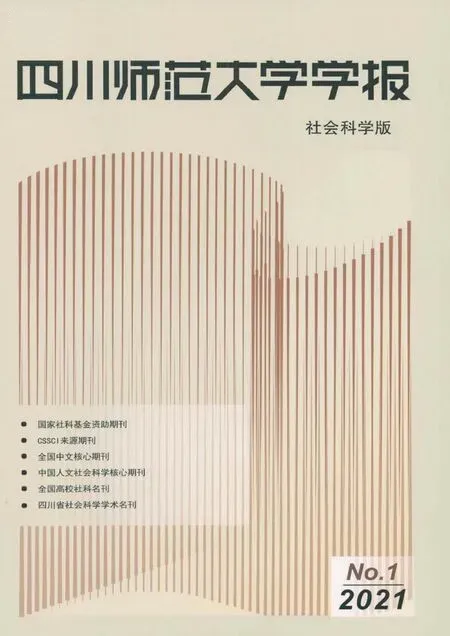《左传》的占断式叙述及其文化史意义
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序》以为“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这个“巫”字,唐代杨士勋疏解为“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①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61页。。其中关键词是“预言”二字,所谓“预言”乃是“立言于前,有征于后”的叙述方式,因此后世遂有《左传》预言研究之目。今人的《左传》预言研究,或则对《左传》中的预言进行分类研究,如张高评把《左传》中预言分为梦寐、卜筮、形相、禨祥、歌谣五类,分析其预示意义②张高评《〈左传〉预言之基型与作用》,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60页。;或则通过“对预言及筮占之辞的分析”去推测《左传》的“成书时代”③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页。,徐中舒、朱东润、杨伯峻、胡念贻、蒋立甫等学者是也;或则对《左传》预言进行文学研究,如潘万木、黄永林分析了《左传》预言的成因及文学作用④潘万木、黄永林《〈左传〉之预言叙述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83-88页。;另外,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第七章《预言》⑤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251页。,也是此类研究。尽管他们对《左传》预言进行了各种分类,但终觉略“隔”,略欠“了解之同情”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版,第279页。。“预言”一词似乎是后起的词汇,翻检各大辞书,未见“预言”的先秦用例,这说明以“预言”来描述《左传》的这种叙述模式,与先秦情势不甚契合。先秦人据象而断,只会是占卜,而不会是预言。预言有较大的随意性,肆口而出,可以汗漫无归,不符合先秦人面对占卜的神圣感。而“占断”一词是从当下预测未来,加上占验叙述,截取一段历史时间,寻找的是历史事件的意义,用“占断”更契合《左传》的历史形态。春秋时期占卜思维非常普遍,一切事、象均可为卜,《国语·吴语》中越大夫文种说“臣尝卜于天……天占既兆,人事又见,我蔑卜筮矣”①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54-555页。,即是此类现象的表征之一。《左传》写作于先秦,受到那个时代卜辞筮辞思维的熏染是必然与当然之事,其历史叙事的判断思维与卜辞筮辞的占卜思维混溶难分必是事实。因此,本文更“预言”为“占断”,以更具了解同情的“占断式叙述”来命名《左传》中的此类叙述方式,力求以更贴近历史现场与本相的方式去叙述历史。
一 《左传》占断式叙述的形式构成
《左传》中以占断为主干的叙述形式,应该承自殷商卜辞。殷商时代龟卜频繁,在学者们看来“几于无事不卜,无日不卜”②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26页。。这些频繁的卜事需要频繁地记录,于是形成惯用的卜辞格式。张光直先生把甲骨卜辞分为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③张光直《商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6页。,叙辞通常记录举行占卜的日期和贞人名,命辞是所卜事项,占辞是占卜结果,验辞是事后对占辞应验与否的补叙。如:
十五年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 吾见赤黑之祲,非祭祥也,丧氛也。其在莅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3版,第1369页。
可以看出,《左传》中的叙事模式与卜辞格式在结构上非常相似:“十五年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可拟于叙辞;“禘之日,其有咎乎”可拟于命辞;“吾见赤黑之祲,非祭祥也,丧氛也。其在莅事乎”可拟于占辞;“二月癸酉,禘。叔弓莅事,籥入而卒”可拟于验辞。这属于简短的占断式叙述。
占断式叙述四分结构有比较复杂的情况,例如庄公三十二年开始叙述的虢国之亡的占断,与卜辞相比,“秋七月,有神降于莘”相当于叙辞,惠王问“是何故也”相当于命辞,内史过、史嚚(庄公三十二年)、舟之侨(闵公二年)、晋卜偃(僖公二年)等人的“虢必亡矣”的分析相当于占辞,僖公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⑦以上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51、252、262、283、311页。相当于验辞。此种占断,结构与卜辞类似,可视为卜辞结构的放大。
另外一种是三分结构,在《左传》中很常见。有学者作了一些三分模式的总结,如郑晓峰说《左传》筮象龟兆之辞的叙述模式是“叙述兆筮之象+据颂解兆或据筮占对象的身、位、时、事+判断吉凶”⑧郑晓峰《占卜异象与〈左传〉叙事的预言式结构》,《学术交流》2017年第1期,第152页。,杨金波说《左传》以“初”字提领的以事释经的模式是“初+时间+结果”⑨杨金波《〈左传〉事始:以“初”为核心》,《北方论丛》2017年第4期,第49页。。其实以“初”提领的叙事,在《左传》中大多以之补叙事件缘由,有时也兼叙结果,相对于占断式叙述,形式上尚不完备。事实上,《左传》中的一些占断式叙述的命辞(贞问)部分常常被隐匿,被作史者的作史之志所替代,就形成了《左传》的三分结构。如“仲尼”称叔向为“古之遗直”,但叔向的羊舌氏被灭族,这如何解释?昭公二十八年就以“初”10以上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67、1492页。字提领,补叙了作者认为的理由,这种解释体现了作史之志,它替代了命辞的功能。所以,类比于卜辞,《左传》的占断式叙述,还存留有可比拟于卜辞的叙辞、占辞、验辞三部分。
当然,如果机械地以卜辞模式规范占断式叙述,也不合适。《左传》与卜辞文字繁简悬殊,其开始部分包含编年、常规事务的叙述、灾异等,但只有以占象为起点,才会形成占断式叙述。占辞部分加上了占断推理,并借以表达史识史意,甚至进行伦理论证,故占辞部分扩大,变成了占断。而占验部分则成为史意的落实,甚至是证明。所以,从内容角度观察,《左传》占断式叙述由占象、占断、占验三部分构成。
二 《左传》占断式叙述的基本内容
占象是《左传》占断式叙述的起点。《左传》有观“衅”而动的叙述,如昭公七年公孙皙曰“受服而退,俟衅而动”,此“衅”与“象”同义;襄公九年士弱说“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大火星)”,以星象为衅。宣公十二年随会说“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庄公十年曹刿说“视其辙乱,望其旗靡”①以上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82、964、722、183页。,“辙乱”“旗靡”是衅,当然也可称为“象”,这都说明“衅”与“象”通。故“观衅而动”等于“观象而动”,是以《左传》的占断式叙述,以“象”为始。
(一)占象
《左传》倾向于以异常的、有占断必要的现象作为叙述的起始。《公羊传》说“常事不书”②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15页。,《左传》说“礼不卜常祀”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86页。,这是以异象作为叙述起始的思想基础。当然还需要解释的是,此处的“异象”是指《左传》觉得“异”,觉得充满意义的象。根据占断的应验方式、应验程度推断,《左传》隐约体现出了“天人”二分思维,故把占象分为自然异象和人事异象两类。
1.自然异象
(1)星象。如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梓慎占断为宋、卫、陈、郑皆火,时间是丙子或壬午;昭公十八年“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④以上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90、1395页。,占卜应验。
(2)地象。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秦获晋侯以归”。⑤以上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47、356页。占卜应验。
(3)动物异象。庄公十四年:“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96页。这是解释性的占象,已经事先应验。
2.人事异象
昭公六年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77页。士文伯根据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隐藏着一种“争辟”,即争夺之象,占断为郑必火。人事异象和天象都预测了昭公十八年郑大火,从卜测的角度可谓殊途同归。
人事异象众多,大体有如下几种。
(1)名字。闵公元年卜偃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59页。《左传》强调名字源自于天,个别名字在天意左右下出现确定的预示意义,就有了“异象”意味。如宣公三年郑文公之妾燕姞,梦天使与己兰,后生穆公,取名为兰。“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 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75页。穆公与兰始终,这接近于一个命运神话。
(2)面相。面相天生,也有“天定”意味。文公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杨伯峻注:“谷,文伯;难,惠叔。”文公十四年:“鲁人立文伯……文伯卒,立惠叔。”文公十五年惠叔“取而殡之”10以上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510、605-606、610页。,应验。
(3)梦。《左传》有梦占26例,如果把申生显灵事件也视为“梦”(僖公十五年秦伯称秦胜晋是“晋之妖梦是践”),则为27条。除僖公三十一年卫成公梦康叔说“相夺予享”,无关于占验以外,其他的梦都是应验的,而且大多融入了占断式叙述之中。如成公十六年:“吕锜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共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锜,中项,伏弢。”①以上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57、487、886-887页。占象是射月,占断是“必楚王也”,“亦必死矣”,均验。
(4)龟卜。龟卜是春秋时期的常规行为,似乎称不上“异象”,但许多占断式叙述皆由卜而发,故必须予以考察。据学者统计,《左传》记载龟卜57例②刘玉建《中国古代龟卜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381页。,但有的卜例仅叙述了龟卜这一现象,如卜郊类,属于礼仪叙述,没有占断和占验环节,故不能称之为占断式叙述。真正以龟卜为核心,形成占断式叙述的有27例。如昭公十七年:“吴伐楚。阳匄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92页。改卜以后大获全胜,说明初次占卜也是应验的。
(5)筮占。筮占是后起占卜法,虽然算不得“异象”,但《左传》叙史,有时会以筮占起收,故亦需考察。《左传》与周易相关的筮占共19例,其中形成占断式叙述的有15例。宣公七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689-690页。,“欲为卿”是占象,以丰卦上六爻辞“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⑤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8页。作为占断依据,亦卦亦喻,占断在不经意之间就完成了。“间一岁,郑人杀之”是占验。
(6)行为异常。《韩非子·解老》云:“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⑥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8页。则意想具化之视听言动,更可称为象。昭公二十一年:“于是叔辄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将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辄卒。”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427页。这是据人的异常行为作的占断,应验。
当然,《左传》的占断式叙述中的起始异象还包括雷电、望氛、童谣等,此处不再罗列分析。
(二)占断
《左传》中有一种没有占断推理而直接叙述结果的占断,这种没有占断过程的卜测,可视为“以天为断”。如襄公三十年:“或叫于宋大庙,曰:‘嘻嘻! 出出!’鸟鸣于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灾。”⑧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174页。人声和鸟鸣都作“嘻嘻”,这是火灾发生的征兆,征兆和事件之间的关系似乎不需要解释,似乎是“天意”为之。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信“天命”,定公元年晋女叔宽说“天之所坏,不可支也”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524页。,认为天意不可改变,即是此类认知的表征。
《左传》一些占断是以德为断的。如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释“黄裳元吉”,以为“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37页。。《左传》中很多占断式叙述,尤其是筮占类,都是以德为断的。
还有以礼为断者,郭沫若说,“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1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60页。。德之践行便为“礼”,故而以德为断又引申出以礼为断。定公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同年“夏五月壬申,公薨”,哀公七年“师宵掠,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12以上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600-1601、1601、1643页。,是其应验,子贡的判断乃是据礼而断。
《左传》中还有以志为断的,如襄公二十七年赵武请郑七子赋诗言志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134页。。论者已多,不再赘叙。
(三)占验
《左传》中绝大多数占断是应验的。可以通过占断的不同应验方式,探测作者想维护、证明什么。以龟卜为例,昭公二十五年臧会以欺骗的方法成了臧氏的继承人,并说“偻句不余欺也”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468页。,连欺骗也应验,说明龟卜非常准确。但昭公五年吴蹶由说“城濮之兆,其报在邲”,杨伯峻注:“城濮晋、楚之战,楚卜吉,而实败,则此吉兆应在邲之战胜。”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72页。也就是说,实际上存在不验的龟卜,只是因为解释或选择,而导致龟卜全部应验,这源于《左传》作者对“天”的坚定信仰。龟卜能够传达天命,龟卜的应验,也是“天意”的实现。《左传》中的天意实现方式有两种,直接的和间接的;天人关系有两种:“天赞”、“天祸”。“天赞”的直接方式是天佑,如“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从年谷和熟中见天意。“天赞”的间接方式是用不好的结果给予善意的警示,如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晋败,士贞子认为战败是“天或者大警晋也”。“天祸”的直接方式是把人祸归结为天祸,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书》说“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即是如此。“天祸”的间接方式是不符合道义的行为暂时取得了好结果,但最终“天意”回归。僖公二年虢公败戎于桑田,卜偃说“虢必亡矣。亡下阳不惧,而又有功,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不可以五稔”③以上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15、748、861、283-284页。,僖公五年晋灭虢。“天祸”的间接方式之所以曲折,乃是《左传》作者试图用文化解释一些看起来不合理的现象,通过天意回归的方式,把“德”“礼”等原则都归结在天意之下,试图论证“德”“礼”与天意一样,终将实现。更深层的意蕴是:《左传》作者透露出对文化终极的信任。
从总体上审察《左传》占断式叙述的占验,呈现出这样的模式:“以天为断”类全部应验,大多不需要解释,而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德类、礼类的占断,有的应验,有的不应验,需要解释。其中的原因,在于《左传》作者笃信天命而又倡言道德的思想二维结构。
三 《左传》占断式叙述的文化史意义
中国的文化起源于巫史,据《尚书·吕刑》和《国语·楚语》,巫史参与了号为“绝地天通”的政治、文化活动,而这一活动所形成的政治文化模式,延续到了殷商时期。陈梦家指出:“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④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第535页。王借助神的名义来治理国家,占卜应验了,可以制造王者魅力⑤吉德炜《中国正史之渊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7-128页。,意味着人间的一切都是神灵的旨意,这样就能维护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但一旦稳定的政治结构形成,王者占卜的记录可以被篡改,形成甲骨文“正史”,而叩问神意的占卜遂流于例行公事,后来更是被礼仪取代,占卜于王族的意义下降了。李学勤先生说:“西周卜辞的格式比商代简略得多。殷墟甲骨的刻辞,一般分为署辞、兆辞、前辞、贞辞、占辞、验辞等项。西周甲骨只见有前辞、贞辞和占辞,而且大多数只有贞辞。”⑥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84页。比较殷商卜辞,西周占卜不记验辞了,因为“按照周代礼法,作为国宝的宝龟,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权收藏”⑦刘玉建《中国古代龟卜文化》,第21页。,如果龟卜不灵验,则隐藏着动摇等级的风险。不记占验,说明稳定的政治结构形成以后,占卜的地位下降了。
周代不仅龟卜不记占验,而且有禁绝巫言的情况,据《墨子·号令》“无(巫)与望气妄为不善言,惊恐民,断勿赦”⑧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08页。,《礼记·王制》“执左道以乱政,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4页。,政治与巫言有对立的时候。置身于这个背景,再来审视《左传》的占断式叙述,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左传》占断式叙述的文化史意义。
首先,《左传》的占断式叙述保存了一些早期的个人占断。卜辞属集体创作,在观兆成辞的过程中“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10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75页。,而卜筮时“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11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5页。,分工很细,卜辞体现了集体的意图。而《左传》中的占断多是个人性的,如襄公二十八年梓慎预言“今兹宋、郑其饥乎?”后文裨灶预言“周王及楚子皆将死”,杜预注:“俱论岁星过次,梓慎则曰宋、郑饥,裨灶则曰周楚王死,传故备举,以示卜占惟人所在。”①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98、1999页。同在一年,同见岁星超辰,但梓慎和裨灶的星野划分却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所以说“卜占惟人所在”,这说明占断是个人的。高亨先生指出,《周易》卦爻辞是“筮人将其筮事记录,选择其中之奇中或屡中者,分别移写于筮书六十四卦卦爻之下,以为来时之借鉴,逐渐积累,遂成《周易》卦爻辞之一部分矣”②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筮人的文化成果保存为《周易》卦爻辞,由此可以反观《左传》对文化保存的贡献。这些个人占断如果《左传》不予保存,就有遗失的可能,我们也就不能在今日见到早期语辞工作者的这些个人性的作品了,而这些早期语辞工作者的作品,具有开文脉之先的意义。
其次,战国史家选取占断进入《左传》,并以史家思维予以组织,实质上变成了史家对文化的整理。如庄公二十二年敬仲筮其前途,遇《观》之《否》,观卦六四爻变,占断为:
“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 风行而着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 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22-224页。
这则占辞分占断语和占断推理两部分,开始至“在其子孙”是占断语,其余是占断推理。周史要从《观》卦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推导出陈完子孙将在齐国代陈有国。在推理过程中,周史解释了“光”“观”“材”,释“光”为“远而自他有耀者”,而于“观”一字,周史通过“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推断出“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观光”是一种战国礼节,杨伯峻注:“‘观’读为襄二十九年传‘请观于周乐’、昭二年传‘观书于大史氏’之‘观’,《仪礼·聘礼》有请观之举,谓使者聘于他国,亦欲请观其国之光也。”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23页。这可能是周史据以展开联想的依据。周史据《观》卦卦辞联想到“观光”之礼,又联想到贵宾受到国王隆重接待的礼节“庭实旅百”(据《晋语四》,重耳到楚国,楚王就待之以“九献,庭实旅百”⑤徐元诰《国语集解》,第331页。),最终断定陈氏后人必将昌大于外;“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亦是同样的意思。对“材”的解释则颇有意味:“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个“故曰”的逻辑非常婉曲,似乎是说一个有才之人在祖先道德光芒的庇护下,于是可以居于他国之土。同时,周史又用《易》象推理来证明“代陈有国”,尚秉和认为,“遇卦之坤为陈国,之卦之坤为异国,而之卦有乾,乾为大为君,故知将代陈有国”。尚氏用《易》象推理,把这则筮占解释得非常圆融,但周史是否如尚氏所描述的那么精于《易》象,且战国《易》象是否如尚氏所谓的“巽为齐,故为姜,犹震为周”,也不得而知,但毕竟尚氏为我们清理了一条《易》象联结的路径。“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这句话从语词角度不太好理解,尚氏注为“巽变乾,故曰风为天。在坤上,故曰于土上。遇卦三五,之卦二四,皆互艮,故曰山;巽为木,故曰材。之卦乾在上,故曰照之以天光。乾为王,巽之乾,故有朝王之象”⑥以上见: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41页。。依照尚氏提供的知识,此段文字周史表达的是《易》象堆积,没有太遵循语词逻辑。而周史的思维模式,似乎就是围绕《观》卦六四爻辞,随意解释词语,杂乱堆积《易》象,其目的仅是设法解释占断语。
解读这则筮占,并没有发现周史有追求超越性的文化意图,但如果把这则筮占放入占断式叙述的序列中,就可以见出占断的意旨所在。庄公二十二年几乎全叙敬仲之事,核心是敬仲之德,其德首先是辞卿,是为能让,《左传》认为“卑让,德之基也”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516页。;而后陈完“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陈完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21页。而“君子”评其为“义”、“仁”。接着,又以“初”字提起了这段卜筮,补充了陈氏能兴盛于齐的天命依据,并叙述了结果:“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杨伯峻注云:“此言‘五世其昌,并于正卿’之征应”;“其后亡也,成子得政”,杨注云:“此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之征应”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224页。。另外,昭公三年晏子说“齐其为陈氏矣! 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35页。,算是这则筮占的草蛇灰线。昭公八年史赵说:“陈,颛顼之族也……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305页。史赵的说法恰可以成为这则筮占的注释,即陈氏“盛德必百世祀”可以与“光,远而自他有耀者”相关联,这个“他”,应该指的是陈氏先祖。通过史赵的解释,就能觑透史家选择这则筮占的意图,无非在于以道德之光穿透时间、照耀广远而给这则筮占赋予天命与道德的意义。
通过这则筮占的分析,可以见出早期的语辞工作者在语词选用及意象连接方面的特色,更可见出史家对占断意义的提升。史家把关注的焦点从神意转到人德,将纯粹解释占断语的卜筮,改造成为阐释个人之德的验证场;将面向贞问人的私密话语,转化成叙史的公共话语;将在巫史时期可以代表权力的文字⑤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陈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66-78页。,转化成一种叙史的工具,史家完成的是一种范式的转化。
最后,《左传》占断式叙述也含有经法、史法、文法意蕴。有学者认为“春秋笔法”一名而含三义:经法、史法、文法。“从史的发展角度看,‘春秋笔法’实经历了由经法到史法再到文法的发展过程,而文法又贯穿于经法、史法之中”⑥李洲良《春秋笔法的内涵外延与本质特征》,《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第93页。,占断式叙述应属于文法,但亦蕴经法、史法于其中。《左传》占断式叙述的经法,体现为宣扬心性之善,如襄公二十九年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成公十四年总结的“春秋五例”中,明标有“惩恶而劝善”⑦以上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168、870页。,均宣扬善心。而以德为断、以礼为断,就是善心原则的落实。《楚语》说“若民烦,可教训”⑧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84页。,教民成俗也是士人职责之一,故宣扬善心,有经世之心,深含经法用意。
占断式叙述的史法,是以顺、逆叙述历史,并确立中国史统。随武子说:“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故之?”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725页。所谓“顺逆”是指与时人认同的德、礼等伦常惯例是否相合,合则顺,不合则逆。《国语》屡言“犯顺不祥”10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65、399页。,说明“顺逆”是当时人常用的评判词,同时“顺逆”也成了史家叙史的标准与法则:“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臣从有司,惧逆之书于后也,故不敢不告”,“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1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47、146页。举一个《左传》叙“逆”的例子:隐公三年石碏谏勿立州吁,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隐公四年“春,卫州吁弑桓公而立”12以上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2、35页。,石碏的占断应验。因为州吁有“六逆”,这可以视为“逆”的应验。再看一个“顺”的例子:
秋,卫人伐邢,以报菟圃之役。于是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83页。
此段文字以卫大旱为占象,初卜以祭祀山川来祈雨,不吉;又根据宁庄子建议,以讨伐无道的邢国来缓解旱情。其占断是:历史上周朝发生饥馑,依靠讨伐无道之纣而获丰年,现在情况类似,卫国是不是可以模仿?其占验是:出兵以后就下雨了。这个占断式叙述的重要性在于:如果遵循历史原则,历史就会重复发生。饶宗颐说:“欧公谓‘正统之说始于《春秋》之作’是矣。”14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史学之正统发轫于《春秋》,而《左传》是《春秋》史学的主体,故《左传》于中国史学正统之确立的意义自不待言。
占断式叙述的文法,以文人尚奇猎趣的心理为基础,广泛捃拾,叙述其应验,为神秘事物预留空间,如僖公十六年:
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鷁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69页。
这其中的“今兹鲁多大丧”,应验于僖公十六年经文“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孙兹卒”;“明年齐有乱”应验于僖公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君将得诸侯”应验于僖公二十一年“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而不终”应验于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②以上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368、372-375、389、397页。既然据征象所作的占断全部应验,他为什么说“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呢?内史叔兴真正的用意是把“阴阳之事”和“吉凶”分隔为二,“吉凶”可问,“阴阳”不可问,想为某种神秘的本元保留空间。《左传》占断式叙述用阴阳之事、含混的卦辞等,摹拟难知的天意,刻意保留了“天意”的神秘性,为天意的延展保留了无限的可能,为后世文章的铺衍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总之,《左传》占断式叙述具有叙述的外形,实质却是一种文化论证,其要义在于占验。《左传》的作者不再依靠占断及其应验来证明氏族政权的合理性,而以叙述历史的方式,论证文化的正确性、可行性、永久性。其对经法、史统、文法的拓凿之功,彪炳千秋。由于其对文化独立意义的揭橥,经后代经史学家不断的努力,使经史之学成为我国文化的主干,洋洋大观。不可否认,《左传》思想中含有神秘成分,其选取的占象有神怪内容,其占断过程有不经之处,而且应验率奇高,似乎有鼓吹迷信的嫌疑,但其据象而断、事后应验的模式却具有实践品格,故其论证出的某些文化人文原则,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四 结语
有学者认为甲骨卜辞就是中国的正史③吉德炜《中国正史之渊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第117页。,而《左传》把卜辞的形式放大,以叙二百余年的历史,体现了史学叙述法的传承。其多叙鬼神、预言祸福虽有迷信的一面,导致了“其失也巫”的批评,但其以鬼神占验作为叙史串联的结点,却是对叙述方式的有益探索,于“巫”中亦有所得。从文化史的角度,史巫参与“绝地天通”的文化与政治活动,以贞问占验助成稳定的政治结构之后,占卜作为一种神道设教的手段,逐渐被政治放弃,在特定历史时期甚至会打压巫言。而《左传》史家又重拾这种模式,以成就其经世之心,完成了一次文化的保存、整理以及建构。其叙述模式之中,兼含经义、史统、文法,使《左传》成为经、史、文混溶的文化元典。通过研究《左传》占断式叙史法,不但能够窥探文脉根源,发现其演进的轨迹,也能从文史互通的视角,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史论开辟一条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