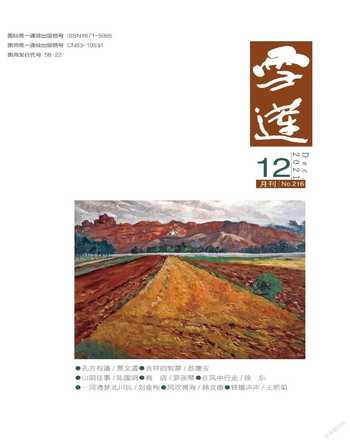孔方有道
1
在我的记忆中,西宁城里的商业市场是西门口城墙边上的水果市场。我的姥姥是个曲儿迷,每天扭动着一双半大的解放脚到麒麟公园去听尕甘姐唱《方四娘》。曲儿听罢,如果时光尚早,姥姥也会带着我们,穿过通济桥(今天的西关桥),来到西门口。那会儿西门口的城墙还未拆除,城墙根下聚集着一长溜小摊贩,最鲜艳最诱人的当属水果。架子车或骡马车上搭着硕大的圆盘筛子,里面是一堆又一堆像小山似的果子,红的苹果,黄的秋梨,白的白兰瓜,紫的葡萄,散发着迷人的香味儿。摊主手里拿着一柄牛尾拂尘,夸张地拂来拂去,是为了驱赶飞虫,主要还是招徕顾客。若有人凑到他们摊位上来,摊主马上放下拂尘提起杆秤:“几斤呐?”
姥姥在海菜铺里称完青盐,买好篦头的胡麻油,如果还有剩余的零钱,她也会给我们买几个果子。那会儿我就知道,光是黄澄澄的梨儿,就分着好多种,循化的酥梅梨,贵德的长把梨,黄南的黄梨,还有民和的吊蛋子和神不知。见我们是小孩,卖梨的小贩会把称好的梨儿用马莲草串起来,挂在我们的脖子上。临走,还会在我们每个人手里塞一个果子:“那是奶奶买给的,这是我送给的,路上吃。”
路上吃的水果不要钱。摊贩半卖半送的生意,如何能赚到钱呢?那会儿我小,还不知道薄利多销这个道理。水果就是卖个当季,那个年代没有保鲜冷藏技术,水果能大量上市,靠的就是小贩们腿勤手勤,一趟一趟往返于城乡之间,赚点辛苦钱。以前的青皮行有很多规矩,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抢季节。在某一种水果某一种蔬菜成熟时,青皮行会组织商贩大量收购,尽快出现在市场上,一是为了避免因过季而遭受损失,二是给城市居民提供新鲜便宜的蔬菜水果,末次才是为自己赚钱。这就是以前西宁古城众多的商业诚信中的一项。如果商贩们图省事,只收购一次果品在市场上卖高价,当然他也能赚到钱,但势必会造成大量的水果蔬菜烂在地里,而城市的居民因无力购买高价水果,只能望着红艳艳诱人的水果咽口水,自然也没有塞在我小手里白送的秋梨了。
2
在我幼小的认知中,我觉得西城门墙根下的自由市场就是最大的市场了。除了卖水果的,还有卖卤肉的,卖酿皮的,卖酸奶的,卖衣服鞋子的,卖车马挽具的,卖日用百货的,还有卖焦疤热洋芋的。大推车上一个红泥小火炉,一口平底大锅架在上面,里面也是堆得冒尖的烤洋芋。烤洋芋散發着迷人的香味儿,直往人的鼻子里钻,引诱着人们往前凑。市场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就连古旧破败的城墙,也因脚下的热闹喧嚣而变得活泼、朗润、明丽。因而我的姥姥,还有别的小脚老太太们,说起城墙根下的市场:“西门口上啥呀有哩,就连晒干的眼泪,都扎成把把着卖着。”——这是一句极夸张的话,晒干的眼泪不可能有,就是形容市场繁华,货物齐全。
后来我才知道,西宁城不止西门口一个市场,城里头的市场多得很。城市就是由马路、商店和住宅组成的。而且早在西汉时期,西宁古城刚刚有了雏形,紧接着就有了市场的雏形。人们要生存,总得需要生存物资。没有货币不要紧,直接就以货换货,《诗经》里都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交易,高原古城的市场上更多。我用羊羔皮换你的粮食,我有吃的了,你也有穿的了;你用多出的一张羊羔皮换来一把头,这样,铁匠有穿的了,你也可以种出更多的粮食。以货换货是一种古老的交易方式,在双方自愿的原则下进行。当然也论货物的高低贵贱,但主要看交易双方的实际需求。如果实在喜欢,用一张珍贵的旱獭皮换一颗玻璃珠子,也有可能。青海俗语“口袋里买毛”大约指的就是这种古老的交易方式。
以货换货的交易方式一直存在,到了唐宋时期,就形成了著名的茶马互市。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马法,用制羌戎。”青藏高原上的人以放牧为生,食物就以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肉吃多了不好消化,必须要喝点茶水来解腻,润肠,帮助消化。故而有“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青藏高原上不产茶叶,茶叶从遥远的南方运过来,极其珍贵。但是青藏高原盛产良马,尤其吐谷浑王国培育的“龙驹”,据说是和青海湖里的龙交配而生,具有蛟龙的特质,日行千里当然不在话下,还能在天上飞。良马在古代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没有马就没有办法开疆拓土,保家卫国。西域的龙驹正好解决了这一大难题。于是,就有机灵的商人率先背起茶叶,到青藏高原上换良马。最早的茶马互市出现了。
由于这一行利润丰厚,后来,朝廷就垄断了茶马交易。在西宁成立了“提举茶盐司”,俗称“茶马司”,由朝廷统一组织商人,统一指定茶叶,到西域来换良马。外地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进来,高原上的龙驹源源不断地运出去,茶马互市热闹非凡。西宁古城的周边,湟源的日月山脚下、湟中的多巴镇、镇海堡、以及化隆、循化的街市,都是重要的茶马互市交易点。朝廷制定了统一的交易价格,以明朝为例,那时候一匹上马可换茶叶120斤,中马70斤,下马50斤,茶叶称之为“官茶”。然而,那个年代交通落后,运输困难,商人们千辛万苦背着茶叶为官家做生意,似乎不太合算。朝廷为了鼓励商人,在完成“官茶”交易的同时,也允许携带一部分“商茶”,商茶所获的利润,自然归商家本人所有。茶马司的人在验货时,把官茶之外的茶叶叫“附茶”。久而久之,“附”成了“茯”,就是我们今天喝的“茯茶”。
3
茶马互市盛行了将近上千年,不仅解决了边疆和内地的供需问题,还开通了漫长的商贸之路。清朝末年,就有零星的内地客商进入西宁古城做生意,高原上丰富的药材和畜产品在内地大受欢迎,也使客商看到了商机,内地客商纷纷涌入西宁古城。到了民国时期,大量的山西、陕西商人入驻西宁,开商铺、设字号,几乎垄断了西宁古城大大小小的生意。本地人把这些外来做生意的商人一律称之为“客娃”,没有贬义,就是一种称呼。当时的西宁古城,有“客娃满半城”之说。
客娃们之所以能在西宁古城立住脚,是他们有一套完整且严格的商业规矩。这些出生在贫瘠土地上,生活无着的农民,跟着他们的乡亲,跟着他们的父兄,长途跋涉,历经艰辛,来到西宁古城,为的就是赚一点银钱养家糊口。同时,梦想着以后成为大财东,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在成為大财东之前首先要做相公。相公就是学徒,期限三年到五年。一般由带他过来的乡亲或父兄作保人,把他介绍进同乡开的商铺里学经商。说是学经商,却没有人教给他经商之道,他就是众人的杂役。在东家,他要给掌柜的洗衣做饭,打洗脚水,倒夜壶。还要给掌柜奶奶抱孩子,洗尿布,几乎承担所有的家务。在店铺里,他要扫灰掸尘,搬运货物,跑腿办事,一天到晚忙得脚不点地。即便这样,掌柜的指责,掌柜奶奶的呵斥,账房先生的奚落,众师兄的取笑,他都要默默地受着。没有谁认为这不公平,所有的相公都是这么过来的。在学经商之前,要先学会忍耐,学会手脚勤快,学会察言观色,学会应付解决经商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琐事和各种各样的麻烦。
磨练一段时间后,掌柜的认为可以继续栽培,这个学徒小相公就可以到店铺里支应了。当然,他只是免除了掌柜家的一部分家务,像挑水劈柴,洗衣服做饭这些活他还得干。店铺的活也一样少不了,尤其搬运货物,跑腿办事就是相公的专职。偶尔有闲暇,他可以跟着师兄们学一学接待客人。
那个年代没有“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但在他们眼中,顾客就是实实在在的衣食父母。山陕商人开设的商铺,不论大小,铺堂两边都设有长凳。客人只要一进门,便有穿长衫的伙计笑脸相迎,恭敬地请到长凳上坐下,相公学徒随即端上盖碗茶。这时候,掌柜的或长衫伙计才笑吟吟地开口。他们开门做生意,阅人无数,只须看一眼,便能大概判断出客人的身份,却绝不会因客人的身份不同而有所亲疏。若是城里人,便称呼先生、老先生、太太、老太太、夫人、小姐,就连小孩子也要称一声“学生哥”。进门的顾客若是乡下人,长衫伙计更加热情,帮着卸下肩上的褡裢,提起牛尾掸子拍去尘土,再端上茶水,这才开口问道:“姑舅哥,看需要点啥哩?”一边殷勤地帮姑舅哥点上旱烟。
待顾客选好东西,他们极其麻利地包装捆扎好,扯下吊在柜台上方的纸绳,十字花绑结实,递到顾客手上。顾客出门,还要送一点小礼物。若是男顾客,送一点烟丝,送一盒火柴;若是女顾客,则送一绺棉线,几枚钢针。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物件,却极易讨得顾客的欢心,认准他们家店铺,下回还来。
相公们若是跟着师兄学会了接待顾客,差不多就可以留在店铺了。工作还是原来的工作,接着扛运货物,打扫卫生,烧水做饭,跑腿办事,也没有人专门讲授生意经。不过,留在店铺的时间多了,可以偷着学一点手艺,就看你用心不用心了。比如,顾客少时,可以在柜台上练习一会儿打算盘,可以练习数钱,用绳子穿麻钱的技巧。还可以学习点货、记账等知识。若能认得几个字,那更好了,可以帮着掌柜的整理账目,写家信,写标签等等,可以学到更多的经商之道了。
经过这样一番严苛持久的磨练,相公学徒们能学出来的也是少之又少。因为做生意还要看天赋,要有经商才能,还要有机遇,还要讲个财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一切都充满了变数,人人都活得极其艰难,山陕商人在西宁古城做生意,更是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虽然有“客娃满半城”之说,但真正发了财的,其实也没几个。
就算他们学成了,有了自己的店铺,做生意也发了财,也是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唯恐哪里出了纰漏,使生意打了水漂。初一十五点灯上香拜菩萨是必做的功课。关老爷更是供奉在店铺的高堂,早晚跪拜。因为关老爷是武财神,关老爷还是山西蒲州人,“君向君,民向民,关老爷向着蒲州人”,有了关老爷的护佑加持,山陕客娃们发不发财心里都感到踏实。除了拜神仙,店铺里还有许多规矩。最主要的规矩,就是不能怠慢顾客。不管人家买不买,都要笑脸相迎,好话相送。顾客就是衣食父母,如果对顾客爱答不理,出言不逊,或看人下菜碟,那就是赶跑了衣食父母,打散了买卖,掌柜的一定不肯答应。轻则训斥责打,重则辞退。还有多如牛毛的禁忌,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要用暗语,什么话要隐晦着说,都要熟练掌握,不能违犯。就连扫地,也要从门外往里扫,据说这样扫可以敛财。如果不小心扫错了,把垃圾扫到了门外,那就是把财运扫出去了,掌柜的一定会气急败坏,定罚不饶。
因而,那个年代的山陕商人,不论生意做得多么大,都怀有一颗敬畏的心,保持着原先的纯真与朴素。即便有钱,生活也是一日三餐简单饭食,维持温饱而已。若是坐在店铺里撑门面,或是外出谈生意,或许有一两身好一点的衣服,其余绝不讲究。那个年代形容发了财的山陕商人,有四大派头、四小派头之说。派头大的镶金牙、戴戒指、穿皮鞋、拄拐棍。派头小的戴墨镜、看三国、吃丸药、喝开水。喝开水算什么派头?在现在看来就是一个笑话。但在当时,能坐下来喝一缸子开水的,说明他的生意已经很稳定了,家底也殷实了,他心里不焦虑,他才能悠闲地一边喝开水一边看三国。
4
山陕商人能在西宁古城站稳脚跟做生意,除了服务态度好,对顾客讲究诚信,最主要的,是人家的店铺里货源丰富,品种齐全,而且价格公道。由于山陕商人的到来,大批的外地物资也随之进入西宁古城。很多新奇好用又实惠的物品,使西宁人大开眼界。如各种结实、轻便又好看的布料;如亮晶晶的糖果;还有散发着迷人香味儿的雪花膏和香胰子,比西宁本地人用猪胰子砸出来的枣儿胰子不知好用多少倍。还有男人们喜欢的礼帽、墨镜和皮鞋,西宁人称之为“洋革”。那洋革就是洋啊,小巧轻便,黑皮鞋面锃亮,能把苍蝇滑个跟头。穿在脚上要多精神有多精神。再看看自己用牛皮缝的“络鞮”,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山陕商人的铺子里,好物件太多啦。
那么,这些货物是从哪儿来的呢?是长途跋涉,靠着肩扛手提,骡马运输,翻山越岭贩运过来的。随着山陕商人的进驻,西宁古城随之兴起一个行业——过载行。主要负责运输商品,调剂市场,同时也为商家转运银钱。由此衍生出来的镖局走镖,歇家待客,行会约定等等,这里不再赘述。
过载行运输也有很多规矩讲究,他们所要运输的货物主要有两类:上货和下货。上货就是从内地运进来的以工业品和手工产品为主的小商品和小百货。下货就是从高原上运送出去的,以畜牧产品和药材为主的原材料。西宁城里主要售卖上货,西宁人感到很新奇。其实,我们的下货(是往下走的意思)运送到内地、沿海地区,也同样大受欢迎。西宁的紫羔皮、西宁大白毛,还有麝香、大黄、发菜等等,在国际市场上都是大品牌,奇货难求。
运送到西宁城里的货,西宁人也按区域分为好多种。从天津、汉口、上海等地方来的货物,一律称之为“洋货”。除了把皮鞋叫洋革,還把火柴叫洋火,蜡烛叫洋蜡,其余如洋线、洋布、洋糖儿、洋袜子、洋胰子、洋脸盆、洋铁壶……日用百货多数从这些地方运过来,无一例外要加个“洋”。从广东、广西一带运来的货物,则叫作“番货”,前面要加个“番”。番茄、番瓜、番纸、番布。产品原产地叫番邦。那个年代西宁城里没有外地水果,如果市场上偶然出现桔子、石榴之类的水果,人们就会说:“番邦里来下的。”意思是极其罕见又珍贵,一般人根本买不起。
而从印度、尼泊尔、英国等地转道西藏运送过来的货物,就叫藏货。藏货主要有佛经、念珠、香水、香料、头油、氆氇、呢料、布料等等,香料一律叫藏香。青海人在那个年代非常喜欢的布料毛蓝布,就叫藏蓝。还有一种带斜纹的布料,叫藏斜。藏斜精密厚实,幅面也宽,属于比较上等的衣料。
藏货运进来也不容易,那年月赶着骆驼从拉萨进一趟货,至少要三个月时间。要翻越风雪茫茫的唐古拉山,还要穿过数千里的高山草甸、戈壁沙漠,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因而,藏货在西宁市场上无论大小,都极其珍贵。后来,藏货泛指一切高级的货物,人们把自己心爱的、秘不示人的东西也叫藏货。就连在学校门口卖炒豌豆的小贩,也称自己的豌豆是“藏豆儿”,以示珍贵。
当然西宁城里的商品不止洋货、番货和藏货,还有从全国各地运送过来的商品。苏州、杭州的绸缎;湖南、四川的茶叶;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安徽的纸张;宁夏的大米;陕西的土布;而开在大十字的庆盛西店,则专门经营京货,所有货物都从北京运来,带着皇族的气息与派头。从邻近的兰州拉运过来的各种瓜果,桃子,苹果,冬果梨,还有香瓜,白兰瓜,甜蜜蜜地堆满了一条街。水果浓烈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香得能让人飞起来。所以我自幼认为,青皮行是七十二行中最温情最可爱的一行。
5
过载行按今天的话说,应该是物流业。说物流也不尽准确,应该是物流兼批发。过载行的人到原产地购买商品,拉运到西宁城里,再贩卖给各个商铺。从事过载行的人基本上是以家族或村庄为单位,为的是互相信任,互相照应。一个家族或一个村庄养几匹骡马几峰骆驼,长途贩运货物,这样的人家有一个专用的名字,叫脚户。现代社会,运输业相当发达,公路铁路航空的发展,脚户这个行业早已不存在了,但由此衍生出一个词:站大脚,是对卖苦力打短工的人一种谑称。可见,古代的脚户是一种非常艰辛又劳苦的职业。
脚户们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自不必说,但既然从事了这个行业,就要遵守这个行业的行规。毕竟,过载行的利润也是非常可观的。
西宁古城里第一家从事过载行业的店叫福盛店,他们家脚户多,分散到全国各地,所以他们家洋货番货藏货都有,品种齐全,货源丰富。每天早晨天不亮,福盛店即开门做生意。各个商号、店铺的经理、掌柜们带着伙计纷至沓来,为自己的店铺补充货源。
值得说明一下的是,西宁古城虽然山陕商人众多,商业发达,却没有统一的度量衡,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成立了“青海度量衡检定所”,在所长顾怀玺的努力下,才在全省统一了度量衡。
不过,这并不耽误过载行做生意。他们自有一套商业计量法。像茶叶、瓷器、日用百货、车马挽具都有固定的包装,按件计算即可。蔬菜瓜果等货物则按大小优劣搭配好,以堆计数。每一堆都很均匀,经理们挑好后,随即招呼自己的相公伙计往车上装。而像粮食、干果,精细一点的水果,则按斗和升计算。以升为例,升有大有小,可以根据顾客购买的数量用大升或小升。但在计量时,过载行还有一种充满人情味的计量方式,即平升、膘升和高升。比如顾客买的是本地产的沙果、楸子、花檎、梨儿之类的水果,过载行的人就用高升计量。就是把升子装满后,还要不断地往上摞,直到把升子装得高高的冒尖,像金字塔一样,才倒进顾客准备好的牛毛口袋里。这种计量方式叫高升。一升的数量,实际上给了两升。如果是干果,像花生、瓜子儿、核桃等等,则用膘升计量。就是在升子装满后,再高出升子一部分。也不多高,高出一寸即可。也是按一升计算,但比一升要高出许多,那高出的一寸就是一升的膘,所以叫膘升。
不过,像粮食、大米、黄米、桂圆这些货物比较金贵,就不敢用高升或膘升了,只能用平升。平升就是装得和升子的口一样平。过载行的人在装平升时,准备一块薄木片,装好一升,用薄木片在升口上迅速刮一下,多余的粮食或干果就刮下去了,绝不多装。这种计量方式叫平升。
不论平升、膘升、还是高升,都是按一升的价钱计算。我不知道那会儿一升水果是多少银钱,但这种灵活的交易方式,一方面彰显着商业诚信,一方面也是为了薄利多销。瓜果蔬菜就卖个新鲜,需要过载行一趟赶一趟地拉运,这样才能在当季的水果和蔬菜中赚一点利润。用高升计量,买主高兴,卖主也高兴,因为他的货很快就出手了,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
过载行经营,所有的货物都讲究周转快,出手快,绝不积压。积压货物就等于积压本钱,是过载行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但有一件货物绝对要积压,并且要积压三年以上,才从库房中搬出来销售。那就是高原上人人需要的茶叶,不论是湖南益阳的砖茶,还是云南的窝窝茶,抑或是四川的松潘茶,从茶叶产地拉回来后,码在特制的茶库里密封。经过三年以上的发酵,茶叶在茶菌的作用下,会生出一种金黄色的霉斑,像菊花一样,特别漂亮,就叫“金花”。长了金花的茶,才算是纯正的好茶,喝起来茶味更香。才可以拆开包装销售。过载行固然以运输为主,但他们还是非常注重货物的品质,这也是那个年代的商业诚信。
过载行不但有储存茶叶的茶库,他们还有自己的房舍、旅店。这是给远道而来进货的店主们准备的。如果某个店铺需要一批什么货,而过载行还没有运来,或者货物还在路上,需要等几天。过载行的人绝不会说:“我家没有,你到别家去看看。”他们会热情地把远道而来的店铺掌柜挽留下来,让到窗明几净的客房里,端茶递水,极尽殷勤。客商的骡子和马匹也牵到牲口棚里,铡草饮水,悉心照料。到了晚上,还有小相公伙计来烧炕铺被,绝不让客人受一点委屈。一日三餐也是送到房中,关怀备至。直到货物运来,过载行的人称量好后,给他装载停当,又带足路上的干粮,这才启程回去。在客店的住宿、吃饭一律免费,绝不向顾客讨要一文钱。那个时候过载行的店门口大多有这样一副对联:主因信实千金可托,客为公平万里来投。
6
过载行对待买主的态度,只能算一种经商之道。而在经营中必须恪守的诚信,是在银钱上。不论是过载行的掌柜的,还是商号店铺的经理,还是挑担摆摊的小贩,做生意就要和银钱打交道。进货的钱,周转的钱,手里时刻离不开钱。当然,也时时有钱不凑手的情况。于是,那个年代做生意,是允许赊账的。
各个买卖行都有自己赊账的规矩。商铺字号的经理到过载行去进货,本钱不多的先付三分之一的货款,本钱充足的付三分之二的货款,绝大多数都是先付一半的货款,没有一次付清的。过载行也认可这个规矩,一般都记在账上。账也分好多种,最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劈柴账,一种是折页账。劈柴账是一种平面的小木条,就如古代的书简一样,只不过,劈柴账不用串起来,随意插在木桶里。折页账是一种像折扇一样的纸质账本。过载行把数量少的,或钱数不多的账记在劈柴账上;数量大的,或者货物比较精细贵重的,记在折页账上。
同样,各个商号店铺也有劈柴账和折页账。那会儿做生意,普遍都赊销。不像现在,所有的店铺都当面算清,两不相欠。即便开在乡村里熟人之间的小超市或小菜铺,也要贴上“本店小本经营,概不赊账”的字条,把没钱的顾客无情地擋在外面。
回溯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的西宁古城,那会儿买东西都是赊欠的。进到店铺里面,有钱没钱不要紧,只要你需要的东西有货,掌柜的即刻拿给你。有时候,还会打发小伙计帮你送到家里。货款记到账上。若是你买的东西比较小,不值啥钱,人家连记都不记。
不过,买东西的人一定会记得,到时候给人家把钱送过去。人家做生意是为了赚钱,不能赔本。
买了针头线脑小物件的人,只要手里有钱,马上就给店铺送过去,不会赖账。从过载行批发了大宗物价的商号、铺堂更不会赖账。不过,他们还钱是有固定的日子,那就是每个月的二十一号,称为标期。标期是专门还账的日期,到了这一天,各个店铺的经理或掌柜的带着银钱,领着相公伙计,到过载行算还欠款。记在劈柴账上的,过载行的伙计当面将劈柴账挑出来,扔进火炉烧掉。记在折页账上的,也当着顾客的面将钱款数额抹去,表示账已还清。
那么,为什么每月的二十一号是标期呢?实际上“标期”应当是“镖期”。那个年月有镖局走镖,专门护送银钱,银钱到达的日期叫做镖期。各个地方的镖期都不相同,到达西宁的时间是每个月的二十一号。所以,这一天是西宁古城的镖期。也是归还欠款的日期。
如果有的店铺实在经营困难,在标期这一天还不上欠款,店铺掌柜的也要到过载行知会一声,请求延长一个标期。过载行的也绝无二话,痛快答应。
但是,决不能欠债不还。诚实守信,一诺千金,是当时商贸行业中最重要的信条,人人都遵守,人人都维护。如果不遵守这个信条,那么,他马上就会失去信用,为同行人所不齿,没有人会出手相帮,在商界将无立锥之地。“自古做人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在古代没有太多的戒律、条款约束,人们就靠自觉自愿的诚实守信经商,把西宁古城的商业贸易维持下去。
7
过载行、商铺、字号、歇家、脚户、镖局都有各自的行业规矩和商业信用,用诚实守信,公平交易的原则维护着西宁古城的商业繁荣。民间的小作坊、小手工业者、小商贩,以至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之流,也有自己主动恪守的商业诚信。有的是在贸易过程中买家和卖家约定俗成的,也有的是卖家单方面遵守的。比如,以前西宁城里面向劳苦大众的早餐杂碎汤,便宜又实惠。天不亮就挂起一盏红灯笼开门营业,那些早起的工匠,赶路的脚户,进城出城的农民,都循着杂碎汤的香味涌向店里。一进门,掌柜的二话不说,先舀一碗热汤端给食客,这叫“挂嗓”。买不买早餐不要紧,这碗热汤是免费的,先让食客润一下嗓子。喝下这碗鲜美又热乎的羊杂汤,既暖了身子,又暖了心,食客们十有八九会掏钱再喝一大碗放了肉的杂碎汤。杂碎店的老板就用一碗免费的热汤,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食客。
在杂碎店吃饱喝足,擦着脑门上的油汗,心满意足离去时,杂碎店门口红灯笼照映着这样一副对联:大羊头小羊头头头有肉,羊小肠羊肥肠肠肠不断。横批是:将碗抓满。就是这样浅显直白的语言,将杂碎店的经营理念,和对底层平民的关爱与体恤表达得淋漓尽致。
其实,开杂碎店的也好,卖其他吃食的也好,老板本人也是穷人,本小利薄,收入甚微。用自己的手艺加上勤快赚几个辛苦钱而已。即便这样,他们也绝不马虎,更不会投机取巧,而是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做好自己的小本生意,体现着对顾客的尊重,也是对自己手艺的尊重。在以前,西宁古城寒冷的冬夜里,常常会听到隐隐传来的吆喝声:“热冬果哎——”那是卖煮冬果梨的小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招揽生意。买他的冬果梨,必定是一个干干净净煮得绵软的梨子,配一颗大红枣,再加一大勺甘甜的梨汤。倘若红枣不够了,或者炉子里的煤火不旺了,他宁愿挑着担子回去,也不会把剩下的梨儿便宜处理了。热冬果,喝的就是那口温热的梨汤,配甘美的大红枣。他要把自己的生意做圆满,做漂亮,绝不将就。
同样,北大街有一个卖凉粉的老汉,姓尹。尹老汉的凉粉是自己馇的,有祖传的秘方。馇出来的凉粉颤颤嫩嫩远近闻名。更绝的是他家的调料,虽然也是辣椒蒜泥酱油醋,但他家的醋里要泡上草果;酱油一定要配上红糖重新熬制。凉粉的灵魂调料辣椒,更是讲究。不止是青海本地的循化线椒,尹老汉还花重金从陕西、四川购得外地辣椒,晒干后磨成碎片,几种辣椒混合在一起,浇上热油,他家的油泼辣子又香又辣。好凉粉配上好辣椒,尹老汉的凉粉成了西宁古城的名牌,大家都叫他尹凉粉。每天一出摊,即可被抢完。即便是这么好的生意,尹老汉却是常常不出摊。慕名而来的食客问他为啥不做凉粉,尹老汉无奈地摊开双手:“调和不全哪。”那个年代交通不便,辣椒调料经常跟不上供应,尹老汉只好关门歇业,不做生意。有的食客认为他太较真,劝他:“调和不全就不全呗,你用别的辣椒芥末代替也是一样的。”尹老汉就气呼呼地撅起胡子:“那就是别的凉粉,不是我尹凉粉的凉粉了。”
和尹凉粉同一时期卖小吃的,还有刘粽子、杜酿皮、魏麻食、冶凉面、杨胖子卤肉等等。刘粽子是西宁古城第一家卖糯米粽子的。他的粽子不但绵软香甜,而且包得饱满周正、有模有样,是妇女们回娘家走亲戚必带的礼物。杜酿皮的水洗酿皮也是妇女们的最爱,他和尹凉粉一样,也讲究调料的配制,一丝一毫不敢马虎。据说他的酿皮吃完,碗底的最后一根酿皮夹起来,碗里的汤汁也随着酿皮一同蘸完,不留一点渣渍,这就是人家配调料的功夫和能耐。
魏麻食没有什么绝活,他做生意的诀窍就是经济实惠,物美价廉。那些牵着骆驼的脚户,抱着鞭子的车夫,扛着麻绳的背背儿,以及在铺堂里忙忙碌碌的手工艺人,都是他家面店的常客。传统的麻食都是烩的,麻食煮熟后捞在碗里,浇上臊子,热热乎乎的一大碗。臊子也分好多种,就和现在的米粉店一样,有肉酱米粉、海鲜米粉、酸菜米粉等等。当然那会儿的臊子没有这么丰富,就是肉的和素的两种。不过,在魏麻食的店里,臊子只有一种,就是肉和菜混合。而且魏麻食也不是烩的,是干炒的。满满一大碗麻食配上肉片,还有各种蔬菜,他家的一碗麻食頂别人家的三碗。人们把他家的麻食叫“干爨”。吃上一碗干爨麻食,再喝上一碗面汤,特别能顶饥耐饿,就能保证那些靠力气吃饭的人一整天精力旺盛,而不像别人家的面食,看着也是汤汤水水的一大碗,可是不顶事,撒一泡尿就饿了。
冶凉面是一位回族老人摆的凉面摊。他改良了传统意义上的凉面,给拌好的凉面浇上牛肉或羊肉的臊子,一下子提高了凉面的档次,比传统的素凉面要丰富好多,谓之“凉面热吃”。这也是最早的羊肠面的雏形。只是,冶凉面并没有将凉面热吃发扬光大,他在积攒了一些钱财后,开了一家清真面馆,研究开发更高端的面食。羊肉拉条儿、炒炮仗、炒二节、粉汤烩面等等,就是现在的三升干拌的前身。而他的臊子凉面则由别人继续改良,发展成为今天的羊肠面,也是一道青海的名小吃。
杨胖子卤肉是兰州人开的,生意做大后,他也就成了西宁人。他家的卤肉自不必说,是逢年过节或出门游玩时大人小孩打牙祭的必需品。单是他家的卤汤油,比卤肉更受欢迎。家庭主妇们买一点回去,盛在瓦罐里,拌拉条儿、拌面片。尤其每天必喝的一顿汤——不论是寸寸面、还是旋面叶儿、还是旗花面,揭开锅盖,舀一勺卤汤油搅到锅里,顿时,那一锅清汤寡水的面叶儿有了灵魂,油花儿像星星一样亮晶晶地漂在汤面上,那香味儿更是勾人魂魄。一勺卤汤油,使一家大小的晚餐变得格外香甜温馨。
青藏高原上的西宁古城曾经是一个遥远偏僻的小城镇,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尽管高原上有着极其丰富的中药材、畜牧产品和民族工艺品,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幸而有了茶马互市,有了唐蕃古道,有了丝绸路的羌中道,青藏高原上神秘又珍贵、闪烁着绮丽色彩的药材、皮张和矿产品才被世人所认知。清朝末年又有了山陕商人的介入,这些珍贵的宝物才流向内地,流向国外。而外面的物资也源源不断地流入西宁古城。在经商贸易中,西宁人凭着高原上朴实、纯真、豪放又善良的本性,做生意,更讲人情,因而形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商业诚信和经商之道。靠着公平,靠着诚信,靠着过硬的货物品质,西宁古城的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直至做到海外。当时,高原上藏系羊产的西宁大白毛,茶卡盐湖的大青盐在国际市场上都是响当当的品牌。西宁古城的商业诚信,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贾文清,青海省西宁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出版有小说集《银簪子》,散文集《老西宁记忆》《望穿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