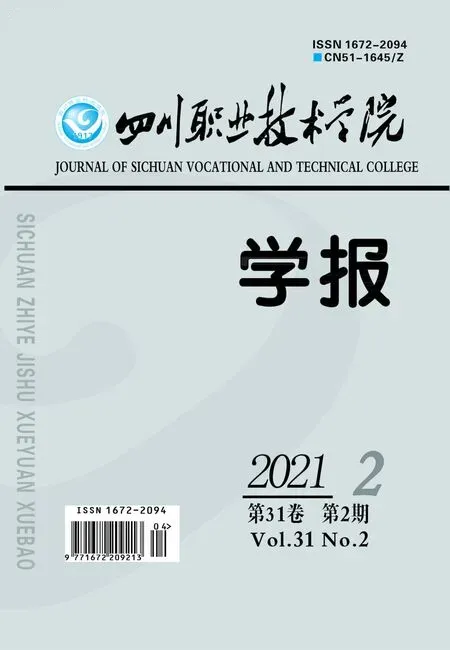非自由状态下超脱自我的“零余者”形象
——从修辞心理学视野解构《春风沉醉的晚上》
钟艳萍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是一篇短小但充满艺术魅力的小说,小说中蕴含的丰富思想、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映射出的独特的“零余者”形象吸引了许多学者对其进行鉴赏与评价。然而,这些研究都未能从修辞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过细致的文本分析,而我们在阅读小说时又会不自觉地与作者、作品进行交流,进而触发我们的心理机制,使作者、读者、作品三要素产生超越时空的对话。因此,对《春》的研究如若缺失了修辞文本的分析,那么对解构小说中的“零余者”是不彻底的。为了使对话尽可能达到圆满,笔者将通过修辞心理学的理论,对该篇小说的主要角色“我”即“零余者”进行细致地分析。
一、环境与自我生活的解构
一开篇,作者就交代了“我”因为失业而辗转流离的生活状态,让我们印象格外深刻的是对他最初居住之处的描写:“最初我住在静安寺路南的一间同鸟笼似的永也没有太阳晒着的自由的监房里。”[1]96这句话说的是“我”最初住的地方既像“鸟笼”,又像“监牢”。这里作者用了两个比喻,结合陈望道对比喻概念的阐发,我们可以知道“最初我住在静安寺路南的寓所”是作者所要表达的“这思想的对象”,即比喻的本体;“鸟笼”和“监牢”是用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另外的事物”即比喻的喻体。这一本体和两个喻体之间在性质上有一个共同的类似点,这就是“非自由”。由于作者将“我”的生活状态与“鸟笼”和“监牢”相联系搭挂,从而最大程度上丰富了其所叙写对象内容的生动性、形象性、新颖性和拓延性,让读者最大程度体认到“我”处境的窘迫,从而引发我们无限的联想。这样产生的效果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双眼就能够将语言文字投射成类似的现实画面,从中看到蕴含在语言文字之中深刻的内涵,看到“鸟笼”和“监牢”就像切实看到他穷困潦倒的生活环境,感受到他的精神渴望如阳光一般自由的释放,看到他内心显露出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如果作者不以上述比喻文本来表达其思想,而是直接说“我因为失业穷困潦倒,住在一个没有阳光照射的狭小寓所。”那么,这样的表达就明显失去了上述表达的生动性、形象性,也失去了新颖性和拓延性,无法给予读者任何想象和回味的空间。但因为作者用了比喻文本,使读者能够愉悦地接受其设定的角色形象,并在一开篇就对“我”有了深刻的印象,又能够让读者在阅读时获得解读上的快慰和审美的情趣。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这两个比喻能够与全文进行一个对照,既可以说他在开头为读者设置了一个“我”为何“非自由”的悬念,吸引读者继续往下阅读,也可以说他为下文的情节做了一个铺垫。
二、身体与自我精神的解构
如同开篇所说的那样,“我”不仅在物质上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在思想和精神上也处于被压抑“非自由”的状态,就如同生活在“没有阳光”的地方。作者在小说第二部分这样写道:
我那时候的身体因为失眠与营养不良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成了病的状态了。况且又因为我的唯一的财产的一件棉袍子已经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散步,和房里全没有光线进来,不论白天晚上,都要点着油灯和蜡烛的缘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缩了[1]99。
“就是我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缩了”是一个借代修辞。作者用“眼睛、脚力“代替“能力(工作能力和行走能力)”,因为眼睛和脚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且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在前半句就已经对“我”的健康状态进行了说明——“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这种表达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画蛇添足”,但如果我们将文本与关系联想的心理机制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作者有意为之的意图。
根据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得知“我”的眼睛和脚力萎缩是因为“我”没有财产,因为没有财产,只有一件破棉袍而无法外出,又因为无法外出所以脚力萎缩,而因为无法外出所以整日呆在狭小的房间,且房里没有光线,因此日夜点着油灯和蜡烛导致的眼睛萎缩。诚然,“眼睛”作为视觉器官,是与外界进行“对话”的一个窗口,但更是“我”作为文学翻译工作者必备的一个能力条件。“脚力”则是行动力的一种体现方式,“我”的脚力非常萎缩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离开寓所,那么也就与上文相对应了,成为“非自由”状态的一个促进因素。
分析到此,我们知道这段话并不是简单的因果陈述,而是阐述了一个因果循环的问题,即“我”没有财产是因为工作能力受到了健康状况的影响,“我”无法外出行走是因为受到没有财产收入的影响而只能穿破棉袍所导致的脚力萎缩。现在,我们再结合陈望道先生对借代概念的阐发:“所说事物纵然同其他事物没有类似点,假使中间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时,作者也可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2]作者在感知反应当前事物——能力的时候,就会与经验中和观念上已经把握了的以往经验过的事物——眼睛和脚力相联系搭挂起来,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了“关系联想”。
这一修辞文本的建构,使用了人们日常可以感知到的熟悉的事物,从表达上使语言更加形象、具体和突出,也使得小说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情节连贯;从接受上看,更引发读者的思索和回味,我们会自然的联想到上文对“我”的介绍,会不禁探究眼睛和脚力萎缩的原因和其导致的结果,这就为小说的阅读增添了解读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情趣。
三、“零余者”自我意识的解构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能够对“我”的形象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一个以翻译外国文学为生的知识分子,因失业而导致的物质匮乏,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也未得到滋养的非健康状态的一个人物。然而,作者对“我”的塑造并没有止步于此,熟悉郁达夫其他作品的人就会知道,他的作品中往往存在一个“零余者”的形象,对于“零余者“存在的意义,我们结合作者在第二和第三部分的描写来看。
首先,在第三部分“我”得到稿费穿着棉袍子走在烈日下的描写中,比喻修辞文本“我颈上头上的汗珠,更同盛雨似的,一颗一颗地钻出来了”,将“汗珠”比作“盛雨”,“这思想的对象”——“汗珠”与“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那另外的事物”——“盛雨”之间有性质上的类同点,即都是“水的一种存在形式”。由于作者在描述“我”穿着棉袍子走在烈日下汗如雨下的场景时将“汗”与“盛雨”相联系搭挂,从而使得语言变得生动、形象。而“盛雨”本身的画面也比直接用“汗”表达更具有张力,“盛”具有“丰富”义,可表示汗从颈上、头上不断涌出的动作,又有数量上多的立体空间感,使读者在阅读时会不自觉地展开联想,并进行再造性想像,从而使语言文字转换为生动的画面,进而获得解读文本的审美情趣。
接着,“同类”和“同胞”两个词抓住了我们的眼球,这两个词出现在上述文本中显得相当刺眼,这是因为作者用了别解的修辞手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对“别解”进行一下说明,这里的“别解”用了谭永祥先生的名称,引用的是吴礼权的概念,即“在特定语境中临时赋予某一词语以其固有语义中不曾有的新义,以达到幽默生动的表达效果的修辞文本模式。”[3]作者将“我”穿着破棉袍走在烈日下的场景描述一番后转写与季节同时进行的“同类”,他们不仅能够正确感知四季与温度的变化,而且能够与繁华的都市融为一体,同时还作为“华美的少年男女”存在,这与穿着破棉袍走在烈日下并被骂成“猪头三”的“我”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上述作者所构建的修辞文本中显得格外刺眼的“同类”和“同胞”所反映的意义并不是其本义,而是作者将二词别解为其反义语义——“异类”。如此一来,作者把“我”排除在“同类”中就能够解释得通了。
这一别解修辞文本的建构,从表达上看突破了“同类、同胞”原本的语义,作者将其别解为反义语义“异类”,化朴实为讽刺,表意含蓄隽永,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从接受上看,“同类、同胞”的语义引起了读者的“不随意注意”,并在“不随意注意”的引导下走向“随意注意”,使读者能够很好地将“异类”转换成前文所说的“零余者”,进而更深刻地理解“我”的角色形象。即便作为全知视角的我们在阅读这段话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以四面注视着“我”的人自居,对被人大骂后看着灰尘竟哈哈大笑的“我”持无法理解的态度,领略到作者文字中辛辣的嘲讽意味。
然而,这部分蕴含的内容还不止如此,继续往下看,作者还用了列锦的修辞手段:
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来往的汽车人力车,车中坐着的华美的少年男女,和马路两边的绸缎铺金银铺窗里的丰丽的陈设,听听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杂的人声、脚步声、车铃声,一时倒也觉得是身到了大罗天上的样子[1]105。
这个列锦修辞文本中,作者将同一时空存在的“汽车人力车”、“少年男女”、“绸缎铺”、“金银铺”、“脚步声”、“人声”、“脚步声”、“车铃声”等名词或以名词为中心的定名词组堆叠起来,突破了常规的汉语句法结构模式,增加了语言的表达张力,诱发读者的联想机制,使建构的文本更具丰富性、形象性,使我们一看到静态的文字就如同动态的画面浮现在眼前一般。这种列锦的手法如同电影里蒙太奇的片段剪辑,既有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冲击效果,展现了都市的繁荣与华美的少年男女和谐相融的美好画面,又与“我”形成了一层天然的屏障,揭示出“我”与环境格格不入,“我”作为“零余者”的鲜活形象似乎也出现在我们眼前。同时,这样形象化、生动化的列锦手法也增添了我们对“我”的不理解及由此衍生出对“零余者”——“我”的同情。而这些蕴含在文字之下的这些内涵正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秘密交流”,我们也由此获得了阅读的快感和审美情趣。
四、“零余者”形象升华的解构
《春》中的“零余者”并不只是个被社会边缘化的形象,更是一个具有“超我”意识的理性人。作者在处理“我”和陈二妹的情感问题时,这样写道:
我当那种情感起来的时候,曾把眼睛闭上了几秒钟,等听了理性的命令以后,我的眼睛又开了开来,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以前几秒钟更光明了[1]109。
这句话是别解修辞文本。“光明”与“黑暗”相对,原指客观环境的光照程度,这里别解为“我”的内心状态变得明亮,思想更加清晰、坚定。这一文本体现了作者语言的灵活性,因为作为全知视角的我们知道“我”在内心做出决定之后周围的世界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别解之义使我们能够窥探到“我”的内心世界,即“超我”战胜了“本我”而感觉精神世界得到了升华,从而说“更光明”了,也即此处的“光明”并不是客观环境的亮度提升,而是别解为“我”的内心世界被理性的阳光照射后精神得到了滋养。而作者建构的这个文本恰恰与一开篇的阳光对应了,这正是作者修辞技巧的高超之处。
这种情感处理正如韦恩·布斯在谈及亨利·詹姆斯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时所说的那样:“大多数故事都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主要人物的道德抉择。”“一部作品的道德性质取决于观念的正确,‘一部艺术作品的道德感’完全取决于‘产生这部作品时所感受到的生活的多少’。”[4]《春》中的“我”同样面临这种选择,即在自身生活窘迫、身体羸弱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释放自我对陈二妹的男女之爱,以及是否应该让陈二妹承受这种爱的问题。显然,作者将“我”的这种情感本能以理性的力量自我抑制住了,从而完成了“我”的道德选择,而“我”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道德选择,一方面是出于“我”作为“零余者”的生活体悟,另一方面是“我”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最终的结果是小说中的“自我”升华为一个道德高尚的“超我”,从而也升华了小说的内涵,为其艺术魅力增添了新的价值。读者在阅读这个修辞文本时,由于注意得到了强化,自我代入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使得阅读过程中能够最大程度地感知“零余者”的内心,从而获得最大程度的审美体验。
五、“零余者”哲思的解构
小说中“我”的“书”和“棉袍”贯穿小说始终,结合别解修辞手段对它们进行分析,从而丰富我们对“我”的认识。
阅读完小说我们知道,尽管“我”生活窘迫,辗转流离也始终带着那几本“破书”。作者用“破”来修饰它并不是因为这些书真的一无是处,通过别解的修辞手段结合注意强化的心理机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书”对“我”的意义重大:既是翻译家身份的象征,也是获取生活酬劳的唯一工具,更是思想和精神上的慰藉,在平日里还充当了写字台和床的器物之用。同时,“书”还具有时代意义,它映射出了一大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以及与他一样所处的窘迫现状,他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对现实感到无可奈何,他们因为落魄而能够感知体悟到类似陈二妹这样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劳苦生活。
同样,“破棉袍”也是如此,别解它本来的意义,我们就知道它虽破但有用。一方面,这个棉袍起到了庇护的作用,能够给长期生活在“没有阳光的监牢”的“我”带来温暖,支撑我走出“监牢”,在无人的寒夜散步,释放内心,以获得短暂的清新头脑。另一方面,它也是我认识自我存在,认清“零余者”身份的一个催化剂。当“我”穿着破棉袍走在烈日下时,我感知到了四季和温度的变化,感受到了与繁华都市下的华美少年男女的格格不入。
别解完“破”的深层涵义,我们容易得知“破”是“我”对当下重要事物的评价,这一评价反映出了深刻的哲思,即庄子的“无用之用”。表面上说“书”和“棉袍”是无用之物,实际上对“我”意义都很重大。作者将如此深刻的哲思寓于“书”和“棉袍”之中且贯穿小说始终,从表达上看,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得效果,从接受上看,引发了读者文本解读的“不随意注意”,进而激发读者进入“随意注意”的思考解读阶段,最终体悟出蕴含其中的深刻哲思,得到文本解读的无限乐趣,感受到作者文本建构的精妙,获得更多审美情趣。
六、对“零余者”的未来态度解构
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作者富有诗意地描写了所居之处对面的环境并由此抒发了“零余者”对未来的态度。一排排点着红绿电灯的洋楼与他所住的不见阳光、只有蜡烛和油灯的贫民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在最后写道:
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沉沉的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像有无限哀愁蕴藏着的样子[1]11。
细细品读这两句话,第一句是比喻修辞文本,作者把“薄云”和“尸体”相联系搭挂起来写出了天色的昏暗和氛围的阴沉。这一比喻的本体是“灰白的薄云”,即作者“这思想的对象”;“腐烂的尸体”即用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那另外的事物”。作者之所以这样写道是其运用心里联想所致。因为薄云与尸体具有两个类似点:一是在颜色上——灰色,二是在给人的感觉上——压抑。由于作者运用了联想机制,把“薄云”和“尸体”联系搭挂,使得作者所描写的昏暗天色变得更形象生动,其想反映的阴沉、压抑的氛围效果也大大增强。
此外,作者还进一步将这种阴沉、压抑的氛围通过通感的修辞手段绵延而开。他将视觉的画面——黝黝的天色转换为人自身的情感——哀愁则是突破逻辑常规的语言表达,这两句话都是以我之思著于客观事物之上的表达。实际上,客观事物是没有情感的,无论是云还是天色,作者让我们透过“我”的视野看到了“我”内心对未来的态度是哀愁的,是苦闷的,是无能无为力的无奈。这样的描写,使读者的想象也随“我”无限的哀愁一般无限地延展开了。
七、结语
《春》作者通过比喻、映衬、别解等一系列修辞手段结合想象、联想、注意等心理机制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形象丰满、立体的“零余者”。使我们在阅读时宛如进入一个真实的画面,与“我”同步感受现实的窘迫和悲凉,感受到“我”被社会边缘化的苦闷和孤独,感受到“我”从羸弱到自我意识觉醒并到“超我”的转变。同时,我们不仅对“我”的角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们与作者的心理距离也缩短了,对作品文字更加亲近了,体悟到了蕴含于文字间的情感与哲思。这些都使作者、读者、作品之间的对话变得更加丰富和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