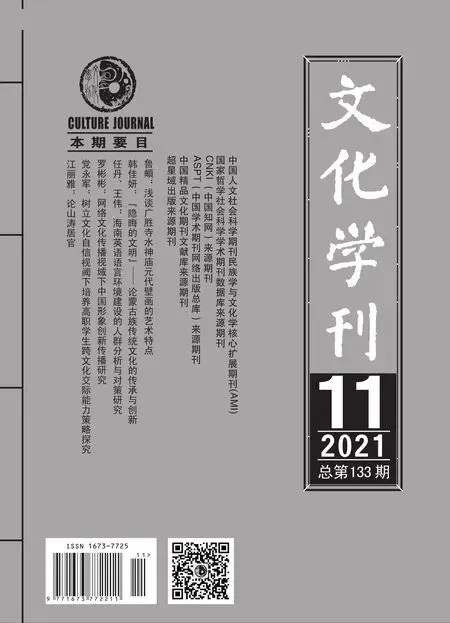王青伟小说《村庄秘史》中女书书写者的女性主体性解读
谢亚丽
女书又称女字,是发源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道县一带,仅在女性之间使用的文字,其出现标志着女性意识的提升和女性身份的建立。湖湘文化孕育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在使用和传承的对象上严格限制了性别,在中国近三千年的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社会中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其社会功能主要用于当地妇女的情感申诉与心灵交流。女书的书写与传唱是湖南江永地区真实存在的一种特殊风俗,2010年6月湖南本土作家王青伟写作的《村庄秘史》在基于其民族身份与地域文化的把握下关注到女书这一特殊的文化遗产并将其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村庄秘史》以五个故事串联的形式,通过故事的亲历者章一回讲述了发生在红湾和老湾这两个相邻乡村里的人和事,表现了湖南乡村隐秘的历史,并借由对乡村历史的叙述表达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思考。其中的一个故事讲述了木匠章顺与地主婆的畸恋以及与自己妻子即女书书写与传承者麻姑的爱恨纠葛。目前学界对于《村庄秘史》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有22篇相关论文,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反思、乡土发掘、人性探索、叙事手法以及小说建构方式的角度等方面来分析作品,仅有蒋艳丽的《身份认同焦虑与艰难认同之路》、田文兵的《身份的焦虑:〈村庄秘史〉中的认同危机与历史叙述》和陈娇华的《个体身份认同与乡村历史叙事》用了极短的篇幅将麻姑作为个案来探讨小说人物普遍具有的身份认同的焦虑。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女书书写对于女性的文化功能和女性主体性在女书书写者麻姑身上是如何体现的,探讨女性企图依靠女书建构女性主体性这种尝试的困难与切实意义,以期能给女书和女性主义的相关研究做一点工作。
一、女书书写者的女性主体性表征
“所谓主体性,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种特性,它既包括人的主观需求,也包括人通过实践活动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把握[1]”,《村庄秘史》中麻姑的女性主体性表征主要是凡事依靠女性自己、要求女性具备独立人格从而能够活出女性自我的生活追求。
首先,对于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麻姑有着自己的追求,她遵循自己的内心情感和观念。所以她能够听从自己的情感需要,冲破男性主导的封建文化对于女性的道德规约和伦理教育的樊笼,大胆地和外地远来且不知根底的章顺在油菜地里野合并独自孕育孩子,还能够抛开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和生活起居主体依靠男人的传统家庭模式。为了保持自己作为女人的独立性,她从来不会主动伸手向男人要钱来维持生活与养育孩子,也并不想依靠男人一直在老湾扎根生活,而是想生下女孩后立马带着女儿去寻找千家峒。即使在男人常年不在家的情况下,她依然拒绝接受乡人们的任何帮助,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独立完成了自食其力和养育孩子的双重任务。在她意外怀孕后,她决定不要孩子时既没有半点女性遇事的慌张犹疑,也没有求助阿贵,而是自行采取了多种办法打胎。传统女性依赖男性的历史惰性在麻姑身上并没有一丝遗留,读者看见的是一个自立自强的麻姑。
其次,对于以丈夫章顺和老湾为象征的男性世界她采取了将其物化并作为客体超越的态度。麻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章顺,迫使章顺担负起父亲责任,并非其全部目的,除了民族文化中男孩只能跟着父亲的规定,她更主要的目的是想借助章顺继续孕育一个女孩儿。从这可以看出,她并未把女性看成是男性的附庸,没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从一而终的陈腐观念。男性在她那里不再是拯救者或给予女性物质供养与情感寄托的存在,而是成为了被她物化的客体,即用来帮助女性生育的种马。面对丈夫章顺哄骗她烧掉女书的甜言蜜语、暴力胁迫以及章顺和红湾地区的人身安全威胁,她倔强地不为所动,仍然无所畏惧地保留着女书文稿。这可以看作是在性别属性上对于玷污女性世界的男性的拒斥和对自己女性私密空间的竭力保护。麻姑想要生育女儿并和女儿一同去找瑶族传说中的千家峒,麻姑对千家峒的深厚感情不如是说是对温情互爱的女性世界的渴望和对老湾象征着的男性世界的坚决逃离。她想带着女儿逃去没有男性的方舟中幸福地生活,潜藏着女性独立意识的初步觉醒,企图通过想象中的女性世界来抵抗男性世界对于女性的身心迫害。
麻姑不再是五四时期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地位低下、被丈夫随意典当而要忍受双重母子分离痛苦的可怜妻子,也不是沈从文《丈夫》中那将自己的身体出售进而缓解家中经济困境与帮助男性养家糊口的无奈娼妓。她有着与俗世格格不入但仍坚持自己书写女书生活方式的主见和物化并超越男性世界的坚韧力量。
二、女书的书写和女性主体性的建构
女书是由女性所创造的一种文字,而麻姑身为女性的主体性存在于自己每日书写的女书对男性的放逐之中,存在于以女书为代表的族群文化和性别文化对于女性悲苦人生的理解与调和之中,她试图通过书写女书来建构自己作为女性的主体性。
(一)在女书的书写传承中述说对于男性的拒斥
女书文化的传承中,“母女传承是女书传承的首要方式,这是女书之乡的女性们为寻求自我生命之源与文化之根的一种内在表达,女书传承方式隐藏的是女性世界中男性角色的缺席,准确地说应该是男性“在场的缺席[2]”。女书的传承对象只能是女性,所以麻姑执着地要生下一个女儿,而且这种文字只有女性才能看懂,当老湾的人们试图让村里学问最为渊博的章大弄懂麻姑的女书时,章大予以拒绝并说:“那些文字祖祖辈辈一直秘传给女人,男人们如果想去弄明白那上面的东西永远不可能,还没等到你弄清楚几个字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瞎掉,你的舌头就会僵硬,你就会变成一个既看不见又说不出话的活死人”[3]93,说明了女书是一种具有性别倾向的文字,它本身就拒斥男性的参与和窥视的妄想。
除了传承方式和传承对象以及阅读范围具有单一性别的限定之外,即男性的存在在女书文化中不被允许这种显性的规范之外,女书书写者还可以通过女书在内在精神世界里完成对男性的放逐,所以《村庄秘史》中丈夫章顺即使整天不回家并疯狂地爱上与自己相差几十岁的地主婆,在男人基本上对自己既无物质援助又无精神抚慰的情况下,麻姑依然能够安然过日,甚至同意和支持丈夫章顺把情妇接来家中当作母亲供养的行为,没有表现出一般女性对于情感侵占所会有的歇斯底里与愤恨等人之常情。这并非是她对丈夫的屈从,而是长期的女书文化赋予的女性结盟与女性同情,是文化基因和性别属性所决定的一种“女同性恋存在”。
由此可见,女书的书写意味着由女性创造出的神秘领域,在这个领域之中女性可以将男性彻底排除在外,营造出只有女性互爱没有男性迫害的理想乌托邦。《村庄秘史》中瑶族女性麻姑就是通过书写女书试图寻找和建构起一个没有男性干扰而女性们自在幸福生活的“千家峒”。
(二)在女书的书写过程中实现女性的自我救赎
女书不仅仅是古代女性只为人际交流使用而创造的一种文字,研究者们对女书作品进行分类研究,发现作品内容十分丰富,涵盖“友情、爱情、诉苦、别离、排斥男性、追求完美家庭生活、用合法手段反抗夫权、联结历史重大事件、控诉国家暴力以及谜语、祭祀等。”[4]大部分内容是诉苦情,表述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不幸经历,并发泄内心的愤慨。由此可见,女书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情感的依托,女性在书写女书的过程中将自己的困苦借用文字倾诉出来的同时,既能从中重新获取继续生活的能量,又能避开和主流社会及男性的情感不适调和自己的心态。
小说《村庄秘史》中的女书书写者麻姑就是通过日复一日地书写女书来倾诉自己的不幸生活并调节心态,完成自己内心的平衡修复。麻姑是一个从遥远地方来的外乡女人,并背负着生育女儿寻找千家峒的民族使命,地域迁移导致的起居饮食和文化观念差异注定使她与老湾有所隔阂,如老湾的老人们经常给她讲述红湾人的罪恶历史,企图以此来同化她仇恨红湾人,但她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邻村会如此地痛恨彼此。对于老湾人对红湾的政治批判与残杀,来自互帮互爱的社会的她百思不得其解。无论她生活在老湾多久甚至孕育了老湾人章顺的骨血,但她始终带有融不进老湾的质地。再加上丈夫章顺的抛家弃子与对老女人的畸恋,以及丈夫章顺对自己的残害,麻姑内心的苦痛屈辱和愤恨可想而知,所以麻姑才会夜以继日地写那些稀奇古怪谁也看不懂的女书发泄自己的情绪[5]。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面对困境时常常会寄托于精神世界来使原本痛苦的心情趋于平静,完成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与平衡,麻姑也是如此。在丈夫离家又迷恋其他女人的情况下,她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是愁苦哀怨的,尤其是当阿贵挑逗起她的情欲后,这种内心的煎熬更是成倍增加。于是麻姑在坚守为人妻的忠贞妇道和作为女性的正常情感需求之间、在贞节锁的有形束缚和作为母亲耻于要求孩子开锁丧失自尊的无形禁忌之间、在情人阿贵欲火焚身的痛苦和自己孩子的生命之间以及在焚烧女书和保护自己之间,无数个艰难的选择横梗在她面前。而她只要心理一开始失衡,便“从那口木箱里取出一摞字稿,发了疯似的写着”[3]116。“麻姑的婚姻生活极其凄苦,女书便成了她抒发自身苦情的集中代表和象征,她不停地书写女书,寻找那个世外桃源般的千家峒,借对家乡的美好回忆,她现实处境的艰辛和感情的凄苦似乎也得到了一种释放和转移。”[6]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女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是一种女性的书写工具和表达手段,它由纯粹的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对于无数个像麻姑这样婚姻不幸生活困苦的女人而言,女书的书写过程给予了他们一种性别文化的理解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得女性能够在男性带来的痛苦之中脱离出来达到自己的涅槃重生。
小说中的麻姑就是通过书写女书得到来自女书构建的观念性女性世界的支持,从女书的书写过程中获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女性性别文化的支持、疏导和调解之下实现了女性的自我救赎。
三、女书的被焚与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失败
“女性作为个体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身份认同有两种情形:一是作为主体自我,通过寻找性别群体的传统来确认自我身份;二是通过认同已有男性中心社会给予女性的角色规范来确认自我身份。”[7]麻姑显然是属于前者,她始终日复一日地书写女书,就是担心失去自我身份认同而丧失尊严,她努力通过寻找女性群体的传统来确认自我身份。
对于麻姑而言女书的书写就是一种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也是她建构女性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她可以通过书写女书活在女书文化构建起来的虚拟女性群体世界和强大的内心世界里,从而抵御以丈夫章顺为代表的男性世界对女性的轻视与损害,忽略以老湾为代表的男性主导的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或有形或无形的压迫。
老湾人始终认为麻姑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他们一直弄不明白这个女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麻姑说的那个地名他们都不晓得”[3]91所以,当麻姑儿子为了母亲免遭杀生之祸,而私自焚烧她的女书时,麻姑“疯了似的上去扒拉那堆灰烬,她以为能够从那里找出一片没有烧干净的字稿”[3]122烧掉女书文稿意味着彻底地清空了她的历史,于是“事情在麻姑那里形成了一片巨大空白,她眼中晃动的那些人影几乎全变成了永远也回不到现实的梦境,她什么人也认不出了”[3]123,意味着失去了民族和家园记忆以及女性集体记忆,同时也是对于自身女性主体性的毁灭。如果说以前所谓的“空白历史”是老湾人对于他人历史的恶意抹杀和其历史的不正确认知,但她心里一直很清楚自己的历史并且凭借自己每日书写的女书为证并加以强化,而至此她的历史真的被男性烧成了一堆纸灰,陷入了没有历史身份和自我性别认同的迷茫与空白中。女书的被焚毁从侧面宣告了女书书写者试图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失败,但细究女书毕竟是一种不为男性所知道的文字,实际上并未与男性世界正面地进行过较量。这种在无声状态下冠名的女性意识的增强和女性主体的强调近似于20世纪90年代陈染等人建构的女性私人空间,待在一个人的黑暗房间里独自呓语或做着幻梦。
四、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各种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女书的性别对峙价值再次被挖掘和衍生,成为了当代的女性宣言。不少的学者和社会人士要求对女书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认为对于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具有文化和心理层面的支撑作用。从女书的性别意蕴或者说女性主义赋予的各种延伸意义来看,女书这种独特文化的确有一种挑战男性权威的现代性,可以说是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标志。可是从女书的存在空间、传承方式和受众等来看,女书更多的是女性一个人的战争或最多是女性们背着男性合谋然而又缺乏实践性的臆想交流。而且从广泛的社会处境来看,在现实中女书文化经常会遭到诋毁,正如《村庄秘史》中的女书书写者麻姑不被外界所接纳,甚至在不干扰他人的情况下其书写的女书也遭致焚毁,这寄寓着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是一种文化必然,但是在实践中能不能真正地通过女书文化建构女性主体性却是个值得思辨的问题。王青伟的《村庄秘史》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女书更多面更形象的思考,为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体性开放意义上的建构提供了更为切实的参考路径。
——女书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