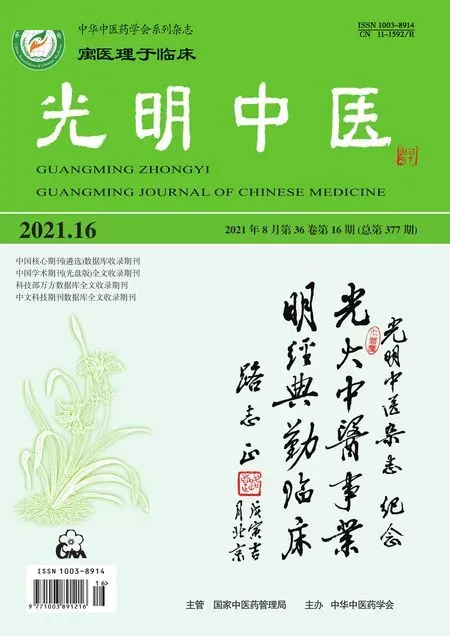冉青珍主任补脾肾、疏肝利水法治疗女性特发性水肿经验*
李冠桦 冉青珍
冉青珍,广东省中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师从国医大师路志正及国家级名老中医李维贤,从事妇科临床工作近20年,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妇科疾病。笔者有幸跟师学习,获益良多,现总结冉主任运用补脾肾、疏肝利水法治疗女性特发性水肿的经验如下。
1 现代医学对女性特发性水肿的认识
女性特发性水肿又名周期性水肿、功能性水肿,是一种特殊的、原因未明或尚未确定的水盐代谢紊乱综合征。此综合征既无明显的心、肝、肾等疾病,又无低蛋白血症,多发生于育龄女性,尤其是有肥胖倾向的神经质女性。临床主要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周期性下肢凹陷性水肿,立位重于卧位,傍晚重于晨起,夜尿量明显多于白天,常伴有肢体困倦、心悸、头晕、腰酸、月经不调等症状,水肿往往在月经前期加重,呈周期性演变。情感变化亦常为诱因,多有精神抑郁,或易激动,面部潮红,易出汗等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的表现。由于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所以缺乏统一的临床诊治标谁。西医多采用利尿剂和激素疗法,其疗效不稳定,停药后易复发[1]。
2 中医病因病机
特发性水肿在中医学称为“水肿”,若水肿发生在经行前后,经后自然消退者,又称为“经行浮肿”。究其中医病因病机而言,《黄帝内经》 对水肿病的发生与肺脾肾的关系早有认识,如《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此段原文阐述了水肿的形成与肺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有关。《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清代《叶氏女科证治》曰:“经来遍身浮肿,此乃脾土不能化水,变为肿”,《皇汉医学·妇训义》云:“经行浮肿因于肾虚者,多为房劳不节,堕胎小产,致肾气内伤,经血下注碍于肾阳敷布,气化失职,水道不利而浮肿生”。故脾肾阳虚,水湿运化不利,聚而为肿,且女子以肝为先天,生理上常“有余于气,不足于血”,故经行浮肿还与肝失疏泄相关[2]。周学海《读医随笔》有云: “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藉肝胆之气化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不病。”可见,肝胆的疏泄功能正常,则脏腑十二经气机调畅,人体方能情志舒畅,气血调和,方可不病。另外,《金匮要略》有“经为血,血不利则为水”之论,指出血脉瘀滞阻碍水液的正常运行,泛溢肌肤而发浮肿[3]。若肝胆郁滞,疏泄失调,气机不畅, 则血行瘀滞,泛溢肌肤而浮肿。由此可知,经行浮肿主要与肝、脾、肾等脏腑密切相关。
3 中医治疗
在中医治疗上,冉主任认为,需处理好脾肾二脏与水湿运化的关系,肝胆疏泄与脾主运化的关系,主张从补脾肾疏肝,利水消肿立法,辨证得当,每每收效显著。冉主任在国医大师路志正、国家级名老中医李维贤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拓展知识体系,选方用药,在辨证论治基础上,多以经方、成方为基础化裁,喜用化水种子汤、五苓散、并提汤、温土毓麟汤等补脾肾利水,小柴胡汤、温胆汤等疏泄肝胆。化水种子汤出自 《傅青主女科》:“使先天之本壮,则膀胱之气化;胞胎之湿除,而汪洋之田化成雨露之壤矣。水化则膀胱利、火旺则胞胎暖,安有布种而不发生者哉!方用化水种子汤”,由巴戟天、白术、茯苓、人参、菟丝子、芡实、车前子、肉桂组成。具有温肾健脾,化湿利水之功。五苓散出自《伤寒论》,由茯苓、猪苓、泽泻、白术、桂枝五药组成,其中茯苓、猪苓、泽泻三药利水而通水道,白术健脾以制水,桂枝通阳化气,气化则水自行。对肾气不足,脾胃虚弱者可用并提汤加减,并提汤出自《傅青主女科·胸满不思食不孕》:“无肾中之水气,则胃之气不能腾;无肾中之火气,则脾之气不能化。惟有肾之水火二气,而脾胃之气姑能升腾而不降也。然则补脾胃之气,可不急补肾中水火之气乎?治法必以补肾气为主,但补肾而不兼补脾胃之品,则肾之水火二气不能提于至阳之上也。方用并提汤”。由熟地黄、巴戟天、白术、人参、黄芪、山萸肉、枸杞子、柴胡组成,具有补肾气,兼补脾胃的作用。对脾胃虚寒者可用温土毓麟汤加减,《傅青主女科》云:“脾之母原在肾之命门,胃之母原在心之包络。欲温脾胃,必须补二经之火。盖母旺子必不弱,母热子必不寒,此子病治母之义也。方用温土毓麟汤。”该方由巴戟天、覆盆子、白术、人参、怀山药、神曲组成,具有温肾暖土、培土制水之功。李中梓言:“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点明肾为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在脾,脾为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点明后天之本在脾,二脏有“相赞之功能”。因此,无论是脾运化水湿的功能失调,还是肾主水的功能失调,脾肾同治则相得益彰;正如《景岳全书》载:“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因此,涉及健脾运化水湿,或补肾温阳化气治水时,冉主任组方常常采用脾肾同治的思路,“补先天以壮后天,补后天以资先天”。丁甘仁言:“治肿之法,勿忘调肝”。《血证论》云:“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水谷乃化”。肝主疏泄,调畅气机,协调脾胃升降,并疏利胆汁于肠道,促进脾胃运化功能。若肝失疏泄,气机升降失常,脾失健运,土不制水而为肿。冉主任临证治疗总不忘疏肝健脾,擅用既能疏利少阳三焦之枢机,又可调畅气机升降的小柴胡汤。小柴胡汤由柴胡、黄芩、人参、半夏、炙甘草、生姜、大枣组成。方中柴胡与黄芩配伍,有升有降,疏肝利胆,调畅气机,开少阳枢机之郁;半夏与生姜相配,辛开与苦降,宣发与降浊,共同调理气机。温胆汤由竹茹、枳实、半夏、陈皮、茯苓、生姜、甘草、大枣组成,方中陈皮、半夏、枳实理气化痰;茯苓淡渗利水; 竹茹入胆经清热化痰; 生姜、甘草、大枣相配调和脾胃。对于温胆汤的方义,后代医家有多种解释,特别是温胆汤调畅气机的作用,为该方广泛应用于郁证等情志失调疾病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新的思路[4]。清代张秉成《成方便读》云:“胆为甲木,其象应春,今胆虚不能遂其生长发陈之令,于是土得木而达者,因木郁而不达矣”。冉老师认为,小柴胡汤中柴胡轻清宣散,可宣畅气机,疏肝解郁;温胆汤中半夏、枳实药性苦降,可降气疏肝,两方合用时,一升一降,共同疏泄肝胆之郁滞,调节全身气机,气行则血利水行,停聚中下焦之水液可得以运化。在临证治疗时,冉主任常根据患者兼症辨证加减,下肢水肿明显者,可加猪苓、泽泻、薏苡仁等以利水消肿治其标;出现胸闷喘促者,可加桂枝、桑白皮等以温阳化饮,降气利水;若短气、气虚无力者,可加白术、黄芪、党参等补肺健脾以助行水;若脾虚泄泻者,可加炒白术、茯苓、山药等健脾利水;若血瘀之象显著者,可加桃仁、赤芍、红花、当归、益母草、泽兰等活血化瘀,利水消肿。
李时珍言:“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故谓之月信,月水,月经”。女子的月经,是中医学“天人相应”理论的一个重要反应。女性在月经周期的不同阶段,阴阳气血与“潮水涨落”一样发生着盛衰消长变化。《素问·八正神明论》载:“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廊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治疗女性疾病,更应该顺应月经周期气血阴阳的消长变化而选方用药,方能取得良好效果。经期血室正开,胞宫泻而不藏,经血下行,宜调理气血,通因通用;经后血室已闭,血海相对空虚,胞宫藏而不泄,宜养经血调肝肾;经间期重阴则阳,乃阴阳转化之氤氲期,宜助阳活血;经前血海充盈,冲脉之气较盛,宜疏导气血,调和阴阳[5]。冉主任认为在治疗女性特发性水肿时要根据女性月经周期气血阴阳的变化调整用药,在经前期和经期宜在辨证论治基础上辅以活血通经药加以疏泄,令水湿伴随经血而去,邪有出路。
4 典型医案
患者冯某,女,37岁。主诉:经前下肢肿胀1年。于2017年9月5日就诊。患者近一年每逢月经前10 d 出现双足肿胀,离经期越近,肿胀越甚,按之凹陷不起,穿日常鞋袜感紧小困难,以足踝下为主,伴下肢肿胀感。月经25~28 d一次,经行4~6 d干净。末次月经为2017年8月28日,月经量可。患者已婚离异,目前无性生活。2017年8月10日查肝肾功能正常,类风湿因子阴性。2017年8月23日经前性激素六项示:FSH:2.27 mIU/ml,LH:1.28 mIU/ml,E2:605.3 pmol/L,PRL:459 mIU/L,T:0.43 mol/L,PRG:459 nmol/L。刻下症:现值经后,患者下肢肿胀已消失,眠差、多梦,夜间惊悸易醒。口干口苦,大便偏软,尿黄。舌质红,舌苔黄厚干,脉弦。西医诊断:特发性水肿,中医诊断:经行浮肿。辨证:肝胆湿热证。处方:枳实15 g,茯神30 g,清半夏10 g,姜竹茹10 g,陈皮5 g,茵陈10 g,炒栀子5 g,佩兰10 g,大枣10 g,生姜10 g。水煎内服,共4剂。
2017年9月19日二诊,患者服药后眠差、心悸有梦等症状略有好转,仍口干口苦,大便偏烂不成形。末次月经为2017年8月28日,现值经前,尚未出现下肢肿胀,畏寒怕冷,腰背酸冷,四肢不温,尿清。舌淡红,苔薄白,脉沉弦迟。辨证为肝郁脾虚证,处方:巴戟天15 g,土白术15 g,芡实10 g,茯苓15 g,菟丝子10 g,柴胡15 g,党参15 g,法半夏10 g,黄芩10 g,肉桂3 g,益母草15 g,泽兰15 g,车前子5 g。水煎内服,共4剂。
2017年9月26日三诊,患者入睡较前好转,仍心悸有梦。口苦好转,仍有口干,大便仍偏软。恶风怕冷。今日月经来潮,既往经前10 d出现下肢肿胀,本次9月23日即经前3 d开始出现下肢肿胀。查体:双下肢内踝凹陷性水肿(++)。舌淡胖,苔薄白,脉沉迟。辨证为脾肾不足,水湿浸渍证。处方:巴戟天15 g,土白术15 g,茯苓15 g,菟丝子10 g,芡实10 g,车前子5 g,党参15 g,肉桂3 g,苍术10 g,益母草15 g,泽泻10 g,猪苓10 g,桂枝10 g。水煎内服,共7剂。
2017年10月10日四诊,患者睡眠较前好转,心悸好转,仍有梦。口干仍有,无口苦,大便仍偏软。末次月经是9月26日,持续7 d,本次经前3 d开始肿胀,10月1日肿胀消退。自感本次行经肿胀持续时间较前缩短,肿胀程度略有减轻。舌淡红,苔薄白,脉沉弦迟。辨证为肝郁脾虚证,处方:当归10 g,酒川芎10 g,酒白芍15 g,茯苓30 g,土白术20 g,泽泻10 g,菟丝子30 g,巴戟天30 g,柴胡15 g,枳壳10 g,人参10 g,黄芩10 g,法半夏10 g,炙甘草5 g。水煎内服,共7剂。
2017年10月31日五诊,患者末次月经是10月23日,本次经前无肿胀,经行第1天开始肿,持续6 d,程度较前明显减轻,穿鞋袜基本不受影响,仅感下肢微肿胀,未及凹陷性水肿。下肢腓肠肌抽搐,经前胃脘灼热痛,嗳气,口干泛酸。舌淡胖,舌苔厚腻偏黄,脉沉迟。辨证为脾胃不和,处方为苍术10 g,厚朴10 g,陈皮10 g,砂仁(后下)5 g,党参20 g,麸炒白术20 g,茯苓20 g,佩兰10 g,姜竹茹5 g。水煎内服,共7剂。
六诊、七诊患者症情稳定,方药随证加减。
2017年11月21日八诊,患者睡眠较前好转,心悸好转,仍有梦。口干仍有,胃脘胀闷,嗳气,无口苦,大便仍偏软。舌红,舌苔薄白,脉弦。辨证为肝气犯胃。处方:柴胡25 g,人参10 g,黄芩10 g,法半夏10 g,甘草5 g,大枣10 g,防风10 g,白芷10 g,浙贝母10 g,紫苏梗10 g,陈皮10 g,干姜皮10 g,沉香5 g,蚕沙(包煎)15 g,益母草15 g。水煎内服,共6剂。
2017年12月12日九诊,患者末次月经为11月23日,5 d干净,此次经前双下肢浮肿不明显,经后略有下肢浮肿感。舌淡红,舌边齿痕,舌苔薄白,脉沉弦。辨证为肝木克土,水湿泛滥,处方:陈皮10 g,柴胡15 g,川芎10 g,香附10 g,枳壳5 g,酒白芍30 g,炙甘草5 g,大腹皮10 g,茯苓皮15 g,干姜皮10 g,桑白皮10 g,土白术30 g,苍术10 g,蚕沙(包煎)15 g。水煎内服,共7剂。
2017年12月19日十诊,患者近日已近经期,未见肿胀。心烦,睡眠不安,舌暗红,苔薄白,脉弦。辨证为气血瘀滞,处方:桃仁5 g,红花5 g,当归10 g,川芎10 g,赤芍10 g,酒川牛膝10 g,柴胡5 g,枳壳5 g,甘草5 g,茵陈10 g,桔梗5 g,防风10 g,泽兰15 g,益母草15 g。水煎内服,共7剂。
随访3个月,患者诉经行前后下肢肿胀感未发生。
按:本例患者水肿发于行经前、经期,初诊时正值经后,下肢未见浮肿,以眠差、多梦、夜间惊悸易醒为主症,分析其病因病机,脾失健运,湿浊内生,蕴久化热,胆为热扰,失其宁谧,故失眠多梦,惊悸易醒;胆热犯胃,胆胃失于和降,故口苦;结合患者舌脉,冉主任辨其为肝胆湿热证,湿热郁结肝胆,肝失疏泄,气机升降失常,脾失健运,土不制水而为肿。方用温胆汤加减。初诊方中以清半夏为君药,燥湿化痰,和胃降逆,臣以竹茹淸胆和胃,茯神宁心安神,枳实降气,陈皮理气健脾,茵陈、炒栀子、佩兰清热利湿。二诊时患者失眠多梦惊悸症状好转,以畏寒怕冷,腰背酸冷,四肢不温为主症,正值经前,尚未发生肿胀,方选化水种子汤合小柴胡汤加减。近代《中医妇产科学》[5]说:“因经前、行经时气血下注于胞而为月经,月经乃血所化,赖气以行,脾肾两脏为气血生化之源,若素体脾肾虚损,精血不足,值行经之际脾肾更虚,精血愈亏,则气化行水失司、水湿生焉,因而浮肿”。即“气行则水行,气滞则水停”。气机升降出入,与肝主疏泄关系密切,肝疏泄失常,气机不畅,则血行瘀滞,肺、脾、肾不能各司其职,水液滞留,溢于肌肤而为肿,故于经前用小柴胡汤疏泄肝胆之气。患者畏寒怕冷、腰背酸冷、四肢不温为脾肾阳虚之象,故用化水种子汤温肾健脾,化湿利水。加益母草、泽兰活血通经,全方疏泻肝胆,温补脾肾利水。三诊睡眠、口苦较前两诊好转,可见肝胆湿热已去,但恶风怕冷,既往经前10 d出现下肢肿胀,本次经前3 d开始出现下肢肿胀,脾虚不能制水,水湿壅盛,必损其阳,久则及肾,脾肾阳虚,不能化气行水,膀胱气化失常,开合不利,水液潴留而为肿,故选方在二诊方药基础上去小柴胡之疏泄,加五苓散温补脾肾,通阳利水。四诊患者行经肿胀持续时间较前缩短,肿胀程度略有减轻,但仍有多梦,口干、大便偏软等症,故以养血调肝,健脾利湿为法,方选当归芍药散合小柴胡汤加减化裁,当归、川芎调经血并兼补虚,白芍养阴柔肝,白术培土养木,茯苓、泽泻渗湿利水,巴戟天、菟丝子补肾益精,小柴胡汤疏肝,全方养血柔肝,健脾渗湿,体现了肝脾两调,血水同治的特点;五诊患者经行肿胀,肿胀程度较前明显减轻,经前胃脘灼热痛,嗳气,口干泛酸,故以理气健脾和胃为法,方选平胃散合四君子汤加减。胃为阳土,喜润恶燥,以通降为顺,脾主饮食精微的运化,以升为常,二者气机升降失常,气机阻滞,不通则痛,故以苍术、厚朴燥湿健脾,行气除满,陈皮、砂仁醒脾开胃行气,党参、白术理气健脾,茯苓、佩兰化湿和中,竹茹清热除烦。六、七诊患者症情平稳,诸证向愈。八诊患者胃脘胀闷,嗳气,大便偏软。脾胃同居中焦,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共司饮食水谷的消化、吸收与输布。脾主升清,胃主降浊,清升浊降则气机调畅。脾湿则其气不升,胃燥则其气不降,故见胃脘胀闷,大便异常。和胃降逆,可使胃气得降,脾气得升,水液输布得以正常运行。脾胃升降枢机也有赖于肝之疏泄,肝气郁结,不得疏泄,横逆犯胃,气郁则胀,故见胃脘胀闷,嗳气,且此时正值经前,故冉主任治以疏肝理气和胃为法,方选小柴胡汤疏肝和胃,再添防风、白芷、紫苏梗祛风除湿,浙贝母、陈皮清痰热,干姜皮利水消肿,蚕沙和胃化湿,沉香行气止痛,益母草活血调经。九诊患者此次经前双下肢浮肿不明显,经后略有下肢浮肿感,冉主任认为应以疏肝健脾、行气化湿、利水消肿为法,方选柴胡舒肝散合五皮饮加减调和肝脾,行气利水。十诊患者正值经前,未发生下肢肿胀,心烦,睡眠不安,舌暗红,苔薄白,脉弦,为气血瘀滞之象,瘀热扰心,故见心烦失眠,又恰逢经前,妇女经期,气血下注于胞宫,冲任瘀滞,经络不通,加之经期正气不足,风湿之邪侵袭人体经络,经络气血运行受阻,易发为浮肿,故拟血府逐瘀汤加减活血行气化瘀。之后随访3个月,患者诉经行前后下肢肿胀未再复发。
5 结语
经行浮肿病机复杂,多以虚实夹杂,涉及肝、脾、肾等多个脏腑,病程缠绵难愈。冉青珍主任治疗此类疾病多从肝、脾、肾诸脏腑的功能协调,以及各脏腑与水湿运化的关系入手,以补脾肾,利水消肿,疏肝健脾,活血化瘀立法,在全面调整脏腑功能的基础上,顺应月经周期的气血阴阳变化,方证相应,故取得良好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