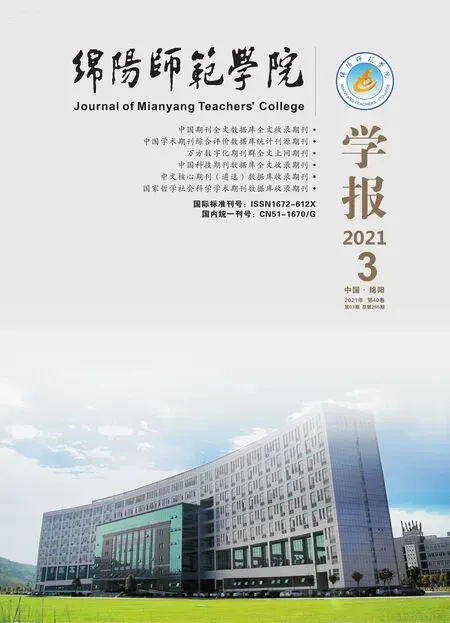严肃精神与时代现场
——论郑小驴长篇小说《西洲曲》与《去洞庭》
秦红玉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06)
近年来,“80后”作家群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中流砥柱,这一代作家是在国家急剧变革中成长起来的,社会的多重因素造成了他们作品叙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中,一批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家,他们生长在农村,成年后因求学和工作的需要到大城市谋生。家乡和现代都市的极大反差让这群带着泥土芬芳的质朴年轻人感到无所适从。一方面,他们渴望在现代化社会生活中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被浮华都市迷乱双眼,深陷“过去”与“未来”的间隙无法脱身。郑小驴是这群青年作家的典型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梅山文化中的“鬼魅”若隐若现,对湘土大地流露出无限的亲近与依恋。在其文本的诗性叙事、隐喻文字背后,是他对青年个体命运的遭际和人生无常的尖锐洞悉和深切反思,并以作家个人的方式对时代都市、外部世界进行反抗。《西洲曲》和《去洞庭》分别出版于2013年和2019年,是郑小驴目前仅有的两部长篇小说。从家族故事的“鬼魅”般倾诉以及农村计划生育残酷历史的单一叙述,到深切反思都市个体的内心畸变和世界现状,郑小驴小说的流变敏锐且深刻,贯穿其作品始终的是文本背后早已超越单一“自我”,转而聚焦时代内核的现实主义精神。
一、本土性:“鬼魅”叙事与湘土遗风
郑小驴是湖南隆回人,从小受到湖湘梅山文化的浸润,他的文字自然也定格在这片土地之上。梅山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巫傩文化的遗存,似巫似道,以鬼魅气质为其特征。青年批评家金理在评论文章《郑小驴的鬼魅叙事》中细致分析了郑小驴作品中的“怪力乱神”与“精神旷野上的‘孤魂野鬼’”[1]。在这些鬼影重重的小说中,郑小驴将本土文化与精神实质相融,在一次次迷离恍惚、人鬼莫辨的描述中,我们逐渐看到那些困囿于自我分裂中的个体,感知到他们的恐惧和痛苦。优秀的艺术创作应当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现实的大地。郑小驴正是以湘楚土地为依托,以触摸大地的姿态,对文化传统之根予以深刻的探寻。
《西洲曲》是郑小驴27岁写的第一篇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内心孤僻又敏感多疑的小男孩,在7岁的雨夜听到了河边传来的沉痛呼喊声后,内心产生的惶恐不安和对外界的质疑。在心情难以缓解的某个傍晚,男孩跑进了一个荒凉的墓地,见到一个身穿黑雨衣举止怪异的人“钻”进了坟墓,并因此与其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愫。在这部小说中,鬼魅巫傩并没有作为现实意象在文本故事中直接出现,而是以一种雾状形态弥漫在叙事空间里,充斥着小说主人公“我”的内心世界。郑小驴借自己对计划生育时期的青涩回忆,带着梅山文化的怪力乱神之气,讲述了一个带有湘土地域色彩的故事。这部被“鬼气”所“侵蚀”的作品,虽谈不上阴森可怖,但读来也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整个故事叙述如“招魂一般”,仿佛无时无刻不在发出“凄厉的哭号”,“仿佛这个世界在他眼中不复存在”一般[2]12。郑小驴以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为依托,在文本叙述和情感宣泄中对鬼神巫傩表达了一种亲昵。这种状态是自然地从骨子里发出的,根源于生养他的这片神秘的湘土。小说中“我”无数次去墓地与“他们”(灵魂、黑衣人)隔空对话,“我一有愤懑和苦闷的时候,总会到这里来坐一坐。好心情意想不到地在这里产生了,那些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灵魂不再背负他们沉重的肉身,可以充当我忠实的听众”[2]15。在现实社会无处排解压抑委屈的“我”,却在墓地里找到了皈依感。“我”不仅给墓地里遇到的神秘黑衣影子“勾勒出一幅迷人的模样”,还觉得“即便是荒草,因为绿得发油,也呈现出一种令人愉悦的美来”。墓地“四周安静得只剩下我的心跳声,这种美,让人萌生出痛哭一场的冲动”。尽管这里毫无“人气”,但却让孤僻沉闷的“我”有了倾吐的欲望、有了安稳的依托[2]13。
2019年,郑小驴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出版了。《去洞庭》承续了他一贯的“湘土气质”,神秘梦幻的“洞庭”成为故事情节的中心。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史谦从开始准备“去洞庭看一场日出”到最后回到“他们命中的危险的归宿(洞庭)”。农村男孩小耿从洞庭走出来,兜兜转转又回到洞庭等等。故事的每一位主人公看似有各自的生活轨迹,但“洞庭”作为地点、作为依托一直贯穿故事的始终。小说的标题“去洞庭”可以说是人物内心的整体趋向。这些围绕洞庭发生的故事,自然而然地带有浓郁的湘土芬芳。《车祸》篇小耿开车准备逃回家,城市里“一路旖旎的风光终于被抛掷身后,他呼吸到了一股熟悉的亚热带气息”[3]12,这是洞庭旁的故乡。憨厚老实的小耿因为生计背井离乡到城市打拼,逐渐走上歧途,做下绑架、游行、恐吓、杀人等诸多恶行,但这样一个恶徒的内心仍然有着对故乡的眷念,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赚钱替患严重尿毒症的父亲治病。每做一件错事一想到故乡的亲人,“内心深处的恐惧不断上涌,忧惧交加中,最后禁不住哭了”[3]17,“故乡雷击闶世代渔民,民风淳朴,没出过杀人越货的事,他做梦也没想到要以这种方式去面对故土,面对亲人”[3]215。
郑小驴作为湘籍作家的中坚力量,其作品风格根植于湘土大地,亲近现实,亲近经典。他的作品带着沈从文式的湘土遗风,又饱含梅山地域文化中的鬼魅色彩,集神秘与质朴为一体,在故事徐徐铺展的过程中,再现了本土经典文化的独特姿态。但作为新世纪作家,他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一些现代性元素。与其将这种现代性的植入视为“入侵”,倒不如说这是郑小驴主动地接受新质方法,在其作品中运用现代性的叙述模式进行写作的实验,从而传达面向时代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
二、新质性:创伤体验与现代性叙事
不同于其他“80后”作家,郑小驴保持着他对大历史的浓厚兴趣和执着书写,远离主流的“经验叙事”“伤感叙事”等模式,保持清醒的认识和自觉的距离,将社会价值观纳入个人思索的范畴,对社会现象进行理性评判和深度反思。郑小驴作为计划生育中“超生”的一员,深切地体验了那段历史,创伤记忆永远地烙印在其思想深处。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在著作《沉默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中将创伤定义为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而主体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反映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事后将以幻觉或其它侵入的方式在主观记忆中反复出现。计划生育的这段创伤体验正是以记忆闪现、噩梦连连的形式在郑小驴的意识世界中再现。作为“幸存者”的他同时存在于“两个现实,两个时间点上。现在的经历常常是模糊的、感觉是迟钝的,而侵入的过去记忆则是强烈的、清晰的”[4]92。创伤经历所造成的生理痛感会逐渐褪去,但心理上的创伤是作用于精神层面的,是对灵魂的一次无法修复的重击。创伤记忆无法被现实生活磨合,导致了“幸存者”内心的“双重意识”——身体与精神的分离。因此,沉痛的创伤叙事成为《西洲曲》行文的重要手段,但我们在把握叙述模式的同时,更应该着眼于创伤本身的社会性。郑小驴通过对个体创伤体验的召唤和重构,透过那段不幸的历史关照被新时代遮掩的人心之上的重压,这是郑小驴对他那一代人的集体身份的认同。
《西洲曲》是继莫言的《蛙》之后为数不多的“计划生育”题材的长篇小说,“相对于其他叙事类型,当代计划生育题材小说呈现出小众化的特点——在文本数量上并不算多,产生影响的小说更是少之又少”[5]。不同于《蛙》的魔幻性书写,《西洲曲》更加直白,将矛头直指制度背后人性的阴暗和自私,因此,《西洲曲》也成为当代长篇小说的“异类”。但早在郑小驴22岁创作的短篇小说《鬼节》中,他就选择了创伤性叙事模式,既是对童年时所见悲惨经历的艺术再现,也是对时代记忆的集中呈现,个人体验与集体经验构成了他创作的基础。郑小驴抛开“80后”作家惯用的空想式叙事,“借用那段青涩的回忆,书写他们这代人对计划生育的记忆与看法”,既然“无法忘掉计划生育给童年时代的恐惧与不安”,那就直面这段“八○后这代人的集体记忆”[2]261,忍痛揭开早已结痂的伤口,使其赤裸裸地、血淋淋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西洲曲》立足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通过小男孩“我”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石门和青花滩地区,由计划生育政策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小说采用双线并行的手法,一边写姐姐左兰的经历,另一边以“北妹跳河自杀”为中心向前后铺叙北妹跳河的原因和北妹丈夫的复仇。从家族故事的大历史叙事开始,郑小驴对时间空间的掌握早已跳出“80后”作家的群体,回溯式和并行式交杂的叙事模式在他的小说中遥相呼应。“我”作为所有事件的旁观者、间接参与者,对亲人朋友们的遭际无疑是怀着异常沉痛的心情,本就敏感多疑且处在成长困惑期的“我”,面对突如其来又无法应对的状况,内心的苦楚与现实的欺压所造成的双重痛苦,压抑得“我”喘不过气,由此造成的心灵创伤必然是痛彻心扉的。与其他“80后”作家的伤痛不同,郑小驴小说中的压抑和创伤源自生活、源于历史,既不是自我沉浸式的宣泄,也不是虚构的精神混乱。
从《西洲曲》到《去洞庭》,从家族历史叙事到个体故事追溯,小说中的现代性个体主义意识逐渐突显。郑小驴的小说创作不再困囿于单一的农村场景,从对乡村故事的再叙中走出来,着眼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融与排挤,从而自觉承担起批判社会的责任。与《西洲曲》的宏大历史背景不同,小说《去洞庭》更倾向于描绘身处农村—都市裂缝中的青年人,写他们身上的撕裂感和复杂性。《西洲曲》的“我”作为旁观者通过外在感观经历悲剧,《去洞庭》则从人物的内心去揭露人性的阴暗面和人际关系的脆弱性,以此传达作者对新时代人性变质的深切反思。叙述视角也从第一人称叙变为第二三人称,作者从文本中完全抽身而去,在故事发展中再找不到零星半点作者自身“回忆”叙事的影子。郑小驴将自己的主体意识深藏在文本背后,将自己的主观情感完全抽离,客观淡然地旁观笔下人物的经历和遭际,写时代中不同个体的同质悲剧,展现他们平常生活表象下的异常精神状态。郑小驴通过对故事结构的灵活把握,从历史视角叙述转移到人性的全知性叙述,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沉溺于现代都市迷惘痛苦的个体得到突显。
三、“严肃”性:现实主义精神与新时代反思
郑小驴在《去洞庭》后记中提到《阿飞正传》中的台词,“我听人讲过,这个世界有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一直飞啊飞,飞到累的时候就在风中睡觉。这种鸟一生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的时候”,“于我而言,写作和无脚鸟是一种无形的契合。写作停止之时,也是‘生’之终结”[3]229。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那位永不放下手中投枪的战士,一样的决绝,一样的痛彻心扉。郑小驴的小说是“80后”作品中的“异类”。他的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沉沉的黑气,仿佛让人又回到那个年代,触摸到人物的内心。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流行作家浮夸绚丽的文字和戏谑虚构的故事,他的小说是质朴、严肃的,这是真正的中国本土小说。郑小驴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他的作品又不限定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之中。在现代性新质的写作技巧背后,是贴合时代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思想没有困囿于新世纪的欲望之海和现象之林无法自拔。作品中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对人性内心的陌生化书写,让我们感受到了“80后”作家应有的人格坚韧性和文化紧迫性。
《西洲曲》后记中,郑小驴将计划生育这段历史描述成“一座黑沉沉的大山,横亘在我写作的前方,选择回避,显然不符合我的性格”[2]261。于是27岁的年轻作家勇敢地直面这段历史,将躲藏在国家体制后贪婪的施暴者狠狠地揪出,向他们“复仇”,就像北妹的丈夫谭青向计划生育实行者们复仇一样。这些麻木不仁的“刽子手”“披着代表国家意志的合法外衣,有恃无恐地制造着一起又一起的暴力事件”。法律和道德的束缚在他们眼里形同虚设,郑小驴将矛头直指这些暴力的个人,但就像小说中的“复仇者”谭青一样,如此庞大的施暴群体又如何报复得完,结果也只能是胡乱从“千人一面的施暴者当中揪出具体的个人,以牙还牙”,不惜牺牲自己,“这场生存游戏最后以血腥收场”[2]262-263。北妹等被迫堕胎的孕妇、付出生命代价的谭青、被牵连的副镇长的儿子罗圭,都是这场“猫鼠游戏”中的牺牲者。“这样的暴力循环并不能终结悲剧,相反只会让更多的悲剧上演”[2]262-263,无穷无尽地发生在中国社会基层。《西洲曲》中的“复仇母题”是当代小说中常见的文学母题之一。郑小驴笔下的复仇是有力感的复仇,是交杂着血与泪的“自杀式”复仇,这更加能体现小说文字的锋利和残酷,展现社会现实的黑暗和惨痛。《西洲曲》中是“同归于尽”式复仇,《去洞庭》中亦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式的复仇。
《去洞庭》仿佛是中国当代的“罪与罚”,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的物质关系和频频出现的三角关系,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真诚岌岌可危(见图1)。小说中的每一个主人公都在欲望之海里沉沉浮浮:张舸因觉得东北小伙图们的家世配不上自己毅然与之分手,随后却因贪恋模样俊美的王竞先,沉迷在他编织的军人身份的谎言里,最后损失了所有积蓄(20万);农村小伙小耿为了筹父亲的治病费,到城市打拼闯荡,犯下滔天罪行,最终连父亲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婚内出轨离婚后的史谦与顾烨结婚又被出轨;顾烨婚内与作家岳廉纠缠不清,甚至连孩子都是岳廉的;而仅在一章节出现的顾烨的好友栗子,被丈夫家暴还只能“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忍气吞声。他们都是被现代社会撕裂的异乡人,笼罩在小说中的悲剧是具有普遍现实性的。个体的悲剧命运丝毫不会影响现代都市的灯红酒绿。人物内心的压抑感和窒息感穿透文字深入读者的内心,产生心灵共鸣。我们是都市中的一员,也正遭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挤压和侵染。“生活在这样复杂多变、暗流涌动的年代”,我们如何“看透世间本质”,如何拨开遮眼的云雾,如何不沦落为“制造云雾的人”,是值得思考的。在云雾缭绕的道路中找到“去洞庭”的道路是我们当下亟待解决的难题,然而我们同郑小驴一样,“眼前云雾缭绕,正处在‘通往洞庭的途中’”[3]234。

图1 《去洞庭》中复杂的各种关系
2020年10月24日,在长沙召开的湖南长篇小说研讨会上,郑小驴提到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所面临的困境——“透明的噪音”。“噪音”是指社会中繁复嘈杂的各式声音,当代人都被噪音洪水所淹没,最可悲的是生活在这样嘈杂社会中的我们,如何成为了一群听不见噪音的当地人,是早已习惯还是自我麻痹?“透明”是指我们当下社会的本质——透明的社会。透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人心之间充斥着怀疑,出现道德混乱。就如《去洞庭》里那一群痛苦挣扎的人,我们正处在一个“同质化监狱”里。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的监狱,禁锢着所有现代人的心灵。自我纯粹的本心被浓雾遮盖,压抑的、狂躁的内心世界得不到舒缓,最终只能是掉入悲剧的旋涡,且这个悲剧仿佛一个无休止的循环。深陷旋涡中的人就好像张舸一样,看着那一只“瓶中船”(自我),“好奇的不是它们怎么进去的,而是怎样出来”,“它被困在里面”,“只有把它放回水中,让它顺流而下,漂流到它该去的地方,那样的人生才有意义”[3]228。
四、结语
郑小驴秉持着严肃写作的态度,将自己从“按部就班的生活中”暴力拉出,置于这“过于喧嚣的孤独中”。“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或许一生都将处在抵达彼岸的途中”,他“更情愿站在美好生活的对立面,继续耽于幻想,在虚无中寻找乐趣,在文字中释放颓然”[3]230。郑小驴将自己放置在当代社会的“无物之阵”中,较之鲁迅的“阵”,或许当下的时代更加复杂多变,人性之下暗流涌动。此时,我们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认清自己。由于新时代飞速增长的物质文化,新兴科技写作与科幻叙事成为时代创作的主流。写作开始依赖博人眼球的素材和虚构科幻的模式,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当“远方”开始消失的时候,“陌生化”写作变得尤为珍贵。一旦文学失去它的审美性,那么文学就将永远失去它基本的活力。想象力丧失的作品,文学中的“他者”也会消失,文学理应高于现实的一部分便会轰然倒塌,跌落泥里,审美文学、现实文学将会变成消费文学、低俗文学。从郑小驴的整体创作来看,无论是创伤体验叙事的《西洲曲》,还是个体魂灵困顿的《去洞庭》,他都善于运用鬼魅性语言和现代性逻辑再现历史的真实。在对历史现实的不断反叛和思量过程中,现实主义精神的张扬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反思过去、关照当下、憧憬未来的文学途径。诚然,一篇优秀的长篇小说必定是根植于历史背景、反映时代特征、彰显现实精神的。而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每一件事必然跟其它事物联系在一起,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精神与肉体、私人利益与公共空间,繁复交错,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