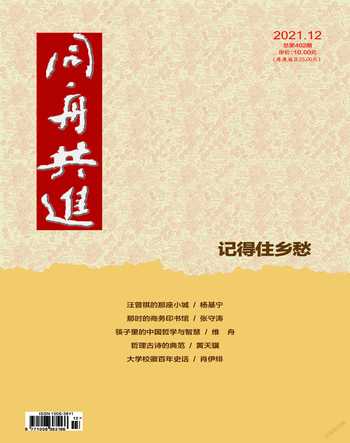“将军本色是诗人”
散木
1961年4月,著名词人及词学家、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承焘先生从杭州赴北京出席教育部召开的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据事后夏承焘的日记,他与陈毅在会上有过一番谈话:
晨九时方欲下电梯,得陈毅副总理秘书来电话,云陈副总理欲邀予与郭老、钱、马诸君叙谈,因告郭老诸君,候汽车来迓。不料十时许予方解衣据案写家片(家信),服务员来报副总理来。去年文代会听其报告,风采如旧。谓读过予所著《唐宋词人年谱》诸书。遍询予四人年龄,自谓今年六十,在此不能称老大哥。予闻其所作诗词,谦谓新旧杂糅,时时在改乙中。因纵谈最近在日內瓦作卢骚(卢梭)湖各诗;笑法国代表不读书;谓在日内瓦、巴黎买卢骚全集不得;谓卢骚回归自然之语,由闻法国传教士诵陶潜复得返自然之诗而来;谓政治由业务表现,学校必须重视业务,每日必有六小时工夫学业务……纵谈至十二时去,谓昨陪巴西古拉特副总统来沪,在京时于北京晚报所载消息知予等四人在此,百忙中抽暇来访,明日即离沪,将来有新著新诗幸相示云云。
当时夏承焘、郭绍虞、钱仲联、马茂元等学者正在上海科学会堂出席古典作品选讨论会,陈毅从《北京晚报》上得知此四人恰在上海开会,遂利用接待外宾的机会与众人聚谈。陈毅在会见夏承焘等人时的这一段话,迄今不曾见诸其它文字,但内容十分丰富和珍贵,如他自评其诗词创作特别是在出席日内瓦会议时所作之作品、笑谈西方谈判代表之窘态、纵谈卢梭文学及其来源等,均显示出陈毅元帅的风貌以及其时中央开展调整工作的方针和原则等。
三年之后,1964年12月,夏承焘先生专程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会议期间,他与众人余暇时讨论诗词写作,讨论毛泽东、陈毅等共和国领袖的诗作。
毛泽东和陈毅都是共和国领袖中著名的诗家,当时也都有作品问世,特别是毛主席的诗词,自此前1957年元月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18首诗词之后,成为中国诗词界最大的热门。及至翌年即1958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在《诗刊》发表的18首诗词之外,又增加了他在1957年新填的《蝶恋花·答李淑一》。随即1959年文物出版社在此基础之上,另增加了毛主席新发表的《七律·送瘟神》(二首),出版了线装本的《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至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以线装宣纸本、毛边纸本、平装甲种本、平装乙种本等四种形式出版了收录有毛主席37首诗词的《毛主席诗词》。一时间,毛主席诗词大热,而“注家”也行动起来,特别是夏承焘先生这样的诗词研究大家,更是关注备至,倾注了极大的心力。
至于陈毅,素有“一代儒将”“元帅诗人”之美誉,无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纵横捭阖的外交场合,他往往挥笔书写瑰丽诗篇,抒发豪情壮志,从未辍断,而自1957年1月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诗歌杂志《诗刊》诞生后,他便在多种场合甚至外事活动的间隙,不仅予以过问,而且径直提出意见,还将自己的作品交给《诗刊》发表,以示支持。他的这些作品也迅速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如《赠郭沫若同志》《莫干山七首》等,“将军本色是诗人”,博得了众多读者的喜好。
1959年4月,全国政协及人大召开会议,陈毅听说借此次文艺界人士来京开会之机,“诗刊社”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召开诗歌座谈会,陈毅当即表示自己也要与会,并在开会时谦逊地一再请别人先发言,随后以一位诗人的身份谈了一些关于诗词创作的看法,如议及诗词创作的艺术表现,他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三分人才七分装”,即须注意表现形式,他希望大家都来“勤学苦练”,即“无论新老作家,都要从基本练习入手”等;在讨论到如何评价“五四”以来诗歌的创作时,陈毅既充分肯定了“五四”以来新诗的成绩,但又认为其“反映革命,反映得还不够;反映生活,反映得还不够”,至于其流弊,则是“重视外国的,轻视中国的;重视古人,轻视今人”。在谈到诗的用韵时,陈毅以为“诗的平仄和用韵是自然的,废不了的。打破旧时的平仄,要有新的平仄;打破旧时的韵,要有新的韵。我不同意反对平仄和用韵。诗要通顺流畅。有韵的,注意了流畅的,朗诵起来效果就好些。形式问题,可以几种并举,各做实验”。所谓“旧瓶装新酒”,陈毅主张诗词创作可以不废旧的形式。此外,他特别反对庸俗地理解和欣赏诗词,并以毛主席的诗歌为例,他说:
艺术就是艺术,写诗就是写诗。上海有人在毛主席诗中寻找战略思想,就有些穿凿附会。毛主席诗词有重大政治意义,但还是诗。有人问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两句,完全是说,这支军队得救了,将要胜利到达陕北了。”
不久后的196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曾举行了一个诗歌座谈会,陈毅又在会上有所主张,并现身说法:
写诗要写使人家容易看懂,有思想,有感情,使人乐于诵读。
我写诗,就想在中国的旧体诗和新诗中各取其长,弃其所短,使自己所写的诗能有些进步。
后来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表述了相同的看法:
又诗要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1964年12月21日,夏承焘参加政协会议的教育界小组座谈会,随即列席人大第三届大会,“再见到毛主席”,是夜,他竟“夕梦与毛主席论词,甚奇”。翌日,夏承焘列席人大会议之后,又与陈毅有一番难得的聚会,并聆听了陈毅的又一番诗论。夏承焘在日记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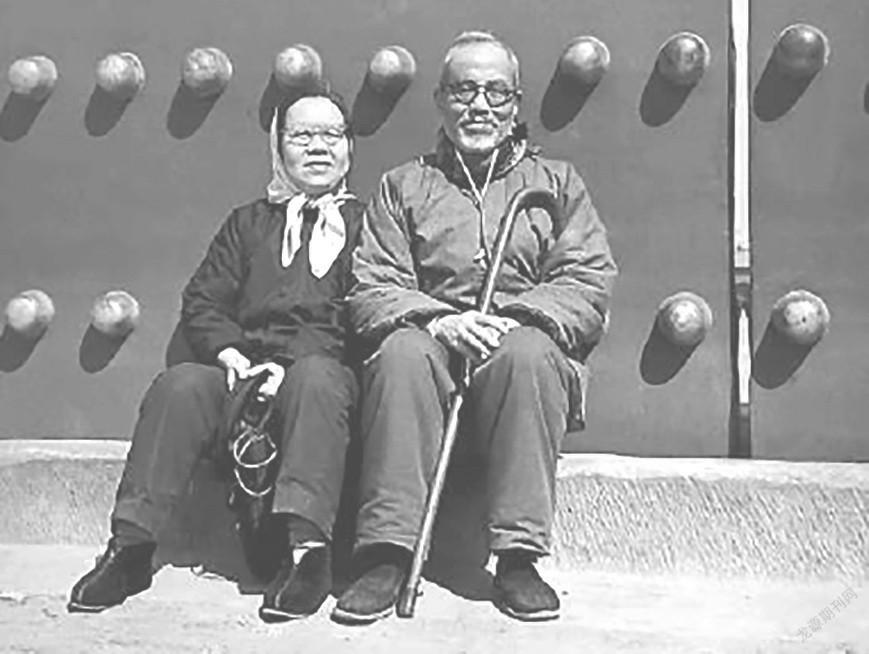
七时夕餐后上楼,小方同志见告,陈毅副总理来看予,顷在马湛翁(即马一浮)房,八时会于小客厅,自六一年夏间见于上海国际饭店后四年矣。问郭、钱、马(即郭绍虞、钱仲联、马茂元)近况,尚了了不忘。云已见予《龙川词笺》,谓少予一岁,今年六十三矣。
予问毛主席诗词,谓早年在军中见其作品约百首左右,今仅存廿余首,殆久已忘之。主席好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好苏(轼)、辛(弃疾),亦好秦(观)、周(邦彦)词,不喜梦窗(吴文英)、草窗(周密),不主纯用白描,好象征性。尝闻其在马上诵“飞絮落花时节怯登楼”,亦时哼“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诸句。主席自谓少时不为新诗,老矣无兴学,觉旧诗词表现感情较亲切,新诗于民族感情不甚合腔,且形式无定,不易记,不易诵。
陈(副)总理谓早年亦曾为新诗,后好为旧诗词,曾问郭老能背自作新诗否,郭曰不能。又谓公事稍闲,必读唐宋诗词,数十年不废。
主席少时古典文学工夫深,诗文词能背诵者多,书法尤其素好,今尚以此自娱,大草好临怀素。予问是否怀素《自叙》?曰然,尤多临怀素之《秋兴》八首。予自喜亿(臆)中。
又问(副)总理所作革命词,谓约有百首左右,当抄出请教于方家。当时以腹腿负伤甚重,不能随军长征,留在江西大庾山中,联系地下工作,被蒋军、日军围困,尝一度绝粮,又不能举火,摘杨梅及蛇充饥,故所为望江南词有“三月过,肉味不曾尝,烹蛇二更长”之句。地民不得送粮,只能于衣袖中装少许炒米相馈。予问“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句何时作,谓当时只二卫士共生死(其一今已当将军),互约如被困当拼死数人,决不作俘虏。幸深山草盛,有时只隔数十步,卒未被发现。其后转入敌后,得人民群众力,日本鬼子变成瞎子,便甚便当。因念文天祥在江西全无群众,故数日即被俘。解放军与群众是骨肉之亲,当时作诗有“你是恩情亲父母,我是战斗好儿郎”之句,当时惟闻长征军西上不利消息,甚为忧虑。
……
谈作新词,谓须往农村与老农同生活,自能得到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学问。

不久后的30日,夏承焘又记录了陈毅的一段谈话:
午陈毅同志招宴于政协礼堂第三会议室,马一浮、熊十力、沈尹默、褚保权夫妇、平杰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傅抱石同席。
与尹默初识,其双目几失明,出所书词数首与陈,自谓于词为外行,陈谓内行不出,亦成外行。此谑语亦有意。
陈又谓川剧有《满江红》等词,不知与词乐有关否。以词体反映新现实,有生命力,严四声则无意义。
又谈及榆生,嫌其胸襟不大,嘱予与熊翁劝其多多出行,看看新社会,不必死钻宋词。
一时宴散,与马、熊两翁同车归,陈于两翁亦有莫“抬扛”之谑,两翁不以为忤。
上述陈毅的讲话,涉及诗词创作、古今诗词的评论(特别是对毛主席诗词的评论),以及自己的一些诗词的写作背景,还有对几位词家的关怀(沈尹默、龙榆生),可谓亲切有加、光风霁月。值得一说的是,夏承焘不仅与陈毅有诗词之交,他还通过陈毅多方了解了毛主席的诗词创作之源和诗论,后来他还与主席秘書胡乔木谈论过毛主席的诗词。
夏承焘的这些日记,为我们了解共和国领袖们的“文学侧面”,提供了珍贵史料。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