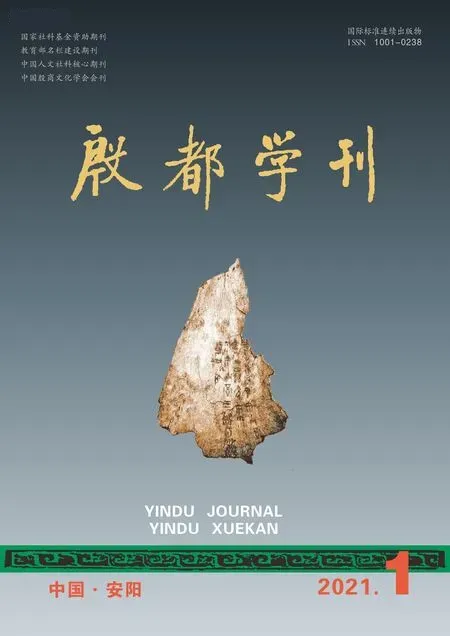关于整理与研究殷墟甲骨文的方法及其它
彭裕商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不久前看到常玉芝先生的文章《殷墟甲骨“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说评议》(以下简称常文)(1)常玉芝:《殷墟甲骨“先用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说评议》,《殷都学刊》2019年第4期。,文中对先以字体分类,再进行断代的方法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根据字体对殷墟甲骨进行分类,由于其观点直接关涉到对殷墟甲骨进行整理与研究的方法问题,故笔者撰此小文,对整理与研究殷墟甲骨的某些方法进行讨论与说明,供大家参考。
由于常文涉及到的是类型学方法与年代学方法,故本文着重对这两种方法进行讨论,以弄清其性质、功用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类型学方法与年代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器物之间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关系,即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前者表示某些器物时代相同,后者则可展示器物之间的相对早晚及发展脉络。类型学即用以找出器物之间时代相同关系的方法,因为类型学是建立在形制相同的器物年代也基本相同的判定之上。对于殷墟甲骨来说,字体是具有类型学性质的。据研究,殷墟甲骨文是由专门的刻手刻写出来的,因此字体相同就可以认定为同一刻手所刻,其时代相同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为什么要用类型学的方法对器物或甲骨文进行整理呢?这项工作有什么必要性呢?这就关涉到类型学方法的功用了。大家知道,零星的器物所能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如能将其联系成群组,则其所能提供的信息将会大大增加,这将有利于下一步的研究工作。这有点像公安机关侦察案件,凡是同一人或同一伙人做的案件都要作并案处理,并案之后,提供的信息就多了,这将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对出土器物的整理与此类同,比如某个单件器物由捡拾所得,我们对其年代、用途等一无所知,但我们如通过器形将其与其它多个器物联系成了群组,在这个器物群组中,如果其中有一件得以明确其年代与用途,则整个群组的多件器物的年代与用途就都明确了。殷墟甲骨文的情况也是这样。单片的甲骨文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如通过字体将同时期的甲骨文联系成群组,则其所提供的信息就会大大增加,这样就可在此基础上作多方面的研究。所以,不论是考古出土的器物还是殷墟甲骨文,对其整理的第一步都是使用类型学的方法,将其联系成群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对殷墟甲骨文来说,根据字体将同一人所刻的卜辞联系成群组,然后总结出称谓系统、所见人物、事类以及考古学依据等情况,在此基础上就可进行年代学、排谱系联、碎片缀合、重大史实等多方面的研究。也就是说,用类型学方法对殷墟甲骨文的分类整理,是其它一切研究的基础,它不仅仅只服务于甲骨断代。
殷墟甲骨文年代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三项,即称谓系统、考古学依据、卜辞间的相互联系。称谓系统是在分类的基础上,从各个群组的卜辞中总结出来的所有称谓,称谓系统可以指示时王在商王世系中的位置,由此可以比照古书以确定其时代。考古学依据提供一切与甲骨时代有关的考古材料,由此可以考见甲骨的相对早晚。卜辞间的相互联系包括各类卜辞之间的所有联系。有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联系可指示某些组类卜辞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并存,纵向联系可指示某些类卜辞的相对早晚。其具体内容,包括卜辞记载的事件、人物、国族以及一切形式上的演变,如钻凿形态、发展演变脉络清楚的字体等,由此也可推定各类卜辞之间的相对早晚。关于三者各自在年代学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及其性质特点,我们在《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以下简称《分期》)一书中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2)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23页。此不赘述,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第三项,卜辞间的相互联系。
关于卜辞间的相互联系,须要注意这样的现象,即A群卜辞与B群卜辞相联系,B群卜辞又与C群卜辞相联系,但A群卜辞与C群卜辞之间基本没有联系,这种现象就说明B群卜辞介于A群与C群之间,其在年代上与A、C两群均有部分同时,而A、C两群则不同时。比如我作为徐先生的学生,与先生同时,我的学生又与我同时,但我的学生没有见过徐先生,他们与徐先生则不同时,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常见的。
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起注意的是,类型学研究的方法与年代学研究的方法性质不同,目标各异,所解决的问题各不相同。所以我们使用类型学的方法,无论作怎么深入的研究都不会得到年代学方面的结果,同样,使用年代学的方法,无论怎么深入地研究也同样不会获得类型学方面的认识。
二、对常文所提意见的回应
常文对我和李学勤先生合写的《分期》一书提了许多意见,为了简明起见,我们不想对她提的所有问题都一一回应,这里只就其中比较简单的,费不了多少文字就能讲清楚的问题做一回应,其余的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可将常文所提问题与我们的书对照观看,相信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常文说我们“口口声声说要运用考古学的‘类型学’方法对甲骨进行分期断代,但他们根本不懂得运用‘类型学’对考古发掘遗物进行分期断代前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必须要明确出土物的地层关系……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就指出:‘运用器物形态学进行分期断代,必须以地层迭压关系或遗迹的打破关系为依据’。”“因此,违反地层关系的所谓字体分类,将毫无时代关连的某些组卜辞主观地用所谓字体将其生拉硬拽地连接在一起,难免有主观臆断的成分。”
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常文未清楚地认识到类型学方法和年代学方法两者各自的特点和各自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用类型学方法对器物进行整理的时候,是用不到年代学方法的。上文已经提到,卜辞的字体具有类型学的性质,在用字体对甲骨卜辞进行分类整理时,其依据是字体的特点和组合关系,而地层关系与之无关,因而所谓“违反地层关系的所谓字体分类”的说法是错误的。苏秉琦先生的话说的是“运用器物形态学进行分期断代”,是属于年代研究,当然“必须以地层迭压关系或遗迹的打破关系为依据”,我们年代研究的标准有“考古学依据”一项,与苏先生的话一致,苏先生并未说在使用类型学方法对器物作类型划分时要以地层的迭压打破关系为依据。
常文说我们研究卜辞年代的方法中,“考古学依据就是‘坑位’,‘各类卜辞之间的相互联系’,就是用字体将各类卜辞连接起来。我们在分析‘两系说’时已指出他们的所谓‘坑位’,实际上是指灰坑所在发掘区里人为划分的区位,是缺乏科学性的。下面的事实又证明,他们的‘类型学’即对字体分组分类,又是违背‘类型学’必须要以地层学为基础的规则的。”
首先,我们要说《分期》一书中的考古学依据绝不是发掘区里人为划分的“坑位”,《分期》中专门有“殷墟考古”一章,对殷墟文化的分期进行整理,后面对卜辞的年代研究都以此为基础,如对宾组卜辞的年代研究,就举出了YH127、YH76、YH006、YH126、E16、YH265、YH38等坑,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等方面,探讨了宾组卜辞的年代上下限。我们所说的“各类卜辞之间的相互联系”,也不是“用字体将各类卜辞连接起来”,关于此,我们已在书中和上文作了说明,因此,常文对《分期》的描述是歪曲的,与事实不符。常文还说我们违背了“‘类型学’必须要以地层学为基础的规则”,我们不知道这条‘类型学’必须要以地层学为基础的“规则”是何人定出来的。
常文说“对于李、彭二氏在《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中对各组卜辞的繁琐字体分类,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去花大量的时间,去一一查对他们对各组卜辞的细分类是否正确,一是因为他们没给出固定的分类标准,二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实际情况是我们在书中对字体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作了详细说明,并对分出的每一类卜辞都列出了特征性字体表,并在书末附表中举出了为数不少的例子,以供参考,只要平心静气地以特征性字体为依据,再参考为数众多的例片,相信大家都能得出与我们相同或相近的看法,怎么会说“没给出固定的分类标准”呢?上文我们已经指出,依据字体将殷墟甲骨文分为若干类别,是整理甲骨卜辞最基本的工作,是其他研究的基础,怎么会“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常文说我们认为师组大字类卜辞的年代应早于师组小字类是“纯系臆测”,列出的证据是我们以见于两类卜辞的人物出现的多少频率而得出来的看法。而实际情况是两类卜辞中人物出现的频率只是我们推测其年代早晚的一个辅助条件,对早期卜辞年代的推测更重要的是考古学依据。我们在分析师组大字类卜辞的时候,首先就指出YM362、YM331都出有文例、字体均近于师组大字类的卜辞,YM388随葬石戈上的文字也同于师组大字类,这几座墓葬的年代都属于我们划分的殷墟文化早期第二组,绝对年代约当武丁以前——武丁早期(或中期偏早),早于武官村59M1,后者的年代也已属武丁时(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考古》1979年第3期;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结合师组大字类和小字类卜辞中所见人物,来对师组大字类卜辞的时代进行综合考察,而得出大字类早于小字类的看法,并非仅仅只靠人物一项来推定其时代,人物只是在考古学依据基础之上的一项条件。而常文对我们所列重要的考古学依据只字不提,其对《分期》的批评是片面的。
常文还说我们在对各类卜辞进行断代的时候,出现了不少状况,“如前面说‘大字类’的人物有12个,后面却说‘大字类’只见其中的4个,‘其余的或见于师组小字,或见于宾组’,这是前后说法不一致。”
关于此,原文是这样描述的。
常文说我们举出的“师历间组”的例子《合集》34120、20038、34991三版卜辞的字体并不一致,在我们看来,这三版卜辞的字体结构均与我们所列“师历间组”的特征字表的字体相合,并且彼此书体风格也一致,其划归同一类是没有问题的,有兴趣的读者将这几片卜辞与书中所列“师历间组”的特征字表对照观看,相信能有所判断。常文又说我们划分的“师历间组”《合集》33077、20383字体都不小,不应分在小字类。其实,我们分类的标准主要是字形结构和书体风格,字体大小只是参考条件之一,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常文还说我们在书中提到的“师历间组”卜辞的重要称谓有“父乙”,而在我们举出的属“师历间组”的《合集》34120等十版卜辞中,没有一版上有“父乙”称谓。其实我们在书中第79页指出有“父乙”称谓的是《合集》32226,该版卜辞属“师历间组”,因此尽管《合集》34120等十版卜辞中没有“父乙”称谓,仍然不妨碍认定“师历间组”的重要称谓有“父乙”,为武丁称小乙。这也又一次证明了卜辞分类的重要性。

现将《分期》原文抄录如下,以供大家评判。

常文又质疑《分期》对师组卜辞的时代所作的分析,说“作者在论述‘小字类’的时代时,再举前面所列的‘大字类’与‘小字类’同版的七版卜辞,说‘小字类’卜辞的时代‘上限可到武丁早期’,‘下限至多到武丁中期’,至多到‘武丁中期偏早阶段’。对‘大字类’的时代,作者说‘上限应在武丁早期,下限不晚于武丁中期偏早阶段’,因此‘大字类’与‘小字类’时代相同。这就与作者的另一个说法,即说‘大字类’的‘下限已联系到小字类’相矛盾。另外,对出土于小屯南地的六块‘小字类附属’(也称‘师历间组’)卜辞的时代,作者说‘上限可到武丁中期偏早’。‘大致是武丁中期’。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小字类附属’等同于‘师历间组’,‘是师组与历组之间的连锁’,而‘历组’卜辞的时代被认定在武丁晚年至祖庚时期,那么,‘小字类附属’的时代即使不是在‘武丁中期偏早’,是在‘武丁中期’它也连接不到处于武丁晚期的‘历组’卜辞。”
常文这一段文字主要提出了三个问题:1.“大字类”与“小字类”时代相同,与“大字类”的“下限已联系到小字类”相矛盾;2.师组“小字类附属”等同于“师历间组”;3.“小字类附属”的时代即使不是在“武丁中期偏早”,是在“武丁中期”它也连接不到处于武丁晚期的“历组”卜辞。
现就以上三事说明如下:
1.《分期》82页指出,师组大字类的时代大致在武丁早期,“其上限应在武丁之初或稍有前后”,“其下限至多能晚到武丁中期偏早”,从未说过师组大字类的时代上限在武丁早期,“上限应在武丁早期,下限不晚于武丁中期偏早阶段”是我们对师组大字类附属所作的时代分析,常文将二者混为一谈,故有“‘大字类’与‘小字类’时代相同”之说。2.“小字类附属”是指可附属于师组的若干小字类卜辞,其中包含有小屯南地出土的六版师组小字卜辞和师历间组卜辞,这些卜辞彼此间有些小的差异,但都可附属于师组小字类,但这些卜辞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我们从未说过小屯南地所出的六版师组小字卜辞等同于师历间组卜辞。3、《分期》认为,师历间组卜辞大致是武丁中期的遗物,其上限可到武丁中期偏早。(6)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105页。至于历组卜辞的时代属武丁晚期到祖庚,是前此讨论历组时代时学者对其时代的大体看法,并未对其时代的上限做专门的探究。而《分期》则在此基础上,对历组卜辞时代的上限做了更进一步的考察,将该群卜辞中较早的历组一类进一步分为一A类和一B类,并指出与师历间组相联系的都是一A类,后者的时代大致属武丁中期偏晚,上与师历间组相衔接。(7)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266页。详情皆请见《分期》的有关部分。
常文还批评《分期》对师组卜辞时代的分析讨论,认为师组卜辞早已被陈梦家等学者考定其时代在武丁晚期至祖庚早期。其实对卜辞时代的考定历来就因人而异,有不同看法也是常见的,比如师组卜辞,胡厚宣先生就认为其中大字类的一部分可能早到武丁以前,(8)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序要。《分期》也从考古学依据、称谓、人物、字体等多方面,论证其时代当属武丁早期,详情皆请见《分期》的有关章节。
总之,常文对《分期》的指责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我们就不一一回应了,有兴趣的读者将常文与《分期》的相关部分对照观看,相信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