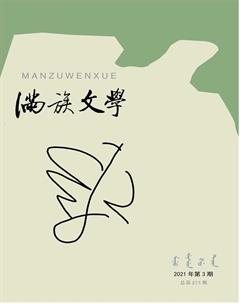满族书面文学流变(二)
关纪新
许多史笔都曾经充分肯定辛亥年间所取得的革命成功,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淡忘了一个并不算小的社会事实:在清朝垮掉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于满族这个民族的全盘否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满族遭受了后人难以想象的民族歧视。而此前作为一个世代以军人为铁定职业、以保国护民为基本使命的民族——满族,自辛亥年起,不仅失去了固有的谋生手段,在生计上被迅速推向了困厄与衰败的无奈境地,而且,还从此担起长久而不堪的骂名。许多年里,满人们不得不在惨淡的生存与肮脏的名声双重煎熬之下挣扎度日。
在清帝逊位前后,为了阻止动员革命时期大量排满宣传繼续在革命军中引发更多的过激举动,也为了化解旗族人民面临革命暴力产生的抵触恐惧心理[1],孙中山适时地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1912年9月,他又来到北京,会见满族上层及各界旗族代表,向他们公开承诺:“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2]“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3]他的这些话语,对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八旗民众,产生了一时的心理抚慰作用。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沿着孙中山设计的“五族共和”蓝图前行,他的有关国内各个民族都应享有平等政治权力的主张没有得到重视,其关于妥筹旗族生计免致失业的构想更是远未得到实施。接续下来的,是袁世凯在京城上演的“加冕”闹剧和封建军阀们围绕北京展开的无休止的割据战争,就连“先总理”的“天下为公”原则都遭到践踏,谁还把“五族共和”放在心里。
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情绪,并没有因辛亥年间的和平易政而收敛,反而持续地风行于市。将旗人们一概贬斥为“封建余孽”“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以及像“鞑子”“胡儿”“满狗”之类的咒骂[4]。当时在京城里流播极广的一则传闻是,有个在新政底下当差的衙役问一个路人:“你是什么人?”对方说:“我是旗人。”衙役动了火,举起鞭子就抽:“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紧辩解:“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衙役更加得理,高声呵斥:“你还敢再骑,我还得揍你!”其时,各类的读物、教科书、报刊也时常登载各式各样仇视和鄙视旗人们的言论,政府及学校等部门招收职员、教员的时候,对旗人几乎是不屑一顾;甚至在法庭办案时,也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加重对旗人一方严办的情况。
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本来按照旗族旧有的习俗是不习惯在各自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氏的,在此形势下,为了防备随时可能遭遇的歧视虐待,也都加冠了姓氏,假如从姓氏上头仍然比较容易被认出是满族的,有些人便不情愿地改用了他姓;为了寻求工作机会,不少旗人违心谎称自己是汉族人。当时,生存在南方各处的旗人们,更须事事留意,防备泄露了身份会遭致打骂嘲弄[5]。后来,虽然还有一部分满洲族的后裔顽强地维持着他们的民族成份,满族所包含的人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下降[6]。
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进程。人民共和国确认了国内多民族共存的政治格局,也确认了国家奉行的各个民族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原则。经过了若干年炼狱般的生存遭遇,满族这棵濒临衰枯的老树,生出了新的枝芽。政府正式认定了满族作为共和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满族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出现在了国家级的议事场所。
当然,满族的新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体制高层,对于该民族的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7]。虽然当时在全国的知识界以至于人民群众中间大力推行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教育却在许多情况下被明显地省略了,人们对国内民族历史和民族现实问题的感受和把握,有些还滞留在想当然和感情用事的阶段。关于满族,社会环境尽管较辛亥年间和民国时期宽松了许多,公开辱骂和诋毁满族的言论少了,但是,在部分主流知识阶层的心底,满族还是个明显地偏于卑陋的记忆符号,在主体民族的成员嘴边,亦时不时能听到对满族的刻薄褒贬[8]。
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已经接近一个世纪,而在社会的某些领域,依旧能看到对满族“不予落实政策”的深刻痕迹[9]。在我们从事满族文化和满族文学研究的过程中,时常会跟此种对满族的鄙薄态度倾向不期而遇。它或轻或重地构成了研究满族及其文化的障碍。关于满族、关于满族文化,迄今仍有相当多的事实与真相被历史的浮尘所遮蔽,为习见的偏执所误读。同时,在我们就某些满族文化及文学史料做出研究结论的时候,亦每每感觉到这种潜移默化然而却是相当顽固的社会舆论力量的掣肘。
20世纪,是满民族跌向命运低谷又逐步从低谷中走出来的时期,就他们的社会形象而言,早已不再值得夸耀。可是,说到他们的文学,我们却很难用“低谷”这样的字眼儿来比喻它。本来,单就满族历史来看,20世纪已不再是重要的一页。不过,为了诠释满族文学的流变,笔者却只能在本文多写几行关乎该民族的文学在这个世纪里走出一些特出步态的因由。
下面需要说一说满族的口承文化。
我们知道,人类学视野中几乎所有的已知民族,都经历过漫长的口承文化发展过程[10]。各个民族的文学有他们相通的内在发展规律。大约在人类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在语言已经产生并较为丰富的条件下,民间文学,这种通过人们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即告产生。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已知的民族都有他们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从问世的那一天开始,便成为切近反映人们社会生活和思考认知的产物,成为表达人们心理感受和审美倾向的载体。在人类共同体由野蛮蒙昧逐步走向文明智慧的不同阶段中,民间文学作为各民族的观念形态,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在由氏族社会向部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民间文学忠实地记录着初民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水平,先后出现了神话创作的繁荣和史诗创作的繁荣,具有为后世所无法摹仿无法替代的艺术价值。
自肃慎时代始,满族世世代代的先民,即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生存途径,捕鱼业、狩猎业和采集业,是他们长久维持生存的主要生产方式。而这样的生产方式,既是其得以久远繁衍生息之保障,同时,也是其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该民族的成员就是在此种生存状态下,获得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观念形态及伦理道德准则。曾有民族心理学的一项研究结论证实,较之于传统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渔猎民族成员们头脑里更少保守观念、更多创造精神与自主意识[11]。况且,东北亚地区冬季长久高寒,夏季日照强烈,山岭纵横,地广人稀,满族先人生息在这样严峻的自然条件下,也铸就了耐受严寒酷暑、不惧艰险困苦、粗犷剽悍勇猛奔放的民族性格。
千百年间,满族初民主要依赖自然物产为衣食之源,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压倒一切的关系。因为生产力低下,人们谙知不可以与自然力冒昧抗衡,遂在民族心理的深处产生了敬畏大自然、崇尚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的特有心态。他们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认定世间万物有灵,就是由此心态而生成的精神依托。民族先人们不仅要从事艰险的渔猎经济生产,还时常须面对部落纷争刀兵相向的存亡考验,于是他们特别笃信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基本内容的萨满教。
满族民间留存的口头文学作品,包括神话、神歌、说部、传说、故事、民歌和说唱文学等,既有自肃慎以来从历代先民那里传承下来的口头创作,也有在满族共同体问世之后的作品。这中间,更具有自身特色和价值的,当属神话、说部和说唱文学。
满族先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体现于原始萨满教的宗教观念,使得讲述世间万千神灵故事的口承文化系统,尤其丰富发达摇曳多姿。它不仅体现了该民族对于外部世界异乎寻常的想象力,也使其族众世代不败地葆有追逐带有奇思异想的叙事文学的嗜好。满族初民将万物有灵观念渗透到神话中,把宇宙分为天上国、地上国和地下国三层,认为人类就是阿布凯恩都里(天神)比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在创世神话《天宫大战》里面,有着关于三位始祖女神阿布凯赫赫、巴那姆赫赫、卧勒多赫赫开天辟地并降伏恶魔耶鲁里的描述,情节跌宕起伏,色彩神奇诡异,体现着原始艺术的无羁与张力。而神话《女真定水》等则展示了洪荒时代初民们与暴虐的大自然周旋到底的坚韧精神。《长白仙女》是一则族源神话,称本民族是天上仙女来长白山天池躬浴时,误吞神鹊所衔朱果受孕,生下婴儿的子孙,后被改称作爱新觉罗家族的始祖神话,乃为民间妇孺皆知。此外,有关民间神职人员萨满降妖禳灾的神话,也多有流传,其最为典型的作品是《尼山萨满传》[12]。
神歌,是满族民间文学中的重要一支,大多是萨满们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的吟唱,内容多为恭请图腾神灵或者祖先神灵的莅临。神歌均用满语表达,即便在后来本民族普遍使用汉语的条件下这一状况也有充分保留。歌词极尽崇敬与歌颂的情感,一般地讲,其间所演绎的情节并不复杂[13]。
“说部”,是满族民间口承文化特有的样式之一。它是一种由满族及其先民世代传承的长篇叙事文学,在其民族语言当中被称为“乌勒本(ulabun)”,有传记之义。“上个世纪以来,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为‘说部或‘满族书‘英雄传的称谓。‘说部最初用满语讲述,清末满语渐废,改用汉语或夹杂一些满语讲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各氏族都凝结和积累有精彩的‘乌勒本传本,如数家珍,口耳相传,代代承袭,保有民族的、地域的、传统的、原生的形态,从未形成完整的文本,是民間的口碑文学。”[14]“说部”在满族民众当中又被俗称为“讲古”,他们常说“老人不讲古,子孙失了谱”,体现出该民族重视自身历史传统延续的精神特点。“说部”作品常以本民族或本氏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题材,许多作品在传承目的上带有显见的教化性质。“说部”作品有的具有神圣性和特定性,是关于氏族内部祖先神灵或先人英雄事迹的讲述,只能在某个氏族内部封闭的处境下传播;有的则具有普适的娱乐性,可在广众场合演述讲唱,有几分相像于中原市井间的说书艺术。“说部”作品的篇幅都很长,往往须把整部大作品分成若干分部来逐次讲唱。由于满族传统文化留存在20世纪的特殊遭遇,“说部”作品的大量湮灭成了一个令人叹息的现实。目前搜集到的长篇“说部”有《东海窝集传》《乌布西奔妈妈》《红罗女》《金兀术的传说》《两世罕王传》《东海沉冤录》和《黑水英雄传》等[15],这些作品普遍的特点是情节震撼人心、人物个性鲜明、语言气势夺人。
在满族民间,还世代传承着一种叫作“德布德林”的说唱文学形式,其基本体式是以散文讲述与韵文吟唱交替出现。“德布德林”均为传统的满语创作,随着满族族众在晚近历史阶段较多地改操汉语,此类作品逐渐失传,迄今搜集到的“德布德林”均为残本,其中有流传于黑龙江流域描绘青年男女忠贞爱情故事的《莉坤珠逃婚记》,流传于嫩江流域叙述侠弟救姊故事的《空古鲁哈哈济》等。
满族先民的口承文化暨民间文学,有许多为中外其他民族早期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内容与价值,需要珍视和维护。
然而,文艺学的基本理论也告诉人们:与后来出现的作家文学相比较,民间文学具有一系列的特征(或曰局限性)。从创作和流布的角度去观察,它的集体创作性、口头传播性、环境变异性和世代承袭性,都是很鲜明的;而从社会功用的角度去观察,它的以实用性为基本要求而以教育性、审美性、娱乐性为辅的复合功用的性质,也是十分明确的。上述这些特征的形成,固然有利于民间文学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满足各民族人民在相当长久的历史过程中对这种文学样式的综合需求,但是,也正是这些特征本身,却又不可避免地给这种精神文化类型向更高层次的提升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由于民间文学对世界的艺术把握,在其历史起源处便同人类各项实践活动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艺术活动与非艺术活动完全混为一体,并且始终担负着过于繁重庞杂的社会功用,致使文学的本质性要求——审美,长期处在从属的而非主导的位置上,甚至有时还要遭到种种非艺术因素的侵入,故而造成了民间文学明显的“审美不纯净”。同时,民间文学的集体创作性和世代承袭性,使它的全部作品在创作主体那里,都只能是群体的而不是个体的,只能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而不是自觉的艺术创造,这就压抑、扼止和否定了那些个性的、自由的、能动的审美创造力,使纯真美好的艺术冲动被久久地无可奈何地捆绑在一个民族的极为稳定的传统共识之上,而得不到应有的飞升。另外,它的口头传播性和环境变异性又意味着,民间文学对一民族一社区的公式化文化积淀的依赖性是很强的,各民族民间文学要么长久地处在自我封闭彼此隔绝的状态,要么稍有(只能是稍有,而绝不会是远足的)外部交流,便势必要失掉它自己的某些原有的品质和蕴含,而不再具有民族间或社区间文化交流的全部意义。
人类文明无休止的上升,或迟或早地,总是能够有效地满足自己的超越欲望。文字——这种记录和传达语言推动人际交流突破时空局限的书写符号,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到阶级社会的初期,在一些民族之中相继产生了。书面文学创作即作家文学创作问世的先决条件,就此为人类所享有。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在完成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之后,又达到了把精神文化不同领域划分开来的局面,终于使作家与作家文学的出现成为现实。文学一经由民间口头文学羽化为作家书面文学,便为文学逐步进取以至最终逼近文学的本体价值宣示了美好的前景。作家文学渐渐摆脱了多重社会功用的羁束,把文学创作从人类其他所有活动形式中剥离开来、独立出来,把艺术的探求认作自己肩负的头等要务,而把教化功能、认识功能等实用性任务,逐步转交由其他类别的文字著述去完成;作家文学又是创作主体的个体化劳动,它使文学的审美追求以富有个性化富有自由创造的特征出现,从而也大大推动了文学作为自足的艺术形态的健全发展。作家文学在民族文学多元发展的历史时期,即开始展示了自己有利于寻找外向交流的运作机制;当作家文学的开拓道路上出现了世界文学一体化的曙光时,其内在的跨越民族和国度的审美潜能,则必将释放出更加璀璨的艺术光华。
满族的族别文学,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规律性的道路走过来的。
民族的作家文学,在其萌动生发之前,曾经受到本民族民间文化土壤的层层覆盖和重压,但是,作家文学一旦冲出重压破土而出,那丰厚的民间文化土壤,便又转而成为该民族作家文学所独占的一方优渥的滋养源。就满族文学来说,传统的民间口承文化在整个民族精神养成中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是深刻的,后世的满族书面文学作者,从先民遗留下来的萨满教的神话神歌以及大量的口头“说部”等作品中,继承了许多东西,而最为精髓的,则是充满无限遐思的艺术想象,长于缜密与宏大叙事的文学结构能力。
各个民族的书面文学向本民族民间文学及文化汲取营养的方式及路数是有差异的。有些民族的书面文学,比较习惯于做原有民间文学样式和题材的脱胎工作,作品还保留和展示着较多与民间文学作品“形似”的成份;而另一些民族的书面文学,则能够较多超越本民族民间文学一些表层特征,向本民族更为深沉的传统精神文化内里发掘,从而打造出一系列“神似”于传统的作品。
我们在观察满族书面文学流变的时候,常常会体会到,它的前一种特点或许较弱,而后一种特点却颇为突出。——这中间的诸多话题,可以留到后面去从容讨论。
注:
[1]1982年笔者参加山东大学主办的全国老舍学术讨论会时,蒙兰州大学马志洁先生(回族)告知,敦煌艺术的“守护神”、现代油画大师常书鸿,出身于杭州驻防旗人,辛亥年间他已弱冠,对革命军攻打当地旗营存有难以泯灭之惶恐记忆。后来笔者曾造访常老,老人证实此事说,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腦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2]见孙中山《在北京八旗生计会等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卷。
[3]见《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
[4]在南方的福建等省份,“漏刀的”,成了对旗人及其后代一种较长期的蔑称,意为他们都是辛亥年间在刀下漏网苟活下来的人。
[5]满族出身的京剧艺术家关肃霜(荆州旗人)谈到过,她幼年随父辈在武汉等处跑码头卖艺,父亲嘱咐,切记途中过关卡若有人叫你数数,数到“六”时千万不可以说“liu”而一定要念成“lou”,不然就会从你的京腔听出你是旗人来,轻则要挨骂,重则要挨打!
[6]刘庆相在《略论满族人口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一文(《人口学刊》1995年第5期)中,对不同历史阶段北京城以及全国的满族人口数字有所证实:清代初年“京师八旗人口数,据《清史稿》记载:‘京旗职官六千六百八十人,兵丁十二万三百有九人,据此数字可以基本推断出京旗人口数,如按每一旗兵平均家庭五口人计算,则京旗总人口为60余万人。”而“北京城在清朝末年京旗总人口达634,925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满族遭到压迫和歧视,很多满人为找一职业,不致饿死,而隐瞒民族成份,不敢提满族事儿,到外地区甚至还不敢承认自己是从北京来的,到1949年建国时满族人口仅剩了31012人。40年来满族人口减少95.12%,年均递减7.2%。”“……全国满族人口也由清朝末年的500万减少到建国前的150万左右。”
[7]早在1946年,在满族出身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向应病危弥留之际,毛泽东去看他,他对毛讲:“我是满族,以后,满族有什么事情,希望主席讲一讲。”毛泽东事后感慨地说,关向应同志那么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们党高级领导干部,但是他的民族感情,还是很深的。这件发生在共和国诞生之前的事,曾有助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认识满族人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共和国建立前夜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没有满族的代表,北京一些满族人因此哭了。毛泽东闻讯后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从第二届起,全国政协更正了这一失误。共和国初创之际,满族未获承认,直到1952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才在相关文件中首次回答了满族是否少数民族的问题:“满族是我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许多大、中城市(多是北方)中有满人居住。由于他们长期地和汉人杂居,其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特点已逐步消失;自辛亥革命以来,他们更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民族特点。有许多人已改变自己的民族成分,但是他们的民族情感,则仍然相当强烈地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各少数民族获得了民族平等权利,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生气象,许多地方的满人也纷纷起来,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并享有平等权利,这是自然的和合理的现象。我们认为,承认他们的少数民族地位,保障他们应有的民族平等权利,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团结满人和发扬他们爱国主义的积极性是有很大作用的。”(转引自赵书《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满族》,第16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满族区域自治的问题,虽在50年代即已提出并获中央政治局原则同意,周恩来还在当时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表示“满族要自治是肯定的。”然而,在国内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均获解决的情况下,满族区域自治问题,却被长期搁置,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先后在辽宁、河北、吉林等省建立了一批满族自治县。
[8]此处仅举二例。一是老作家冰心,1979年读罢老舍遗著《正红旗下》,感慨系之,坦言:“我自己小的时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民族团结》1979年第3期)二是当代作家余秋雨,他的散文名篇《一个王朝的背影》,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篇为清朝和满族写的翻案文章,其中也谈到:“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人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9]不妨翻开当下仍畅销应用着的两部词书,便可了然。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联合出版)上,“八旗子弟”条目的诠释如下:“八旗成员的后代,泛指贪图享受、无所事事的贵族后代。”而《现代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8年版)中对“八旗子弟”条目的释文也是:“享有特权而完全没有本领的名门子弟”。
[10]谈到这里,总会有人以为我国的汉族有些例外。其实未必。只是汉族文化发展很早,创制文字及形成文献也很早,故而遮盖了其先民在久远而悠长的历史过程中以口承方式来传递文化传统的事实。加之汉族文字产生以后,“文化官司”层出不穷,权威话语“一言堂”的情形古往今来无时或已,这就不但排斥了“民间话语”,同时也排斥了“多元话语”。所留下来的文化史册上面,早已罕见初民与先民们瑰丽多姿的口承文化的原貌。
[11]张世富主编的《民族心理学》中谈到:“著名人类心理学家卡丁纳(A.Kardiner)认为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一个产生于某种共享的文化经验的基本人格。社会上成年人的人格应该是由共同的文化经验塑造的,这种共同的人格倾向产生于社会的基本制度,而基本制度与传统的谋生方式,传统的家庭组成及育儿习惯有关。基本的人格结构又反过来产生文化的诸方面,现在经常运用的‘基本个性‘国民性‘民族性等概念均是指某一社会中存在着的一套典型的个性特征。卡丁纳提出的这些观点被许多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田野工作得到了证实。如巴里(H.Barry)和培根(M.Bacon)提出,在畜牧和农业社会里,未来食物最可靠的保证是坚持既定的放牧和耕作常规,因为一旦失误就会影响一年的食物来源。但是在大多数渔猎社会中,一时失误只会影响一天的食物来源,因此墨守成规就不是那么必要了,就有可能鼓励人们的创造活动。跨文化研究也表明,农业社会培养的儿童往往强调顺从与责任,而渔猎社会往往强调独立与自力更生。”(张世富主编《民族心理学》,第4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2]《尼山萨满传》是一部在满族历史上广为流传的萨满教神话,描述了一位名叫尼山的女萨满(即萨满教的女性神职人员),为了救人性命而去阴间夺魂的过程。在一个山村里,富人巴尔都·巴彦50岁上才得到的儿子塞尔古岱·费扬古,15岁时进山打猎而不幸死亡。巴尔都为了让爱子重生,去求救于尼山萨满。尼山在一位助手的帮助下,穿戴上神衣神帽,带上神器,便上路了。她们如风疾行,连闯三关,才在阴间从尼山萨满的舅舅那里,把小费扬古夺到手。在返回的路上,她遇到了自己死去的丈夫,因为他已死多年骨肉早就腐朽了,便拒绝了帮他还阳的要求。随后,她们又路遇子孙娘娘,观看了地狱奉图城中各种恶鬼因生前作恶而遭受刑罚报应的情形。子孙娘娘让她回到人间把那些情形讲给大家听。尼山萨满回到巴尔都家,把其子的灵魂放还到死者的身上,经祷告作法,塞尔古岱·费扬古复活了。巴尔都很感激,以部分财产回赠尼山和她的助手。此后,塞尔古岱·费扬古一生多行善事,结果子孙满堂,都居高官。
[13]当然这里也存在特例,比如下面介绍长篇“说部”时要提及的《乌布西奔妈妈》,就是一部题材极为宏大情節异常曲折的、对氏族始祖女神不朽业绩的传记性表达,同样也具有萨满教的神歌性质。
[14]谷长春:《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总序》,《乌布西奔妈妈》(鲁连坤讲述、富育光译注整理)第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2007年12月与2009年4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当中的第一套、第二套作品,共28部,其中包括《尼山萨满传》《乌布西奔妈妈》《东海窝集传》《扈伦传奇》《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东海沉冤录》《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萨布素将军传》《萨布素外传》《绿罗秀演义》《碧血龙江传》《比剑联姻》《女真谱评》《阿骨打传奇》《恩切布库》《平民三皇姑》《木兰围场传奇》《金世宗走国》《红罗女三打契丹》《元妃佟春秀传奇》《伊通州传奇》《天宫大战》《西林安班玛发》《苏木妈妈》《创世神话与传说》《瑞白传》《八旗子弟传闻录》等。
【责任编辑】李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