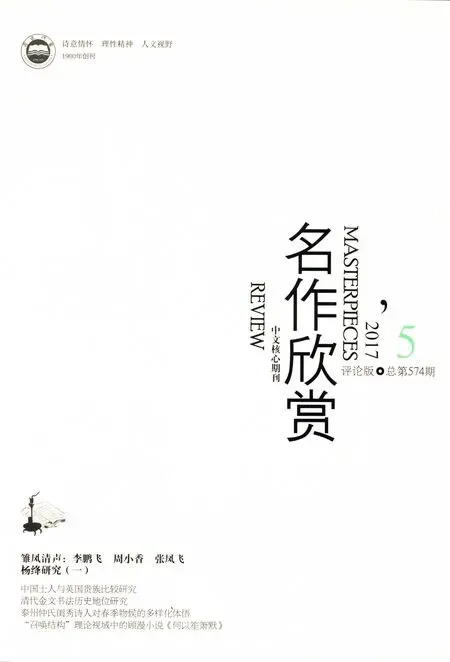假寐者深藏自我
——青年诗人赵目珍诗歌论
⊙余文翰[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香港 999077]
往日里高潮迭起的诗歌运动与论争已偃旗息鼓,代际成为今日诗坛更受瞩目的出场式,在这当中“80 后”是较为沉潜的一支。它并非是借助诗歌运动而异军突起的一群,更主要的是以年龄划分的松散区间,甚至可以说,“80 后”“90 后”等目前仍属媒体和读者为大量文学作品和创作者打造的目录索引。这些诗人及其作品,仅从主题或技术层面皆难以归纳,他们走在各不相同的写作道路上,一如罗小凤所言:“相当多的‘80 后’诗人都在安静、沉潜、默默地认真写诗,并将诗歌当作安顿灵魂的居所,他们在默默地书写自己对时代、历史、自我的体验、感受与理解。”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在断裂的时代空间里生活,“少有艰辛生活的磨难,更没有追求伟大理想的经历,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对当代都市消费文化和流行时尚的追捧与放纵……对于传统文化就有一种天生的叛逆性”。然而亦不得不承认,这一代人在表面风光、快节奏的物质增长下,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就诗歌而言,“他们中间有人总结出四大主题,即情爱、成长、日常和反讽等。就美学特点而言,也有人梳理出:事境中诗意的提取;谐隐和娱乐;情感重现;主体缺席”等。而陈仲义则以为春树的话更好地概括了这一代的书写本质:“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绝对不会考虑‘慢慢写’的叮嘱与劝告,任何‘高贵、经典、文本、抒情、意境’到了我们这里统统失效……诗不再是一个形而上学、阳春白雪的概念,而是像金钱、网络、音乐、足球一样,成为我们的玩物。”
倘若,以上述整个群体及其相关论述为背景,可以发现我们将讨论的是一位同样认认真真写诗却并不叛逆的“80 后”诗人。从学习工科到转投文科,从爱好者成长为文学研究者、写作者,赵目珍对文学的看法总带着一腔热诚,他不可能像“玩物”那样看待诗,除了主动汇入广阔的诗歌传统,甚至产生“赓续传统”的志愿,他始终对真正的“诗”、对一首“好诗”保持敬畏——它“一定会从思想的深刻处反衬出诗人人格上感性并淳真的一面……它体现为诗人主体对生活、社会以及文化经验天然感知和后天认知、浸润的强度,以及其对汉语本身所具有的美之特质的巧妙把握”。赵目珍在山东郓城出生、成长,后求学于武汉,毕业后任职并定居于深圳,一路南下,长期生活在车水马龙、蓬勃发展的现代化都市,但他的诗并未娱乐化或呈现出某些后现代表征,置身消费时代却没有流行时尚的影子,从事着独立于尘嚣却同时能够与尘嚣对话的写作。进入其文本后,可以看到主体不仅没有消隐反而自得其道,相比“向外看”日常的“事境”,他着重表现的是“向内解剖”的内心生活,相比“拼贴”和“游戏”,他更突出“我”的言说,在字里行间赵目珍书写并反思的是诗的“理趣”和诗人的“人格”。
一、书写“内部的潮汐”
如姑且抛开期刊的用稿标准、出版体制与市场选择,以及各类政府或民办的奖项,我们很难明确今天的诗坛何为主流,但就大量文本来看,即便不存在主导范式,仍旧存在一种主流的写作意识:它主张表现现实人生,从日常生活经验提取素材,向读者传递“我”的观察与体验;它拒绝泛滥的情感,也拒绝抽象的天马行空,部分通过叙事等手段让诗的想象“落地”。在赵目珍诗集《假寐者》中亦有能够反映这种写作意识的诗作,如《在妇儿医院》《一段光阴》《东门即景》《田贝一路》等立足深圳的城市诗歌,着力处理在地、即时的经验。然而实际上,此类诗作并不能够代表赵目珍的写作面貌,在作品数量上仅占少数;尽管他的许多作品仍然与新世纪以来主要的诗歌写作精神相通,关怀现实、立足真实人生,但在赵目珍诗中更加突出的,并非写实笔触,而是以独白形式展开的内心生活,他另辟蹊径,通过心路历程的记录来表现“日常”,敢于把饱含思辨、在矛盾中挣扎的心理活动曝露出来,在首先做到真实、真诚的情况下使诗意变得可能。
书写内心生活使诗人获取了自如的言说方式,他不需要在口语或书面语之间挣扎(纵然整体风格上仍保持着臧棣所指出的“雅颂语体”),无须分清个我与非我的界限,他的作品之所以成熟、自如、整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舒适的发声位置:“泥头车在夜晚肆无忌惮,/带来一个无限嘈杂的空间。/此时此刻,各种寂寞归集一处。/说实话,这样巨大的空虚,/太不适合像我这样的人……我意识到,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我开始慢慢地向阳台推进,/将自己推入夜空的胸膛。”(《异乡》)空间的推移显而易见,从泥头车所在的外围工地,到“像我这样的人”“我意识到”“我开始”等“内在音响”,再到“阳台”和“夜空”;不过,“夜空”已不是纯粹的外部或一般可视的无限空间,而是经过消化转为心境的符号,“胸膛”以其空间的具体化和审美化象征着内心的笃定、安谧。诗人有意借助这种朝“内”的推移和“自言自语”的写作方式,使抒情变得节制,使内心的混沌终于变得有迹可循:“我们还是不是在依循着曾经的/路线找寻自己?还是已经/变得非常富有弹性,埋下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存在》)“我不喜欢有人租种我的内心/眼帘中的山水/如果能将暗藏的锋芒带走/那它就是我——值得信赖的人”(《两难之境》)。诗人的内心生活既包含了自我审视的一面,也包括心迹的表白,他没有在意象、风格等层面来追求诗歌的个性化,而是直接通过赤诚之心、写出自己的态度来彰显个体的存在,甚至于当诗人试图对整个时代进行描摹、概括时,他都是从自己的内心感受来切入的,“这泛滥着困惑与蒙昧的文明,/被狂放与挣扎合力包围。/羞耻感随意到没有任何门槛。/诗意的栖居,如同神话。”(《近思录》)
从大部分作品可见,一方面赵目珍试图以诗表现内心生活,用“内部的潮汐”取代平庸、琐碎的日常;另一方面,他的古典“大梦”以及现实生活的纠缠在其内部推波助澜,后者仿佛徒劳跋涉而不可变迁的岸,前者则似海水一般潮涨潮落,引领诗人看得更远、思想更开阔。由此诗人提出他的诗观:“诗歌创作的来源也应该有两个,那就是生活和文化……(且)文化经验的重要性之于诗歌,绝不亚于生活经验。”
古典在诗人的内心生活及其精神结构中,以“梦”的面目出现。李白诗《春日醉起言志》曰:“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白驹过隙,回首时人总会觉得过去恍然如梦,只有理解了所谓现实的虚幻和短暂,才会倍加珍惜内心的自在天地。赵目珍的《醒来诗》无疑响应了李白,“醒来的最佳方式,是把醒来当作又一场大梦”。只是,李白借梦“避世”,不满社会现实而自我开导;赵目珍则借助“梦”的延续以及人在梦中的自由思维,把过去与现在、文化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彼此联结,以重新认识我们的存在:“我们永久地生存在梦中,我们像极了梦蝶的庄周/像极了栩栩然的庄周。不分你我,不分彼此//不分历史与现实。”弗洛伊德的观点至今有效,“梦不是毫无意义、杂乱无章的‘乱弹琴’,而是完整的精神现象,是心灵的错综复杂活动的产物。它们完全可以与清醒状态下的精神活动连接起来”。在现实的音量远远压过虚构的当下,诗人仍然看重做梦的能力,因为只有“退回到自我的心脏”才能“更好地区分自己”。难怪他能够看见“溢满了古诗十九首的河滩”(《牧羊人》)、体会到“‘渚清沙白鸟飞回’的幻境再次置身”(《秘境:关于一座城市的断想笔记》)。在赵诗中,文化记忆不仅构成了一个足以与现实接续、并置、重叠的梦境,且在梦中讲述着一个诗人的精神归途:比如,《庄子·应帝王》所载没有七窍的“混沌”出现在了《鹏程三路》,相比“目迷五色”的都市人,混沌看似什么也不能享受,其实更在意“找寻有限的知音”。又如,诗人化身不可阻挡的大鹏,摆脱个我的渺小和懦弱,开拓心灵的视野和格局,他的《逍遥游》写道:“我的栖息只能陷入梦境的核心/看不见现实主义的忧愁。把酒临风,宠辱皆忘/我知道,我已经站在了‘逍遥’的阵营。”总的来说,对话古典,就固有的文化记忆实施创造性转换,既是秉承诗人最初对古典文学的热衷,又使他有条件脱离世俗困扰,获取更丰富的写作资源以及现实以外的想象空间。
一如前述,在诗人的内心推波助澜的,除了古典的大梦,终究避不开现实生活的纠缠。但赵目珍并不倾向在诗里再现生活,尽管处在物质高速增长、快节奏生活,以及人人相竞的现代都市,可他的生活经验鲜少依附于城市意象,不直接与日常事境对抗,而是把城市经验还归内心,不动“声色”地流露出来。身处都市《喧嚣》,大鹏的姿态并不时常能够展开,相反多数时候,诗人意识到“我不过是一个被动的聆听者/ 无法逾越泡影的鸿沟/ 只能任凭击打,任凭蹂躏/ 然而只有忍受,是内心唯一的真实”。在此,抒发内心不仅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易、自然,且格外苦涩、纠结。赵目珍惯于把日常隐藏到“玄言”式的诗句里,期望把一时一地的感受提炼为整体观察和具普遍性的思考,如“顽疾多么可怕/ 而最可怕的,是众生的盲从”(《暗疾》);“在‘规则’里,我们/ 一起玩着孤单的‘游戏’/ 寄望于受伤的鱼儿早点还魂/ 如果想主动出局/ 就不要酝酿太久”(《摸鱼儿》);“如果你已听出了河流有恙……最好是判断出河流的机心所在”(《听风》)等。恰如刘波已指出的,“赵目珍诗歌中隐秘的反思,其实有意无意间指向的是人世的情理”,而非脱离现实的纯粹哲思。
二、向内解剖·向现实发言
赵诗在表现“自我”方面是多变、多面向的,有时“我”很容易被孤独淹没,有时“我”主动找到精神依凭而有所释然。他可能在一个审美化的进行写生的环境当中表现“我”,如《在洪湖公园》:“我俨然一个无知的盲从者。/就比如,满湖的垂钓人/除了多放钓钩,就只能临摹鱼饵”;也可自心底发声、表述内在的共鸣和认同,如《秘境:关于一座城市的断想笔记》:“当壮丽的图景与一代大潮相拥/即使面对另一个劲敌/在风骨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相容的爱”。就整部诗集而言,我们必然遭遇一个分裂甚至自相矛盾的主体形象,当中亦必然混杂着个人的认知、理想、犹疑和焦虑。进一步说,在自我形象或主体性的审视过程里,形象的真实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不仅因为我们只能根据给定形象与自身视域的距离,去感受形象的真实性与说服力,而且,正如伽达默尔早已指出的,诗人不可能站在自身之外、在自己的历史性或视域之外对自我形成客观认识。也就是说,不论相悖与否,在文本内部,肯定性的建构和否定性的批判都可能同时存在,二者皆是诗人主体性的具体表现,比起“真实”的被动检验,它们更主要是归属于经验与实践范畴,出自诗人“有效”的自发体验。
《途中手记》最能代表赵诗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一面。“如今,我看待‘过去’/就像是在看待消亡/但说实话,如果不经意间/得到一点模糊的回音/我还是会存有幻想/我深知自己还没有到/悠然见南山的高度”。它看似否定过去,其实却力陈已是过眼云烟的文化记忆如今仍有生命力。悠然见南山的高度一方面在于“心远地自偏”以及得意忘言的心境修为,另一方面就在于超然的、自足的主体性。但显然在《途中手记》里诗人把姿态放得足够低,“而我的骨子里装满软弱/稍微有力一点的风吹草动/我都抵挡不住”。他没有一个超脱乃至于封闭的自我,而是试图更深入地批判、解剖自己,以足够低的姿态获取更多向上的可能性,保持谦卑和真实以获取更高精神追求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诗集《假寐者》中较精彩的一卷,即十九首寓言诗,把“坐井观天”“亡羊补牢”等中国成语及其背后的寓言故事重新解构,而“我”的言说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尤其突出,代表了诗人主体性积极建构的一面。“坐井观天”原是强调视野狭窄导致了知识或观念的狭隘肤浅。诗人却说:“我是一只‘井底之蛙’/我只向往我镜中的天地/万物辽阔不尽/我不存半点觊觎之心”(《坐井》),指出人不可心随物转,要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追逐物质是无穷无尽的,只有心灵的满足才不会被时间轻易取缔。《好龙》则是挖掘了“叶公好龙”的当代意义,叶公喜欢龙,衣饰器具都喜欢有龙的元素,然而有一天真龙出现,却被吓破了胆。在诗人看来,“这是对权力的一次疏远/往古来今/有多少人期望得遇真龙/他们对九五之尊/梦寐以求/而我惊恐万分”,这便是说,过去叶公只是喜欢龙的元素却不真的喜欢龙本身,今人为了种种好处追逐权力,最后也易为权力所害。不难看出,这些古典文化的再创新,都是面向当代发言,针砭时弊、敢于表露诗人自己的态度观点。《滥竽》就表露了对社会现实的某些不满:“然而天下滥竽者多矣/好歹也是一介处士/如果饱学者在世已无立锥之地/他应该选择如何活着?”在一个向“钱”看、科学技术压倒人文知识的社会场景中,知识分子如何自处?况且“在其位”的腐败者一再出现,这些今天的滥竽充数者已经连“处士”都不如。《还珠》或点明了这一系列寓言诗写作的主旨:“我就是要转移你们的视线/打破定型的世界观。”诗人发现,在当下人人都是卖珠人,卖的是“眼珠中涨满急切的现实”,能够像“买椟还珠”里的卖珠人那样,把价值远胜所卖之珠的时间、心思花在像“椟”那样装着现实的“内心”,从而真正做到“是非经过我的面前/我只以内心的觉悟为转移”,遵循内心而不盲从现实,一如诗人所言,“这个转换,需要一定的勇气”。
除此以外,或得益于古典文化的浸染,或源自内视、自省的精神生活,诗人把写作视为对现实的“内炼”,在现代的焦虑、都市的紧张外,难能可贵地找到了一种从容自适的状态。《取栗者》写道:“我真正的陶醉在于,我已从陶醉中逃脱/很显然,我不是一个取栗者/与此同时,我更不愿做一个无聊的看客”。赵诗在追求内心丰满的同时,同样看重内心的自由、开放。真正的陶醉是从陶醉中逃脱,也就是获得了自由。鲜明的态度还赋予了“我”的形象以额外魅力,这种自由不是超然于现实之外的,开放也不意味着全盘接受,要知道“我”可以成为怎样的人就必须首先知道“我”不是什么样的人。诗人从不以世俗的眼光、他者的标尺来衡量自己,所谓从容自适,就是打从心底信任并坚持自己的选择,“打开包装,那行走在过度包装中的人/他的虚假的名声赋予他更高的价值/ 而我的坚硬,石头般的栖居/ 赋予了我不朽的风骨,并让我勇敢活下去”(《术中书》)。《沉潜》道出真正的美好出自内心深埋的宇宙,《会飞的房子》相信“众生中总有不朽的兽性”能够实现生命本能和道德的平衡,“必然有一滴雨悬浮于众生之上。/ 它可以唤醒一颗将死的生命,/ 也可以砸死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同类文本仍有许多,不过难免有一些为了表现理想世界而脱离了“我”的真实状态,比如《静默》中“我觉得,我的内心/ 已经达到了最纯粹的和平/ 其实仍旧是万物归一”,这种极端体验或绝对抽象只是针对某种“理想”的描摹而非“我”的自然流露了。
三、理趣与诗的发散
赵目珍的诗没有陌生化的执着,某种程度上亦减弱了想象力的强度,他把写作的重心放在“言志”上,换言之,语言在诗歌内部的自足性不能取代诗人自己的言说欲望。他在写作中思考,形成“诗想”,或者依穆木天的说法是“用诗的思考法去思想”。纵使绝大部分声音来自他内在的音响,不免有柔软、敏感的一面,可从整体上看,比起“丰神情韵”,他的写作更偏向于“筋骨思理”。
维柯曾把“诗性的智慧”追溯到原始人类,那种起初用于认识世界的玄学就是诗性的,因为他们没有被理性以及抽象推理所覆盖,反而“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这一点道出了诗性的根源,诗的思考和说理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服膺真理的客观性,它一方面鼓励个体的创造,另一方面又极力促成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更深入的相互理解。与此同时,中国诗学在理字上讲求“理趣”,反对凭空说教和被动听取,主张诉诸具体形象、情感并要求自觉的体悟。钱锺书《谈艺录》就已指陈“理趣”有赖于“目击道存”,须“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理因物显,赋物以明理,非取譬于近,乃举例以概也”。
赵目珍的诗自始至终保有其文雅、严肃的面貌,它们在思辨、说理的同时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其《乌鹊记》是与曹操《短歌行》对话的作品。曹操诗中的乌鹊是贤才高士,期待一番作为,寻觅明主和施展拳脚之处;赵目珍笔下的乌鹊却“辨不清历史的黑白/它们鸣鼓入蜀,或入江东;与入鲍鱼之肆/抑或芝兰之室,看似并不相关/月仍旧明,星依旧稀。良禽择木而栖”。这些乌鹊再有能耐,他们又如何可能洞悉一切、逃脱历史的摆布呢?反而诗人借乌鹊的形象抒发了“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叹,又写出“当局者迷”的恒常处境。《击壤歌》赋予思想的言说以歌谣的节奏和炽热的情感,它试图像先秦古诗那样做到节制、典雅,却也丝毫不放弃歌咏之美。《对雨》用大雨来勾勒一种心境:“我坐等一场夏天的大雨/准确一点说,我是在等待/时间背后一种训练有素的力量/习惯了在寂寥之后打破常规/喧闹突然死去/元知一切不过都是万事空谈”,由此可径直联想到暴风疾雨清空了街道上的行人,各类喧嚣淹没在雨声之中的情景,也暗合宁静以致远的状态。
既是思理居多,赵诗便淡化了诗性的跳跃,行与行、句与句之间或黏连或撕扯,但基本保持连贯,并进一步以议抒相济的表达方式为其争取到语言上较强的灵活性。一者,议抒相济并不仅是简单地把议论和抒情结合起来,而是意识到了现代人的根本处境,《我们只是身处一隅》一诗即属典型。“城市有它失落的部分/也有它的游戏性让人苦苦淹留//我们只是身处城池的一隅”,当我们的思考试图揭示自身遭遇,得到的必然不是某种客观认识及其规律、进而服从理性的判断和纠正,相反,现实的深刻性从未远离人的情感,我们最终总会进入情感的左右为难。乍一看,“城事”对人的愚弄,就体现在足以遮蔽“失落的部分”、使人麻木的“游戏性”;然而,真正深刻揭示了“异化”的,在于人的“苦苦淹留”、明知故犯,在于“这座浩大的城中/我们只是在相依为命/而她更深陷于傲慢的孤独”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在于“我企图在话语的无效中振作/从城市的一角,努力地打量上去/却控制了自己想要实现的假想”的无力感。可以说,“我们只是身处一隅”既是思想性的发现,也是源自内心深处的抒怀。再者,议抒相济也表现在谋篇布局上,《疲倦伤身》《还原诗》《在野诗》等作均可见思想与情感的彼此传递、相互补充。
可就“理趣”而言,或许更重要的是,议抒相济的语言表达及其结构,就主干内容不断“发散”,或于潜在“主旨”下开辟出“离题”的空间,或为“言志”争取到审美的时间,此额外的时空最具诗的表现力,是赵目珍的诗吸引人的地方。《彷徨者》的本意是重塑一个陷入彷徨、无助者的内心世界,“仿佛在经历一场突如其来的霜降/他随着抑制不住的暴风雨呜咽了”,此时诗人灵机一动,突然发现“这彷徨中有大美/这乃是人类之中最纯粹的彷徨”,由移情转为礼赞,重新肯定彷徨的价值,只当人开始回返内心、当彷徨呈现出精神的纯粹性。《临难日》书写的是妻子分娩前的艰辛,诗末注意力忽而转移:“此刻,小小的出租屋里/云集的忧愁带来春天的宏大叙事/无能的铜炉/正在灼烧一壶滚烫的死水。”“死水”指向新生命降临之前,它承受着“灼烧”和“滚烫”;可以说“无能的铜炉”是帮不上忙的丈夫,亦不妨说是出租屋里琐碎庸常而不见起色的生活。《秘境:关于一座城市的断想笔记》写道:“公园近海/一大群鹭鸟在红树林边翻飞/细微的风,回旋在原地/礼物遍地流淌/我们阻挡不住有些谦卑的事物/它们始终保持着低垂。”“谦卑的事物”无疑是公园里的景象,与鹭鸟相比,它们是在低处生长的草木和水流,不过诗人在此将“洞察自己”与观察公园同构,写景的同时想起那些深藏内心没有消逝,仍然坚信而不随外物转移的事物。
四、结语
整体上,赵目珍的诗自内在的精神生活着眼,即便“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他也寄希望于“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他从大量物品挤占了的日常退场,为的是“关心自己”,“关注与己有关的直接的东西,关注某些指导自己和控制自己所作所为的法则”,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反求诸己,在自身中得到实现和快乐,从自己开始做出改变。与此同时,他敢于向社会现实发言,亲近传统的目的是向“当下”提供不同的视角和新的发现,从不为写诗而写诗,回归诗人何为的命题后,言语之间总埋藏着丰富的思考和切身体验。
但从长远地看,考虑到写作的丰富性和艺术的独创性,此类写作还有必要于“理语”之中更多地专注“理趣”,在调取古典传统资源的同时避免写作的惯性,跳出久远的苍凉孤独之境和时间主题,在“我”的解剖、重塑之后再度投入具体生活,进入现实在日常以外的更多面向。除了坚持有态度的书写,留住不吐不快的力量感,亦需开拓诗的发散空间,让一颗赤子之心继续发挥它的想象力。思的新发现最终应表现为语言的创造,只有语言的创新才会保证诗意栖居的可能性。当然,毫无疑问的是,在强调诗歌语言表现力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诗人像赵目珍一样说出心声,而不是一味地雕刻日常,以更开阔的格局,把审美真正建立在精神生活的深刻挖掘上。
①罗小凤:《80后诗歌写作的精神脉象》,《诗探索·理论卷》2012年第4辑。
②冯月季:《沉沦、挣扎、救赎——对新世纪中国诗坛诗歌写作现象的考察》,《当代文坛》2011年第4期。
③④陈仲义:《在焦虑和承嗣中立足》,《文艺争鸣》2008年 第12期。
⑤⑦⑨ 赵目珍:《假寐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46页,第248页,第269页。
⑥赵目珍:《假寐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本文所引赵目珍诗作皆出自本诗集。不一一注引。
⑧〔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⑩〔意〕维柯:《新科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82页。
⑪ 钱锺书:《谈艺录(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63页。
⑫ 〔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