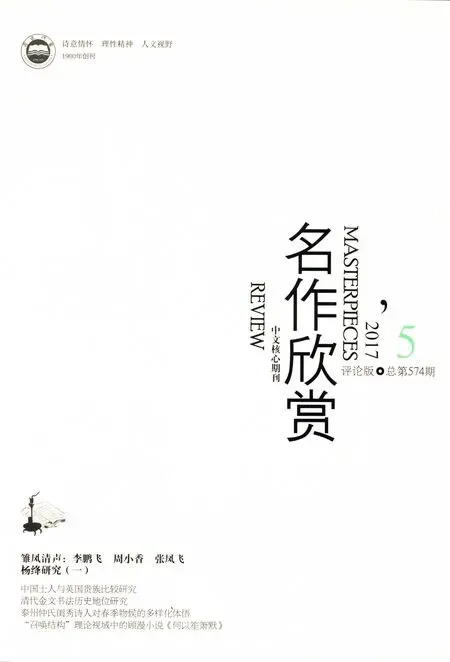论饶宗颐《瑶山集》的情感世界
⊙胡 碟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汕尾 516600]
一、哀:饶诗之诗心
《瑶山集》是饶宗颐现存最早诗集,诗人在《自序》中谈及当时的创作经历:“去夏桂林告警,予西奔蒙山,其冬敌复陷蒙,遂乃窜迹荒村。托微命于芦中,类寄食于漂渚……以东西南北之人,践坱轧罔沕之境。干戈未息,忧患方兹。其殆天意,遣我奔逃,俾雕锼以宣其所不得已。”对于饶宗颐而言,《瑶山集》是那个国家危亡、颠沛流离时代诗人“感序抚时”之作,虽皆为“危苦之词”,但诚不可忘。半个世纪后,有过同样流离漂泊之苦的钱仲联言:“桂峤南北,违难时哀吟之地,今诵《瑶山》一集,所以感不绝于余心也。”
饶宗颐晚年谈及自身学问之道的家学渊源时指出,受其父影响,少年时喜好读清儒著作,其中顾炎武对他的影响最深。少年饶宗颐一方面佩服顾炎武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气概,另一方面顾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世致用之治学路径也影响了他的一生。饶宗颐《论顾亭林诗》言顾诗之诗心在于一个“哀”字:“家和国两重的血泪,交织成他诗里的哀思。”翻开《瑶山集》我们发现,饶诗之诗心也在一个“哀”字。
二、家和国两重的血泪
饶宗颐自言《瑶山集》是“危苦之词”,据笔者统计,全集六十四篇诗,“愁”字出现十一次,“哀”字八次,“苦”字六次,“泪”字六次,此外还有诸多“断肠”“离忧”之词。细分饶诗之哀愁,大体可为两类。
一是山河破碎,黍离之哀悲。如“破碎河山揽一围,极天零雨只霏微。坐怜壮士秋风里,九月天寒未授衣”(《秋怀三首》其二),山河破碎,秋雨霏微,面对如此凄寒萧瑟之景,诗人思及抗战将士衣着单薄,顿生怜惜之情;又如“破壁历残惊岁暮,碧江山赭失秋妍。南东行处悲禾黍,触眼荒畴不复田”(《冬至》),时值1944年冬至,本是家人团圆佳节,却是抗战最黑暗的时期,湘桂战役惨败,国家破败,满目疮痍,江山失色,诗人不禁兴发黍离之悲。此类诗中最杰出的当数《哀桂林》:
狠石怒不平,平地每孤峙。谅哉石湖言,瑶篸差相似。久无肠可断,负此峰 头利。乡心苦邅回,日夕望漓水。飒飒东来骑,奔狼兼突豕。回首嶒峨地,血泪夹清泚。魂散孰为招,愁烟非故垒。人事有逆曳,丧元知谁子。徒言山河固,我欲问吴起。
1944年11月10日桂林、柳州失守,千里江山坐付敌寇,数十万将士为国捐躯,尸横遍野,数百万难民颠沛流离,奔走逃亡。诗人仿佛觉得嶙峋的山石都因战事惨败而愤怒不平。望着眼前壮丽山河,收复失地徒然无望,诗人对国民党政府失望透顶,满腹愁苦已无肠可断。诗人悲愤至极,只能化泪为诗。
这一时期的诗篇中,诗人频频使用“泪”字抒发哀愁之情,如“滔滔桂水流民泪”(《哀柳州》)、“休谱厄屯歌,哀时泪如雨”(《冼玉清自连州燕喜亭贻书及诗,予避兵西奔,仓皇中赋报》)、“故乡不可望,泪与浮云浮”(《寄怀俞瑞征丈以尚有秋光照客衣为韵》)、“劝君休唱黄牛歌,泪似秦川呜咽多”(《黄牛山歌和天水赵文炳》)、“残山剩水好平章,知君涕泪满奚囊”(《柬方子》)等。在这些诗句中,《哀桂林》“血泪”一词情感尤为激烈。饶宗颐《人间词话平议》论古今穷愁之词时评王国维“血书”之喻:“余意以血书者,结沉痛于中肠,哀极而至于伤矣。词则贵轻婉,哀而不伤,其表现哀感顽艳,以‘泪’而不以‘血’;故‘泪’一字最为词人所惯用……故泪虽一绪,事乃万族。词中佳句,盖无不以泪书者,已足感人心脾,一唱三叹,特不至于‘泪尽而继之以血’耳。”王国维以“血书”一语评李后主之词,饶宗颐认为“血”字哀极而伤,不如“泪”字哀而不伤更得文辞轻婉之美,故古今穷愁之佳句多用“泪”而不用“血”字。然当桂林、柳州二城沦陷敌手时,诗人再也无法克制内心的愤恨与痛苦,情感冲破了哀而不伤的法度,“泪尽而继之以血”,悲之至也。
二是奔走流离,思乡之愁苦。诗人只身漂泊于岭西,而亲人皆在故乡潮汕,羁旅思乡之情无时无刻不萦绕在心头,特别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时。如诗集首篇《人日》:
穷阴皂白不能分,谁遣春风散重云。岭西千古断肠地,酒浇不下胸轮囷。僵卧松毡数人日,流年似鸟遄飞疾。仍是东西南北人,此身归去安能必。万里风波一叶舟,青山百匝绕蒙州。流离岂是长无谓,怀古端须志穷愁。
1945年正月初七人日,本是家人团聚吃七菜羹祈求人口平安、丰衣足食之日,然诗人却孤单一人避难于蒙山。断肠思乡之愁无处宣泄,不得已借酒消愁愁更愁。诗人自嘲为“东西南北人”,四处流离漂泊,就像连天波浪里的一叶扁舟,归家无望,顿生穷愁。《瑶山集》创作于1944年夏桂林告警至1945年秋抗战胜利这段时期,诗篇大体按时间顺序汇编成集,然《人日》一篇却被诗人置于集首,可见诗人欲以此篇统率全集之情。又如《文墟早起》:
支颐万念集萧晨,独立危桥数过人。一水将愁供浩荡,群山历劫自嶙峋。平时亲友谁相问,故国归期倘及春。生理懒从詹尹卜,荒村只是走踆踆。
1944年秋诗人避难于文墟,一日清晨立于桥头,望着眼前秋色晨景和过往行人,触景生情,引发高桥羁旅之哀。首联“独”和“危”二字点明了当时的处境,颔联秋水浩荡,群山嶙峋,萧瑟凄凉,景中含情,落于一“愁”字;颈联由景入情,诉说亲友故国之思,归期难料;尾联言及当下心境,多年流离于荒野,苟全于乱世,前程难测,只能在无尽的奔逃中空度流年。半个世纪之后,蒙山县政府欲请饶公赐墨,饶公题“旧游萦美梦,羁旅忆皋桥”一联追忆当年羁旅漂泊之愁,联句后被刻于文墟桥上。再如《梦归》:
频年惟梦以为归,梦绕故山日几围。鹊噪妻孥惊我在,鸿飞城郭觉今非。天留世弃同无妄,海立山颓岂式微。賸有茫茫游子意,八千里外念庭闱。
此诗头两联言梦中归乡之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频”字言思乡苦愁之甚,“惊”字言喜出望外之情;后两联由梦境返回现实,在这天倾海立的乱世,诗人漂泊他乡,思念千里之外的亲人,忧思茫茫。
《瑶山集》中此类羁旅穷愁之诗喜用“浮云”“流水”等古典意象,如“碧涧中藏万斛愁,浮云偏滞古蒙州”(《九日杂诗》其三)、“故乡不可望,泪与浮云浮”(《寄怀俞瑞征丈以尚有秋光照客衣为韵》)、“山头流水长呜咽,客心此日悲未央”(《金秀村迟蒋毅庵不至》)、“滔滔二水合成愁,处处人家水上楼”(《武林口》)、“临水谁相送,望乡可当还”(《题北流江亭》)等,浮云如游子,涕泪如泉流,诗人在俯仰天地之间,将自己的故国思归之情融入眼前之景中,达到情境交融的境界。
三、苦中作乐的诙谐
“危苦之词”虽是《瑶山集》的情感主调,但也时常有一些苦中作乐的诙谐之语。例如国专师生常年避难荒山之中,条件极为艰苦,诗人自嘲“此身忽落瘴烟里,以豕为兄蚊为子”(《岭祖村夜宿》);在蒙山同好友亲自创建黄花书院,诗人自夸“凿垣聊可追王霸,作赋何曾让小山”(《遣怀》);在六排山时国专师生冒着战火危险在牛矢山房继续授课,诗人自侃“虎尾何堪青草瘴,牛矢竟似黄金台”(《寄题牛矢山房课子图为简又文》)。即便是在蒙山中赠答友人之作,诗人也时常有诙谐之句。如言好友简又文,诗人既调侃他胡须如猬刺:“笑公须眉如蝟戟,岭南人似关西客”,又称赞他的为人和为学:“昔岁转游涉陇汉,文渊豁达世共叹”(《乱定晤简又文有赠》),又如在瑶山陪俞钟彦老先生饮酒,诗人描绘俞老先生和诸友饮酒之状:“瑶俗悭卖酒,先生频捋须。薯蓣久充肠,旬日远庖厨。闻有落花生,其脂可医癯。招呼二三子,盍簪入市屠。得酒出望外,虽薄酌须臾。一饮足去冰,再饮颜胜朱。”(《瑶人宅中陪瑞征丈饮酒》)瑶民习俗不爱卖酒,俞老无酒可喝失落时频频捋须之态,显得既生动又可爱。山中生活非常清苦,偶尔得落花生已属不易,没想到市屠中有酒可买,众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宁可赊账也要饮酒,酒过三巡,诸友脸色微红,略显醉态。此诗只选取了诗人和国专诸友避难瑶山时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但对人物动作、神态、情感的描述非常具体而真实,“频捋须”“颜胜朱”,初读时觉幽默而风趣,再读时却不忍让人落泪,叹民生之多艰。
胡适《白话文学史》云:“陶潜与杜甫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人,诉穷说苦都不肯抛弃这一点风趣。因为他们有这一点笑话做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穷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其实,困于瑶山的饶宗颐跟漂泊西南的杜甫非常相似,他们都在用诙谐抵抗着穷苦,用笑语抵抗着哀愁。然而,无论是诙谐与危苦,还是笑语与泪愁,所有的悲欢忧乐都被诗人记录于诗中,给我们展示了青年饶宗颐最真实的内心世界。
①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4》,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8页。
②钱仲联:《近世名家诗词平亭——饶宗颐〈选堂诗词集〉序》,《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③饶宗颐述、胡晓明、李瑞明整理:《饶宗颐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④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2》,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第219页。
⑤孙立川:《避难蒙山的文人们——饶宗颐、简又文、梁羽生的一段难中轶事》,《文史春秋》2006年第2期。
⑥胡适:《白话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