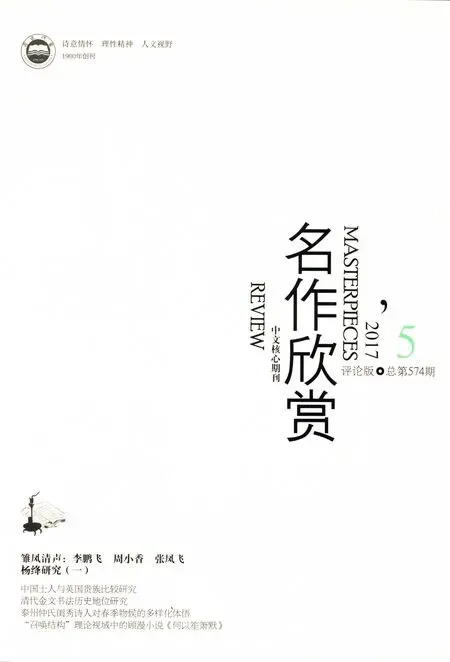《被掩埋的巨人》中的创伤叙事
⊙宋佳雯 [湖南大学,长沙 410006]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了恐惧的阴影中,大屠杀带来的种族悲剧、越战后“战争神经官能症”的再度出现、冷战带来的虚假和平和恐怖主义的涌现,都推动着心理学中创伤理论的发展。安妮·怀特海德认为创伤理论在20 世纪90年代初出现在美国,随后在凯西·卡露丝、苏珊娜·费尔曼和杰弗里·哈特曼的研究下,“揭示了文学批评和创伤理论之间那种独特的密切关联”。凯西·卡露丝所著的1996年出版的《无人认领的经验》(Unclaimed Experience
)将创伤理论运用于分析电影《广岛之恋》,这是较早地将创伤理论用于文学影视批评的著作。从此之后,创伤理论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领域,石黑一雄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构思《被掩埋的巨人》的。1989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看起来似乎迎来了真正的和平。但随后的南斯拉夫战争让石黑一雄意识到:和平只是表象,二战留下的创伤已经使民族之间埋下了仇恨。随后美国的“9·11”事件也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想法:世界早已千疮百孔,古老的创伤得不到解决,必将撕裂出新的伤口,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廓尔克和哈特指出,对于较为严重的创伤受害者来说,会经历一种“无言的恐惧”(speechless terror),这种遭遇通常超出了人们的理解,不在经验的范围内,因而无法用言语表达。这就是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的“创伤后应激综合征”带来的“创伤叙事障碍”。由于创伤会激发人类的心理防御机制,许多创伤受害者会压抑创伤记忆,导致他们不能说出事件的经过,只能通过闪回、梦魇、行为上的重复等方式不断重新体验创伤。医学性创伤是文学性创伤的元创伤,“是文学性创伤的原型和根基”。那么医学性创伤中的叙事障碍势必也会影响到文学性创伤的书写,就像怀特海德在《创伤小说》的导论中说的那样:“如果创伤包含着一种令人不知所措并抗拒语言或表达的事件或经验的话,那么它怎么能够在小说中被叙述?”凯西·卡露丝也曾在采访中指出,对于创伤的叙述总是会有背叛,一方面在言语中存在背叛,另一方面创伤中包含的心理表征难以被语言还原。她认为创伤不可以被认知,只能被“见证”,在文学作品中亦然。因此,作家在作品中必须通过文学手段表征创伤。
不同于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石黑一雄诸多作品中的故事都并非他的亲身经历。他的创作素材主要来源于他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从事的帮助流浪者的社工工作。与流浪者群体的密切接触使得他明白“人是如何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跌倒,又是怎样因此而毁掉自己的人生。……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以至于无法回归社会”。但创伤记忆和创伤经历、文学和真实、作者和读者间的差距使得小说与事件本身的差异巨大化。表现创伤的作品该如何将创伤体验传达给读者?石黑一雄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探寻着这一问题,并在不同的作品中尝试了不同的写作方式。
一、呼出“迷雾”的母龙:创伤的隐喻与象征
《被掩埋的巨人》用古老的亚瑟王传说作为背景,构筑了一个现代的寓言故事。龙、魔法、食人兽等非现实因素塑造了一个虚构的魔幻世界,再辅之以改造后的真实,巧妙地将心理运作机制隐藏在了魔幻之后。这个特点使得《被掩埋的巨人》区别于传统的创伤小说,它依靠种种象征和隐喻来完成创伤叙事,而不仅限于靠创伤主体的独白或心理活动。“巨人冢”象征着屠杀、古老的仇恨,也代表着被埋葬的难以启齿的创伤记忆;比特丽丝(Beatrice)与《神曲》中的引路女神同名,《神曲》中贝娅特丽齐引导但丁喝下忘川之水以遗忘罪恶、获得新生,这与埃克索和比特丽丝过上幸福生活从而忘记过去相一致;埃克索和比特丽丝躲雨的残破的罗马宫殿,暗示战争与毁灭一直在循环;埃德温被龙吸引可以理解成被欲望所吸引,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叙事长诗《贝奥武夫》中有一只会喷火的龙,它喜欢囤积、看守财宝。也是从此开始直至现代,西方的龙常与欲望相关。埃德温希求的对象是离开他的母亲。
除了这些,最重要的隐喻是石黑一雄虚构的那条能呼出“迷雾”的母龙。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只要被“迷雾”笼罩着,过去的记忆就会不断流失。船夫将亡者送往海中彼岸,比特丽丝被小精灵拖向水中,高文回忆起自己的战友死前渴望水,这些都表明在这部小说里水与死亡密切关联。雾由水而生,暗示着死亡的阴影萦绕着这片土地,而这死亡就是因为昔日的战争与种族屠杀。迷雾虽然看起来像是玄幻因素,但是它却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遗忘之雾一方面是亚瑟王的阴谋,代表了强权统治下的人们的被迫遗忘,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心理防御机制,是一种不堪回忆之苦下的主动忘却。将经历创伤性事件后人的逃避和自我保护用迷雾来代替,模拟了创伤的不可言说性。迷雾导致的遗忘就是心理防御机制中的记忆压抑(repression)。“也许上帝为我们感到耻辱,或者是我们做了什么事,以至于他希望自己能够忘记。”并不是上帝感到耻辱,而是不列颠人自己感到耻辱。所有像埃克索这样相信着和平条约却又被同胞们背叛的人,都会对这一事件感到耻辱。埃克索后来回忆起大屠杀的那天,他在村子里目睹了战友们的暴行。自己一手缔造的和平被摧毁,曾和自己亲密的撒克逊友人被屠杀,他感到深深的无力,而心理创伤的痛苦就源于无力感,这一事件导致埃克索产生了“压抑”的心理机制,想要永远忘记这段经历,具体表现为:一是他不再当亚瑟王的骑士,选择过和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二是当维斯坦询问起他的过去时,他表现出了抗拒和拒绝回忆。对于比特丽丝来说,小说中更多描写了家庭创伤的压抑。埃克索和比特丽丝这对看似从没有过争吵的恩爱的老夫妻,在寻找记忆的过程中渐渐发现丈夫的冷漠、妻子的不忠、儿子的离世,一件件残酷的事实回来了。越是痛苦的越是想忘却,所以他们一直坚信着儿子还活着,甚至想象他长成了一个正直、勇敢的青年。
小说中并不是所有人的记忆都被迷雾抹除了,高文爵士一直都有着完整的记忆,这使得“迷雾”魔力的强制性让人怀疑,也正是这种设定上的“不严谨”使人觉得小说中“混乱和前后矛盾无处不在”。但是,情节设定和逻辑严谨与否并不重要,就像《无可慰藉》创造出的亦真亦幻的“现实”一样,故事本身是为了展现人物的复杂内心。所以,高文爵士并非不受“迷雾”的困扰,只是他不以“压抑”的形式抵御创伤。“合理化(rationalizationl)”又称作“文饰作用”,是一种自我欺骗机制。“屠杀婴儿的刽子手。但我当时不在场啊,就算在,我和一位伟大的君王争辩,能有什么作用?他还是我舅舅呢。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年轻的骑士,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事实不是证明他是正确的吗?”在高文爵士的这段内心活动中,他首先用“不在场”来拉远和屠杀的距离,强调他并没有参与屠杀;其次他强调自己没有能力反抗亚瑟王(但根据埃克索的经历,高文也可以选择离开);最后,为了说服自己没有做错,他将亚瑟王的决策归为正确的,认为人们因为母龙得以在和平中慢慢变老,选择性无视了挡在他前面的因为遗忘而无法安然死去的寡妇们。
由于《被掩埋的巨人》的奇幻寓言体风格,人们很容易用魔法等超自然设定来理解故事。但剥开魔幻的外衣,考虑故事的象征意义,人物的经历会显得更加真实和残酷。就像书中那一望无际的静谧草场只是表面,重要的是下面掩埋了什么。
二、寻找母龙时的挣扎:创伤症状的文学表现
“起决定作用的心理创伤和癔症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指这种创伤只是起一个释放症状的诱发因素(agent provocateur)的作用,而且随后它还可导致症状单独存在下去。”这就意味着,一个人一旦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影响便是终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不会因为事件的结束而消失,只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因各种原因反复触发。当比特丽丝“迈步朝石冢走去,身体前倾、肩膀缩着,以抵挡大风,那样子让埃克索隐隐约约回想起了什么往事。这在他心中激起了特殊的情感……一方面强烈渴望立即走到她身边,为她遮风挡雨,另一方面却又清晰地感受到了愤怒与怨恨”。比特丽丝在大风中的可怜背影激发了埃克索的保护欲,但同时也勾起了隐秘的往事,即她曾在婚姻中不忠。相似场景的重现虽然没使记忆本身完整浮现,但当时的感情却再次被激发,就好像事情再次发生了一样,因此面对比特丽丝单薄的背影,埃克索“感到记忆更加清晰,愤怒也更加强烈了……”这就是朱迪思·赫尔曼提出的记忆侵扰(intrusion),“就算危险早已事过境迁,受创者还是会不断在脑海中重新经历创伤事件,宛如发生在此时此刻。……就连一件看似不怎么相关的小事,也可能勾动这些记忆,而且逼真程度与强烈感受一如事发当时”。创伤受害者会深受记忆侵扰之苦,于是遗忘成了最好的解药。但即使自我防卫机制启动,时不时也会触发记忆的“闪回”。第十一章中,埃克索和比特丽丝乘木桶顺流而下,比特丽丝受到了小精灵的袭击,埃克索用锄头攻击小精灵。“接下来的一锄头,产生了更大的破坏——这次锄头的刃口肯定是朝外的,那被他砸飞到阳光之中的,难道不是带血的肉吗?”即使已经遗忘了骑士生活,但当埃克索依靠着本能挥动锄头时,拿着剑砍向敌人的自己的双手在脑海中闪回,一时间又仿佛回到了厮杀的战场。如果说“记忆侵扰”强调的是某一特定景物或者行为对创伤体验的唤起,那么“闪回”就是强调记忆侵入是一种含混的、碎片化的方式。精简来讲,“记忆侵扰”导致创伤者的创伤记忆不断“闪回”,“闪回”的内容多为重复的,并且混杂了虚构的或象征性的事物。高文等一行人从地道里离开修道院时,比特丽丝不小心踢到一具蝙蝠的尸体,尽管埃克索告诉比特丽丝那是蝙蝠的尸体,但是她坚持认为那是一个死去的孩子;比特丽丝在河面上遭受小精灵攻击后称她看到许多孩子的尸体浮在水面上。孩子的尸体就是一个象征,比特丽丝并没有经历过战争,即使在母龙死后她也不觉得撒克逊人会对不列颠人开战。由此推测,她对于孩子尸骨的特别的恐惧并非来自于屠杀,而是来自于潜藏在潜意识中的丧子之痛。即使记忆被压抑,创伤并没有因为遗忘而被治愈,一具小小的蝙蝠尸体就能重新勾起创伤体验,甚至引发了幻觉的产生。
同样的一具蝙蝠尸体,在高文爵士看来又有了不同的意义。尸体与屠杀的紧密相关,埃克索夫妇几句无心的话就使得高文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体现出高文存在“过度警觉(hyperarousal)”的症状。文中没有明确交代修道院地道里的尸骨与屠杀是否有直接关系,但是幽暗地下的大量遗骸与战后战场和被屠杀后的村庄有着同样的残酷景象。记忆与现实重叠,高文爵士将埃克索夫妇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了对自己的指责,他时而愤怒反驳时而无奈承认。这并不是对于灾难可能再度来临的警觉,而是自己心中隐秘创伤被窥探到的警觉。在第十五章,埃克索向高文爵士借马,比特丽丝说她不想离开,高文说自己不会被维斯坦打倒,看似三个人在对话,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说自话,试图掩饰心中的恐惧。石黑一雄擅长使用语言描写,用人物拖沓重复的语言和心理活动来反映角色的隐秘内心。重复能彰显病态,说一次听起来像客观描述,两次像是强调,三次就像是隐瞒。反复强调的语言背后往往才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埃克索在逃避比特丽丝快要死亡的事实,比特丽丝对记忆恢复感到担忧,高文爵士心里清楚和维斯坦决斗必死无疑。
埃德温则表现出更加丰富也更加严重的创伤应激症状。埃德温幼年失去母亲,本就缺乏母爱的他在经历过食人兽袭击后又被本应抚慰自己的亲人视作怪物。“他又想起了阿姨扭曲的面孔。她又开始尖叫着诅咒他了”,但是他“真正的母亲”不一样,埃德温坚定地认为。于是在这一状况下,埃德温对母亲的需要更加滋长,甚至出现了幻觉。他开始听到“母亲”的呼唤,以前的经历在记忆中闪回。被关在谷仓里时,他感受到强烈的“异化感”,即认为自己不再是人而是某种东西或者某种动物。他认为自己是一头骡子,只能通过模仿骡子拉磨盘转圈才能阻止谷仓外尖叫着的人群的攻击,这就是在人陷入无力改变的绝境时会强迫自己做一些事以求安慰的心理。随着创伤症状的加重,埃德温出现了茫然、麻木、幻觉等症状,他幻听到歌声和低语,将三棵倒在湖边的树看成三只断头的食人兽;他的注意力只停留在母龙所在的山坡,沉浸在自己的幻觉里,对周围的人、物和事失去反应。
三、杀死母龙:创伤如何抚慰
跨文化作家能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建构他的身份,而这种对自我身份的建构会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在形成个人人格的过程中,有跨文化经历的人会有更多的机会面对创伤的世界,感受创伤的体验”。尽管石黑一雄一再强调自己处于一个观察者的客观位置,但他的独特经历和跨文化作家的身份让他对于创伤的捕捉更为细腻敏感。“写作的冲动源于创伤,而写作的目的则是治疗伤痛。”仅仅捕捉创伤是不够的,创伤小说作家还需要在小说中完成创伤的愈疗,或者为创伤的治愈提供方向。由于创伤的不可诉说性,创伤叙事通常作为衡量创伤痊愈与否的标志。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能够直面创伤不再逃避,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将自己的创伤经历客观完整地叙述出来,那么他的创伤就得到了治愈。《远山淡影》中悦子对女儿妮基的倾诉、《浮世画家》中小野的自我坦白都意味着创伤愈疗的完成,《无可慰藉》中瑞德虽然没有完成创伤的治愈,但指出唯有沟通才是消除隔阂的良药。
从埃克索和比特丽丝重获回忆后平静地和船夫讲述往事,甚至是关于儿子的死这段痛苦的创伤记忆,可以看出他们完成了创伤的治愈。在这段平静缓慢的叙述中,埃克索作为创伤主体叙述了创伤事件的经过,船夫作为一个倾听者与埃克索进行交流,二人共同实现了创伤见证。除埃克索和比特丽丝之外,维斯坦对不列颠人态度的缓和、埃德温意识到母亲不会回来,都是对创伤愈疗的完成。不仅仅是书中角色,读者通过阅读创伤主体的回忆也参与了创伤见证,甚至可能包含了作者自身的创伤。“如果迷雾没有剥夺我们的记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爱是不是不会如此牢固?也许有了迷雾,伤口才得以愈合。”在母龙被杀死后,关于过去的回忆涌进了埃克索的脑海,痛苦的记忆远比欢乐的记忆清晰,于是埃克索提出了这个疑问。创伤如何抚慰?小说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轻微的创伤也许能靠时间抚平,但是严重的创伤是无法靠遗忘愈合的,唯有直面创伤,才能得到救赎。个人创伤尚能治愈,但是《被掩埋的巨人》给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关乎种族、国家,甚至说人类的集体创伤该如何完成愈疗?石黑一雄自己在采访中也说过,《被掩埋的巨人》的基本命题就是“应不应该杀龙”。“杀”意味着被遗忘的记忆复苏,唤起新的仇恨。“不杀”意味着伤痛一直被压抑,无法彻底治愈。小说中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都表现出强烈的创伤体验。在战争这样的极端环境中,不能单纯地以是非对错进行划分,而善恶的边界也变得模糊起来。就像小说塑造的高文爵士,他是屠杀的执行者也是谎言的维护者。但石黑一雄在采访中说:“高文爵士有一颗充满良知的善心。”他一方面因为忠于亚瑟王而坚持着“平庸之恶”,一方面他又本能地觉得屠杀与欺骗是错误的,这两方面的互相冲突,构成了高文独特的创伤性体验。小说中的维斯坦是一个勇敢又正直的青年,但同时有着悲惨的过去。“我的亲人们很久以前就被杀了”,“我自己的母亲也是被抓走的”,后来又被不列颠人抓进要塞,视不列颠同伴们为亲兄弟却遭到背叛。那些亲密的不列颠伙伴在知道维斯坦是撒克逊人后,反过来和布雷纳斯爵爷一起欺侮他。过去的创伤化作维斯坦坚强活下去的动力,但是他对不列颠人的仇恨永远烙印在了心上。最后,这样一个乐于助人的勇敢青年原来是新战争的发起者,这又是何等讽刺。创伤作为一种“刻骨”的记忆,会从一代向下一代传递,“创伤无须被说出即可交流,作为一种沉默的在场或幽灵,留存在下一代之中”,最终演化成集体的记忆与伤痛。斯特法和维斯坦对于埃德温来说是两个人生导师式的人物,两个人都对不列颠人心存敌意,这种仇恨延续给了埃德温。高文爵士渴望永久的和平,有着好的初心却成为“恶”的帮凶。维斯坦希望正义得到伸张,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和高文爵士并无两样,固执服从国王的命令,掀起又一场只会带来痛苦的战争。本对不列颠人并无特殊恶意的埃德温被灌输种族仇恨的思想,受害者转换成加害者,这种思想也将在代际间继续传递。仇恨与战争无休无止,创伤自然不可能被治愈。“在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中,总有一些事情需要被掩埋,即使有时这意味着恶劣的行径不受惩罚,正义得不到伸展,冤屈无所申诉。”但就像书中被掩埋的种族屠杀一样,遗忘并没有结束仇恨,“有时我们必须回顾过去,回望那些不曾被关注的历史角落。若不如此,那些遗留在社会中的溃烂伤口将无法自行痊愈”。
四、结语
从埃克索到埃德温再到高文爵士的独白,石黑一雄试图挖掘基于屠杀事件的不同立场的群体的心理,展现更加复杂的创伤影响。石黑一雄提出自己是“国际小说作家”,指出自己的作品并非为特定的地点和历史事件所写,而是为全人类所作。诸如《远山淡影》《浮世画家》等作品,还是有较为强烈的事件和地点的指向性。但《被掩埋的巨人》涉及的事件和奇幻要素拉开了同读者的距离,其寓言体的风格和强烈的象征意味使得读者关注的不再是故事情节本身,而是背后蕴藏的关于创伤、记忆、历史、真相的命题。创伤的不可言说性使创伤书写变得困难,石黑一雄用会呼出遗忘之雾的“母龙”来模拟心理机制。寻找母龙的过程就是揭开创伤记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更加强烈的创伤体验侵袭着书中人。最后杀死母龙,代表人们剥去了记忆的伪装,直面创伤记忆。但优点往往伴随着缺点,这种写作方法减少了心理活动的表达,这就使得创伤主体隐秘的心理创伤难以通过自述表现出来。寓言体又使得人物过于平面化,失去了石黑一雄以往小说中人物的饱满感。可以说,《被掩埋的巨人》令人钦佩地找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创伤叙事方式,但同时它又显得“太直白又太模糊,就像一个珍贵但不受欢迎的魔法”。
①⑤㉕〔英〕安妮·怀特海德:《创伤小说》,李敏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第3页,第15页。
②⑦〔日〕石黑千鹤子:《如何直面“被掩埋的巨人”——石黑一雄访谈录》,陈婷婷译,《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106页,第112页。
③王欣:《创伤叙事、见证和创伤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73—79页。
④⑰ 李桂荣:《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第30页。
⑥解友广:Trauma Theory Today:An Interview with Cathy Caruth,《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1—6页。
⑧⑪⑬⑮⑯⑳㉑㉒ 〔英〕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周小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75页,第217页,第276页,第236页,第91页,第327页,第224页,第246页。
⑨⑭〔美〕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施宏达、陈文琪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第33页。
⑩李浩:《〈被掩埋的巨人〉:匮乏逻辑的设计与僵硬的牵线木偶》,《文艺报》2018年第1期,第5页。
⑫ 〔奥〕弗洛伊德、布洛伊尔:《癔症研究》,车文博译,九州出版社优秀2014年版,第146页。
⑱⑲ 周桂君:《现代性语境下跨文化作家的创伤书写》,东北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2010年,第22页。
㉔㉕〔英〕 肯·陈:《我自己的日本(访谈)》,何汨耘译,《西部》2018年第1期,第207页。
㉖ 〔英〕詹姆斯·伍德:《遗忘的作用——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周梦玫译,《西部》2018年第1期,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