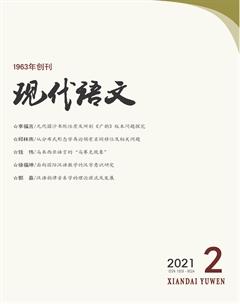汉语韵律音系学的理论源流及发展
郭嘉 周朝岚
摘 要:基于韵律层级共性观和韵律层级类型观,对汉语韵律音系学的理论源流进行梳理,将汉语韵律音系学分为“英律中用”“英律中借”和“中律中用”三种研究视角。前两种研究视角以英语韵律音系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认同重音在汉语韵律音系中的必要性,致力于将汉语纳入普遍重音类型学的研究范畴。“中律中用”视角则强调汉语语音特点,否定汉语属于重音语言,强调建立以声调为特征的汉语自身的韵律层级。汉语韵律音系的后续研究需要找到与英语韵律音系结构可比较的相同层面,将两种不同音系类型的语言放在同一层面进行比较,才能更好地构建汉语韵律音系结构。从语用重读的视角展开研究,也许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韵律音系学;重音;音步;重读
形态句法、音系和语义是生成句法学的三大模块,这三个模块之间相互对接的方式和途径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重点[1]、[2]、[3]。其中,为了与句法成分相对应,音系学家提出“韵律成分(prosodic constituent)”这一概念,以期解决音系与句法模块之间的接口问题,韵律音系学(prosodic phonology)由此产生。韵律音系学认为,任何语言都不能仅凭单个音素或某个音段独立发音得以实现,它旨在研究人类语言韵律结构单位的构成以及韵律基本单位彼此之间的关联。韵律音系结构是语义表达的重要支撑手段,具有区别词义、表达情感、体现形态、区分语言结构的功能,是人类大脑思维的系统性语音显现。
一、英语韵律音系研究对
汉语韵律音系研究的影响
韵律音系研究始于英语,可以说,现代汉语韵律音系的研究主要借鉴了英语韵律音系的研究。自韵律音系学提出以来,英语的韵律音系分析结合了重音、节律、语调以及生成句法等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从点到面、从微观到宏观的层层推进的构建。基于乔姆斯基的音流线性观,非线性音系学提出了以音节为基本单位的多线性音流模型,肯定了音节在英语语音中的重要性,为随后的英语韵律单位的确立、自主音段音系学、节律音系学、CV音系学等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非线性音系学研究,尝试将韵律单位纳入到音系学研究框架中,使韵律音系学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
作为韵律音系学的重要代表人物,Selkirk的一系列研究,系统性地阐述了语法规则和语音表达的映射关系和途径[4]、[5]。Nespor & Vogel对韵律音系学理论和假设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6],他们提出韵律层级是句法和音系的接口(interface)。虽然各位研究者划分层级的标准不同,但都认同韵律是从小到大按照层级排列的一系列韵律单位组成的结构体系。
按照英语轻重音交替的发音规则,英语的韵律音系结构从底层到表层依次为莫拉—音节—音步—韵律词—黏附组—韵律短语—语调短语和话语[7]。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了韵律句法学、语义韵律学、程式语韵律研究等前沿学术,激发并引导了世界上不同语言的韵律音系学研究,现代汉语韵律音系研究便深受影响。
二、汉语韵律音系学研究的理论源流
总的来看,现代汉语韵律音系研究的发展稍晚于汉语语调研究。受汉语声调的影响,致力于语调的“大波浪”与声调的“小波浪”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更为多见。随着英语韵律音系学的逐步引入,汉语语调研究逐渐让位于汉语韵律研究,成為汉语韵律音系研究中的一个次层级,属于韵律结构层级中的显性表层层级——语调层级,并与功能和焦点紧密结合。正因为这一点,汉语韵律音系的功能研究先于形式研究,在这逆向倒推的过程中,功能研究或多或少影响到了形式研究,因此,汉语韵律音系的形式描写往往和功能性分析混杂在一起,语音的重音现象和重读现象未能得到有效区分。
由于现代汉语韵律音系研究起步较晚,一直处于对英语韵律音系的学习借鉴中,它不断地吸收以英语为主的西方音系学的各种理论,然后把各种理论或套用或应用到汉语语音的相关现象中。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采纳和调整。本文归纳出国内汉语韵律音系三种主要研究视角:“英律中用”“英律中借”和“中律中用”,并对其基本观点进行简要概述。
(一)“英律中用”
所谓“英律中用”,主要是指对英语韵律音系研究方法的直接运用。它是汉语韵律音系学形成时期的主要研究视角,并对现在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研究视角基本上全面接受了英语韵律层级的划分方式,并直接套用在汉语中。如冯胜利[8]、叶军[9]、庄会彬[10]等,直接把英语韵律的诸多概念应用到汉语普通话韵律分析中。冯胜利提出汉语音步三分法,将汉语句法结构中的二字组、单字组和三字组词直接对接为英语韵律单位中的“常规音步”“蜕化音步”和“超音步”,对早期的汉语韵律音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研究视角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就是直接肯定了音步在汉语中的重要性,即汉语也是建立在轻重交替的基础之上的。冯胜利采用英语韵律学重音研究的方式分析汉语,建立了汉语韵律句法的结构层级,并直接提出汉语是重音语言[11]。这种直接将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英语的音系韵律单位的对应,虽然在当时容易理解,但因其忽视了汉语作为声调语言、“一字一音一义”的本质语音特征,凸显出句法对语音的影响,在后来的研究中引起了较大的争议[7]、[12],至今争论的各方都在寻求基于汉语本身语言特征的解决方案。可以说,这些争论和尝试推动着汉语韵律音系学不断向前发展。
在汉语韵律音系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汉语韵律音系研究者采用“英律中用”方法,将大量的英语韵律音系的相关成果引入国内,为国内的韵律研究打开了大门。因为是直接的套用,便于研究者快速吸收和学习,所以国内的韵律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不过,将研究英语韵律音系的方法径直嫁接到汉语上,就忽略了汉语本身的特点,因而在对汉语的进一步分析中,出现了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
(二)“英律中借”
所谓“英律中借”,主要是指对英语韵律音系层级结构的间接借用。在接受英语韵律层级的划分标准和相关术语表述的同时,根据汉语具体的语音和句法特征进行阐述。如端木三提出了双重扬抑格理论,认为汉语的重音是莫拉左重音步的观点,汉语的重音既拍莫拉又拍音步[13]。作者指出,不同的语言在音步结构表现上是可以不同的,如重音的承载单位可以是音节,也可以是莫拉,并认为节律音系学理论和重音理论“终究可能会合并为一”[14]。因此,他借用了英语韵律学的概念(如音步)来研究汉语的重音,并肯定了汉语重音的普遍性。王洪君则提出“句法韵律枢纽”,认为“句法韵律枢纽”是句法单位和音系单位的最小交汇单位,肯定了音节在汉语中的重要性[15]。杨国文认为,汉语的音步由音节数目决定,遵从“二常规,一三可容,四受限”的原则[16]、[17](P330)。
与此同时,汉语的重音是左重还是右重,也一直存在争议。林茂灿支持“后重/右重”论,认为汉语词的末字重于首字[18]。王晶则主张“前重/左重”的观点,认为汉语词的首字重于末字[19]。王志洁、冯胜利采用声调对比法,即尽量建立相同发音、相同声调而不同重音类型的“最小差别对”或“近似最小差别对”来判定重音[20]。侯兴泉提出了四种音步重音类型[21]:
音节步 摩拉步
重音在左 扬抑格 扬抑格
重音在右 抑扬格 抑扬格
无论是“英律中用”还是“英律中借”,基本上都认同汉语韵律的基本单位是音步,音步构成韵律词,韵律词构成韵律短语,韵律短语的上一层次是语调短语。两者在基本观点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相比之下,“英律中借”更注重汉语自身的语言特征,因此,它虽然借用了英语韵律音系的相关术语,但在研究汉语韵律音系时更多注意到两种语言的不同,也得出了更加符合汉语实际的结论。不过,二者均把音步视为汉语韵律的基本单位,这引发了较为广泛的关注。“英律中用”和“英律中借”确定韵律成分主要是通过句法成分,如上面介绍的把汉语的二字组视为“常规音步”,这种做法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秦祖宣明确否定了韵律句法学通过韵律结构与形态句法结构之间的映射关系来构拟韵律成分,并指出某韵律成分只能通过与之相关的音系现象来界定,形态句法结构成分和韵律成分之间的映射关系只是在这之后分析的结果,不能事先用于论证该韵律成分的存在[22]。
汉语韵律音系学中“英律中用”和“英律中借”所引发的讨论,直接导致了第三种观点“中律中用”的产生。
(三)“中律中用”
与“英律中用”和“英律中借”有所不同,“中律中用”更强调构建符合汉语语音特征的汉语韵律音系学的重要性。基于汉语以声调为主的语音特征,这一观点认为,汉语应该有自身的韵律层级。张洪明就直接指出汉语没有音步这个层级,因此汉语没有词重音[7]。江荻指出,“汉语词重音的物理实验很可能是一项伪命题,因为汉语是‘基频—音高—声调语言”,“不存在类似英语利用‘振幅—音强—重音材料的对比重音”[12]。石锋、王萍认为,汉语韵律层级分析应采用“多级二分”的方法,根据对声调调域的分析,提出汉语韵律系统分为三个层级,包括词汇调(单字音、连读音)的层级、语调基式、变化模式(语言学调节、副语言学调节)[23]。周韧指出,“汉语非轻声词汇并不具备语言学意义上的词重音”[24]。
秦祖宣、马秋武认为,韵律层级观大致可分为两类:韵律层级共性观和韵律层级类型观。前者认为,人类所有语言具有一个相同韵律层级;后者则否认人类语言具有相同的韵律层级[22]。据此观点,“英律中用”和“英律中借”属于韵律层级共性观,而“中律中用”则属于韵律层级类型观。“英律中用”和“英律借用”体现了汉语语音学家致力于将汉语納入语音普遍类型学的努力,“中律中用”强调了汉语韵律学应建立在汉语自身语音特点的必要性,二者都对汉语韵律音系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汉语韵律音系学研究的
挑战与展望
(一)汉语韵律音系学面临的挑战
就目前来看,借鉴英语韵律音系深层研究机制的汉语韵律音系研究,在两个方面遇到了难题:一是理论层级的构建,二是韵律单位的确定。后者直接影响到了前者的构建,从而导致受制于英语韵律音系研究的结构分析,无法有效地脱离出来,难以形成自身的韵律音系研究体系。如果不将汉语与英语两者的韵律音系结构的深层机制梳理清楚,将会对汉语的韵律音系研究产生偏离。如上所述,“一字一音一义”的汉语中是否有词重音,即汉语韵律音系结构深层机制中是否有英语词重音中轻重交替的基本韵律单位音步,在汉语韵律研究中历经了从无到有再到被质疑的过程。目前,关于汉语韵律音系类型的争论,会更好地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审视汉语韵律的音系结构。
“英律中用”“英律中借”和“中律中用”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汉语是否是重音语言,即汉语是否有词重音,词层面是否有轻重交替的音步这一层级。作为英语音系学研究的重点,重音是英语中重要的超音段语音表征之一。克里斯特尔的《现代语言学词典》对重音的解释是:在语音上“用力发出一个音节”;同时,对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进行了明确区分,“前者比后者突显(记音时在上角加短竖线标记[?])”[25](P337)。很显然,克里斯特尔此处定义的重音是词重音,其首要任务是标记语音突显,并有自身的符号标记系统,便于区分和习得;同时,重读音节伴随着非重读音节出现,因此,英语的词重音中的重音具有相对性,是相对于相邻音的语音突显。
而以声调为语音特征的“一字一音一义”的汉语中是否有重音,即汉语韵律音系结构深层机制中是否有音步,是当前汉语韵律音系学争论的焦点。赵元任承认汉语中轻重音的存在,但认为正常情况下汉语的这种轻重差异察觉不到[26]。罗常培、王均[27](P151),曹剑芬[28]、[29],贾媛[30]等均认为汉语具有词重音。杨锦陈、杨玉芳发现单词产生过程中,存在一个独立于音段内容的抽象韵律结构,其中包含了词的重音模式和音节数量等信息[31]。而高名凯、石安石则认为“汉语没有词重音”[32](P68),刘现强认为汉语的重音只是在表达层面,也就是信息层面起作用,只与信息焦点有关,而与词汇语义没有直接的关系[33]。
与此同时,虽然音步在汉语韵律深层结构中并没有被完全确定,但是目前大多数国内学者很自然地接受了汉语韵律音系中存在着具有重音标记的音步这一深层机制。冯胜利认同人类语言中“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韵律单位是音步”[20]。吴为善、王洪君认同英语中音步这一说法,但认为汉语是松紧型而不是重轻型音步[34]、[35]。杨国文认为,汉语音步基于音节数目不同,英语的音步基于重音[16]。也有学者不认同汉语韵律音系中音步的存在,如张洪明[7]、江荻[12]等。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汉语韵律的音系结构。
更为重要的是,英语的多音节词中,每一个音节不一定都有意义,词重音按照一定规律落在某个音节上。因此,英语的词重音是独立于句法和语义之外的。而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有意义,重读不同的音节就可能在强调对比等语用意义上造成表达上的重大差异。周韧以汉语中动宾结构、定中结构等为列,强调了音节在汉语中的重要性,淡化汉语中(词)重音的概念,形成“信息量—音节数目”的直接关联;作者还指出,当前关于汉语词重音的分布,只是一种大体倾向,缺乏较为一致的观念和可行的规律[36]。由此可见,无论是语音事实,还是理论层面,尚没有充分的依据将汉语归为重音语言。
(二)汉语韵律音系学的研究展望
如前所述,如何有效地对英语(重音语言)和汉语(声调语言)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推动汉语韵律音系学研究的发展,是当今汉语韵律音系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杨军、张娜、陈震宇指出,由于英、汉语音系层级不一致,韵律句法映射的英汉对比研究首先需要确定一个统一可比的音系层面,并提出语调短语作为可比的音系层面的可行性[37]。我们认同这一观点,认为首先必须寻找到英语和汉语的可以进行比较的维度,这样才能更为客观地探讨汉语韵律音系学的相关问题;同时,认同从语用重读的层面将词重音和句重音区分开,将英语和汉语置于语调重读的语用层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有助于汉语韵律音系学更为客观的构建和发展。
人类发音所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省力原则和经济原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说话时不会一直以同样的力度发出声音(很快就会声带疲惫),也不会一直喃喃低语(言语双方会听不清楚)。因此,轻重交替(无论是词层面的还是句层面的)是人类发音的共性,只是不同语言中轻重交替的频率和相对程度各有不同。那么,是否只要一种语言的韵律音系深层机制中存在着轻重交替,这种语言就属于重音语言呢?研究表明,二者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因为虽然都表现为语音层面的重音和相关声学参量的突显(如音高提升、调域拓展、音强加強和时长延长等),词层面的重音和句层面的重读显然属于不同的研究范畴。前者是形式语言学研究的内容,与语言自身特征相关;后者是功能语用学研究的内容,与语言的使用者相关。由于词重音不一定是每个语言都有的特征,但是基于语调层面的句重音却是语言的共性,而句重音和语调息息相关,因此,将英汉两种语言的韵律音系置于语调重读的层面进行比较,是具有可行性的。
语调不同于声调(有固定声调)和重音(有固定重音),语调的语音表现完全依赖于线性语音特征的排列和说话者的意图,即人与人之间交流时表强调、突出或对立产生的语音重音。当我们把韵律音系学与功能语言学结合在一起,来解释汉语的焦点重音,即焦点重读重音时,很多问题就能较好地得到解决。许希明、沈家煊从语用的实际出发,认为重音和声调同属音系内部的同一音层,它们都受位于较高音层重读的控制,因此,汉语属声调重读型语言而英语属重音重读型语言[38]。作者指出,重音和多音词是英语音系的内部属性,而声调和单音字是汉语音系的内部属性,重读是两种语言的外部证据和共性特征。从语音声学分析的角度,采用语音“突显”来避免重音和重读的混淆与冲突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受声调的影响,“大波浪加小波浪”的声调与语调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汉语语音研究中早于汉语韵律音系学的研究。因此,汉语韵律音系的功能研究先于形式研究,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韵律音系的形式研究,使得汉语韵律音系中的重音现象和重读现象混淆在一起,难以区分,这对汉语韵律音系学产生了不利影响。从汉语自身的语音特征出发,避开重音的讨论,而从重读的视角展开研究,也许是解决汉语韵律音系学当前问题的较好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文首先介绍了英语韵律音系学对汉语韵律音系学的影响,并基于韵律层级共性观和韵律层级类型观,将目前的汉语韵律音系学分为三种研究视角。“英律中借”视角和“英律中用”视角以英语韵律音系学的研究为基础,直接套用或者借用其相关术语和表述,尝试从汉语句法特征中推断汉语的韵律成分与韵律特征,认同重音在汉语韵律音系中的重要性。不过,在研究结论上二者有所不同。“英律中借”倾向于寻找汉语与英语的共性,“英律中用”则强调基于英语韵律音系学基础上的汉语自身特征的探索和归纳,二者都致力于将汉语纳入普遍重音类型学的研究范畴,而忽略了声调在汉语中的重要性。由于它们都没有从汉语的韵律成分来界定汉语的音系现象而遭到了质疑,并促进了“中律中用”研究视角的出现,学者们开始重视汉语语音特点,尝试建立汉语自身的韵律层级。不过,由于“中律中用”研究视角没有有效地对重音和重读进行理论层面的系统性分析,因此需要进一步找到更好的突破点。
基于对汉语韵律音系学理论源流较为全面的阐释,本文指出,汉语韵律音系的后续研究需要找到与英语韵律音系结构可比较的相同层面,将两种不同音系类型的语言放在同一层面进行比较,才能更好地构建汉语韵律音系结构的深层机制。我们认为,从汉语自身的语音特征出发,避开重音的讨论,从语用重读的视角或声学层面的语音“突显”来展开研究,也许是解决汉语韵律音系学当前问题较为行之有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赵永刚.韵律结构音系—句法接口研究:问题、目标及对策[J].外语教学,2016,(4).
[2]Zhang,H.-M.Syntax-Phonology Interface:Argumentation from Tone Sandhi in Chinese Dialects[M].New York:Routledge,2017.
[3]Sun-Ah Jun & Xiannu Jiang.Differences in prosodic phrasing in marking syntax vs. Focus:Data from Yanbian Korean[J].the Linguistic Review,2019,(1).
[4]Selkirk,E.The Role of Prosodic Categories in English Word Stress[J].Linguistic Inquiry,1980,(3).
[5]Selkirk,E.On Derived Domains in Sentence Phonology[J].Phonology Yearbook,1986,(3).
[6]Nespor,M. & Vogel,I.Prosodic Phonology:With a New Forward[M].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7.
[7]张洪明.韵律音系学与韵律研究若干问题[M].当代语言学,2014,(3).
[8]冯胜利.韵律构词与韵律句法之间的交互作用[J].中国语文,2002,(6).
[9]叶军.汉语韵律词语音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2).
[10]庄会彬.韵律语法视域下汉语“词”的界定问题[J].华文教学与研究,2015,(2).
[11]冯胜利.北京话是一个重音语言[J].语言科学, 2016,(5).
[12]江荻.重音、重调和声调[M].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4).
[13]端木三.重音理论和汉语的词长选择[J].中国语文, 1999,(4).
[14]端木三.重音理论及漢语重音现象[J].当代语言学, 2014,(3).
[15]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增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6]杨国文.体现汉语韵律特征的分联小段[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6,(4).
[17]王洪君.基于单字的现代汉语词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8]林茂灿,颜景助,孙国华.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的初步实验[J].方言,1984,(1).
[19]王晶,王理嘉.普通话多音节词音节时长分布模式[J].中国语文,1993,(1-6).
[20]王志洁,冯胜利.声调对比法与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J].语言科学,2006,(1).
[21]侯兴泉.广东开建话的轻重音节步[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22]秦祖宣,马秋武.韵律音系学研究综述[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23]石锋,王萍.汉语韵律层级系统刍议[J].南开语言学刊,2014,(1).
[24]周韧.争议与思考:60年来汉语词重音研究述评[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6).
[25][英]戴维·克里斯特尔编.现代语言学词典(第四版)[Z].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6]赵元任.中国字调跟语调(英文)[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2,(2).
[27]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8]曹剑芬.汉语普通话的节奏[J].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2001,(17).
[29]曹剑芬.汉语声调与语调的关系[J].中国语文, 2002,(3).
[30]贾媛.普通话同音异构两音组重音类型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9).
[31]杨锦陈,杨玉芳.言语产生中的韵律生成[J].心理科学进展,2004,(4).
[32]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33]刘现强.现代汉语节奏支点初探[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3).
[34]吴为善.双音化、语法化和韵律词的再分析[J].汉语学习,2003,(2).
[35]王洪君.试论汉语的节奏类型——松紧型[J].语言科学,2004,(3).
[36]周韧.汉语韵律语法研究中的轻重象似、松紧象似和多少象似[J].中国语文,2017,(5).
[37]杨军,张娜,陈震宇.韵律句法映射的英汉对比研究:新闻和故事朗读语料[J].外语研究,2010,(4).
[38]许希明,沈家煊.英汉语重音的音系差异[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