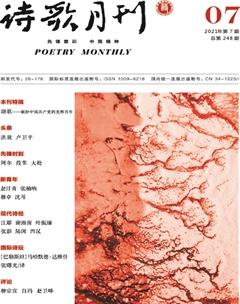我想把人间唱遍(随笔)
洪放
逝川
早些年读日本的俳句。那种清寂之美,让我动心。骨子里或许就是个清寂之人,只是到了这人世间,也必得努力地风风光光地走上一遭。因此,读俳句,还有像《雪国》这样的小说,往往是沉得进去,脱不出来。犹如《诗经》所言:不可脱也。
水波晃动的下午,
一大片旧时光,
被带进了深处的阴影里。
这也学着写上几句。于是想到我故乡桐城乡下的那条名不见经传的栀子沟。
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如同桐城这名称来源于万桐之城一样。栀子沟宽仅丈余,据徒步走过它全程的人说,长也仅仅三四华里。它在经过我们村庄时,细如竹节。只是到了下游,有了一座大塥。塥下有深潭。潭是乡村上最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溺亡者的身影,潜在石缝里的有刺的鱼,刮风深潭里发出的如游丝般的哭泣声……某一年,我上初中,逃学坐在潭埂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坐在那里,一个人,坐了一下午。直到黄昏,夕阳照在深潭里。我忽然觉得潭水慢慢收拢,最后缩成了一块树叶般大小的水晶。我伸出手,似乎就能触摸到它。但事实上,我的手再怎么努力,也永远与它保持着三寸的距离。然后,它消失了。从深潭回来,我觉得很快我便能听见游丝般的哭泣声。我起身离开,在那个年纪,我无法经得住那哭声。
后来,栀子沟也消失了。现在是工厂。
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那深潭的位置。就像诗歌,写过去了,没有人能再次回到它的源头。
小学校
黑板上写下的那些字,或者那些拼音,到底能留存多少年?这是一个十岁的孩子的问题。老师回答不了,同学也回答不了。他只好站在教室里,他看见窗外稻子正飘着白色的稻花。那是他第一次看见稻花。后来,很多年后,他又想起那个场景——
小学校坐落在山岗上。山岗上没有松树,没有杉树,只有两棵柳树。柳树在塘边上,柳树根伸进水里,像一条要爬上塘埂的大鱼。老师们大都来自乡下,甚至同村。当然也有来自城里。老师们其实都还年轻,因此,那些让孩子们读不懂的眼神,往往在男女老师之间传播。后来,眼神打了个弯。一个哭着的女老师背着行李,站在小学校门口。而我们的班主任,正躲在他的房间里。班主任的女儿坐在我前排。她问我:她是要走了吗?
半夜里,蜡烛依然点亮。乡村小学校最后的晚自习一直延续着。我在作业本上写道:
一粒稻花,
又一粒稻花。
都是稻花,開在田里,
像本子上我们写下的一个个字。
这是诗吗?如果是,那一定是我的最初的诗作。往往是,等我们消失纯朴与天真多年后,再回头,我们看见的就是那山岗上的小学校,看见的就是那稻花,然后,我们心底里,幽幽地升起那些长短不一的句子。
这就像宿命里的安排。诗人,注定是个为自己打补丁的人。
鱼刺
我总是小心翼翼。我总是先于鱼刺到达恐惧。
而且,不仅仅是恐惧,还有一种极其深刻的幽冥气息。我总是先于鱼刺到达死亡。
那是年轻的死亡。三十年了。一张巨大的诗报,将时光折叠。而折叠的转折处,便是那个黑色的名字。他第一次飞舞,衔着诗歌。而半年后,他死亡,带着鱼刺。那年,他二十三岁。姓张。一个刚刚毕业的中专生。一个诗人。他死于南京的医院。鱼刺,败血症。他回到了另一个世界。而我们却一直苟活到今天。
我一直想不明白:在他的死亡中,诗歌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也许,与诗歌根本无关。他只是个诗人。而他死亡,他只是个鱼刺的受害者。
但,诗歌加速了这一切。我总是无故地设想:他在吃鱼时,想到了诗歌。诗歌掩盖了鱼刺。然后,诗歌又掩盖了死亡。
我无法将所有的诗写完。因为我总看见他就站在所有诗歌的结尾处。
缓慢
有些人现场吟诗。有些人背诵自己的诗歌,像流水。有些人在别人的诗歌里感动。而更多的人,活在诗歌之外。
日子漫不经心。日子不因为诗歌而充满诗意。日子缓慢,这让我想起我故乡那位活到寿终正寝的老人。
她就在村子南头。我们的村子,有南有北。她在南头,屋前有一条一尺宽的流水。流水几乎漫上了她的脚背。她坐在小竹椅上。那竹椅闪着肉红色的光亮。她每天坐着,从早到晚。她总是看着天,看着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看着流水,看着树木,看着家禽,看着灰尘,看着那些说了多年的话语,看着那些在村庄上流传不绝的传说,看着鬼怪,神,与村庄外连片的祖坟……事实上,她什么也看不见。但她看着。
她看着,就像那个年代的诗歌。。
如果她是个诗人,那么,她看着的一切,便是诗歌中的那些繁复的意象,那些高低起伏的情感,那些散发出来的高于人间却立在人间的气息。
最后,她寿终正寝,依然坐在竹椅子上。
没有人读到过她的诗歌。换句话说,没有除诗人之外的阅读者。生活的缓慢,与诗歌的前行,悖逆而合理。那些吟诗的人,那些背诵自己诗歌的人,那些在别人诗歌里感动的人——谁注意过角落里坐在竹椅上的人?
而她,才是真正的明了一切的人。
当金山口
我记得的最阴郁的山口。满山的阴影。像一只大鸟的巨翅。没有人能逃脱它的覆盖。一阵寒冷,再一阵寒冷。天地开始收紧。我后来明白:阴影总是小于阳光。阴影的部分,总是小于有阳光的部分。
后来,我为此写过诗。
早些年,我是个诗人。如此说,并不仅仅因为我写分行文字,而是因为我的激情,理念,思维,行动与形而上的步伐。我留过长发,瘦,而充满幻想。我穿越千里,成为当金山口阴影中的一部分。那一刻,我除了寒冷,别无察觉。然而,多年后,在一个有阳光的午后,那阵寒冷再次袭来。而同行者,已经成了逝者。也就在那一刻,我放下了诗歌。或者说,我放下了一直高高在上的诗歌的神龛。我转而进入最世俗的生活。我描摹世俗,如同描摹我自己的内心。
我想把人间唱遍
说书人离开村庄后,村庄一下子空寂下来。但随后不久,某一个夜晚,说书人曾经说过的那些部分,又在村庄上活跃起来。传诵,或者被记录,复制,默想,甚至唱出。说书人的背影似乎还印在油灯照耀的墙上。那是一方古老的黄土墙。墙上有风干的茄子、黄瓜,有模糊的祖先的画像,或覆盖于其上的那些排笔刷成的标语。
当说书人坐下,调弦,开口。
一切便隐没了,只有说书人了。整个村庄都只有说书人了。
我要把人间唱遍。说书人闭着眼睛。甚至,我怀疑他也闭着嘴巴。他的声音发自胸,腹,和身体的全部。他的声音发自墙,油灯,昏暗而呈现各种神情的脸,半掩的门,和门外那些依次进来的,我们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影子。
人间如同流水。
人间如同阴影。
人间如同花开。
人间如同日落。
人间演绎。故事在说书人的声音中,高亢,或者沉郁。而它们,一经说书人说出,就像把人间唱遍一样,再也不属于说书人。它们只属于村庄,夜晚,贫苦而荒凉的世俗……它们其实本就在村庄之上。只不过借着说书人的声音,再次提醒村庄:永远别忘了这村庄本来的一部分。
写作者(一)
茫然与不确定性,往往是一个写作者最初的源头。当我注视凌晨的天空,巨大的空洞般的茫然,被刚刚消解的夜色所平复,然后又或许将重新被新的一天,所抬升,笼罩。而它的内核,正是不确定性。
万事万物从不由我。人生因此才漫长,曲折,疼痛,和丰厚。
写作者從来都不是孤立的。他永远挟着一颗渴望融入与回到大千世界的心灵。“一切理性的表述,缘于呓语!”安·拉莫特因此始终记得小时候飞过头顶的那些鸟群。她说:只要一只接着一只地写,按部就班地写。是啊,按部就班地写!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恰是化解茫然的最重要的步骤,与最切合的途径。
我们可以忽视这世俗的繁华,却无法漠视这人间的荒凉。写作者,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认定不确定性与解决不确定性之间,游离,恍惚,思考,进而写作,放弃,并最终否定自己因为写作而留下的一切。包括片语只言,甚至他曾在人世间所说过的一切有关写作的话语。
如此想,写作是没有意义的。但写作的目的,往往正是破解这种无意义。这是一个天大的悖论。事实上,它如同黎明前那即将跃起的第一缕霞光。虽然茫然,不确定,但它的冲击却如同陨石。
——表述霞光初升,那是诗人。
——表述太阳照耀大地,那是散文。
——表述夕阳,那是小说。
我如今企求整整一天。写作便是诗、散文与小说的渐次展开。我因之抒情,委婉,但最终沉入薄暮。
写作者(二)
“作家总会想尝试成为解答的一部分,去了解一点点人生,并把这些心得传下去。即使冷酷实际如萨缪尔·贝克特,他也通过了剧中坐在垃圾桶或将头埋在沙中的疯狂人物,以及他们不断翻出包包里的东西,停下来赞叹每一件物品的生存状态,让我们深入思考并理解人生当中何者为真,哪些才是对我们有帮助的。”这段关于写作地的论述,仍然是安·拉莫特说的。她是基于指出写作者仅仅仍道德意识之后说出此话的。而真正的写作者,往往忽视那些大师的细微与缓慢。
人们看见大师,只有光芒,只有思考,只有箴言,只有那浩如灰烬的巨著。
然而,却总是无法洞见他们对问题的解答,包括对茫然与不确定性的抽丝剥茧般的烛微冥思。
从二十岁开始写诗,一直到四十岁开始写作小说。过程如此漫长,却恍如一瞬。我刻意寻求对各种大师的阅读,往往被崇拜与更深的茫然所覆盖。理论何为?诗意何在?回到诗歌,那一点点人生况味,都被形而上悬挂、敲打、隐匿。而小说,浮世绘般的,将夕阳之幽静、复杂,形而下地呈现。写作依靠语言,却到语言为止。写作成为了语言,无论是诗,散文,小说,便是它意义丧失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