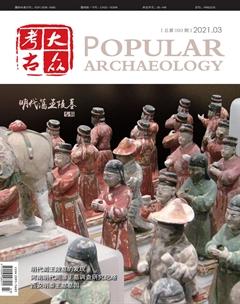明代藩王陵墓
刘毅

明朝皇子封亲王,成年后出藩,驻守于冲要或边塞之地。藩王府第完整保存到今天的很少,但藩王及其子孙墓葬却有不少保存较好,是我们今天了解明代藩王制度的重要资料,也是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
明藩王陵墓现状
自太祖至神宗,明朝先后共有50位皇子以亲王身份驻藩京外,其中后来升为帝系者2府(燕、兴)、始封而被废黜者4藩(潭、齐、谷、汉)、成化(1465—1487)以后始封无后而还葬京师者7藩(秀、歧、雍、寿、汝、泾、景)、未及承袭而遭逢易代者2藩(瑞、惠),其余35藩皆在封国建有陵墓。35藩中始封而无后者4藩(湘、安、郢、梁),福藩仅一代有亲王陵墓,桂王一支承袭已到南明,剩下29府皆有2代或以上亲王传承。
综合多种不同性质的资料估算,各地应该有明代亲王等级的陵墓大约280座;在南北两京附近还有夭折的皇太子、诸王之墓约40座。尚有一定遗迹存在的、进行过考古调查或清理发掘的明代藩王陵墓的保存状况不一,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陵园基址基本完好,有些还有部分原建筑遗存,经整体或局部修复后,已实现全部或部分开放,如河南新乡潞简王墓、山东曲阜鲁荒王墓、湖北武汉楚昭王墓、广西桂林靖江庄简王墓等。也有一些是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仅将墓室部分整修后保护开放,如河南禹州周定王墓、湖北江陵湘献王墓和辽简王墓、四川成都蜀僖王墓等,其中有些是因现代工程建设清理发掘后搬迁至异地重建,如蜀定王次妃墓、蜀昭王墓即迁移至蜀僖王陵园所在的正觉山集中保护开放。这类王墓大多已被列为省级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实现了有效的保护,有些还以单体王陵或陵墓群为依托,建成了考古遗址公园或森林公园,成为知名的旅游景点。
第二种,地面建筑基本无存,墓室部分做过考古清理发掘,在原地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性措施,有专职或兼职文物保管员负责日常保护管理,处于半开放状态。如四川成都蜀悼庄世子墓、甘肃榆中肃庄王墓、江西新建宁献王墓、山东长清德庄王墓等。还有一些是考古发掘后实行了保护性回填,如湖北钟祥郢靖王墓、四川成都蜀怀王墓等。其中有些陵墓的具体维护措施尚未完全到位,但从整体上评估,其保护工作尚处于良好状态。
第三种,地面建筑基本无存,墓室已经被局部或大部分破坏,但仍有明显的遗迹现象,有些曾经做过清理发掘工作。一般都遗存于原地,有一些保护措施,近年来普遍安装了监控探头,至少竖立了文物保护标志,但缺乏日常管理维护。如宁夏同心庆康王墓、甘肃泾川韩恭王墓、河南安阳赵简王王妃墓和赵康王墓、湖北钟祥梁庄王墓、湖北南漳襄庄王墓、山东滕州鲁庄王墓和邹城巨野僖顺王墓、江西南城益端王墓和益恭王墓,以及荆藩若干王墓等。

第四种,尚有部分地面遗存,如封土、石像生等,有些做过简单的考古调查,但未经正式清理发掘,基本都已列入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有些设置了文物保管所等机构,也有监管保护措施(如砌墙或以其他方式圈围、安装监控等),但不一定每座王墓都能够严密监管,如陕西长安秦藩诸亲王陵墓、山西太原晋恭王墓、山东青州等地的衡藩王墓等。
除上述四种情况之外,更多的明代藩王墓葬已经湮没无存,具体可分为3种情况:一是本身已无地面遗存,包括地方志等文献记载也很少,基本找不到有价值的考古调查线索,如岷藩诸王墓、韩藩若干亲王墓等;二是地方志等记载言之凿凿,甚至早年还有碑碣、墓志等重要佐证物存在或出土,但现在已经很难有遗迹可寻,如河南南阳唐藩诸王墓、洛阳福忠王墓等;三是因现代工程而毁坏或将残余迁移他处异地保护,前者如江西南城益庄王墓等,后者如四川成都蜀昭王墓等。
明代藩王陵墓制度
无论是陵园地面建筑还是地下墓室部分,各地明代藩王陵墓都有着突出的地方特色和明显的年代早晚差异,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模式,但它们也存在突出的大时代共性特征和身份等级象征的一致性。归纳起来,明代藩王陵墓制度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選址
明代宗藩墓葬选址有近山建茔和即平原高地卜兆两种情况,具体受到藩府所在地周边实际地理环境的影响。如秦藩诸王都是即平原高地(塬上)而葬,而楚、鲁、德、益等藩至少亲王是近山建墓,也有一些藩府王墓选址规则前后有所变化,如周藩等。近山建墓者墓室位置卜选大体遵奉《葬书》中的有关规则,与皇陵宗奉的风水法术基本相同。
陵园规模
各亲王陵园的规模差别甚大。关于王墓占地,洪武中叶有超过千亩之例(如鲁荒王),洪武末是800亩(如晋恭王),永乐八年(1410)限定为80亩。此后随着正统十三年(1448)限地令、天顺二年(1458)王与王妃合葬令、弘治五年(1492)宗藩子孙祔葬令等朝廷限制性指令的出台,各藩陵墓的占地面积整体上一直呈缩减之势。从永乐朝开始,藩王陵墓地面建筑的房屋间数、开间等逐渐都有了明文规定,正统以后明显逾制者并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各藩始封王,嗣王大都是在始封祖陵园规制的基础上降杀等制。
营造规制
各地明代亲王陵园的具体营造规制并不完全相同,比较突出的差异包括宫门有一道或两道之别、享殿面阔有五间或七间的不同、封土大小及形状不等、神道碑及碑亭的或有或无等,各陵园之间细微环节上的差异则更多。宫门、享殿、封土是各藩王陵园都具备的基本要素,在整体平面布局上和皇陵一样也是模拟“前朝后寝”之制。亲王陵园建筑一般以绿釉琉璃砖瓦装饰,郡王墓葬至少在墓室门檐等局部也可以用绿釉琉璃装饰;也有少量藩府亲王陵墓建筑不用绿琉璃砖瓦,而只用青砖灰瓦,目前所知至少有山西代王、甘肃肃王等例。
玄宫制度
各藩王陵墓玄宫制度不一,甚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其差异之大远超陵园平面布局。玄宫个性化突出之例颇不少见,以周藩最为明显。总体看来,各藩府自成体系的案例居多,如楚、鲁等府墓室规制前后基本一致;荆、益等府因地理环境不利而由券室葬改为石灰椁葬,但变革前后各代亲王的玄宫制度基本一致。蜀府玄宫规制前后有比较大的变化,由繁而简的发展轨迹十分明显,但在基本装饰风格上保持了一致。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墓室结构不断简化的趋势为明代中晚期各藩府所共有。
葬式
明代藩王的葬式大体上都属于仰身直肢葬,所知诸例均以常服殓葬,墓主头向皆与墓门方向相反。嘉靖(1522—1566)以前,亲王一般使用重棺,之后则是重棺、单棺互见。根据已公布的确切考古资料,亲王至镇辅将军、中尉等棺的尺寸差别不大,但其材质往往不同。这种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应该是经济实力,并不一定都关乎礼制。


随葬品
相比同期其他墓葬,各地藩王墓的随葬品大多丰厚,既有身份等级礼仪表达所需的器类,如谥册、谥宝和仪仗类明器;也有传承自唐宋或更早的民俗类葬仪用品,如酒醴瓶罐等。另外还有大量的实用器。除实用器外,其他类别的随葬品大都出现了走向衰退的征兆。
总体来看,明代藩王陵墓是在洪武末年,因秦愍王、晋恭王之死而开始形成制度,永乐时期王陵制度正式形成,此后按照朝廷意旨不断限制性地完善,嘉靖改元(1522)前后呈现出更加简化的趋势。由于各藩府墓葬制度的发展惯性,总体上看来,明早期所封诸王,特别是太祖诸子后裔的墓葬规格相对更高一些,晋裕王直到崇祯时期仍用三室玄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与同时代皇帝陵的对比
明代藩王陵墓比一般墓葬的规格要高出许多,但和皇帝陵墓相比还是存在着明显的等級差异。
首先,陵园建筑规制和主体建筑物上的覆瓦颜色是最显著的等级标识。亲王陵墓享殿(享堂)的开间有五间、七间之制,但绝对没有出现面阔九间的例证(如孝陵、长陵)。皇陵红墙黄瓦,太子、诸王只能覆以绿釉琉璃瓦,甚至是灰墙灰瓦。亲王陵墓的封土一般都是半球形,有时底部环砌砖石一周,但通常并不像皇陵那样形成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城”;仅有个别例外(如襄宪王、潞简王),并且除潞简王及其次妃墓外,也都没有“明楼”之制。
第二,明代亲王墓室通常为砖石拱券结构,多见石基砖壁,也有纯以大青砖成造者,玄宫内壁有些涂红灰或加饰彩绘。如明神宗定陵一般纯石构的亲王玄宫见于襄藩、潞藩少数几府,潞简王及其次妃墓室规格之高是罕见之例。
第三,明代亲王陵园石像生之制有无不一,甚至同藩亲王前后陵园亦有所不同(如晋藩、周藩),但亲王石像生通常不会超过8对,远逊于孝陵(16对)和长陵(18对),且比较少见麒麟、象等瑞兽。
第四,明代有些风水上的禁地,王府使用有一定的禁忌。宁王朱宸濠罪状中有“西山青岚龙口穴,先朝所禁者,濠复以葬其母”(《明武宗实录》卷一七五,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子)之条,可为一证。

第五,关于明代亲王陵墓的称谓,在官修列帝《实录》等官书中一般使用“坟”“墓”“寝园”等字样,在地方志中亦见有称“陵”者。可见在朝廷层面关于王墓的表述和皇陵还是有明确的等级差异,但在地方则没有严格界定。从等级制度考虑,对明代王陵最准确的称谓或许应该是“寝园”,与皇帝(陵)及诸王以下普通人等(坟、墓)可以明显区分。
明藩王墓的突出标志
在没有身份证明物伴出的时候,如何在考古工作中便捷准确地辨识出明代藩王墓?或者说,明代藩王陵墓的标志物或象征性符号是什么?在对若干案例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可以归纳出明代藩王墓三个突出的标志:
其一,明藩王墓有比较大的封土(直径数米至数十米不等),封土前有夯土基础的祭祀建筑遗存或遗迹现象,特别是绿釉琉璃砖瓦、带有云龙等纹样的砖石雕饰残件等,有些还会有石像生或其遗存。
其二,墓葬部分通常为券室(一至五个甚至更多),材质为砖石混筑或纯用大砖,江西淮藩、益藩,鄂东荆藩等王室所用无墓室的灰隔墓,通常也比同时同地其他等级身份者的墓葬考究一些。
其三,王室成员通常使用朱漆木棺,其随葬品(包括衣冠及装饰物)工艺精良、材质贵重,有些带有比较明显的皇族身份标记,如金银饰、龙凤纹等。
明代藩王陵墓研究方法
明代藩王陵墓研究属于考古学科领域,因此基本研究方法理所当然地也应该是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其核心是通过若干实证分析,归纳出一般性的发展变化规律,继而总结其制度层面的特征。此外,还有一个如何充分有效利用历史文献,以及结合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利用相关学科知识,对明代宗藩墓葬进行多维度探索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从实证性的考古资料出发,充分利用多种不同性质的其他资料和研究方法,在最大的程度上还原明代藩王陵墓的历史原貌,阐释其制度特征。
考古学研究方法
在中国考古学中,古代墓葬研究通常都是运用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地层学与类型学,明代藩王陵墓也不例外。但因其时代距现在较近,遗迹地层浅薄,还有不少已经被破坏殆尽;并且,明代王墓大多经过认真选址,叠压(而不破坏)前代遗迹的可能性也很小,因而单靠地层叠压关系来认定明墓年代的机会不多。包括普通明代墓葬在内,具体年代更多是通过墓志等文字资料或随葬品的大致年代来确定的,明代藩王墓葬的认定则有更多的佐证,包括墓葬形制、结构、装饰,以及埋葬方式、随葬品组合与特征等,其中谥册、谥宝、圹志、买地券等直接关乎墓主身份的文字记载更具有关键性意义。因此地层学在明代藩王陵墓研究中的作用并不大,主要是用于分析陵园建筑的叠压关系、通过辨析墓道填土以判断是一次还是多次葬等。
关于类型学的应用,笔者曾经尝试过对明代藩王的玄宫(墓室)结构进行型式分析,归纳出一个发展变化的大致规律(详见《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但这只是一个相对正确的结论,且随着研究资料的丰富、精细、准确,不符合这一发展变化规律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周藩亲郡王墓葬的形式多变、不完全按“规律”发展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典型,而楚藩玄宫结构前后基本没有变化则是另一极端例证。
对于明代藩王墓这种已知墓主身份和具体埋葬年代的墓葬(有些连造墓年代都历历可考)的研究,与早期墓葬考古学研究相比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区别,通过型式分析排列早晚或许有画蛇添足之嫌。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类型学的功用,除了按分析对象的型式特点分类,根据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排列前后顺序外,这种分析还能够通过排列已知前后顺序的研究对象,反过来观察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对于明代藩王墓(玄宫部分)这样的基本都能够知道具体年代的例证,这个方法依然有其便捷利用之处。这颇像某些自然科学领域的实验环节,可能已经预估到了结论,实验只不过是以符合所在学科规范的手段和过程加以证明而已。
文献资料的使用
中国古代文献类史料汗牛充栋,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特别是宋金及以后的考古学研究中必须正视古代文献的地位。宿白教授在《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中提到:“秦汉以后的考古学是不能离开古代文献的,因此它和以前文献记载较少,甚至没有文献记载的阶段的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上多少就要有些不同”(文物出版社,2010年),这个表述实际上已经把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文献的利用问题提升到了方法论的视角。
就明代藩王陵墓这个具体的研究对象而言,同期文献资料之多远超以往,甚至有一些细节的记载也有幸保存了下来。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可以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佐证,而且明清以来地方志中关于各地藩王陵墓方位的记载还往往是这些墓葬勘查、指认的最初线索,而与陵墓营造、制度设计等重要事件有关的当事人的记录等原始资料(文字或图样文件),其价值也决不亚于考古资料。如果陵墓本体业已消失,则这类文献的资料价值也会相应更高。
文献记载提供了考古学研究的佐证,但同时也增加了考古资料分析解读的难度。如果考古材料的释读与文献记载相吻合,则文献提供了另外一重证据,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这是一种皆大欢喜的结果。但问题在于,二者如果不一致怎么办?是不是一定要以考古資料否定文献记载?从明代藩王墓研究的实践来看,考古发现的事实并不一定都具有普遍意义,如果都用之为绝对正确的标尺,很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疏漏。在这方面,可能暂时并存备考更好,也就是说,除了那些“小说家言”或明显谬误的传闻等以外的正规文献记载,似都不宜轻易否定。
其他研究方法
明代宗藩陵墓研究的对象是以分封到各地的亲王墓葬为主干,兼及南北两京的太子墓、皇子墓,以及仅有少量资料的郡王及其等级以下的其他明代宗室成员(含公主、郡主等女性)墓葬。由于墓主身份等级普遍高端、随葬品丰厚,这些墓葬的内涵十分丰富,要全面准确揭示其历史真谛,考察的角度也应该多样化。因此,借鉴其他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方法论和相关知识,对明代宗藩墓葬进行多维度的探索不仅可能,而且十分必要。
比如明代各地藩王玄宫(墓室)有很强的特异性,这种差异与距离都城远近没有直接关系,但可能与不同藩府受中央政府控制或影响的力度有关。同时,作为身份等级一致者的最后归宿,明代王墓也存在着明显的共性,如何归纳这些共性,进而确立明代王墓的认定标准,除了出土物佐证和对墓葬形式一般性的归纳总结外,还可以借用符号学的思维,通过共同的表现符号找到当时社会对王墓内涵的理解和认知。另外,对于明代王墓陵园、玄宫的营造方式、装饰内容等,也可以借鉴图像学的方法来辅助解读,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建筑的布局或装饰意义等已不为后人所理解,这就需要分析其表现的最初驱动力,从具象到抽象、再到象征物,找出明代王陵的共同标志物。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还可以交叉使用多种方法,如随葬品中的文化(宗教)因素分析法、玄宫结构与地域特征分析借鉴文化传播理论等。
随着学术界对于宋元及以后考古学的日益重视,最近十余年来关于明代藩王墓,无论是考古调查或发掘报告,还是专题性研究或相关研究的成果,都比以往更为多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有了明显的推进。明代藩王陵墓研究显然不能停留在资料整理和编排,也不应该仅仅限于归纳基本特征、揭示发展规律,至少应该回到大的历史学学科门类范畴中去,变成一种考古学语言的历史记录。明代藩王墓葬在同期所有墓葬中只是等级接近最高(皇帝陵)的那一小部分,其规格和等级远远超越了包括官员墓葬在内的其他明代墓葬,这些特殊身份者的墓葬以实物表达(叙事)的方式,印证了明代宗藩远远凌驾于当时社会之上的史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明代藩王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也是广义的明代历史学研究。
考古学价值
一个朝代的诸侯王陵墓因封建皇子而散布于全国多地,秦以后惟汉、明二代最为典型,相应的墓葬具有多方面的研究意义。相比于汉代诸侯王墓,明代藩王陵墓的研究成果太少,更应该引起特别的关注。作为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墓葬类别,明代藩王陵墓具有比较高的考古学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过考古学认定的明代藩王陵墓的年代从明初到明末,前后200余年持续不断,涉及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甘肃、宁夏10个省区,墓主等级身份一致,提供了相对完整的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砖石券室结构墓葬发展演变的诸多实例,其序列具有很强的标型学意义。由于各藩王陵墓大多能够考据出准确的纪年,故其年代学意义也比一般墓葬更大。
第二,明代皇子分封各地,后嗣子孙世代驻守,不同地区的藩王陵墓融合了各自王府所在地的墓葬风格,地域性与等级性、共性(共同身份、全国性)与个性(地方性)交互作用,纵向和横向发展变化的对比效果十分突出。
第三,明代藩王陵墓是一种特殊的家族墓葬,各藩从亲王、郡王,到各级将军、中尉,都具有明皇宗室的身份,墓葬形式和随葬品具有一定的共性。由于这些人的辈分、等级身份都有严格的区分,可以由此进行多维度的分析研究。以纵横两个维度为例,纵向上从首封到子孙嗣王的发展变化,横向上夫妻妾之间、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不同等级人群之间墓葬制度的差异等,都值得进一步专门探讨。这些墓葬基本都有墓志或其他身份标识明显的材料出土,它们直观地记录了明代皇室生活史,可以勘正史传,补《明实录》《明史》等重要文献之缺漏。由于墓主身份族属的确定性,还可以考虑利用其遗骸进行皇室疾病史研究,以宗室人骨研究遗传基因,或许可以破解许多历史迷团,甚至有可能建立古DNA专题资料库,提供多维度的研究案例。
第四,作为社会等级结构中的上层,明代藩府普遍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即使是贫弱的宗室远支,其生活质量也高于普通平民。宗藩成员随葬品数量巨大、材质优良,各种出土遗物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用这些资料可以进行多学科领域、多角度的研究。其中有些文物还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如鲁荒王墓中出土的宋元书画、梁庄王墓中出土的海外宝货等,都丰富了人们对于不同学术领域的认知;而不止一座墓葬中出土的衣冠服饰资料,以其具象而详实,极大弥补或匡正了《大明会典》等文献记载的疏漏。
第五,明代皇陵的石像生制度不完备(北京十三陵中仁宗献陵以下均无此制),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帝陵玄宫也只有神宗定陵一例,作为研究资料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明代藩王陵墓的考古资料恰好在这两方面可作为同期帝陵制度研究的参照。明代一部分藩王陵园前部设置石像生,而且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别是同一藩封);其墓室考古资料虽然不如按等级制度构想的那样整齐划一,但至少可以归纳出亲王玄宫發展变化的规律性特征。
第六,我国现存明代建筑并不少,但王府、住宅等却鲜有实例,明代王墓丰富了学术界对明代建筑工艺和装饰艺术的认识,各藩陵园建筑的营造法式,墓室(如门楼等)的装饰技法和形式(传统石木雕构件)、特别是成都地区蜀式玄宫的内部结构及装饰等资料的揭示,都有助于推进明代建筑,特别是王府建筑的研究。
第七,明代藩王墓自成体系、信息丰富,以相关资料为基础进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晚期段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归纳总结。同时,明代藩王陵墓考古学研究相应成果的公布,也将有助于促进所在或相关学科领域拓宽视野,推动诸如宋元明清考古学以及明清史、明代宫廷史、皇族史、上层社会生活史、古代建筑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明藩王墓研究意义
长期以来,古代帝王陵墓的调查和发掘一直是中国秦汉至元明时期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相应的研究工作有时也成为中国考古学成果的闪光点。刘庆柱先生认为:“半个世纪来的秦汉至宋明时代帝王陵墓考古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人们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明代藩王陵墓的研究、开发和合理利用问题越来越为大众所关注,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和理论意义。
全国各地明代藩王陵的保存程度和保护力度不一,分别属于国家级、省级、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不少尚未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只是文物点。明代藩王陵墓的全面调查和研究,将为这批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最核心的基础性参考资料和工作依据,同时也将最终推动这种保护工作落到实处。明代大多数皇帝陵墓现在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或其扩展项目,以此为基础,保存状况和保护条件相对较好的明代藩王陵墓,经过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工作,完全有可能进入“明清皇家陵寝”世界文化遗产扩展项目,从而使其保护与利用找到更好的契合点,形成一个更高的发展和展示平台。由考古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明代藩王墓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