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岛敦文学中的“人格阴影”研究
尼凯凯

摘 要:中岛敦在改编中国古典传奇《人虎传》时,主人公李征异化成虎的过程中加入了大量心理描写,进一步明确了其作为现代小说的独特光芒和价值。本文结合荣格的“阴影理论”,运用原型批评法考察《山月记》中虎的原型就是李征內心的“阴影”,进而用历史传记批评法考察虎的原型与中岛敦的生平、成长经历和创作经历之间的关联,这些改编正是作者生活中“阴影”的投射。
关键词:中岛敦;山月记;阴影
一、引 言
《山月记》是中岛敦于1942年发表在《文学界》上的短篇小说,是中岛敦根据唐传奇中的中国古典传奇小说《人虎传》改编而成的。相比《人虎传》的说理性和猎奇性,中岛敦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感赋予它新的生命,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想要出人头地却又不愿努力的迷茫痛苦的现代人物形象。
我国关于《山月记》的研究可追溯到其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的1944年。但其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岛敦在中国几乎不为人所知。1985年赵乐甡[1]指出李征异化成虎是日本社会的产物,虎的嚎叫是对当时社会逼人成虎的控诉,这是我国最早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对《山月记》的评论。1991年马兴国[2]从中岛敦创作的三十多首汉诗来解读《山月记》,指出主人公李征正是作者的化身。2004年李俄宪[3]通过分析《山月记》中李征和《李陵》中李陵的形象,并结合对中国史料的考察,揭示了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历史文化原因。2011年郭勇[4]则重点关注李征的陇西出身,并指出出身高贵才是导致其悲剧的原因,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出发,揭示了中岛敦怀疑主义的文学观和历史观。
日本学界对中岛敦的研究始于其离世后,大量的研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视角。战后,《山月记》被收录在国语教科书后,松村明敏[5]将李征异化成虎的原因归结为现代人“自我意识过剩”和“存在的不确定”。山敷和男[6]通过对《山月记》出典的考察,指出其在人物性格塑造和创作手法上与古代文学的区别,并进一步指出其创作意图。木村一信[7]着眼于《山月记》的对话部分,指出主人公面对毁灭的恐惧,是对当时那个过分执着于诗作的自己的否定和批判。木村瑞夫[8]指出中岛文学像一道光给了战后文学的新的希望和可能性。
从中日研究成果来看,前人研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各种各样的视角。前人通过对《山月记》出典、人物设定、语言风格、情节编排等各方面的考察,多维度解读了中岛敦改编《人虎传》的创作意图及其艺术特色。但由于研究方法的单一和基础理论的欠缺,从人的意识层面对主人公心理的分析较少。叶舒宪[9]在《神话——原型批评》中指出:“艺术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活动,因而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去研究,由此看来,艺术同(源出于心理动机的)其他活动一样,对心理学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课题。”文学创作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其本身就是心理活动通过文字得以外化。“阴影”原型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荣格的“原型”理论之一。阴影是人性中不愿表现出来的阴暗面。阴影不可否认,不可抗拒,如果我们个体试图忽略个体,甚至去压制它,可能会遭到阴影的报复,严重时甚至有可能吞噬整个个体。因此,笔者将借助卡尔·荣格的“阴影理论”,在马兴国[2]指出主人公李征正是作者的化身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李征异化成虎是中岛敦内心“阴影”的外现,从而讨论中岛文学的更多的侧面。
二、《山月记》中“虎”的原型分析
傅道彬[10]在《晚唐钟声》中指出:“人类的精神是有遗迹的,这就是原型。原型又称原始意象,它是精神文物,是人类的‘种族记忆’。”虎是一种起源于中国且较为常见的动物,身形巨大,吼声如雷,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百兽之王”,给我们留下雄壮威严的种族记忆。由于虎是食肉动物,农耕时代一直对人们的生存造成威胁和困扰,因此,人们只能敬而远之,长久以来形成了谈虎色变的民族传统。由此以来,虎凶猛残忍的形象被吸纳进民族文化,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并常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传奇故事之中。
另一方面,虎外表强悍而内心软弱。它总是肆无忌惮地残害其他动物,使之变为食物,因此没有别的动物靠近。《山月记》中的李征平日不与别人交流,更是不屑与别人来往,这和作为“百兽之王”的老虎独行、孤高、不合群的习性高度契合。老虎总是步履威重,享受着“百兽之王”的称号也就意味着孤独,孤寂的内心更加重了它的兽性。李征一味地执着于自己的文学抱负,即便是异化成虎后,也还是先将自己的诗作托付给旧友袁傪,然后才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可见这种有违于人类常理的非人类性正是他异化成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相比谦逊圆滑、仕途顺畅的旧友袁傪,李征的这种孤傲、过度痴迷诗作而忽视家人朋友的“阴影”在其内心不断发酵,最终,兽性大发异化成虎。
中岛敦在改编中国古典传奇《人虎传》时,为主人公李征加入了大量心理描写,并在异化成虎的原因中加入了心理方面的因素(见下表)。
相较于《人虎传》中宦海沉浮、郁郁不得志的士大夫形象,《山月记》中的李征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其内心的“阴影”不断被压抑,最终反扑吞噬其人性,酿成恶果。因此,《山月记》中虎的原型就是李征内心的“阴影”。

自卑与自负的“阴影”把李征逼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循环迷宫。想要以诗流芳百世,又难以满足妻儿生计,故而不敢刻苦雕琢;想要谋求生计,又不甘与自己所鄙夷的官吏同流合污,故而每日郁郁寡欢;想要追求诗人的志向,却又丧尽家产、心智迷狂,故而挣扎于入世与沉沦的夹缝之中,这林林总总使其难以承受外界威压和内心痛苦的重负。这些“阴影”在李征心中挥之不去、难以克服,如此社会又没有才华施展之处,使其一味地压抑内心的“阴影”,作为人性中阴暗面的阴影比任何其他原型带有更多的动物性,最终发狂出走,以异化成虎的形式得以具象化,可以说变身成虎就是其内心阴影面的极端异化的结果。
三、中岛敦内在阴影的多元因素分析
如果进一步考察李征变虎的原因以及变虎后独白与中岛敦的生平、成长经历和创作经历之间的关联,不难发现这些改编正是作者生活中对生命、对存在不安的“阴影”的投射。接下来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挖掘中岛敦生平、创作、生活中的影子。
(一)性格因素
“在我还是人的时候,尽量避免与人交往,人们也因此说我倨傲不逊,妄自尊大。人们不知道,其实是我心中某种近似于羞耻心的东西在作怪。当然,曾被譽为乡党之鬼才的我,并非没有自尊心。然而,这种自尊心,无疑是一种怯弱的自尊心。我想以诗成名,却又不进而投师访友,相互切磋琢磨。与此同时,我又不屑与凡夫俗子为伍。这都是我那怯弱的自尊心和妄自尊大的羞耻心在作怪。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故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于是我渐渐地脱离凡尘,疏远世人,结果便是一任愤懑与羞恨日益助长内心那怯弱的自尊心。”[11]
这是李征关于自己性格的独白,“怯弱的自尊心和妄自尊大的羞耻心”是李征对其性格的自我剖析和反省,不难看出其中自我否定的成分。面对功名利禄他选择淡泊无欲,却又不甘一生碌碌无为,于是将希望寄托到自己的诗作上,一心想要实现自己以诗名流芳百世的文学抱负,却又绝望于常年的郁郁不得志。面对恶俗不堪的达官显贵,作为弱冠之年而名登虎榜的他难以忍受每日的卑躬屈膝,却又无奈于生活的窘迫,只能屈膝受命于自己所不齿的官员。这种作为昔日才俊的优越感和作为文人的风骨与现实生活中的无奈之间的矛盾不断冲击着他,使其自尊心大受打击,从而产生了一种羞耻感。
这种种矛盾都是作者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岛敦从童年开始就不善交际,两岁就挥别了生母,跟着祖父祖母生活;八岁又跟着父亲到奈良生活,后期父亲频繁的工作调动使其童年不断辗转,因此他的朋友并不多。步入文坛后依然清高孤傲的他,在文坛的交际圈也十分有限。这与当时社会上所提倡的国策文学也有很大关联。1941年,以“奉公报国”为目的的文学创作风靡二战中的日本社会,而中岛敦却始终认为战争是战争,文学是文学,没有把为当时社会服务当作其文学创作的首要目的。因此,孤高的他与文坛格格不入。虽然李征和中岛敦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面对整个社会的浑浊,他们都难以忍受现实生活带来的各种冲击。
(二)诗作因素
“他的诗作有长有短,共三十来首,然每一首都格调高雅,意趣卓异,一读之下便可感受到作者那非凡的才华。然而,袁傪在感叹之余又隐约觉得稍显不足:作者作为诗人的资质无疑是一流的,却总还在某个地方(某个微妙之处)欠缺了一点什么。”[11]
上文是李征异化成虎后,偶遇旧友袁傪,请求他笔录诗作时的描写。关于此处“不完美的诗作”,马英萍[12]通过考察中国唐朝的官位制度和科举文章的评价标准(文辞、义理),指出袁傪作为监察御史对少与人交流、不关心时政的李征诗作的评价,恐怕最缺少的就是对时局的看法。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此处“不完美的诗作”是中岛敦在改编《人虎传》时添加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此处应结合作者中岛敦本人的创作经历加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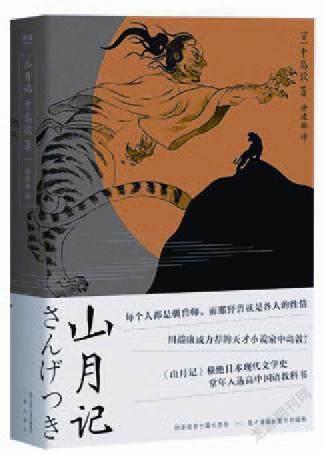
在他离世后的第九年(1951年),发表于其在人世间最后一年的《山月记》被中学国语教材收录,被人们奉为经典,代代传颂。不难想见在其三十三年的短暂生涯里的绝大多数的前三十二年,时运不济的他在文坛是如此的沉寂,作品未能得到广泛认可而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产生怀疑和不安。
不仅如此,1942年发表于《文学界》的中篇小说《光与风与梦》,被推选为第15回芥川奖候补,遗憾的是最终却没能获奖,评审结果获奖作品为空缺。而评审小岛政二郎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该作品“缺乏现实色彩”。芥川奖一直是日本纯文学的最高奖项,获得芥川奖是作家在文坛确立地位的象征,而此次空缺似乎比别人的作品获奖对中岛敦打击更大。同年12月4日,因哮喘病发作,中岛敦与世长辞。短暂的一生像一颗流星一样划过苍穹,转瞬即逝,但其作品闪耀着恒星般的光芒,时刻照耀着现代人的内心,引人深省。可见所谓“不完美的诗作”是中岛敦对其文学尚存遗憾的自我批评。抑或是对评审们以实用性理论来评价其作品价值的一种不满和讽刺,更凸显了自身和李征类似的悲凉感和破灭感。
(三)心理因素
“当我明白这绝非梦境之时,我便惊恐万分,茫然不知所措,怎么会有这等事?我不明白。事实上我们原本就是一无所知的,不知情由地逆来顺受着,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这便是生灵之宿命。”[11]
上文为李征异化成虎后的自白。此处的“生灵之宿命”是李征面对自己异化成虎的结果所能想到的第一个原因。异化成虎后他不知所措、惊恐万分,却还是在短暂的挣扎后想到这是无法预测、难以摆脱的命运,面对命运他只能选择接受。其实在中岛敦的作品中不乏此类形象的存在,无论是《李陵》中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李陵还是《狼疾记》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三造,都是挣扎在命运沼泽中的平凡人的化身。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因无奈与命运的不可捉摸而显得渺小和无助,给人一种命运的悲凉感和无力感。可见这种类似于佛教无常观的宿命观正是中岛敦对生命、对人生的理解。
中岛敦始终背负着童年的孤独和虚无的阴翳,投射到文学创作之中,就呈现为这种对人生和命运的不安与怀疑。可以说不断的颠沛流离和亲人频繁离世的童年时代是其创作生涯的潜伏期和酝酿期。生母、继母、祖父、伯伯、同父异母的妹妹的相继离世无疑对他的生命观造成巨大冲击,未经世故的中岛敦面对这一重又一重的打击之后,内心里浓厚的死亡“阴影”难以消散。而中岛敦自己似乎也被上苍赋予了短命的人生,他二十五岁刚走上工作岗位之时就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与病魔毅然斗争八年之后他还是离开了人间。上述异于常人的人生经历在中岛敦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极大地影响着他对人生和生命的看法,并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投射,赋予主人公李征如此不安的内心和悲惨的命运。
四、结 语
作为志怪小说的《人虎传》满足着人们的猎奇心理,并发挥着它的教化功能。作为现代小说的《山月记》则聚焦于李征的内心,在古典和现代之间,为我们展现了人们在进退两难的境遇中的蹉跎和无奈。正如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一头猛兽,每个人心中都有着难以消灭的“阴影”,而李征没能敌过才华和欲望的斗争,一味地压抑心中的“阴影”,“阴影”就变成了恶虎,最终使其丧失了人性。
中岛敦借古讽今,通过改编李征变虎的故事,使自己内心的“阴影”得以重见天日。读懂了李征,也就读懂了中岛敦,也就读懂了自己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步入文坛的中岛敦,在文学的暗黑时代中摸索前行,在生存的罅隙中书写着现代人的迷茫和不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赵乐甡:《不成长啸但成嗥——中岛敦的〈山月记〉读后》[J].《日本文学》,1985年3月。
[2] 马兴国:《唐传奇小说与日本近代文学》[M].《日本研究》,1991年。
[3] 李俄宪:《李陵和李的变形:关于中岛敦文学的特质问题》[J].《国外文学》,2004年。
[4] 郭勇:《中岛文学的比较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5] 松村明敏:《中敦の〈山月〉》[J].クレス出版,1958年。
[6] 山敷和男:《〈人虎传〉与〈山月记〉汉文学研究》[J].1960年。
[7] 木村一信:《〈山月記〉論》[J].《日本文学》,1975年。
[8] 木村瑞夫:《中敦》[M].《和泉书院》,2003年。
[9]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10] 傅道彬:《晚唐钟声》[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1] 中敦:《中敦全集Ⅰ》[M].《筑摩房》,2001年。
[12] 马英萍:《论日本战时体制下中岛敦的文学者姿态——再读〈山月记〉》[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

